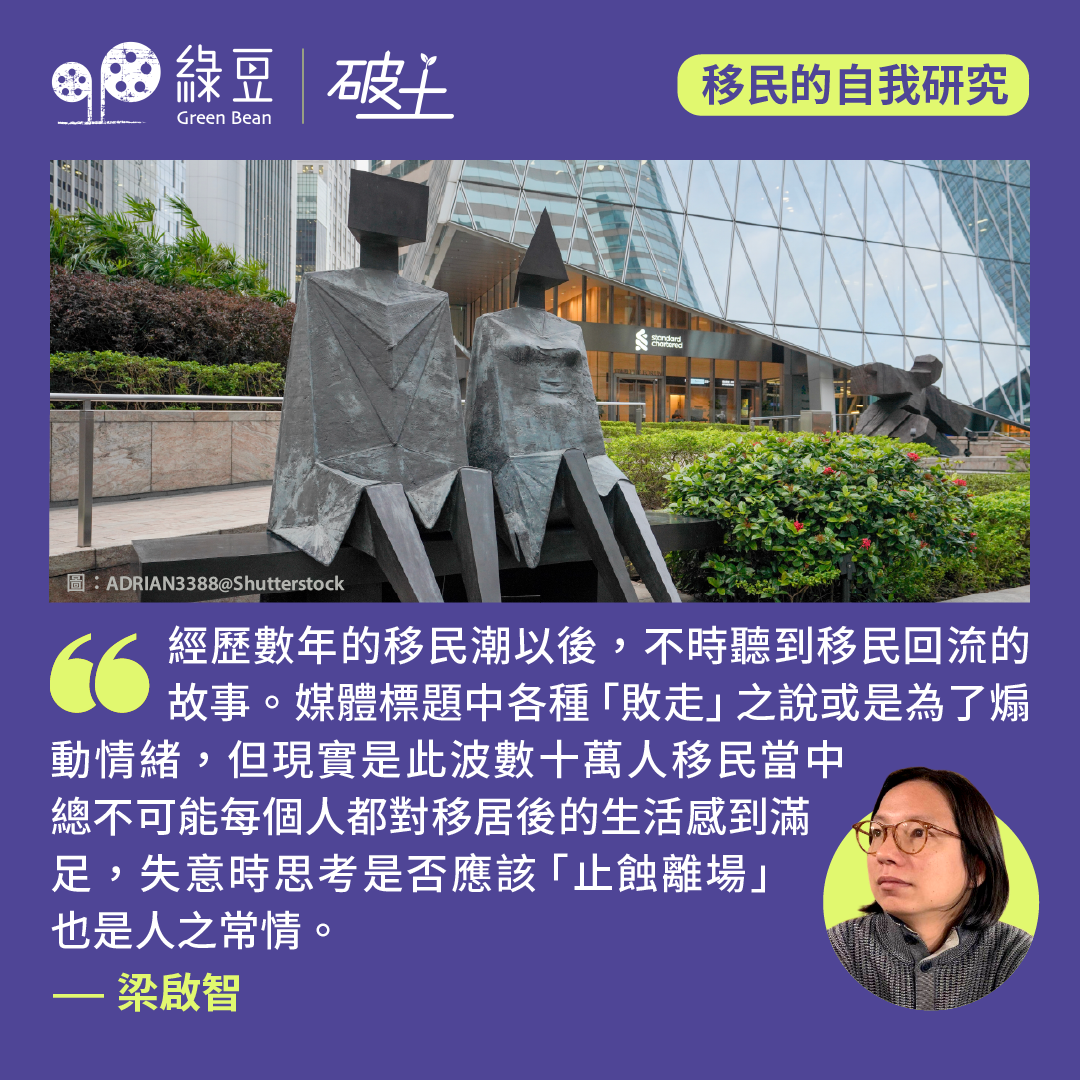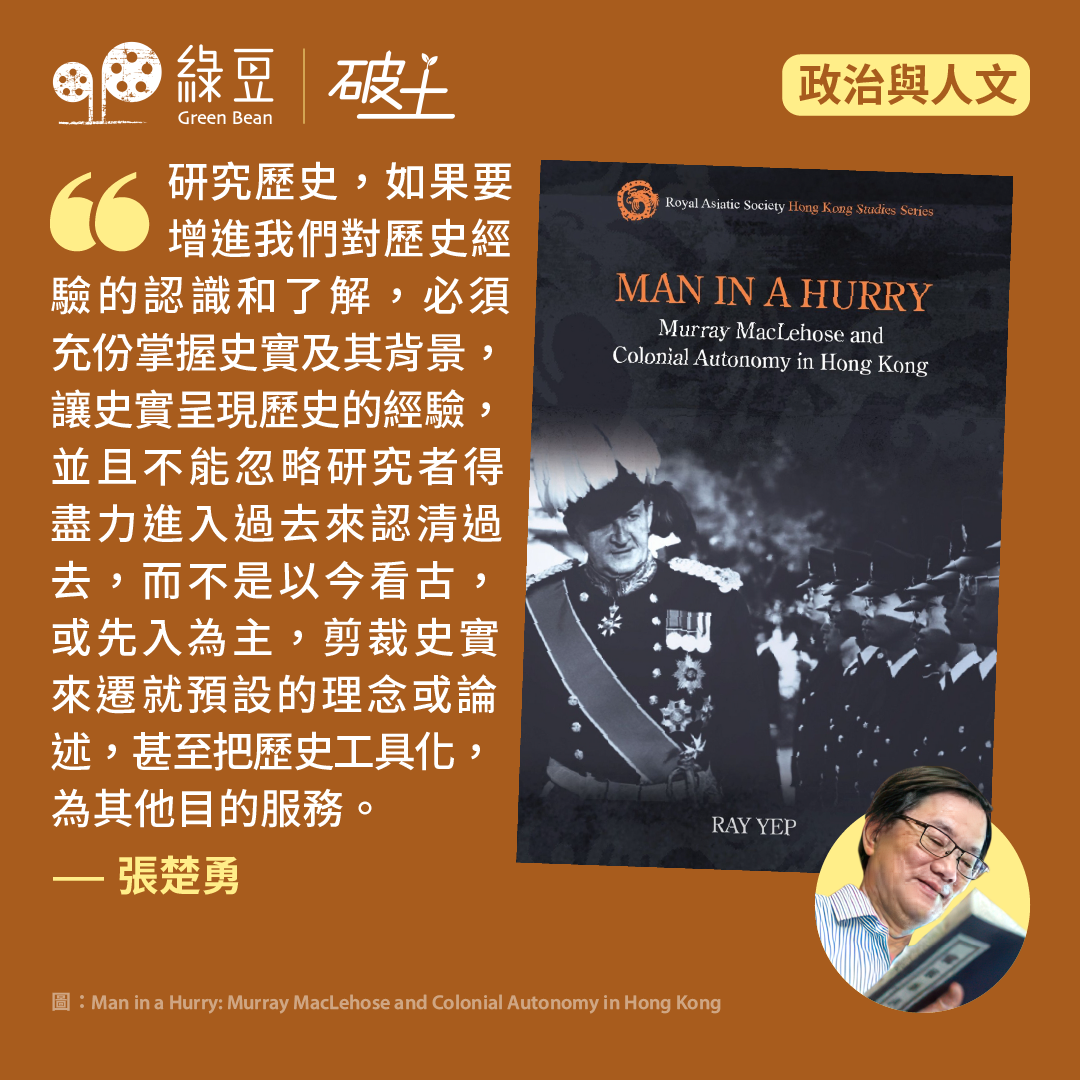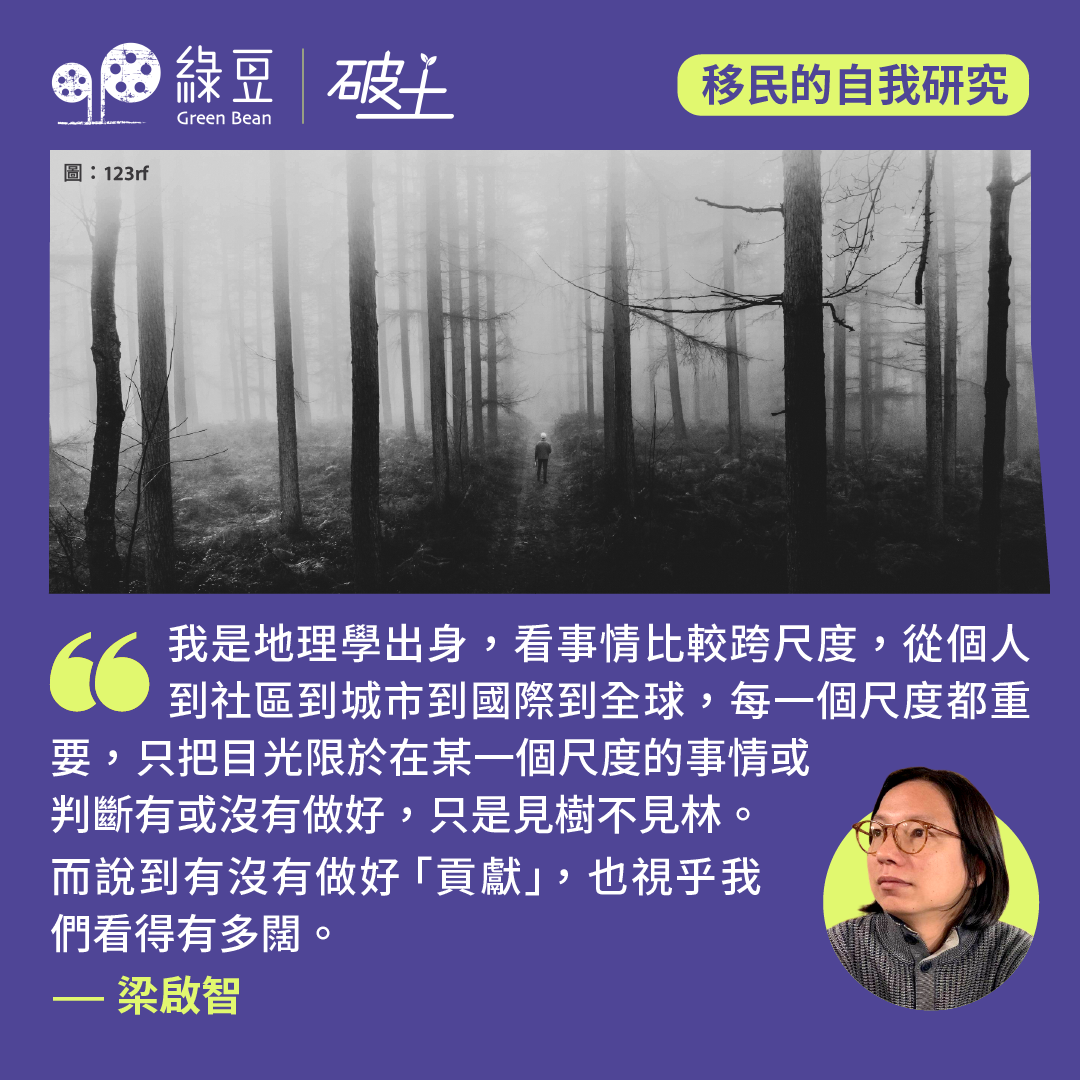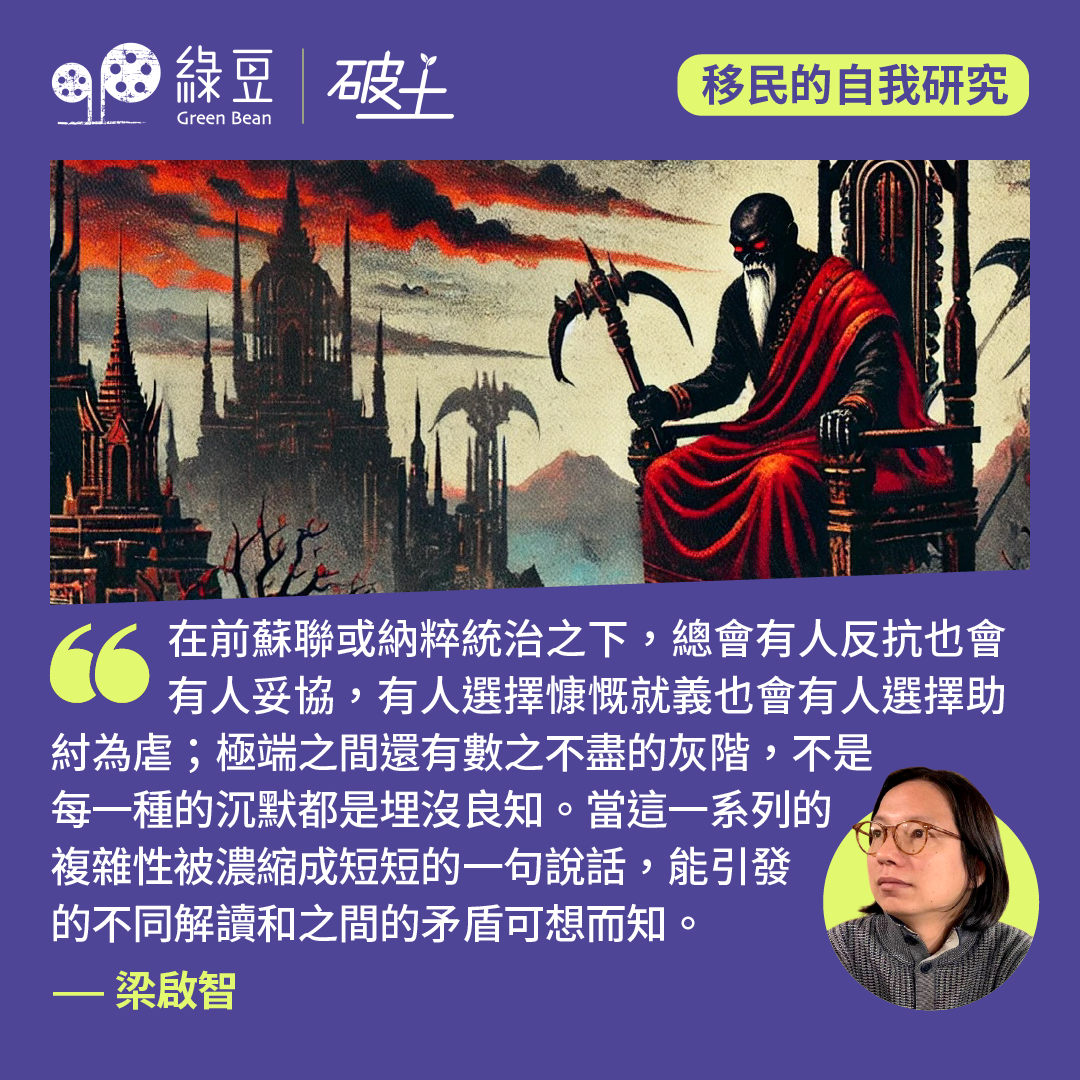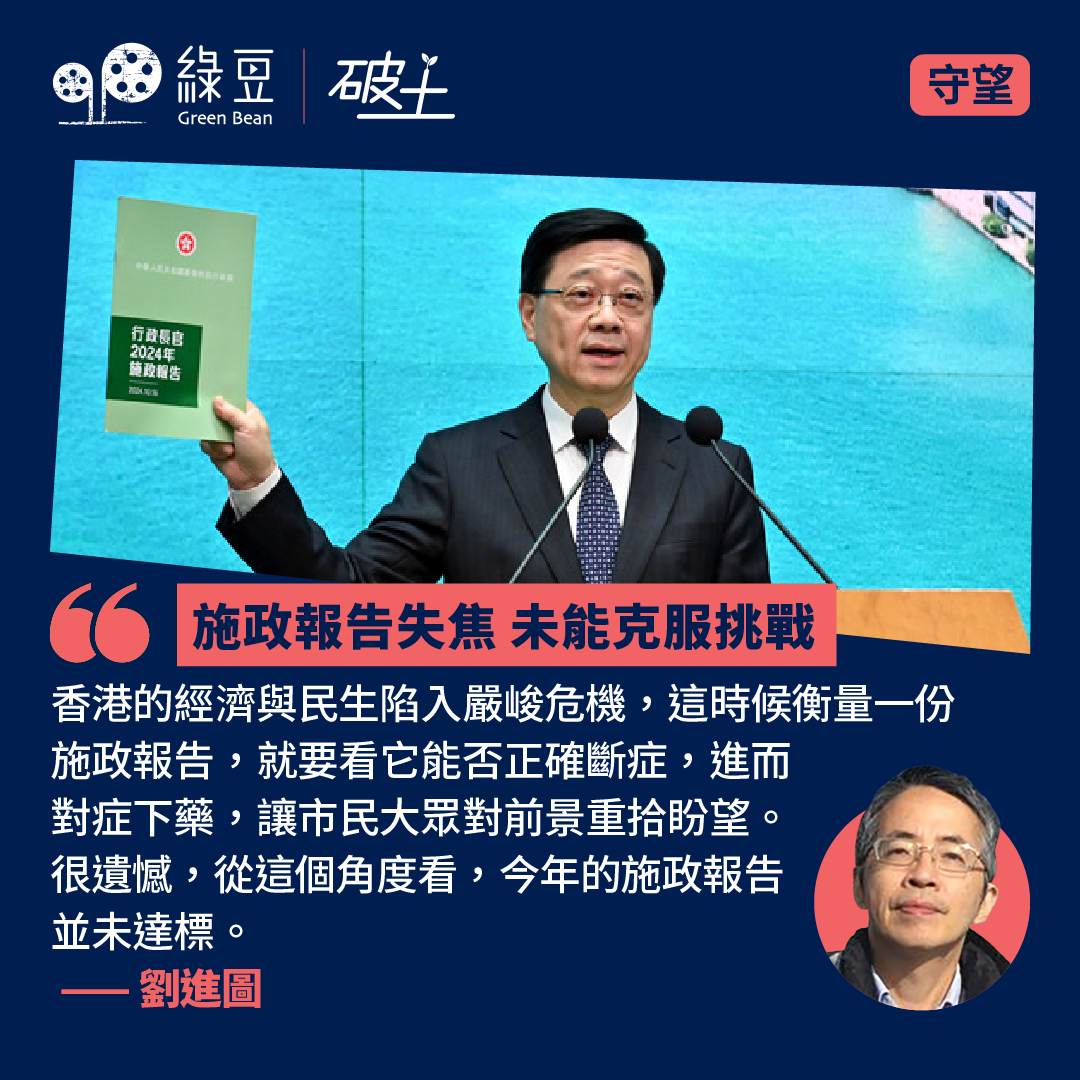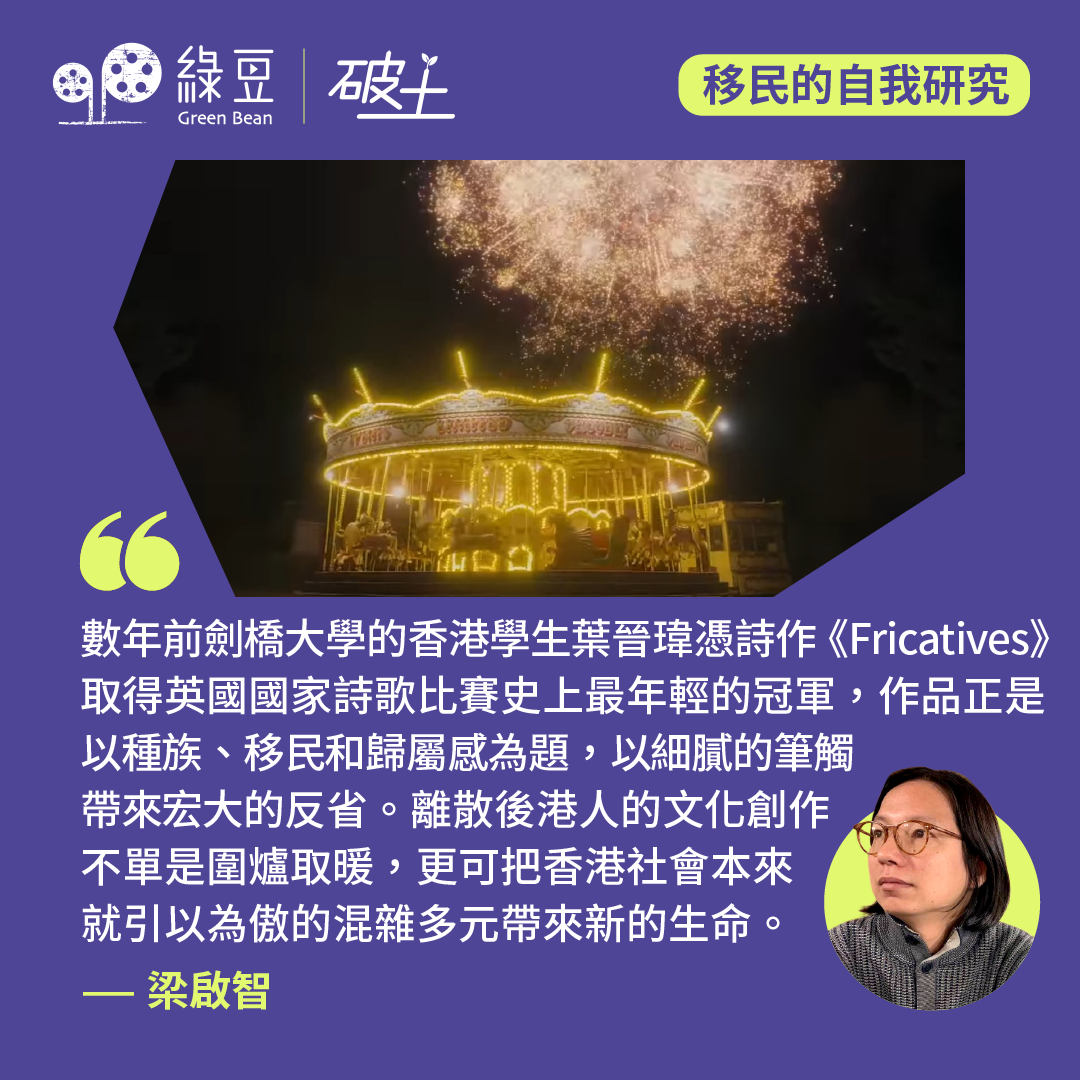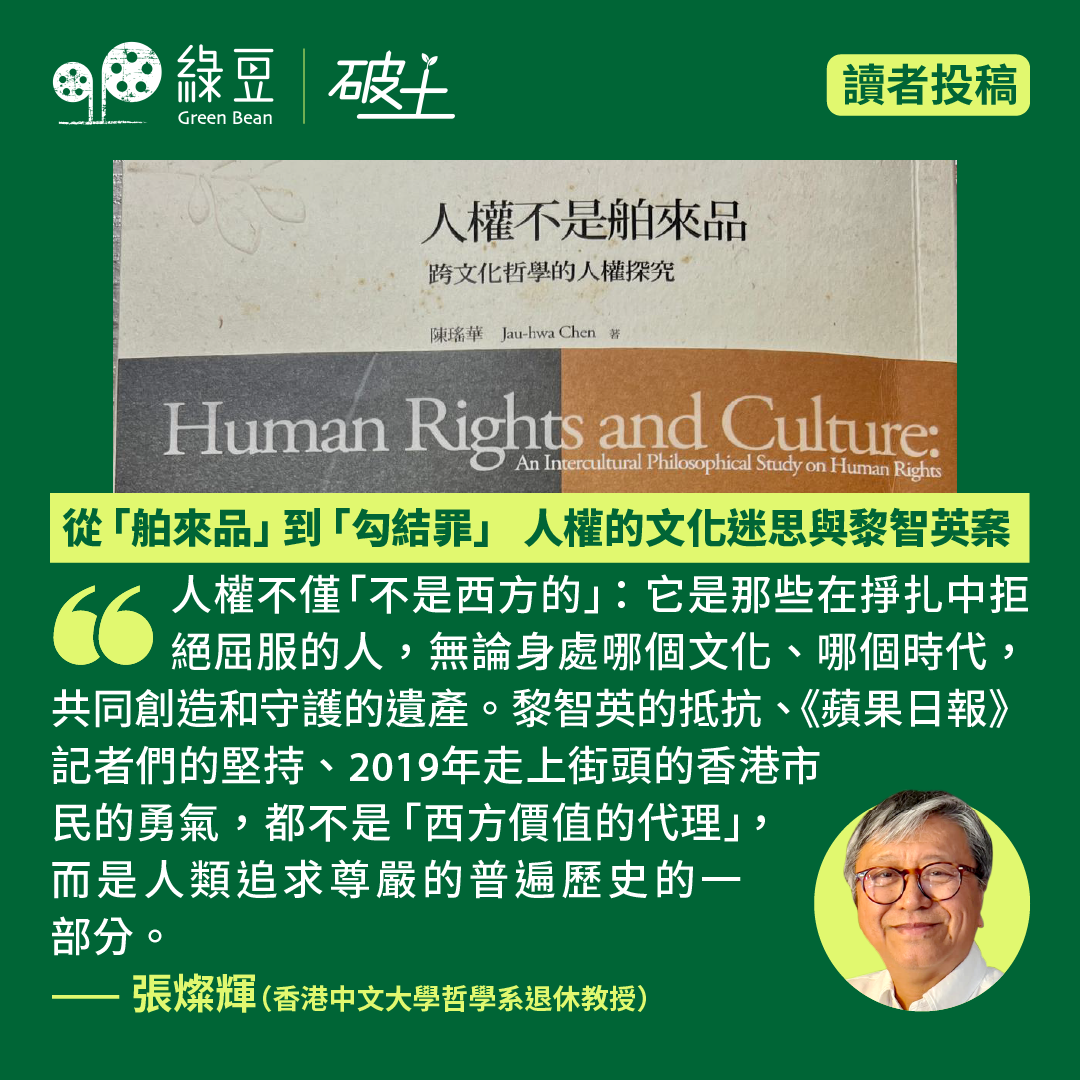經歷數年的移民潮以後,明顯見到香港人離港趨緩。與此同時,也不時聽到移民回流的故事。媒體標題中各種「敗走」之說或是為了煽動情緒,但現實是此波數十萬人移民當中總不可能每個人都對移居後的生活感到滿足,失意時思考是否應該「止蝕離場」也是人之常情。 回看兩三年前針對移英港人社群的研究,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不會回流。現在看起來,這個比例或有高估之嫌。首先,此波移民潮是在香港發生巨大震盪之下產生的,對移居者的推力十分強大;與此同時,他們大多剛剛到埗,對英國生活的各種問題仍未有切身感受,即使遇上也因為蜜月期而視而不見。經過數年的心理調整,當初信誓旦旦說不會回流的,今天即使有了新的懷疑亦不應意外。 為什麼要移民 引用最古典的經濟模型,移民是為了得到某些好處,當到埗後得不到這些好處,或發現背後的成本增加至不能接受,便只好回頭是岸。這說法當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為它假設了移居者本來就很知道移民的目的和成本是什麼,實際上完美信息和理性決策者在現實社會中都不存在。不過反過來說,我們也可藉此追問:那些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移民,或移民前沒有「做好功課」的,到埗後的經歷會否特別困難,是否更容易產生回流的念頭。 舉個例,有朋友聲稱是為了下一代而移民,但這句說話後面是甚麼意思?是為了子女入讀世界排名更高的學校,還是為了更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這兩個目標不一定完全重疊,如果最初的目標只是為前者,那得不到自然就會感到氣餒;後者卻是相對普遍,因而也不會那麼容易失望。推而廣之,如果移民的目的是為了物質生活(例如「住大屋」、「前園可以種花」),則恐怕更容易被日常生活中大小事務的不便所擊倒。最怕就是很多港人本來對前宗主國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到達英國後發現不如現實便處處都看不順眼。 回想以前在美國讀書遇到中國留學生,當時中國發展迅速機會處處,留學生群體都流行說如果僅僅是為了物質生活,其實不應該前來美國,留在中國前路更廣。但如果你追求的不是物質生活,而是無法在中國滿足的文化社會體驗,則明顯對回流與否會有不一樣的判斷。當然,現在香港的經濟情況相對於二十年前的中國差距甚遠,即使為了物質生活回流也得認真考慮自身行業的兩地前景,無謂「兩頭唔到岸」。 世上無樂土,有時移民或回流與否,選擇並非在於尋找最理想的環境,而是要避免最差的情況發生,又或者是在面對逆境時有尋求一定的自主權。聽過不少移民後的生活困難,無論是飲食習慣或是工作機會,甚至是制度歧視等結構性困難,或多或少可以通過自助或群體互助應對。那麼當初把你推離香港的那個理由,又是不是同樣可以應對的呢?只怕有些人一開始移民的時候也沒想清楚原因,現在應該回流與否也無法衡量。而這些人如果不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甚麼,則移民或回流也不見得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布里斯托爾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的香港史研究中心,是英國學界研究香港歷史的重鎮。2025年9月6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香港歷史日」,吸引了200多人出席。 那天的研討活動十分豐富。第一部分由三位資深的居港英裔歷史學家進行討論。其中新界鄉鎮史專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 介紹了他40多年來深入研究新界歷史的心得;文基賢...
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
台灣有文學雜誌評選90後作家,有移台港人入圍,評選紀錄當中「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一句,「馴化」一詞引發許多不滿。許多港人論者,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台灣的,都批評說法不尊重留港港人。文學雜誌後來表達歉意,並表示將會在紙本雜誌中發出勘誤與更正啟示。 自移民潮以來,如何描述仍然留在香港的港人一直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題目。有些離港者經常強調「香港已死」,批評留港者沒有看清形勢拒絕離開,一旦香港政府作出甚為荒謬決定便會揶揄一句「留港者值得擁有」,這些說法常常引來留港者的不滿。畢竟不是每個人可選擇離開,離港者如果不相信香港還有未來,又何必還要落井下石?於是又有輿論批評說這些話的離港者只不過是在艱難的生活適應中尋找自我安慰,意圖通過貶低留港者來合理化自己的移民選擇。類似的離港留港之爭,自移民潮以來已不停出現。 另一個類近的面向,是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朋友,見到香港情勢近年的急速逆轉,亦會表達各種類近「香港已死」的慨嘆。畢竟這些朋友都是在外面看香港,甚至本身從來沒有到過香港,相關說法往往流於概括或過於扁平,留港者聽到難免感到有點離地。近來網上常見一般台灣人外遊,擔憂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會否被警察拘捕,引來港人取笑「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高」。接下來就是台港雙方罵戰無限輪迴,這邊說不懂就不要亂散播恐懼,另一邊說蔑視恐懼正正代表走向麻木。 複雜性被濃縮 這次台灣文學雜誌帶來的反響,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爭拗的延伸。最初讀到「馴化」一詞時,坦白說反應並不是很大。有文友查字典說馴化是應該用在動物身上,用來形容港人是侮辱。然而在社會科學的語境,以馴化來形容威權統治下的公民社會不無案例,亦無侮辱之意;即使在文學雜誌中看到,自問也不太感到突兀。當然,每一位讀者的背景都不一樣,相關議題本來就十分敏感,而且早已被附加各種意義,帶來爭議亦不應意外。 當然,在學術世界談馴化,總會帶上一系列的條件和說明:政權意圖馴化社會,不代表社會已成功被政權馴化;馴化有程度之分,而即使表面上被完全馴化的社會,底層仍不難尋找到異議。去歐洲參觀各地的佔領博物館,看到各地在前蘇聯或納粹統治之下,總會有人反抗也會有人妥協,有人選擇慷慨就義也會有人選擇助紂為虐;極端之間還有數之不盡的灰階,不是每一種的沉默都是埋沒良知。當這一系列的複雜性被濃縮成短短的一句說話,能引發的不同解讀和之間的矛盾可想而知。 承認轉變是回應的第一步...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是香港特首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雖然在房屋供應上做出成績,就取締劏房也交了可行建議,但仍未能聚焦應對當前香港的三大挑戰,因而無法對症下藥,制訂振興經濟民生的良策,讓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重拾信心。 評價一份施政報告,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盈餘山積,那只需看政府怎樣花錢,錢是否用在市民最著緊之處,是否用得有智慧。但如今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移民潮導致大批專業精英流失、中美脫鈎等因素觸發內地經濟蕭條連累香港、傳統支柱產業褪色新經濟引擎卻欠奉,在這三大挑戰夾擊下,香港的經濟與民生陷入嚴峻危機,這時候衡量一份施政報告,就要看它能否正確斷症,進而對症下藥,讓市民大眾對前景重拾盼望。很遺憾,從這個角度看,今年的施政報告並未達標。 社會環境難吸納國際人才 先說移民潮帶來的衝擊:李家超上任之初,已知道這是巨大危機,迅速推出了多個輸入人才計劃,今年施政報告盤點成績,說「至今共收到超過38萬宗申請,約16萬名人才攜同家人抵港」。這個數字雖然不俗,但相比移民離港人數仍遠遠不及,所以政府也承認,「未來五年,各行業人力短缺估算約18萬人」。 除了數量上的不足,質量問題也必須關注,過去兩年港府成功吸納的,絕大多數是內地人,這些新來港人士或會帶來一定的資金和技能,但卻欠缺國際都會發展所需視野和經驗,而且不少視香港為跳板或中途站,最終目的是把家人和財富都搬到海外。因此,特區政府若要聚焦於彌補人才流失,就不能只看輸入總量、只靠內地供應,必須著眼於吸收海外人才,尤其要設法鼓勵已移居海外的港人回流香港。 要吸收海外人才和鼓勵港人回流,單靠物質待遇並不足夠,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不受審查的資訊流通,以及面向國際的優質教育,均極其重要。遺憾的是,香港特區政府雖對外強調社會已回復穩定,但假維護國安之名進行的種種政治打壓沒有半刻消停,針對傳媒工作者、學者和公民組織的政治抹黑與滋擾仍無日無之;學校奉命推行「洗腦式」愛國主義教育;民間人士批評政府動輒被檢控,整個社會仍處於白色恐怖氛圍下,這樣的社會環境若維持不變,特區要吸納國際人才或鼓勵港人回流,便極難取得成效。 突顯香港與內地不同之處...
早陣子聽了一場學術分享,題目是張敬軒歌曲《隱形遊樂場》官方影片的留言區,變成了離散港人互相打氣加油的場域,發表者本身亦是一位在英國讀研究院的港人。生於亂世,際遇經歷巨變,集體情感需要尋找梳理的渠道。離散社群在外地展開了新的生活,自然也會有新的文化生產,回應特殊情感需求。 移民文化產物移民的文化生產在香港不是新鮮事,畢竟香港本身就是移民社會,可以說香港文化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移民文化。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香港流行文化和身份認同相輔相成,不少都是關於移民(甚至是難民)心態。甄妮在《東方之珠》中提問「若以此小島終身作避世鄉」(鄭國江填詞)、林子祥則在《抉擇》當中高呼「任那海和山 助我尋遍 天涯各處鄉」(黃霑填詞),都強烈地帶出了移民社會嘗試重建家園的情懷。在主流的港人認同結構外,香港社會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移民經驗,例如通過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港的新移民、來自來越南的船民、自菲律賓和印尼的移工、來自南亞各地的少數族裔,還有在中環蘭桂坊的一眾外籍僑民或回流港人等等……都有和他們相關的文化書寫,不過在香港主流社會受關注的程度就明顯較低了。至於港人移民外地所產生的文化產品,同樣也有歷史可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大批港人移民到英美澳加等地,移民潮本身成為香港社會重要的文化議題。經典港產喜劇《富貴逼人》系列的第二集《富貴再逼人》,就講述標叔標嬸一家移民加拿大,買當地649彩票中頭獎的故事。片中標叔發現大女兒在當地認識了像米高積遜一樣的黑人男孩、頭髮豎起的龐克白人男孩,以及騎馬穿著民族服裝出現的印弟安男人,於是埋怨大女兒「識埋成班怪獸」。這些刻板印象,也反映了對種族議題毫不敏感的港人,如何帶著歧視目光移民外地。九十年代初探討移民適應議題的電影還有陳友和毛舜筠主演的《兩屋一妻》,描述他們一家移民後丈夫隨即回流香港,剩下在陌生環境中的兩母子,在恐懼無助中重建自我。同期還有鄭丹瑞和鄭裕玲主演的《吳三桂與陳圓圓》,鄭丹瑞移民加拿大後才發現比他早到達的妻子已移情別戀,繼而與鄭裕玲發展感情。當然,要說海外港人的愛情故事,還是以《秋天的童話》最為經典:唐人街小混混周潤發與赴美留學女子鍾楚紅之間的浪漫糾纏。 港人文化新一章隨移民潮退卻,類似的文化產品好像有段時間在香港消失。到了近年移民潮重現,才再見到一波講述移民經歷的創作興起。例如歌曲《係咁先啦》雖然表面上以酒局聚會中要趕尾班車回家為題,不過評論普遍認為歌詞實際所指是港人在移民潮中選擇去或留時的內心拉扯:派對完了,是時候離開了,再不走可能來不及了。歌曲的官方影片以通往機場的北大嶼山公路作為背景,亦清楚說明背後所指。回到《隱形遊樂場》,歌詞本身由現居英國的殿堂級香港填詞人黃偉文,在張敬軒於倫敦辦演唱會期間所寫,並趕及在最後一場首次演出。官方影片包含三段在英港人的適應故事,其中在超市和餐廳打工,做錯事被老闆責怪等的畫面,似乎最能引起移英港人的共鳴。這些片段讓我想起上一個移民潮時的《情心說話未曾講》,當上雜貨店送貨員的黎明遊走紐約街頭的場景。不過那時候的音樂影片其實是要為電話公司賣廣告,想念家人的黎明在歌曲完結時便打長途電話回香港問候家人。《隱形遊樂場》則直接得多,受盡苦頭的港人伴侶在英國街頭擁抱啕哭相互安慰,不再尋找來自香港的情感安慰。這是否預視了新一波移民潮中的港人,和香港的切割會更為決斷?我沒有答案。但我期待更多書寫離散港人情感的作品出現。數十萬港人在巨大的壓力驟然離開,這種集體經驗很需要也注定會衍生出新的作品去表達和紀錄。數年前劍橋大學的香港學生葉晉瑋憑詩作《Fricatives》取得英國國家詩歌比賽史上最年輕的冠軍,作品正是以種族、移民和歸屬感為題,以細膩的筆觸帶來宏大的反省。離散後港人的文化創作不單是圍爐取暖,更可把香港社會本來就引以為傲的混雜多元帶來新的生命。( 圖:《隱形遊樂場》官方MV )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收看節目 不少人說這是個散聚時代,近年的移民潮的確掀起香港人對去留的思緒。RubberBand 2023年的歐洲巡演,不只兌現了他們「說了再見,約定再見,就會再見」的承諾,更造就了他們跟已移民隊員的重聚。 這一集《記・香港人》是《綠豆》製作團隊在香港、溫哥華及倫敦三地追蹤拍攝,我們決意要好好記錄這次的散與聚。因為離散,才有重聚。 ...
收看節目 香港人到英國創業重新上路,陌生環境重頭適應會遇上什麼問題,如何踏出第一步,家庭成員看到的前景會否一樣? 移居他鄉,無論條件如何,總得重新上路。在不同社會文化下創業,應該順應當地潮流? 還是堅持本身優勢? 不用愁於生計的,是否就免於適應新環境的困擾? 一家人一同來到,一同面對新生活,但看見的前景又是否一樣?...
收看節目 香港人在2022年經歷移民潮和世紀疫症,太多生離死別和不辭而别令人不知所措,整個城市彌漫著低沉的氣氛。 前區議員林進的搬屋公司一開業便遇上移民潮,移民客人經常將「內疚」兩個字掛在嘴邊,他反過來安慰他們,叫他們不要自責,明白離開的人都是迫不得已。幫手清屋和入倉,陪伴這些家庭走一小段路,是林進在這大時代下的一點小使命。 Pasu從事殯儀業18年,第五波疫情下政策每天都在變,令人無所適從。有人因為未能好好送親友最後一程感到遺憾,有些先人的遺體因為冷藏問題而變壞,家人面對不止哀痛,更是一種創傷。Pasu希望陪喪親者們走出哀傷,做到去者善終,留者善别。 林進和Pasu都選擇留下來,學習好好說再見後,繼續在小城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