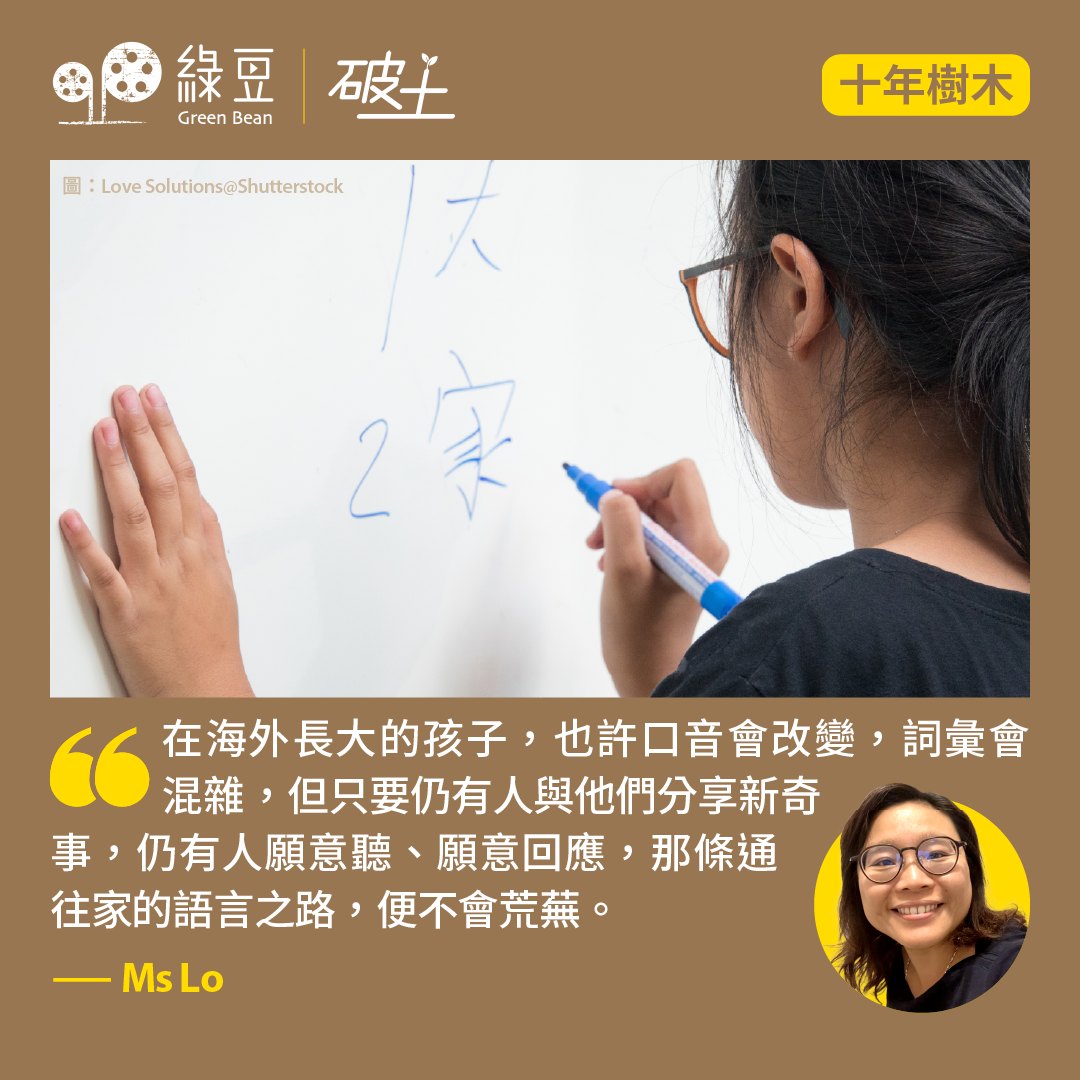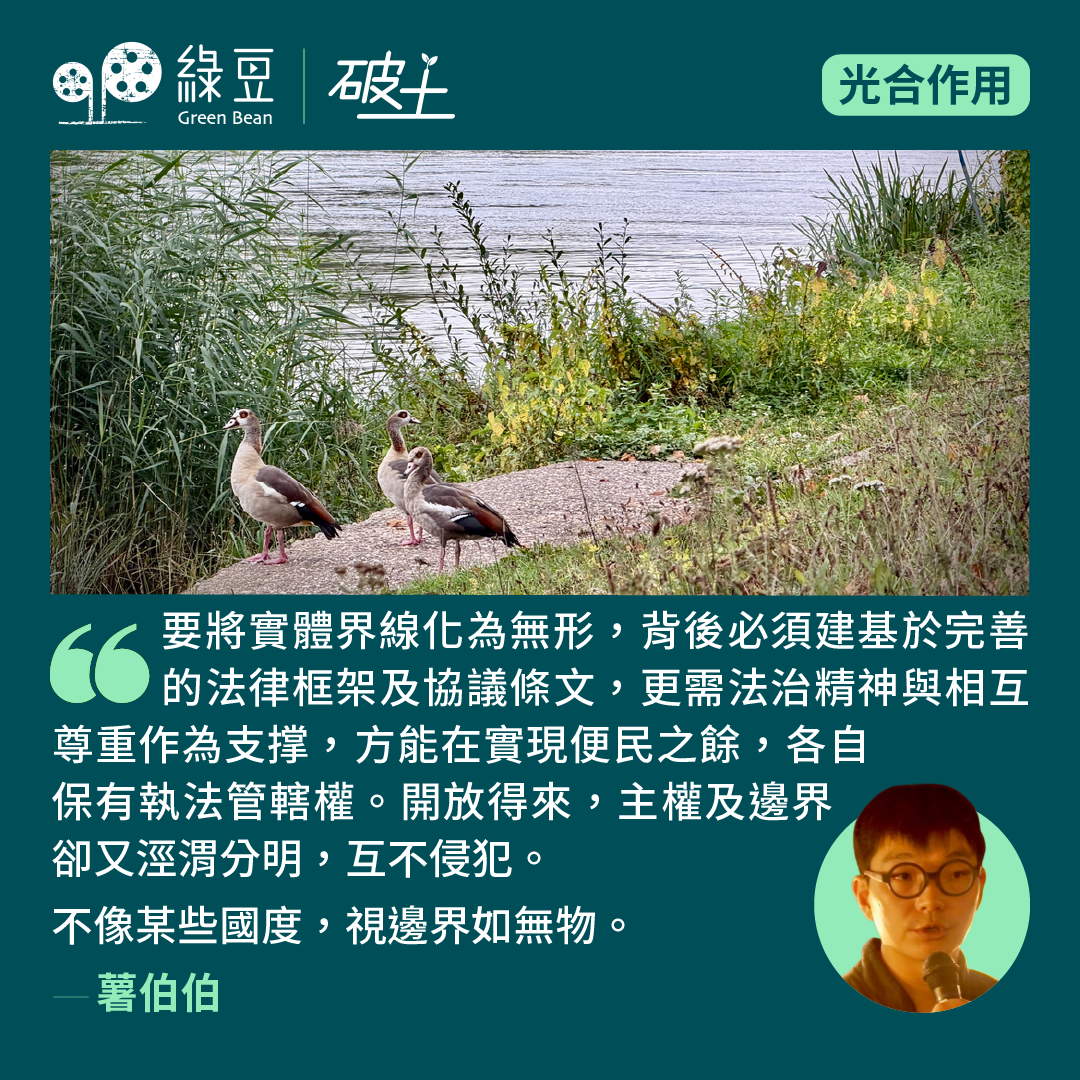跟在外國的朋友談移民經歷,我發現當問到有沒有遇過族裔歧視時,對方的回應十分奇怪:如果對方是近兩年移民外國的話,近乎全數都跟我說沒有;但如果對方是已經在當地十數年甚至是數十年的移民,則大多數會跟我說有。我很好奇,為什麼同樣是移民,不同世代之間對族裔歧視的經歷會有這樣明顯的差別? 理論上,如果觀察屬實,可能的解釋有很多。例如不同世代遇到的社會情境不一樣,可能現在的社會本身就沒有那麼多歧視,又或者經歷過二零一九年之後外國人對香港人多了同情,所以減低了對香港人的歧視。不過我認為這兩點的解釋力都很低,畢竟許多社會的族裔歧視明明仍然很嚴重,也有其他明顯獲得大眾同情的族群亦面對巨大歧視。 移民新鮮人 另一種解釋,是我遇到的一位老移民告訴我的,我覺得比較合理:歧視當然存在,只是新一批的港人剛剛到埗,如果不是還處於慶幸自己成功離港的蜜月期,就是忙於適應當地日常生活所需。對於歧視問題,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只是還未察覺得到,並不代表不存在。朋友還特別提到英國文化中的挖苦傳統,剛到埗的如果一不留神,就連對方已經「轉了個彎取笑你」也未必知道。 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合理,因為它能解釋到那些例外情況。對於少數近期移民而又有經歷歧視的朋友,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到埗後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例如教育。有位朋友在香港本來是教師,到英國後在學校當教學助理。他發現學生面對他的時候明顯比較不合作,但面對擔當同一職級的白人同事時就不會;而因為他的華人面孔,學生挑釁他的時侯,甚至會夾雜兩句假扮的中文模仿,明顯是出於對族裔的取笑。 對於這些經歷,朋友有以下分析:很多港人到達英國後,日常接觸到的當地人其實不多,要像他這樣從事公共服務的才有機會遇到各式各樣(不一定友善)的本地人;又因為他從事教育工作,道理上處於權威位置,但小孩子總愛挑戰權威,又不會隱藏自己,於是潛在的歧視就表露出來了。按此理解,歧視問題確實存在,只是很多港人暫時未察覺到,但難保遲早會有所經歷。...
收看節目 跟王惠芬傾談,一定會聽到她的笑聲。如果談的時間足夠長,或者去到沉重的地步,應有機會聽到她彷似不經意說出的笑話,適時地把氣氛舒緩過來。 這次的訪問長度相當足夠,內容亦沉重非常,所以王惠芬在過程中說過不少笑話,多次將沉重到不知如何繼續訪問下去的氣場扭轉,所以在傾聽的製作團隊,整個訪問過程中,有如冰火X重天,情緒過山車放題。 她的笑話題材,主要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兒時身處的荒謬年代;草根新移民面對陌生環境的思想衝擊;挑戰社會不公的「無知」事蹟⋯⋯ 現場聽,配以她的神情動作,無可能忍到笑。後來製作時回看錄影,才發現當中的黑色:這些經歷在事發當時的處境,其實相當驚心奪魄。若再參照現時香港形勢,其實應該笑唔出。不禁問,經歷過怎樣的人生,才說得出這般地獄的笑話。...
收看節目 香港社福界不會對王惠芬感到陌生,她創立了專門服務少數族裔的融樂會,更先後獲得行政長官社區服務奬,優秀社工,與及人道年奬等業界的肯定。人權和民主的信念支持了她多年的社會服務工作,但這個信念亦帶她走上要離開香港的不歸路。 王惠芬十歲由中國內地來到香港,她自言雖然新移民的身份曾經讓她嘗過不少辛酸,但香港這個地方教懂她什麼是自由和平等,同時令她明白民主和尊重人權的環境才可以保障像她一樣的弱勢社群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因為香港教懂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價值,所以她願意投身去守護讓其不受侵蝕。 王惠芬是出了名的「大笑姑婆」,任何人都一定會受到她說話中夾雜的笑話、笑聲和能量所感染。經歷了自「八九六四」以來三十年民主運動,她坦言在「佔領行動」一役感到重大挫折,亦令她自此患上抑鬰症,至今仍未痊癒。「反修例運動」後,她在不情願下,亦要「避走」英國,不但再次成為新移民,成了當地的少數族裔,更意外地變成了難民。 王惠芬訴說了來英的曲折,訴說了和戰友的經歷和情誼,一篇有你有我的香港「年代志」慢慢浮現出來。那怕當中充滿傷痛,她也會適時地以笑聲來調解一下。 雖然舊傷仍未撫平,新傷仍在添加,但原來王惠芬己經再次出發,繼續民權信仰之路,她的腳步和笑聲,一直沒有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