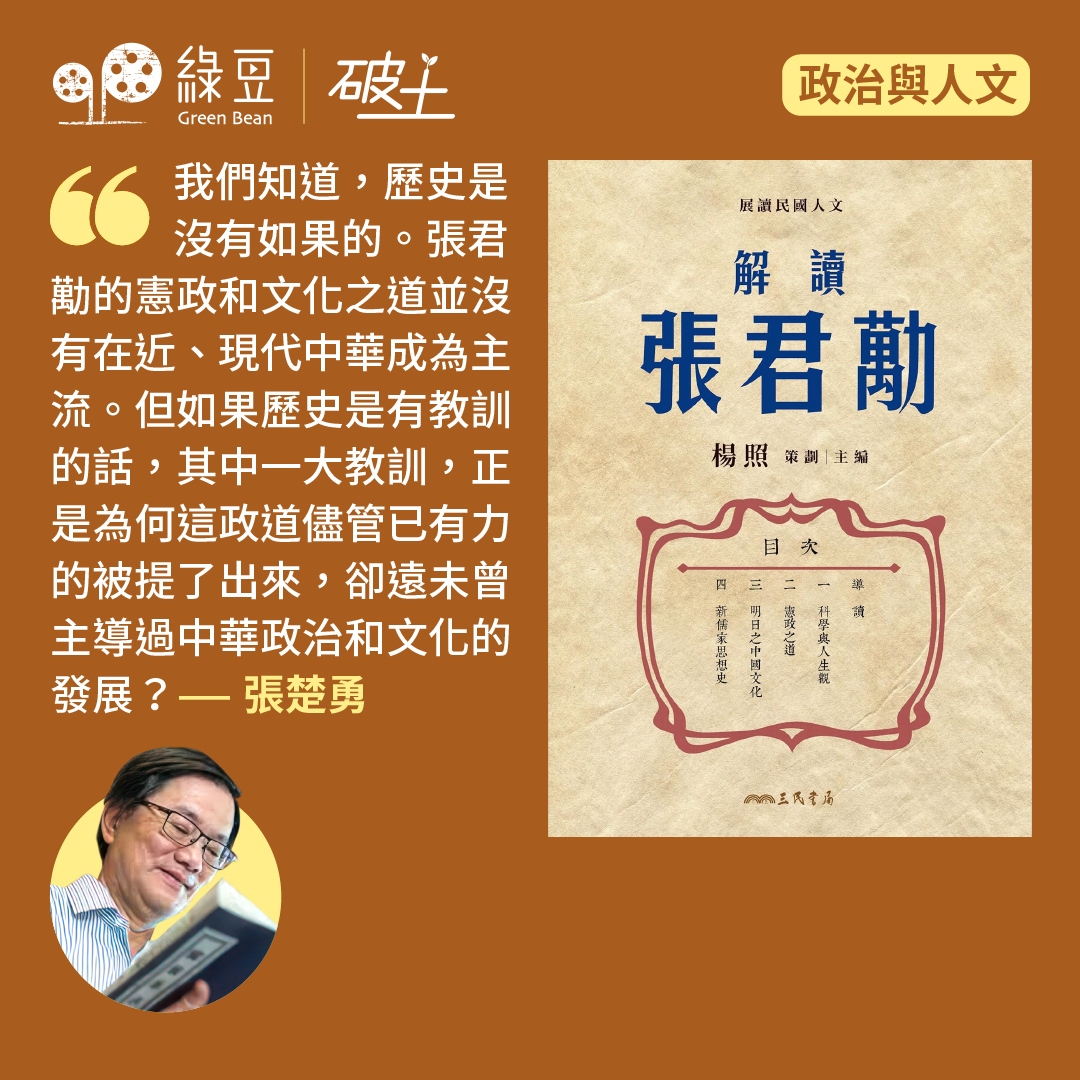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評論近期的歐洲選舉時說:「當選民對中間派聯盟或脆弱的少數派政府感到厭倦時,他們餘下來的選擇,便只有政治上的激進派了。」回顧人類社群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當温和中道的政治力量或方案,被認為是未能解決有關社群的重大挑戰時,激進政治往往便會抬頭,主導了社群的政治發展。中華的近、現代政治,正是見證了這種邏輯的一個例子。 甲午戰敗後,清朝菁英階層的救亡意識,可說是達到了高峰。但也是從這個時期起,積極尋求救亡之道的領袖和知識人,在選擇和推行其救亡的方案時,一次又一次的,讓激烈基進的主張和行動,蓋過了相對温和中道的做法,使前者大體上主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由革命派到共產黨 例如當時被視為是激進的、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推動的變法維新,在戊戌政變後便被更激進的、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蓋過了。1905年,當把西方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嚴復,在倫敦見到孫中山,並討論到中國的出路時,嚴復認為中國人民的民智不發達,「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對此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事後證明,革命方案蓋過教育改良方案,從而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激進政治繼續在中國發展。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改組中國國民黨,使之成為效忠黨領袖,以列寧革命先鋒黨的模式,繼續其志在建國和統一中華的革命事業。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要全面跟隨蘇聯蘇維埃的革命政權,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向剝削階級專政,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當時,就是相對温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例如胡適,在文化上也激進地主張要全盤西化,支持打倒孔家店,並認為跟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傳統當時得承認是百事不如人。 當然,近、現代中華的激進政治並非是突然間從天而降的。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晚青的改革和自強運動,不是被深厚的傳統保守思想和制度所阻撓,便是被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自己權位拖延中國轉型至建立現代政體的努力,導致改革救亡者不單止對保守的當權者失去信任,更為了急於徹底推翻這些反動勢力,便毅然採取不斷把其政治思想和行動激進化的進路,因此而形成了激進政治主導了近、現代中華政治的格局。...
基本上,人類世界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完美。正如佛家所說,人和其餘一切有情眾生,不過是五蘊、十八界、十二因緣偶爾聚合結成,生死煩惱墮落沉淪等「苦」,亦由是積集,人間之苦根本不可免。因為苦與人間同起共滅,甚至可理解為人間即苦,苦即人間。 相對於宗教家,思想家及科學家(尤其後者),則認為人類本性可憑藉人類自身力量改變,如理性、道德、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等加以矯正。只要創造正確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人類完美性(Human Perfectibility)有望成真。 正如上述,每個人都希冀更美好的世界出現,無論從宗教、哲學、科學角度切入,以追求人類完美性,這種夢想,曼努埃爾(Fritzie P. Manuel)稱為烏托邦傾向(Utopian Propensity)。何謂烏托邦傾向?一言以蔽之,即每個人都會有「明天會更好」那種正向潛意識,對於未來憧憬、希望、幻想、渴求,如披頭四的歌,《想像》(Imagine)。譬如各位大抵會認為,自己可透過完成大學學位改變現狀,有更好的前途,這就是烏托邦傾向。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必定有人不具備烏托邦傾向,而我們通常會用「悲觀」來形容這類人,不過大部分人通常「樂觀」,儘管這種樂觀多少含有幻想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