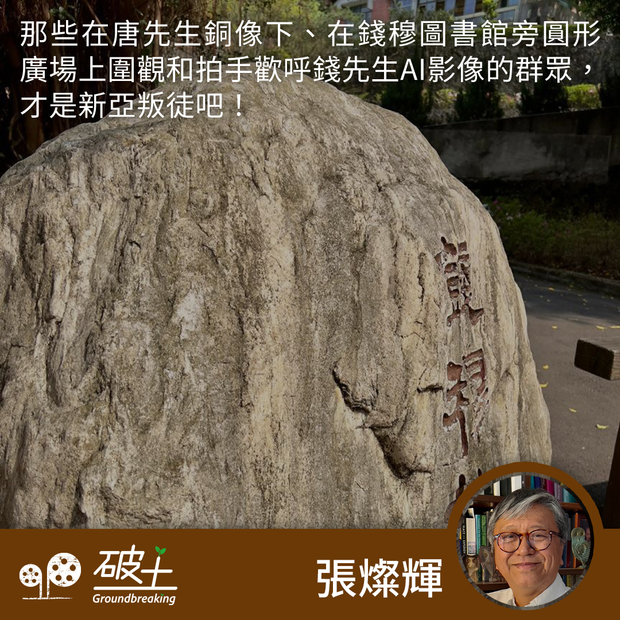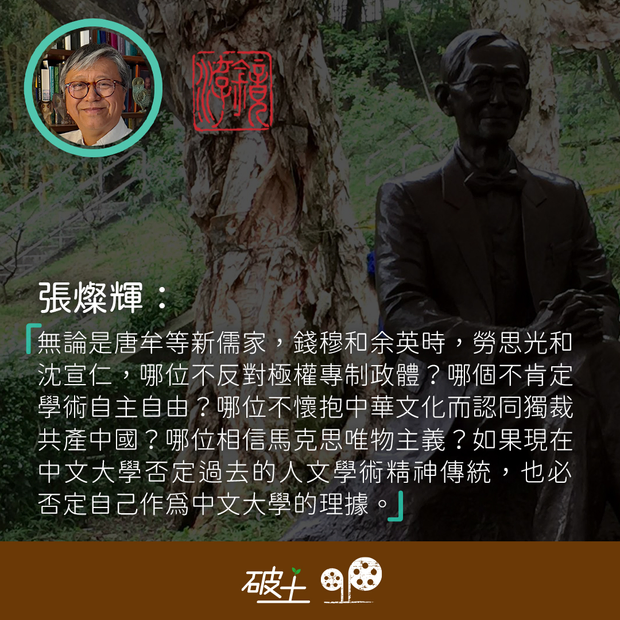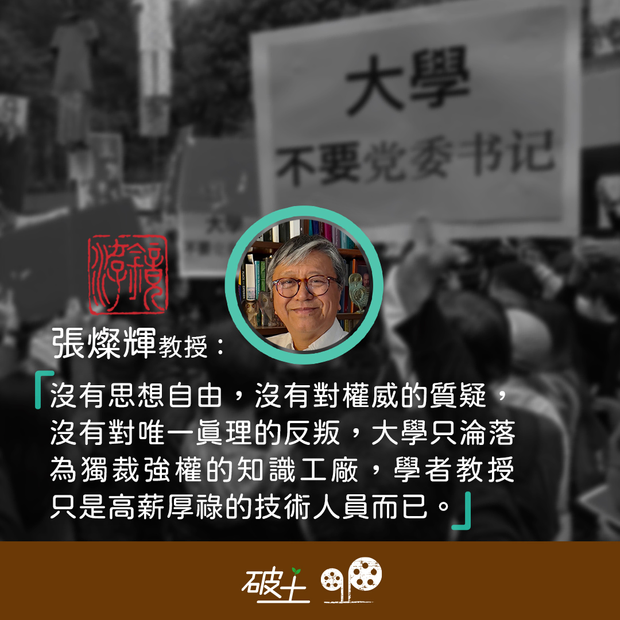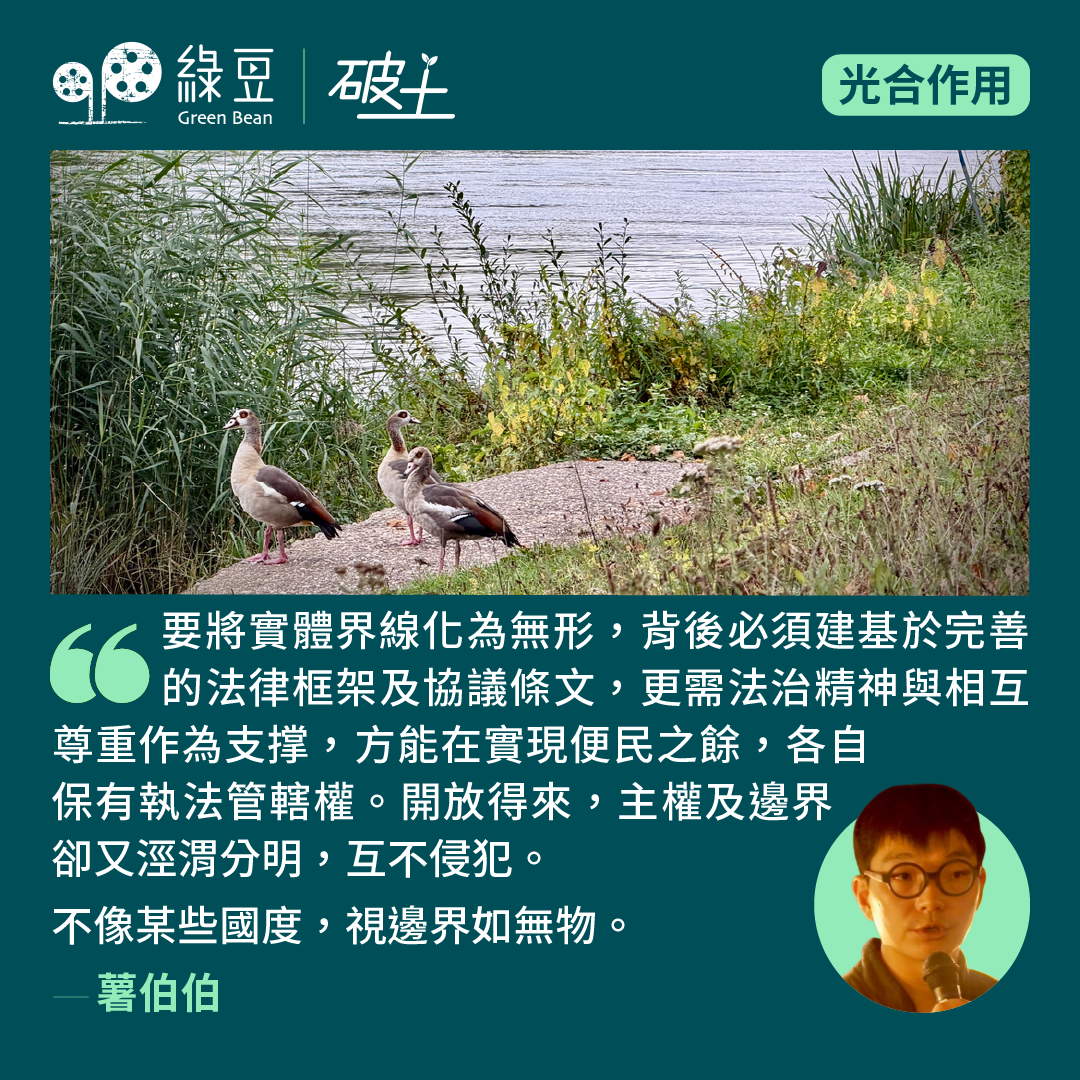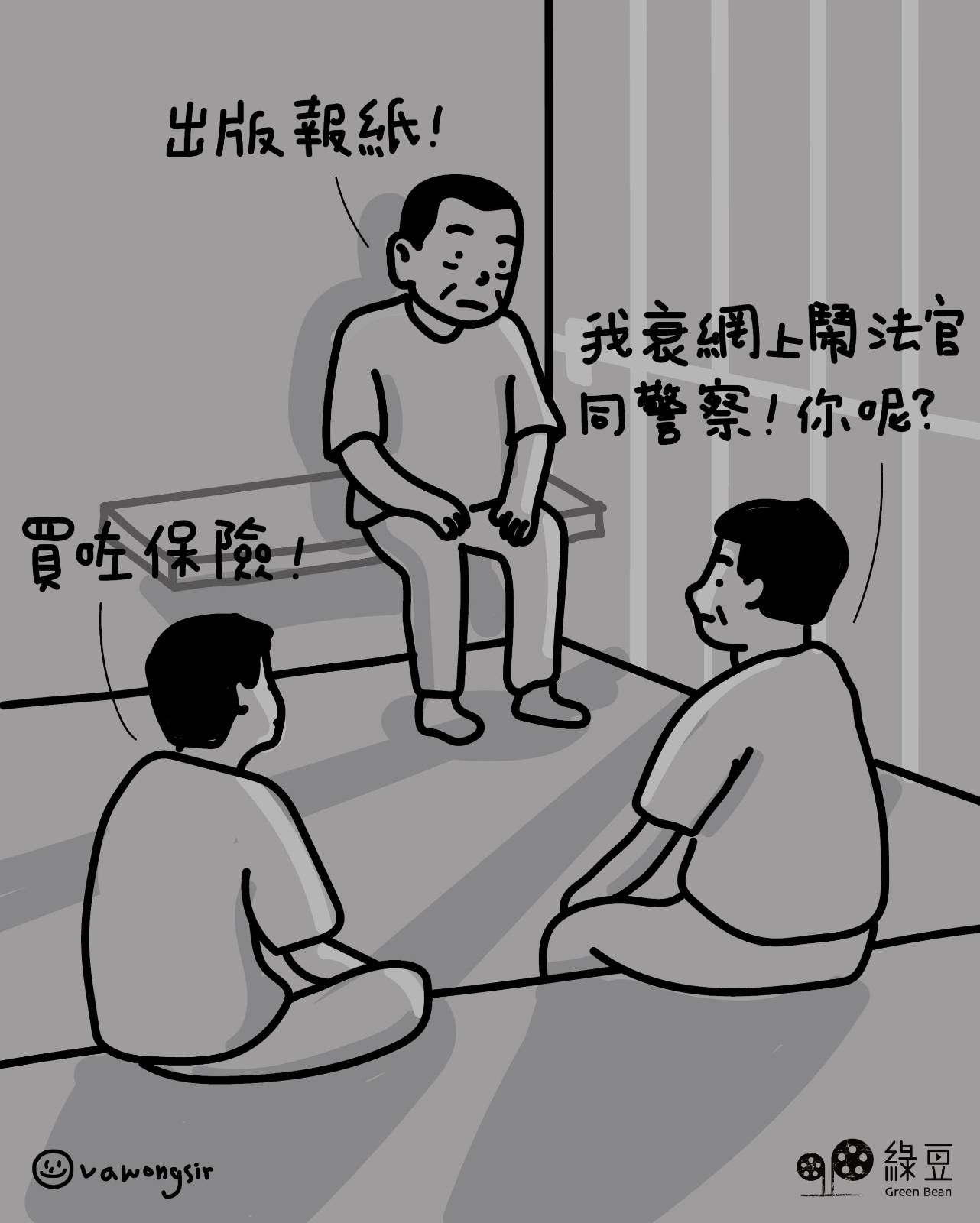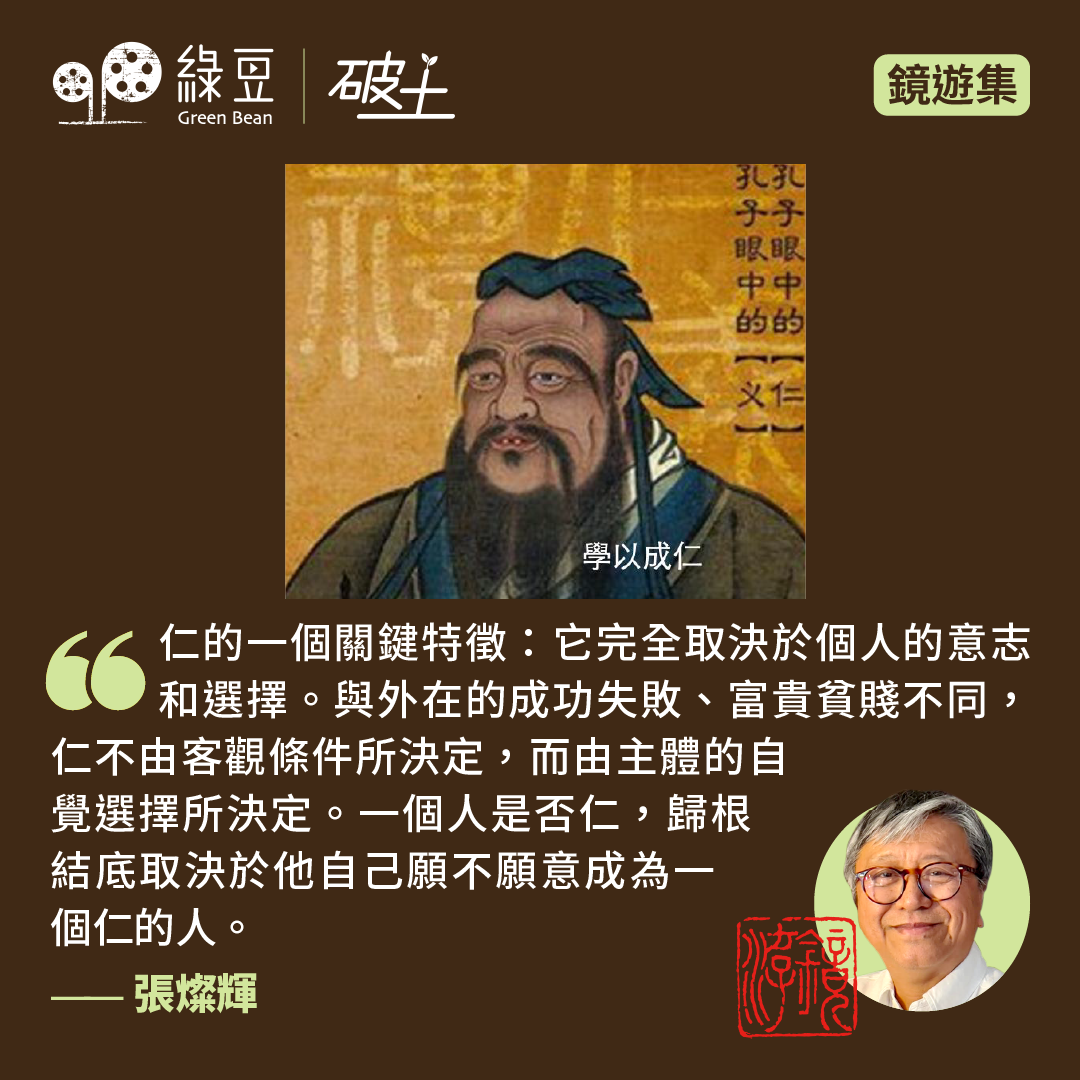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日前到了台北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參觀。錢先生一生漂泊,生逢戰亂,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停留不少時間。他高壽離世,最後二十年便在台灣士林區「素書樓」渡過。名稱是以錢先生母親在無錫之居所「素書堂」為據,作為先生晚年終老之所。這間是在一小丘上的兩層中式建築物,附近並沒有其他房屋,有點遺世而存之感。當然,錢先生晚年在住所仍接見朋友和講學。屋內書房,飯廳和睡房,簡單高雅樸實,可見先生和師母過的平實無華簡樸的生活。除了掛在牆上的字畫,裝飾不多。我與錢先生沒有緣份見面,入中大唸本科時,先生已離開中大,不,應說離開新亞書院已多時。但讀文史哲的中大人,哪個不認識錢先生!他是一代大史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其中最出色的當然是余英時先生。錢穆和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沒有異議。但對我們中大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他作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他由始至終都是反共學者。他是1949年避秦而來香港!新亞書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對抗共產主義。錢先生公開在新亞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他指出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大陸極權專制的「中國」。中文大學2019年11月12日變成戰場、2021年底民主女神像深夜被拆毀、2022年7月1日中大校長宣稱大學教育是服務政權,我以為中文大學已經完全淪亡。但想不到2023年2月20日,校方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AI 技術重現,與大陸合唱團「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國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網上圖片)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即是説活動得到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首肯!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但似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的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香港中文大學已成為歷史,相信新亞書院是時候改變名稱了,乾脆改為「朝陽書院」吧。反正上任新亞院長已承認相信唯物主義,所謂新亞精神早而成為糟粕。當我進入錢先生的書房時,看到54册《錢賓四先生全集》,和其他重要著作,極為佩服。但最感動的是看到他為新亞書院寫的文章手稿。面對新亞校歌的手稿,想起2月20日新亞圓形廣場的醜劇,哪一位中大人新亞人不憤怒和悲哀!當年唐君毅先生批評余英時先生為新亞「叛徒」。事隔多年,所有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余先生不單不是叛徒,而是繼承錢唐二人的學術,發展出另一學術層次。余英時當然是「最」新亞人。那些在唐先生銅像下、在錢穆圖書館旁圓形廣場圍觀和拍手歡呼錢先生AI影像的群眾,才是新亞叛徒吧!張燦輝2023年3月24日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山城滄桑之十一我在中文大學從學生到教授度過了幾十年,中大所有校長都認識,除了現任校長段崇智。學生時代是李卓敏和馬臨,我當然見過但沒有機會接觸。後來回母校任教,上任第二星期便獲高錕校長接見,親身見證這位親和、平易近人、關心學術自由的科學家,在這次會面也略談民主和通識教育的關係。接著便是李國章、金耀基和劉遵義。李國章委任我當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但只跟我面談過兩次,我的感覺是他是上流社會出身、長袖善舞、八面玲瓏,但我和他卻沒有認真討論過通識教育問題。金校長是我敬佩的老師,沒有他,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會這樣有規模和成果。(註1)劉遵義是知名經濟學家,他任內的作風引起同學和校友強烈不滿,是以未能續任便離開中大。(註2)然後是沈祖堯校長,正是他將劉遵義和學生、校友的隔閡修復過來。周保松的的文章「以學生為念」(註3),已經將沈祖堯和學生種種活動十分立體的描述出來:「博群計劃」、「百萬零一夜」、「中大登高日」、百萬大道看世界盃等等,以前中文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和同學一起做過的事,沈校長本着「與民同樂」之心做到了!在此不再詳述。沈祖堯為甚麼可以如此?我想因為他是在中大所有校長之中,真正是「香港人」的校長:一個在香港出生和受教育的香港人、明白香港和關心人文的醫生、沒有架子的學者、到大牌檔吃飯,為低層同事咖啡店開幕、在同事拍攝的電影中做「茄哩啡」的大學高層!(註4)更重要的是,他在2014年10月2日晚上,他和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到中環金鐘探望同學;2019年11月12日帶領一群醫生進入中大戰場,救護學生。環顧香港,可有其他大學的校長不顧政治考慮,頂著以「學生為念」的信念和勇氣去處理這兩件香港大事嗎?(註5) 沈祖堯當日出席校長就職典禮 以上提及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會知道,這些都是公開的事實。我在《山城滄桑》第八、九和十輯有關中大銅像文章中,已提過沈祖堯的支持和幫助:相信沒有他首肯,勞先生銅像不會在中大校園出現;沒有他的批准,唐君毅銅像繼續風化和被新亞人遺棄。但我想在本文再多説一點沈祖堯與通識和人文教育的關係。2010年沈祖堯仍為候任校長的時候,我第一次到醫院拜訪他,談論中大通識教育。離別時我恭賀他,並説中大慶幸來了一位「人」的校長。他上任後不夠兩個月的某天,一早八點,和幾位同事來到通識教育部聆聽我和同事報告通識教育課程、理念、行政和面對的種種難題。會談進行差不多兩個小時,校長都是專心聽並提出相關問題,這是第一次有校長來通識教育部開會,之前沒有,相信之後也沒有吧。沈祖堯對通識和人文教育不是敷衍之説。如果翻查中文大學每一位校長的就職演講辭,沈祖堯的是唯一一個談論大學理念、通識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校長。(註6)讓我們重讀他當年的講辭重點:「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奧爾科特 (Bronson Alcott) 說過:「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放出來,與外界事物聯繫,並反觀自省,從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當國家高談經濟發展之際,大家不要忘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發展科學、生產食物和延長壽命之時,請牢記『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者痲瘋,而是愛的貧瘠』(德蘭修女)。在中大這所綜合大學,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符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將繼續捍衞人文價值、培養學生敏於體察別人的需要和苦難,以及教導他們欣賞藝術和音樂。」「泰戈爾 (Tagore)...
民主女神像唐君毅先生的銅像在2009年豎立在新亞書院草坪後,跟著進入中文大學校園的雕像並不是2017年的勞思光先生銅像,而是在2010年6月4日深夜時分從銅鑼灣維園運到中大的民主女神像。這個像由美籍華裔藝術家陳維明以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為材料,參考1989年天安門廣場象徵學生運動的民主女神像而製成,中大學生會倡議把「新民主女神像」永久安放在中大校園。 (張燦輝攝) (張燦輝攝) 筆者和當時的中大學生會主席黎恩灝和新民女像雕塑家陳維明不熟悉,不知道整個造像和搬到中大校園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想必經過不少困難和討論才能有6月4日晚上的歷史性事件。(註一)新民主女神像相較其他中大户外雕像的獨特之處,是整個造像規劃原與中文大學無關。新民主女神和中大傳統並沒有連繫,不屬於中大科學和人文傳統,不是對中大有貢獻的哲人或學者,它代表的是一個概念!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六四運動引發出來,每年在香港維園以燭光延續不斷的一個盼望,一個祈求民主自由在中華大地可以開花結果的心願:這個雕像就是這樣的一個象徵。1989年之後中國大陸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公開宣洩對屠城的憤怒和對民主的期盼,只有在香港,可以向全世界顯示香港人不敢忘記這件歷史。六四二十一週年紀念的晚上,中文大學的學生、校友、教職員決定,將陳維明先生雕塑的新民主女神像搬到中文大學校園,讓六四精神不單在每年的六月四日才呈現,而是讓這個放在大學火車站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向每天經過大學站來回大陸香港的乘客,向每天進返中大校園的同學教職員,宣示「毋忘六四」的理念。中大民女像和其他銅像不同,不需要按中大校園地圖找尋,她就在大學火車站前,讓所有人都看到:民主和中大精神是連結在一起的。2010年開始,新民主女神像便和其他中大銅像一樣,成為中文大學的象徵(icon)。但從一開始,中大民女像便存在模糊狀態。她的質料是玻璃纖維,不是精銅,不能永遠存在;立像沒有正式銘文和造像記,一切都好像不穩定,只是暫時性的。立像初期,學生會和校方多次磋商如何永久處理雕像事宜,但似乎最後都是不了了之,沒有一個確定恆久的規劃。沒有人認真負責維修工作,如是這樣,中大民女像又似乎是理所當然地存在下去。直到2021年12月底,一夜之間,中大民女像便被校方黑箱搬離摧毁。翌日,除了中大不同書院學生會聯合公開譴責外,並沒有其他校內外人士發聲抗議。大家恐懼了,國安法之下,誰人再敢發聲送頭?幾天之後,中大民女像再沒有痕跡。新民主女神像的意義新民主女神像能夠在2010年進入中大並存在了11年,其實是一次,或者是唯一一次中大的「民主」勝利。中大校方本來並不贊同這事件(註二),但最後仍然可以安全運抵大學和成功豎立,全程沒有任何干擾。一方面是學生會、校友和教職員無私無畏的公開支持,同時亦因為當時新任校長沈祖堯的開明態度,能聽取各方意見而成事。中大民女像的原型據稱是從天安門的民主之神而來。1989年5月29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放民主女神像的時候,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久違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聲呼喚過妳的名字。為了妳,難道我們還要再等70年嗎?...民主之神,妳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妳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註三) 照片來源:六四紀念館 ...
2009年5月唐君毅銅像揭幕典禮時,勞思光先生是主禮嘉賓之一。唐先生銅像雕塑家朱達誠當然也在其中。筆者趁機會細語向朱達誠説:「老師,請留意勞先生的臉容、表情和身體,可能有朝一日你會為他造像。」想不到,這句話不到十年便成為事實! 勞先生銅像能夠在2017年於崇基未圓湖旁安放,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因為在唐先生銅像後,中文大學高層向筆者說:這應該是校園户外最後一個銅像,除非有很特別的原因,大學當局再不允許竪立雕像。事實上申請擺放雕像十分困難,人物肯定是學術界有特殊地位和對中大有影響力,加上要批地建立像基等等問題。建築物內是另一情況,錢穆半身像在新亞圖書館;沈宣仁頭像在崇基圖書館側的宣仁通識教育中心;馮景禧、許讓成等等捐款人的頭像擺放在對應的中大建築物內。 唐先生1974年從新亞退休,1978逝世,聽他的課和見過面的同學很多已經不再在學術界活動。但勞先生不同,儘管他1985年正式從中大哲學系榮休,直到他逝世為止,先生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活躍於學術界,著述講座無數。在世最後十多年他的學術成就更廣為世人肯定,獲學術榮譽不少,受無數後輩學生學者尊崇。 沈祖堯赴台送別勞師 2012年10月21日勞先生逝世。同年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送別儀式。筆者和幾位與勞先生有親切關係的同門師兄弟在殯禮兩天前已到台北。勞先生在台灣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重要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晚年極受社會和學術界尊崇,是以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到場親臨悼祭,並頒贈褒揚令,感念這位學貫中西、敦厚包容、清流議政一代哲人的嶙峋風骨。但令筆者感動和驚訝的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從香港趕來台灣,代表大學悼念勞先生。多年後我才知道是周保松建議沈校長到台北出席喪禮。(註一)儀式中馬英九和沈祖堯、關子尹、劉國英及筆者握手致意。相信這聚會令沈校長留下極深印象,埋下為勞先生做像的種子。 同年12月16日中文大學哲學系舉辦勞先生追思會。香港學術界、大學同仁、先生的學生和朋友聚首一堂懷念這位我們最尊敬的老師。沈校長致詞,極度讚揚勞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不屈的學者風範。致詞後公開向筆者和聽眾建議為勞先生造像,將老師從台灣再請回來香港,安放在中文大學校園內,成為中大人文精神的典範。...
中文大學戶外豎立的七個銅像中,唐君毅和勞思光雕像是由中文大學哲學系校友會策劃和推動,同學、老師和海外校友齊心協力而成的。相信這由下而上、眾志成城的造像過程,除了唐、勞兩個雕像之外,中大沒有其他例子,在香港其他大學似乎也沒有。那個是自由開放包容的年代,由哲學系校友會發起,循正常程序向校方申請放像和地點,然後向全世界校友和各方人士眾籌,標誌著中大人和世人對豎立兩個銅像的支持與肯定,不是由校方高層的決定和捐贈而成事。選址安放唐先生銅像經過不少磋商,最後決定放在孔子像下的草坪。能夠讓唐先生的精神具體地重回新亞,當然是雕刻家朱達誠老師的藝術成就。2009年初校友會同仁探訪朱老師在廣州的工作室和鑄銅廠,目睹朱老師透過唐先生的一張照片,由石膏模型到銅像,將青銅從無生命的物質,演變成為有精神生命栩栩如生的雕像,大家讚嘆不已。同年5月14日,朱老師將已完成的銅像穩穩安放在新亞圖書館側的草坪上,讓唐先生重回新亞書院。我們深信個人生命雖然短暫,但藝術和思想卻是永恆的。這個䇄立在新亞的銅像,只要新亞書院繼續存在不變,也會長存於世上,永遠是新亞精神的象徵。朱老師説:「銅像所要體現的就是一個『憂』字,即唐先生憂國憂民的精神。另外一個重點是銅像懷着希望,看着遠方,視線和同在新亞草坪的孔子像一致。近觀這兩米高的銅像,彷彿回到那神州板蕩、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時代。」(註一) 唐先生頭像模型(朱達誠提供) 雕刻家朱達誠對唐君毅像在鑄銅廠作最後的修飾(朱達誠提供) 2009年5月14日唐君毅像安放當天(張燦輝攝) 余英時為唐君毅銅像銘文2007年我們開始眾籌,不論捐錢多少,都不顯露捐款人姓名。我們收過一位中學生幾十港元的捐款,並寫上對唐先生敬佩的話,令我們甚為感動。但在芸芸捐款人中,最令我們驚訝的是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的來信和支票!眾籌當然要向全世界的中大、新亞和哲學系校友去信募捐,但我們沒有,也不敢寫信給余英時先生談及造像此事,更可況籌款!因為學術界知道中文大學在1974年改制時期,唐君毅和余英時的衝突和嫌隙。當時余先生身為新亞院長主張支持中大改革,從聯邦制改成為單一制的大學。唐先生與新亞元老竭力反對改制,指責余先生違背新亞理想,是為叛徒。(註二)即使唐先生去世後,二人的關係似乎都沒有辦法釋懷。余先生是次主動來信並捐款,令我們雀躍不已。眾籌結果很成功,款項超過造像工程所需。接下來便是決定誰寫銅像下的銘文。我們討論很久,但都想不到最合適的人選。筆者是唐先生和余先生後輩,不敢評論他們兩人的關係,但作為造像當事人,決心大膽去信余先生,懇求為銅像撰寫銘文,因為當今之世沒有人比余英時先生更合適。未幾即收到余先生正面回覆,答允執筆!唐君毅銅像加余英時銘文,肯定是華人學術世界的一件大事!翌年九月,余先生寄來銘文,才得悉先生之前抱恙多月,患病中仍執筆撰寫,我們實有難以言喻的感動。信中寫出銘文三百七十八字,分成三段:「首段説先生之學及其主要著述,次段論香港施教之成就,三段則説先生與新儒家之淵源。此三層皆先生學術生命之精要部分,無一可省。」(註三) 余先生銘文原文(張燦輝提供) 銘文全面肯定唐君毅的學術價值,以及對新亞及人文世界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余先生以這銘文冰釋他和唐先生多年來的恩怨。余先生銘文末段落款以唐君毅門人自稱,重新確認他和唐先生的師承關係。此見余先生的謙虛和寬容,胸懷坦蕩,不計前嫌。...
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在香港強行推出之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已經變成滿紙空言,香港淪為大陸一個沿岸城市,150多年來英國殖民統治下建立的種種優點,如法律、教育、新聞和公務員傳統全面被清洗。符合獨裁政權的需要,再沒有獨立自主精神。香港已死:自由、法治、開放、多元的公民社會全消失了。 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七所香港的大學,隨著李家超成為大學監督之後,學術自由再沒有什麼意義。國安法是每個學生和教職員共同遵守之法,任何對大陸、香港政府和大學的批評,任何不符合當權者角度的標準都是錯誤的。從此再沒有反對聲音,每個學生和教授都要接受現實,明哲保身,絕不碰撞紅線;教授埋首做純粹學術研究,不問政治,不理時代問題,保存學術生命。 在獨裁政權下的大學學者教授就這樣便滿足,無愧於心嗎? 業師勞思光先生在生前多次教誨我:「在共產黨專制下生活是無可奈何之事,但一定不要做幫兇,不搖旗吶喊,不阿諛奉承!」 勞先生1955年從台灣到香港,逃離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逼害,直到1989年重回台灣清華大學為訪問學人。那時台灣已慢慢成為民主和開放社會,已確立學術和言論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因此之故,勞先生實在從未有在共產黨暴政下生活過。他自由地在香港生活和做學術研究超過30多年,除了哲學研究外,還深入理解共產黨思想和歷史發展,對共產獨裁政權的批判從未間斷。他鄭重的告訴我:共產黨是不可以相信的。 如果2019年勞先生仍在生,親眼看到中文大學變成戰場,2020年目睹香港政府利用國安法將幾十年的自由香港毁於一旦,他又會如何評論?如何在中文大學繼續教學和研究?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絕對不會在五星旗下苟且殘存,做一個為生活而營役於獨裁政權的學者。他肯定會離開香港前往自由的地方。現在仍留在香港的學者教授,如何忍受在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繼續工作?除了謹記勞先生的教誨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民主女神像自2010年6月4日晚上開始豎立在中文大學火車站前,一直是中大人引以為傲的象徵,而自由和民主也是中文大學尊崇的理念。但2021年12月24日民女像隨同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被大學當局深夜清拆,大學高層當然沒有解釋真正原因。翌日,中文大學眾書院學生會公開指責:「我校本學術自由,開放批判精神。惟今淪落至搖尾乞憐,苟且偷安之學店。我等身為中大人,對校方如此失信無恥之舉嚴正譴責,並要求校方立即交代民主女神像處理事宜及將此事交還中大全體師生共同商討決定民主女神像未來去向。最後藉此(聯署)促請校方毋忘創校先賢訓勉,莫做奴顏媚骨之舉,重申學術自主之風骨。」中大學生面對不公義挺身而出,為所有中大人發聲,值得我們敬佩。 當然中文大學校方沒有正面回應,校長段崇智沒發一言,對學生會的要求不置一詞。令人沮喪的是,事後並沒有任何中大教職員發聲支持同學。 為什麼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對社會和校內發生種種不公義事情的批判精神喪失了?幾十年來教職員和學生都站在一起,對大學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公開抗議,據理力爭向高層表示不滿,但為什麼這次卻全部噤若寒蟬,不出一言?放棄批判思想,遺棄同學? 2019年前大學開放兼容並蓄 中文大學六十年的優秀傳統去了那裡?2019年之前的中大並不是這樣的。 2010年民女像豎立於中文大學的那天早上,我和中大哲學系超過二十位教職員在幾小時內草議和聯署一篇聲明,明確支持同學迎接民女像當晚從維園移入中大校園。我們是如此寫的:...
2022年7月1日中文大學香港回歸25周年紀念升旗禮,校長段崇智致辭時表示:「今天是香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標誌著『一國兩制』發展的重要里程,大學仝人很榮幸與各界一同慶祝。過去25年來,中大積極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並作出貢獻,藉著今天的重要時刻,讓我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 這天同時是沒有唸過大學的警察特首李家超成為中文大學監督的第一天,作為2019年11月警暴鎮壓中大和理大的主管,同時是另外七所大學的監督,以國安法為統治香港的「合法」權力武器,香港大專學界還可以繼續有「學術自由」嗎?中大段校長還可以捍衛「教學自主、言論自由」,不受政治干預嗎?段崇智在上面致辭中,已將中文大學變成為大陸的知識工廠,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大學不再是追求真理和公義、肯定思想自由和科學精神、以及敢於批評社會的地方。因為「真理」已被領袖決定,「學術自由」的標準隨當權者定義。喪失了真正的學術自由,中文大學仍然是大學嗎?段崇智所言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就是中文大學隨著香港的淪落而變成歷史。 最美麗山城大學 筆者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哲學系,當時火車站是馬料水,崇基校園在山下,山上只有水塔兩座和半山的范克廉樓。然後一座一座的建築物慢慢出現,新亞、聯合搬入,逸夫也成立了。崇基未圓湖和新亞天人合一亭也陸續建成,中文大學校園是全世界最美麗山城大學之一! 與此同時,中文大學教授和學生從「手空空,無一物」開始,全憑自己的努力,令中大學術與研究,慢慢成為世界級大學之一。當然因為中大有真正大學具備的條件:學術、研究、教學、出版和言論自由,還注重人文與科學精神,尊重人權、法治和個人尊嚴。 筆者和無數中文大學的同學、教職員和校友在這些理所當然的條件環境中渡過了幾十年的學術生命。這些人權所賦予我們大學成員的自由,從未被懷疑過,因為我們深信大學管理高層、教授和學生,都不言而喻的肯定和捍衛這些學術生命賴以存在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