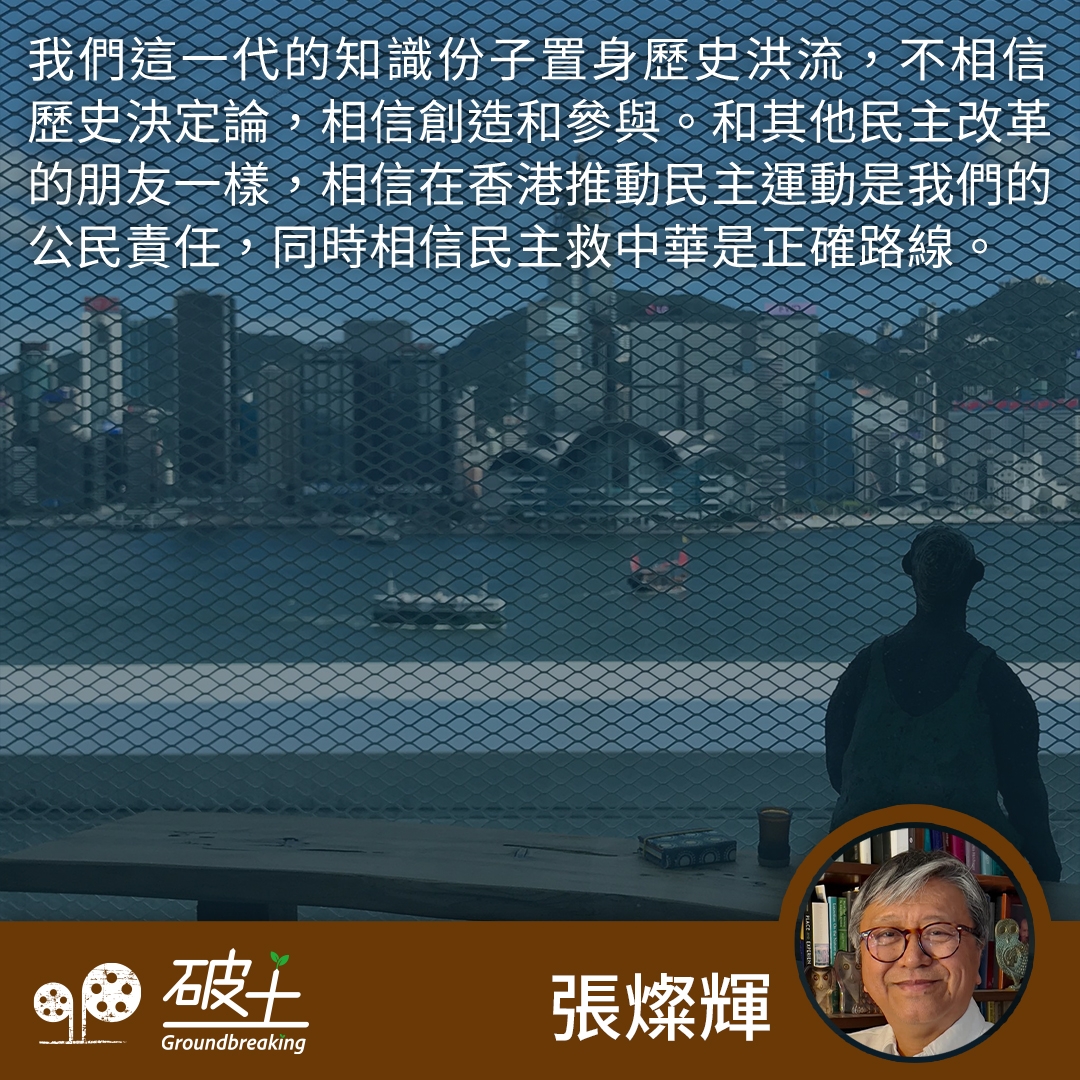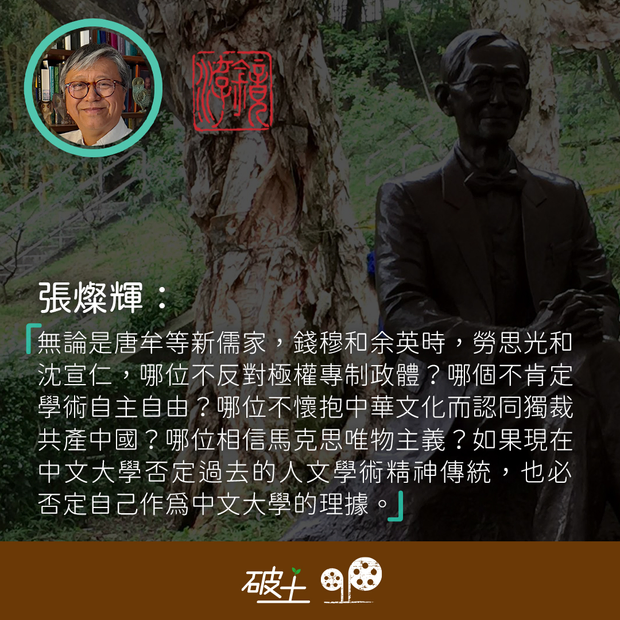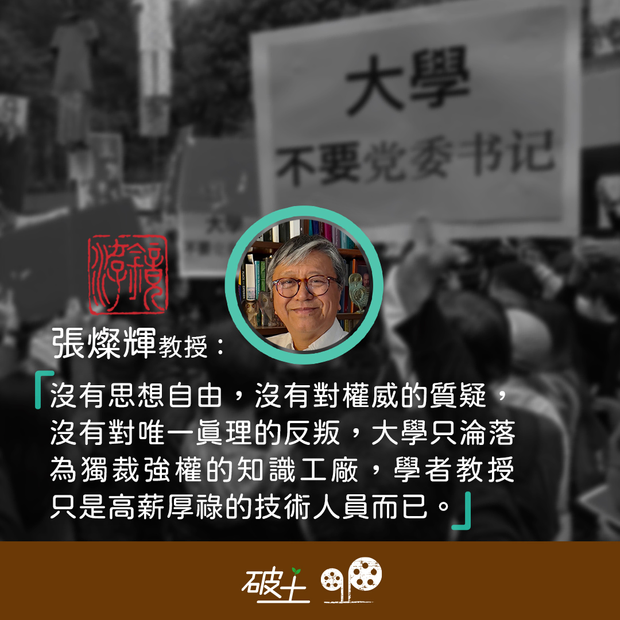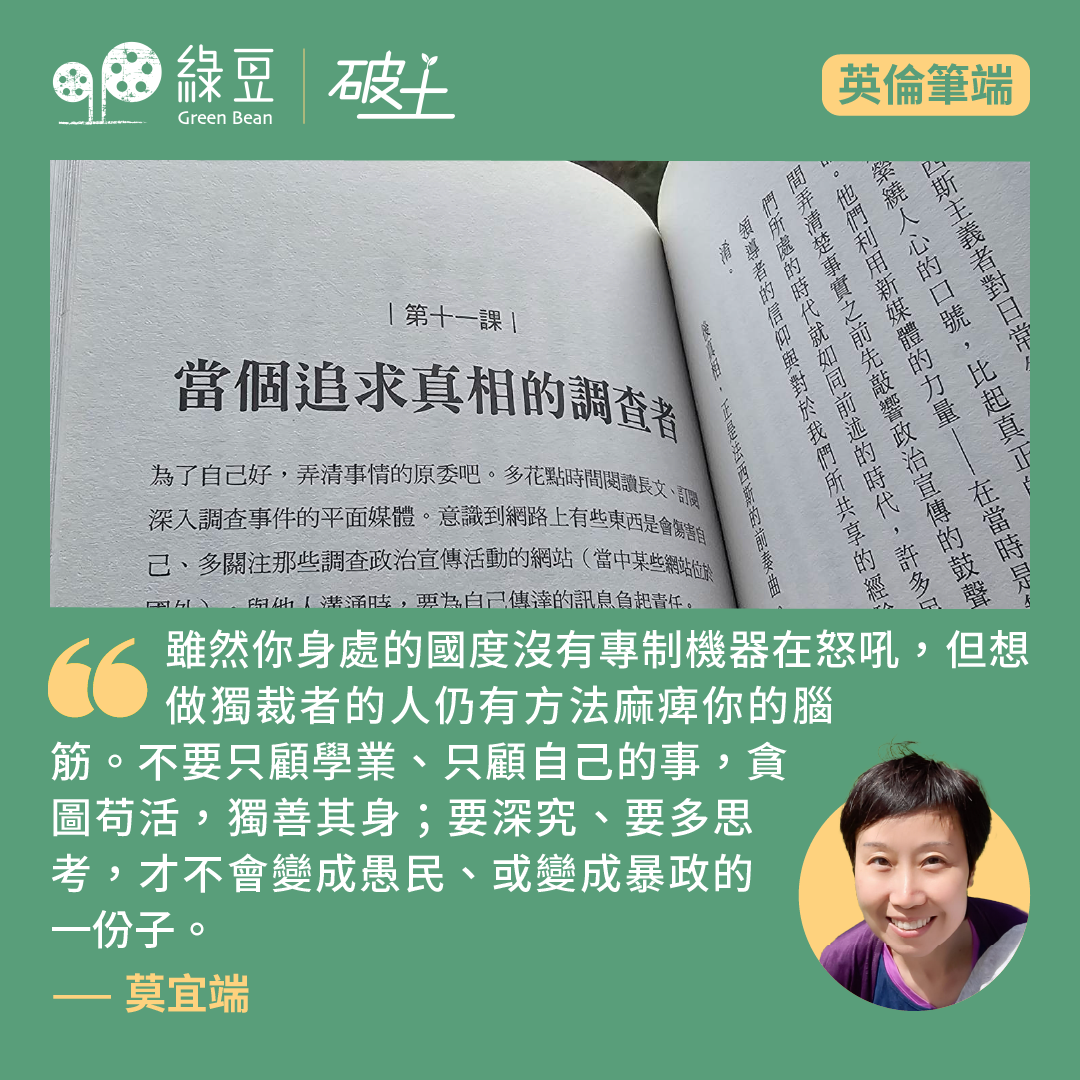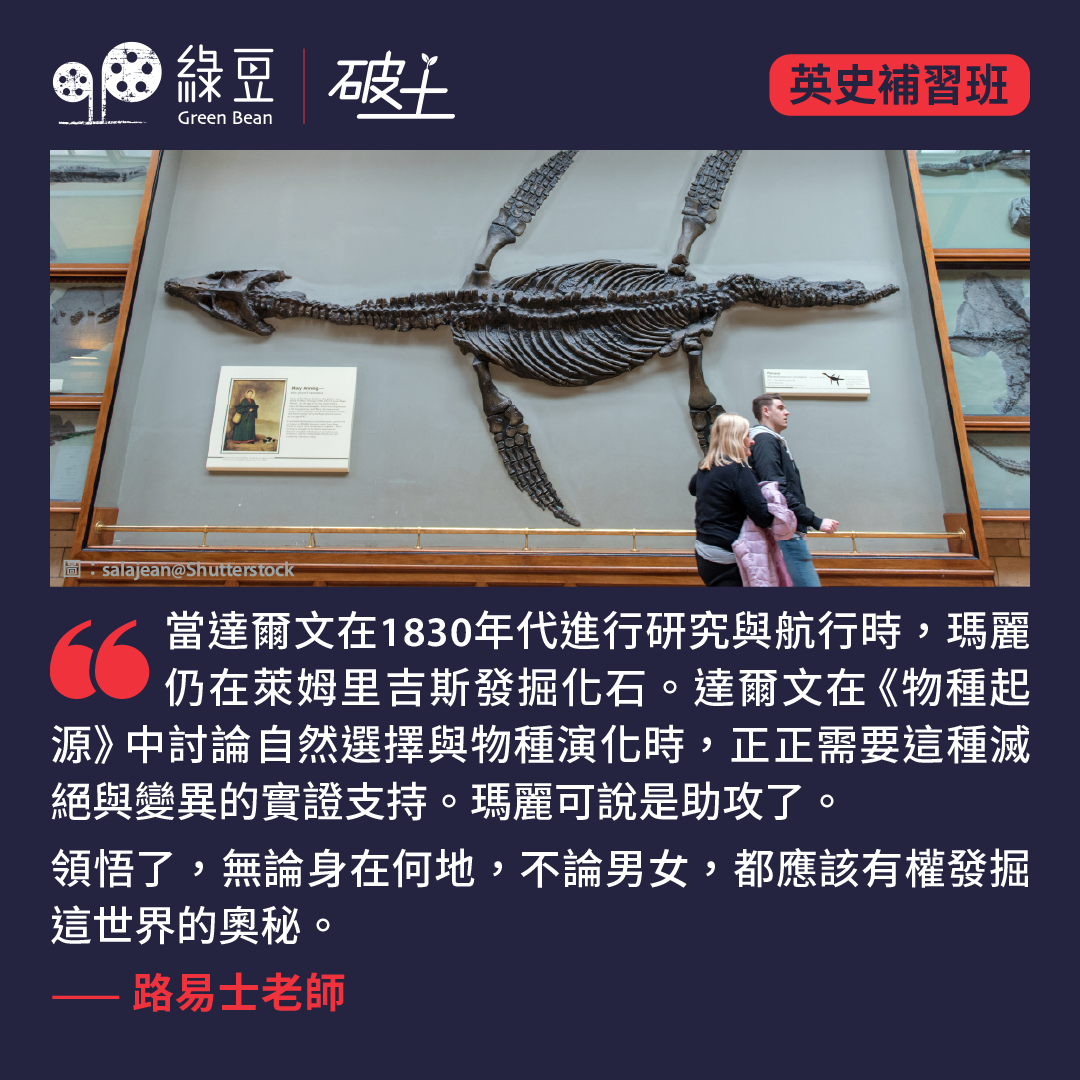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逝世,大批民眾自發悼念,政府嚴格管控悼念活動及言論;以色列拒絕國際社會的停火呼籲,持續轟炸及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加沙,巴人死傷數目急增;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向中大學者何曉清續發簽證,令她無法回港授課,中大隨即把她解僱。 李克強突然逝世 李克強突然逝世,官方宣稱死因乃突發性心肌梗塞,全力搶救無效。海外評論者卻普遍認為事有可疑,因為李克強年僅68歲,在退休領導人中屬於極其年輕,他擔任總理長達十年,在任期間和退休後都有專屬的醫護人員照顧健康,病發時在上海一個高級賓館游泳,距離醫院不過十數分鐘車程,大部分心肌梗塞病患在黃金兩小時内搶救都能救活,李克強卻返魂乏術,難免引起許多忖測。尤其中共高層正處於內鬥激烈時期,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擢升高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垮台,肇因卻秘而不宣,令中共高層人人自危,就在這敏感時刻,論資歷聲望唯一可與習近平比肩的李克強突然英年早逝,在政壇上引起的震動和忖測,自然非同小可。 李克強在任期間並無重大建樹,因為習近平非常強勢,他長期活在習的陰影下,重大事情都要向習請示,整個國務院被黨中央架空,總理的權力被大幅削弱。但這位「一事無成」的卸任總理,逝世後卻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悼念,追悼內容主要集中在他個人操守清廉、經濟學知識豐富、對中國經濟情況敢說真話,以及堅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市場改革路線。把這幾點內容,連繫到網絡上瘋傳的諷刺語句「為何不是他」,令許多評論者相信,民眾普遍對現狀不滿,對習領導下的政府施政有怨言,所以借追悼李克強來宣洩不滿,帶有強烈的控訴意味。 嚴厲管制悼念活動 由於李克強故鄉和全國多處都有大批民眾自發悼念,而追悼內容又不時語帶雙關,令北京當局高度緊張,害怕歷史重演,像過去周恩來與胡耀邦逝世,民眾追悼活動演變成大型政治抗議,但又不能禁止民眾悼念這位前總理。因為李克強是完滿落任,在政治上並無明顯過錯,中共中央因此一面給予高度評價,全國官媒高規格報道他去世的消息,喪禮也按正國級領導人規格進行,所有官方機構下半旗致哀。與此同時,安排盡快火化遺體,責令各地政府嚴格管制悼念活動,對公眾場所和網絡上的悼詞輓聯等也從嚴審查,阻止民眾對李的功績給予過高評價或搞公開告別活動。這些措施,明顯是希望平息悼念潮,使其盡快過去。...
第七封信 7.1 明慧, 今年(2023)是中文大學創校一甲子。我於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和中大的關係超過半世紀。成立60週年紀念應該值得大事慶祝,遺憾的是我和不少中大校友只能在香港以外懷念山城美好的時光,因為中文大學已經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讀書和研究的地方,而是為極權服務的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 當我們中大校友看到校長段崇智在校慶所説的話,便一再確定學術自主與自由的理想已是空言,為共產政權服務才是目的。他說:「中大創校時已背負結合古今、連結中西,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的理想……60歲是特別的歲數,象徵新開始,而國家正步入現代化發展,中大將融入國家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也將致力加強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註一) 但是,我們認定學術自主和自由的大學理想是否一廂情願的想法、美麗的主觀意願?追尋真理是否大學最重要的意義?大學的功能是應社會的需求而建立有什麼不妥?大學的目的是根據其效益而存在,為極權服務是理所當然;「學術自主和自由」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憑什麼去反對段崇智的呼籲?大學教授只不過是政府的合約僱員,傳遞知識和訓練學生是職責。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不重要。...
第六封信 6.4 明慧, 我大半生在中文大學渡過。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幸受到不少老師的錯愛和鼓勵;朋輩的支持和幫助。業師沈宣仁院長在崇基本科一年級教授大學理念和他的教學熱誠,尤其是他對人文和自然知識的追尋,是「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使我終生受益良多。何秀煌老師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肯定和規範性之確立,使我從他手中接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時,可在堅實的基礎繼續工作。但在我理解大學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上,最重要的是受金耀基教授開啓性的影響。他的《大學的理念》一書為所有華人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必備的經典。我思考大學精神和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很多方面從他的思想引發出來。 14年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可算是我教學生涯中較滿意的一部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有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於各崗位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熱誠參與。任期中多次課程改革和變更,沒有校方和同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金耀基校長和楊綱凱副校長對通識教育的執著,是中大通識教育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沈祖堯校長對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信心至為重要,但最難得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上下同事積極的參與才能推動。其中特別要致謝的是梁美儀教授、崔素珊女士、吳曉真小姐和趙茱莉博士。和他們共事多年是我的榮幸。(註一)...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第三封信上篇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需要認真回答,但第三封信繼續説我從德國回來後的故事。「民主」、「政治人,知識人」與「民眾」的矛盾問題,可能是等到第18封信才能和你討論。你信下半部尖銳的提問大學教育本質、學術自由、社會責任,我會在之後的信回答。這些是大問題,是我們學術人和知識人要嚴肅面對的。在大學中經歷超過半世紀,所為何事? 轉眼已是第三次給你寫信,回顧人生路,今天想和你返回我的第二階段初起步的時候,由我博士畢業後從德國回港後說起。 冷戰氛圍下...
前言: 我在第一封信末曾提及,之後討論的內容是以我過去45年的經歷為引子,以帶出討論的議題。早在2017年我已構思這本書,回應40年前《將上下而求索》第一版,而首四封信文稿,亦於2018年已寫好。 但2019年香港的巨變和淪亡,令我覺得要有必要重新審視立場和思考方向。2019年正如上世紀的Holocaust(猶太大屠殺),對西方知識份子是重要文化、政治和哲學思想的分水嶺;對我們來說是存在的覺醒:「香港人」是什麼意思?從1949年到2019年,對在香港出生的我是什麼的經歷?從殖民地到極權專制對我的生命有何影響?作為流亡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過去和將來?這些議題2019年前是沒有出現的。 我絕對沒有資格像李怡先生,能寫出《失敗者回憶錄》,因為我參與政治有限,也沒有全面認識共產黨。我只是一個在香港出生、資質平庸、領悟力一般和沒有背景的人,但因緣際會在這自由法治的地方成長、憑自己努力唸大學、拿獎學金讀博士,回來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當教授至退休。這些已經在第一封信序言談到,不贅。 以後的十九封信,並不會直接回應《將上下而求索》的每一課題。回首這本少作,儘管感受、方向至今未改,但信中的論述顯然是理論層次不高和不成熟,相隔幾十年後肯定有不同看法。想強調的是以下之反省和思考,是無數與我同年香港人經歷其中一個而已,相信比我更有深度和文采的朋友很多。如果有獨特的觀點就是我作為一個哲學學生和老師的經歷。...
2009年5月唐君毅銅像揭幕典禮時,勞思光先生是主禮嘉賓之一。唐先生銅像雕塑家朱達誠當然也在其中。筆者趁機會細語向朱達誠説:「老師,請留意勞先生的臉容、表情和身體,可能有朝一日你會為他造像。」想不到,這句話不到十年便成為事實! 勞先生銅像能夠在2017年於崇基未圓湖旁安放,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因為在唐先生銅像後,中文大學高層向筆者說:這應該是校園户外最後一個銅像,除非有很特別的原因,大學當局再不允許竪立雕像。事實上申請擺放雕像十分困難,人物肯定是學術界有特殊地位和對中大有影響力,加上要批地建立像基等等問題。建築物內是另一情況,錢穆半身像在新亞圖書館;沈宣仁頭像在崇基圖書館側的宣仁通識教育中心;馮景禧、許讓成等等捐款人的頭像擺放在對應的中大建築物內。 唐先生1974年從新亞退休,1978逝世,聽他的課和見過面的同學很多已經不再在學術界活動。但勞先生不同,儘管他1985年正式從中大哲學系榮休,直到他逝世為止,先生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活躍於學術界,著述講座無數。在世最後十多年他的學術成就更廣為世人肯定,獲學術榮譽不少,受無數後輩學生學者尊崇。 沈祖堯赴台送別勞師 2012年10月21日勞先生逝世。同年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送別儀式。筆者和幾位與勞先生有親切關係的同門師兄弟在殯禮兩天前已到台北。勞先生在台灣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重要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晚年極受社會和學術界尊崇,是以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到場親臨悼祭,並頒贈褒揚令,感念這位學貫中西、敦厚包容、清流議政一代哲人的嶙峋風骨。但令筆者感動和驚訝的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從香港趕來台灣,代表大學悼念勞先生。多年後我才知道是周保松建議沈校長到台北出席喪禮。(註一)儀式中馬英九和沈祖堯、關子尹、劉國英及筆者握手致意。相信這聚會令沈校長留下極深印象,埋下為勞先生做像的種子。 同年12月16日中文大學哲學系舉辦勞先生追思會。香港學術界、大學同仁、先生的學生和朋友聚首一堂懷念這位我們最尊敬的老師。沈校長致詞,極度讚揚勞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不屈的學者風範。致詞後公開向筆者和聽眾建議為勞先生造像,將老師從台灣再請回來香港,安放在中文大學校園內,成為中大人文精神的典範。...
2022年7月1日中文大學香港回歸25周年紀念升旗禮,校長段崇智致辭時表示:「今天是香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標誌著『一國兩制』發展的重要里程,大學仝人很榮幸與各界一同慶祝。過去25年來,中大積極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並作出貢獻,藉著今天的重要時刻,讓我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 這天同時是沒有唸過大學的警察特首李家超成為中文大學監督的第一天,作為2019年11月警暴鎮壓中大和理大的主管,同時是另外七所大學的監督,以國安法為統治香港的「合法」權力武器,香港大專學界還可以繼續有「學術自由」嗎?中大段校長還可以捍衛「教學自主、言論自由」,不受政治干預嗎?段崇智在上面致辭中,已將中文大學變成為大陸的知識工廠,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大學不再是追求真理和公義、肯定思想自由和科學精神、以及敢於批評社會的地方。因為「真理」已被領袖決定,「學術自由」的標準隨當權者定義。喪失了真正的學術自由,中文大學仍然是大學嗎?段崇智所言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就是中文大學隨著香港的淪落而變成歷史。 最美麗山城大學 筆者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哲學系,當時火車站是馬料水,崇基校園在山下,山上只有水塔兩座和半山的范克廉樓。然後一座一座的建築物慢慢出現,新亞、聯合搬入,逸夫也成立了。崇基未圓湖和新亞天人合一亭也陸續建成,中文大學校園是全世界最美麗山城大學之一! 與此同時,中文大學教授和學生從「手空空,無一物」開始,全憑自己的努力,令中大學術與研究,慢慢成為世界級大學之一。當然因為中大有真正大學具備的條件:學術、研究、教學、出版和言論自由,還注重人文與科學精神,尊重人權、法治和個人尊嚴。 筆者和無數中文大學的同學、教職員和校友在這些理所當然的條件環境中渡過了幾十年的學術生命。這些人權所賦予我們大學成員的自由,從未被懷疑過,因為我們深信大學管理高層、教授和學生,都不言而喻的肯定和捍衛這些學術生命賴以存在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