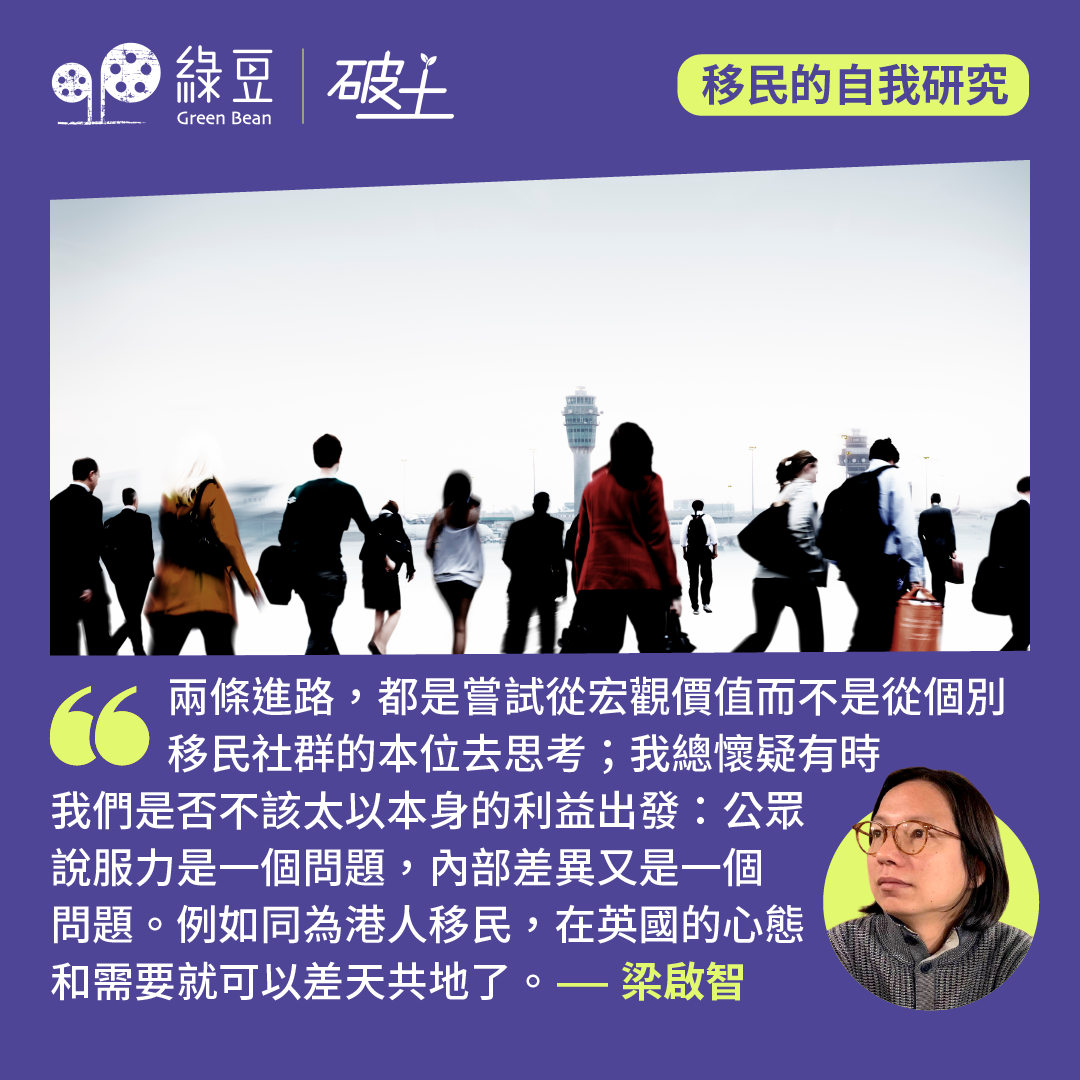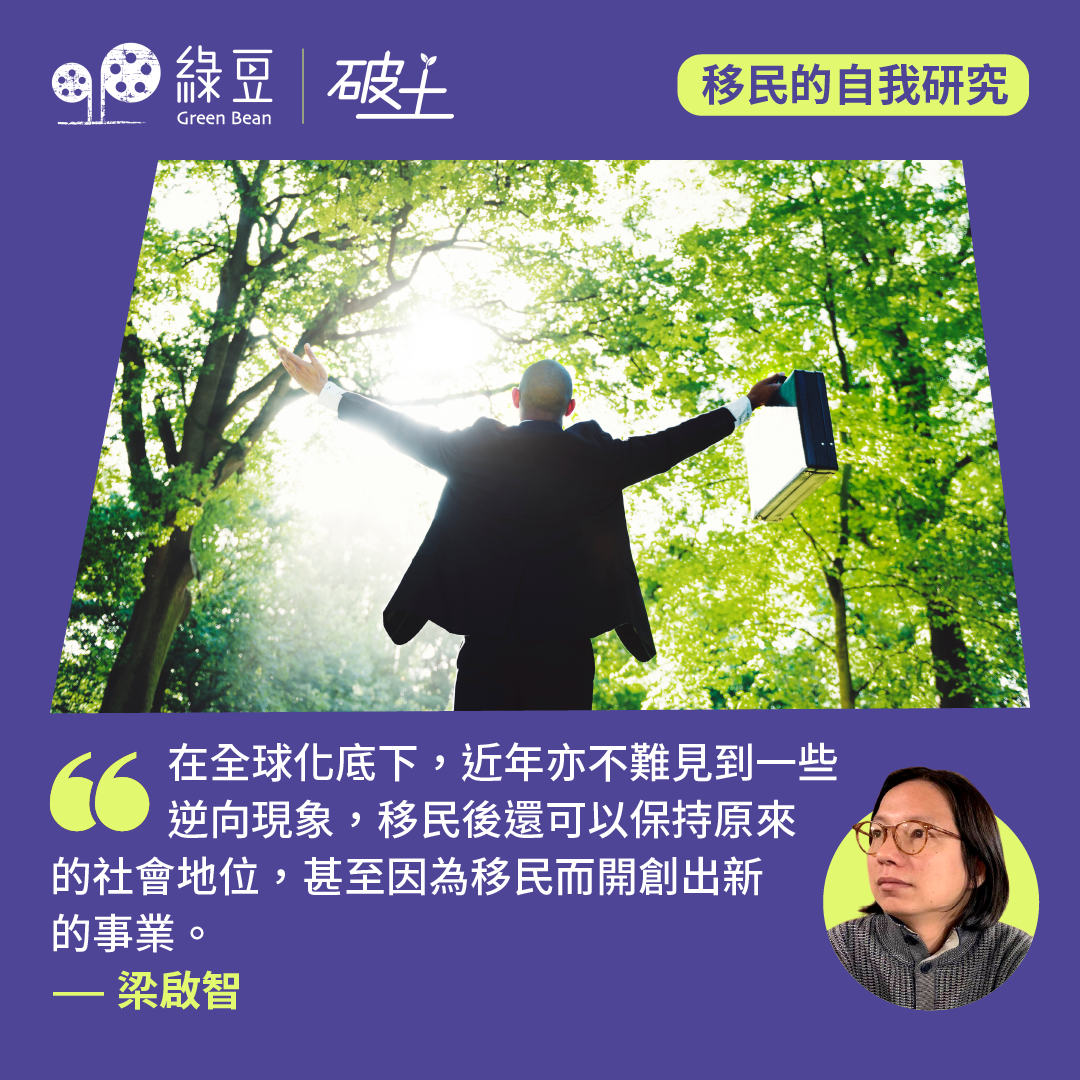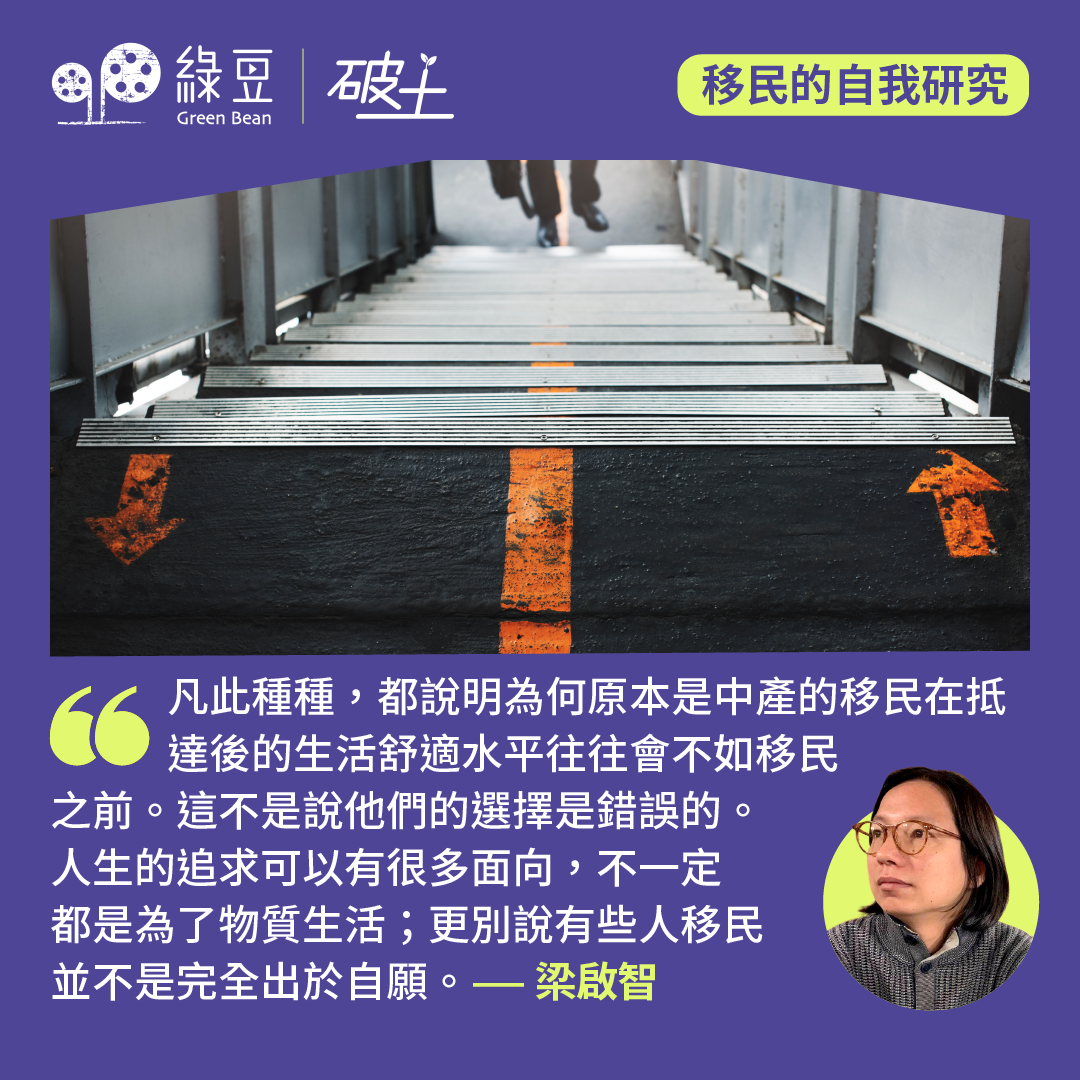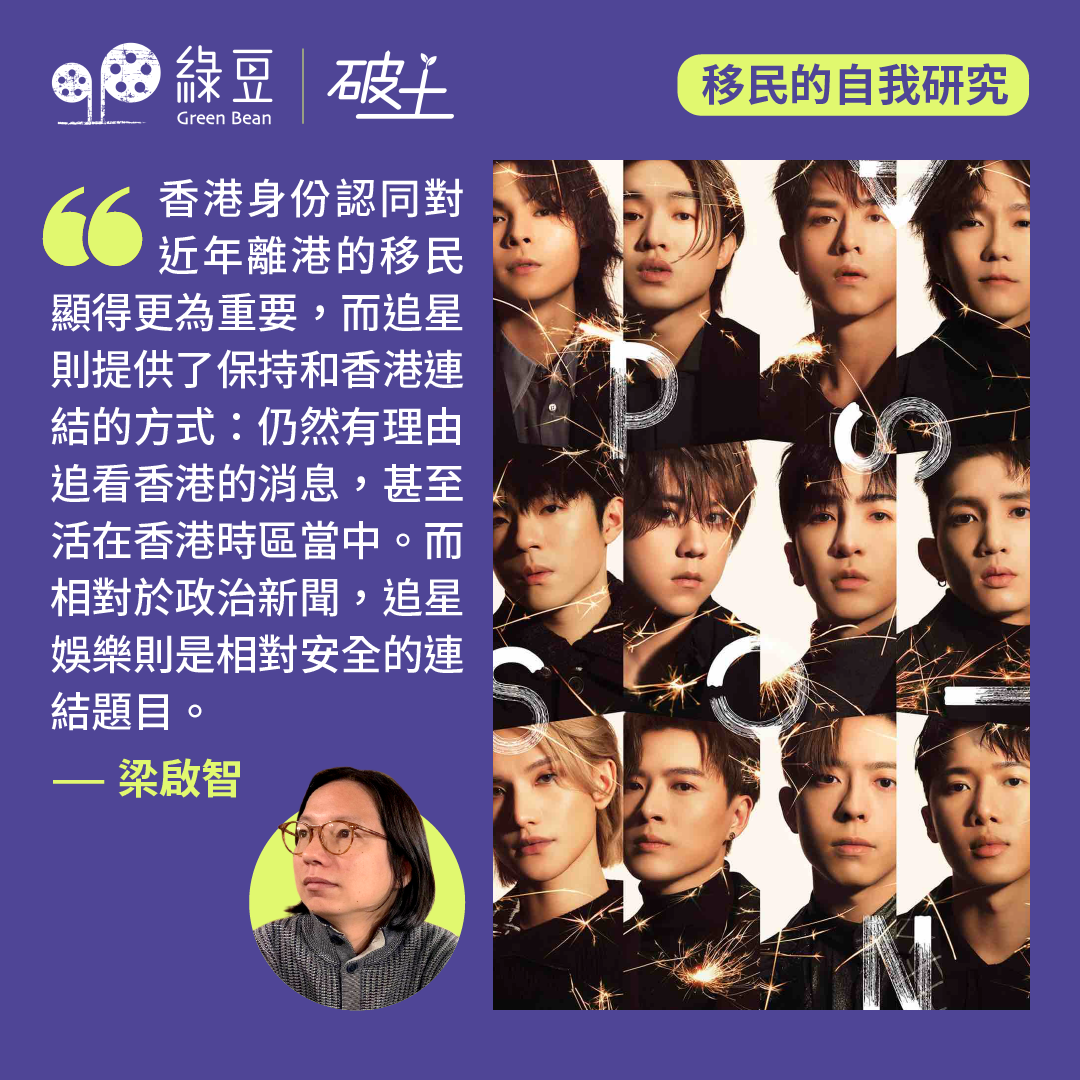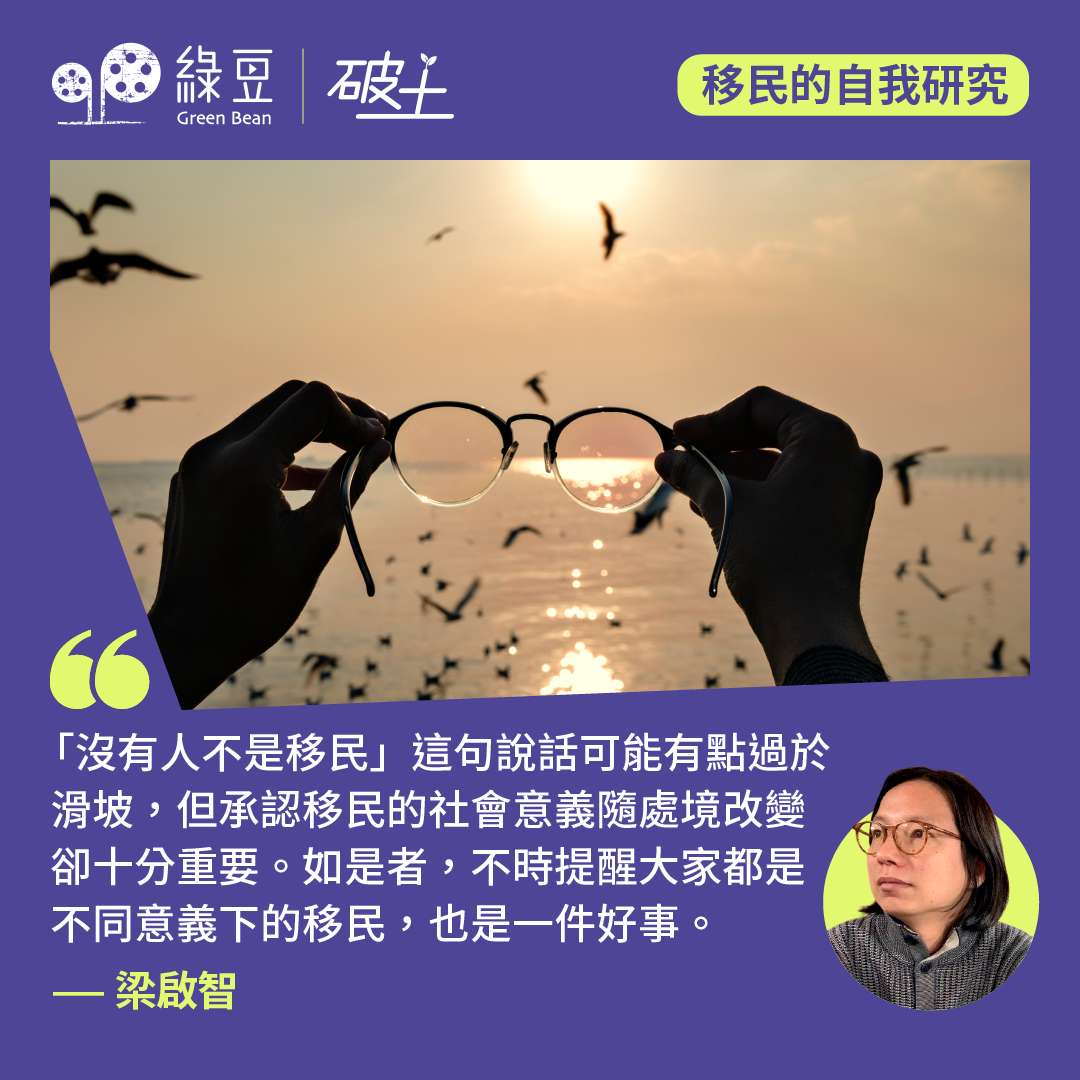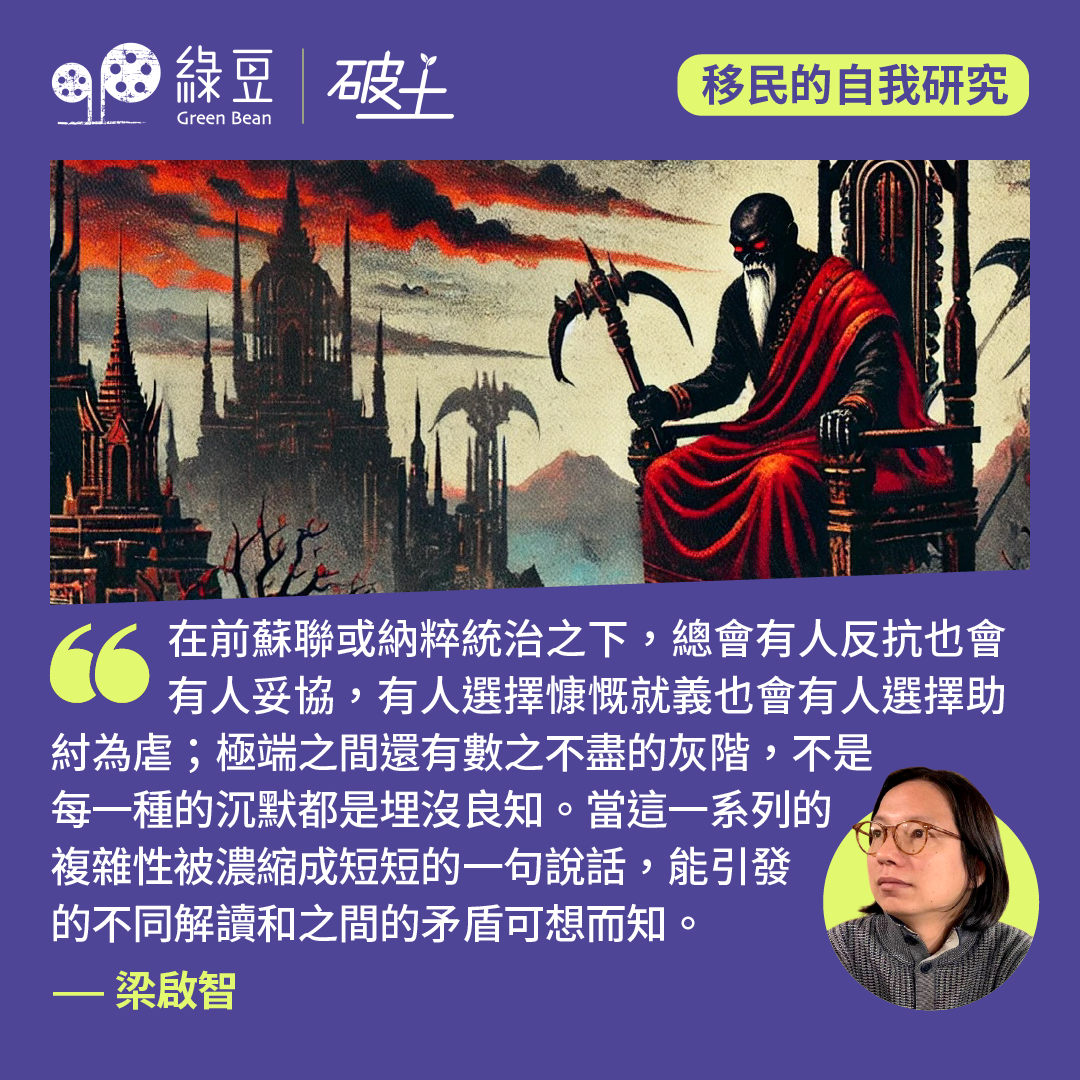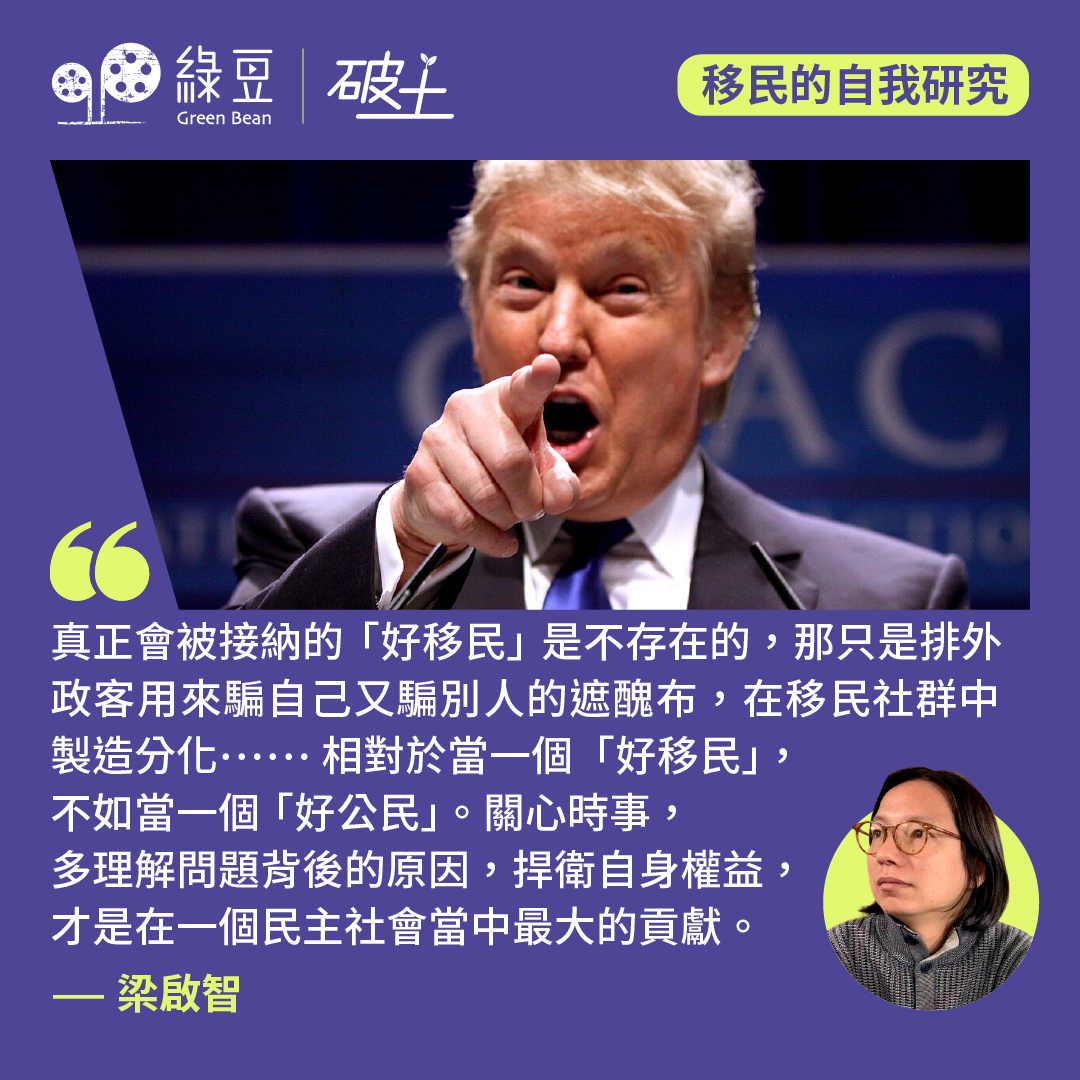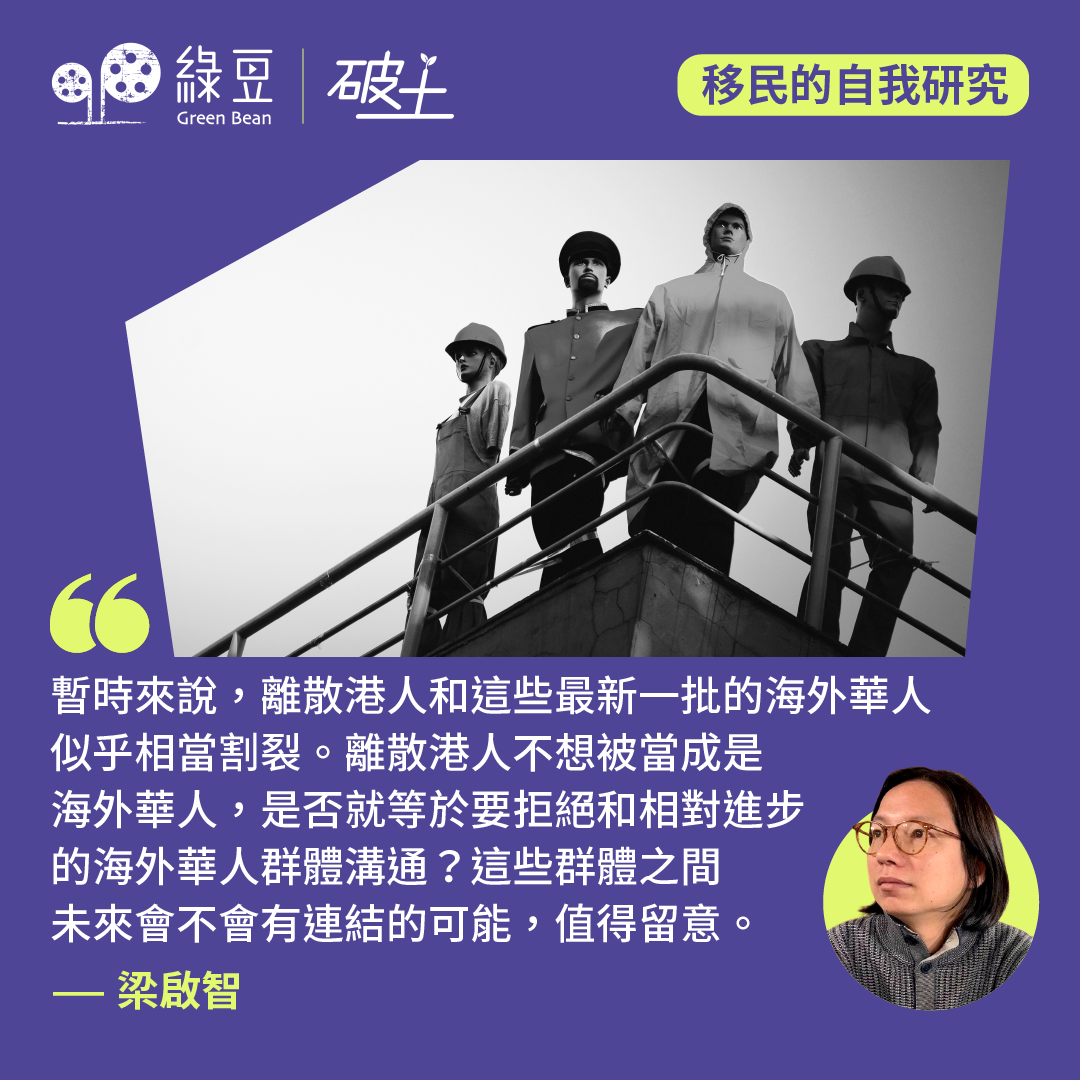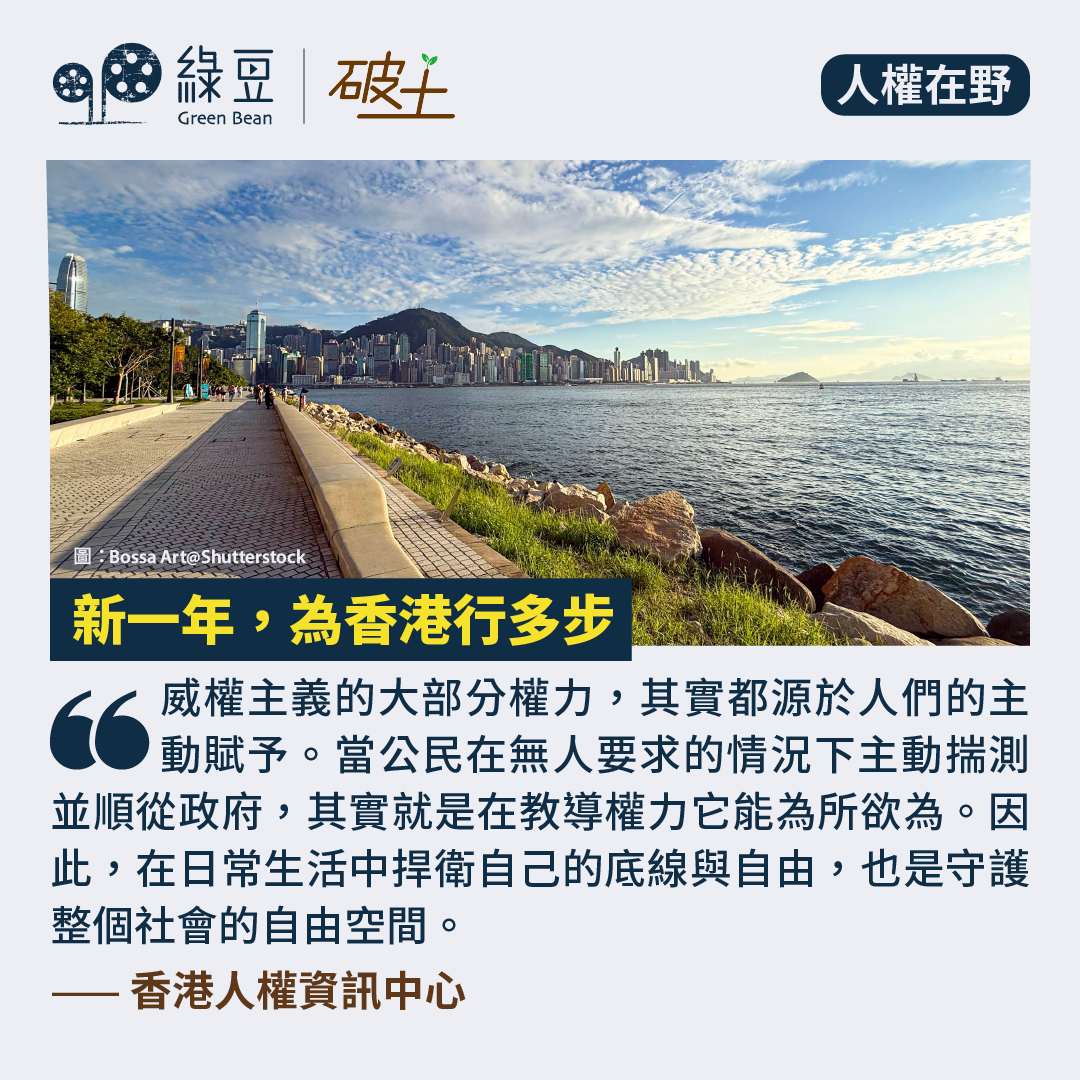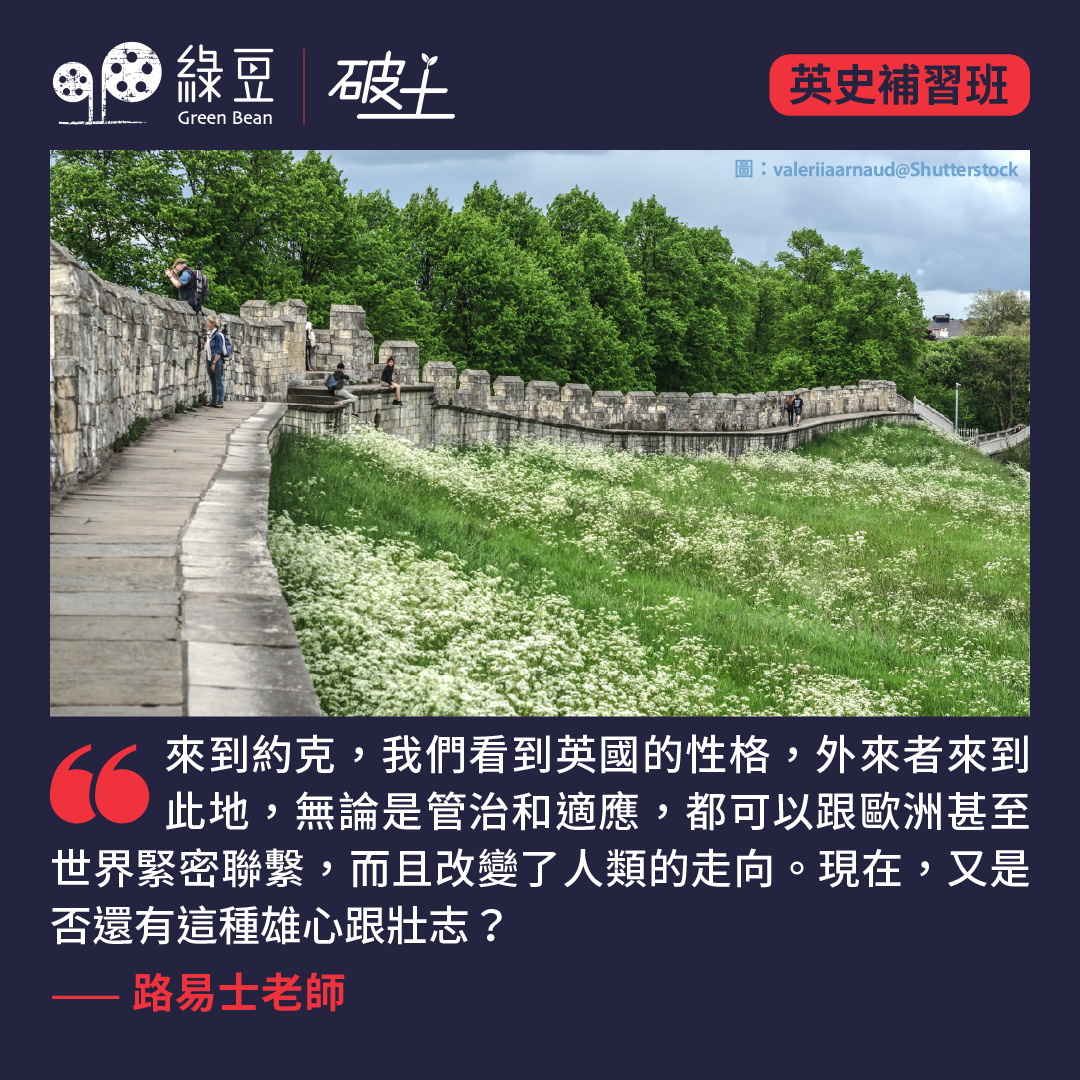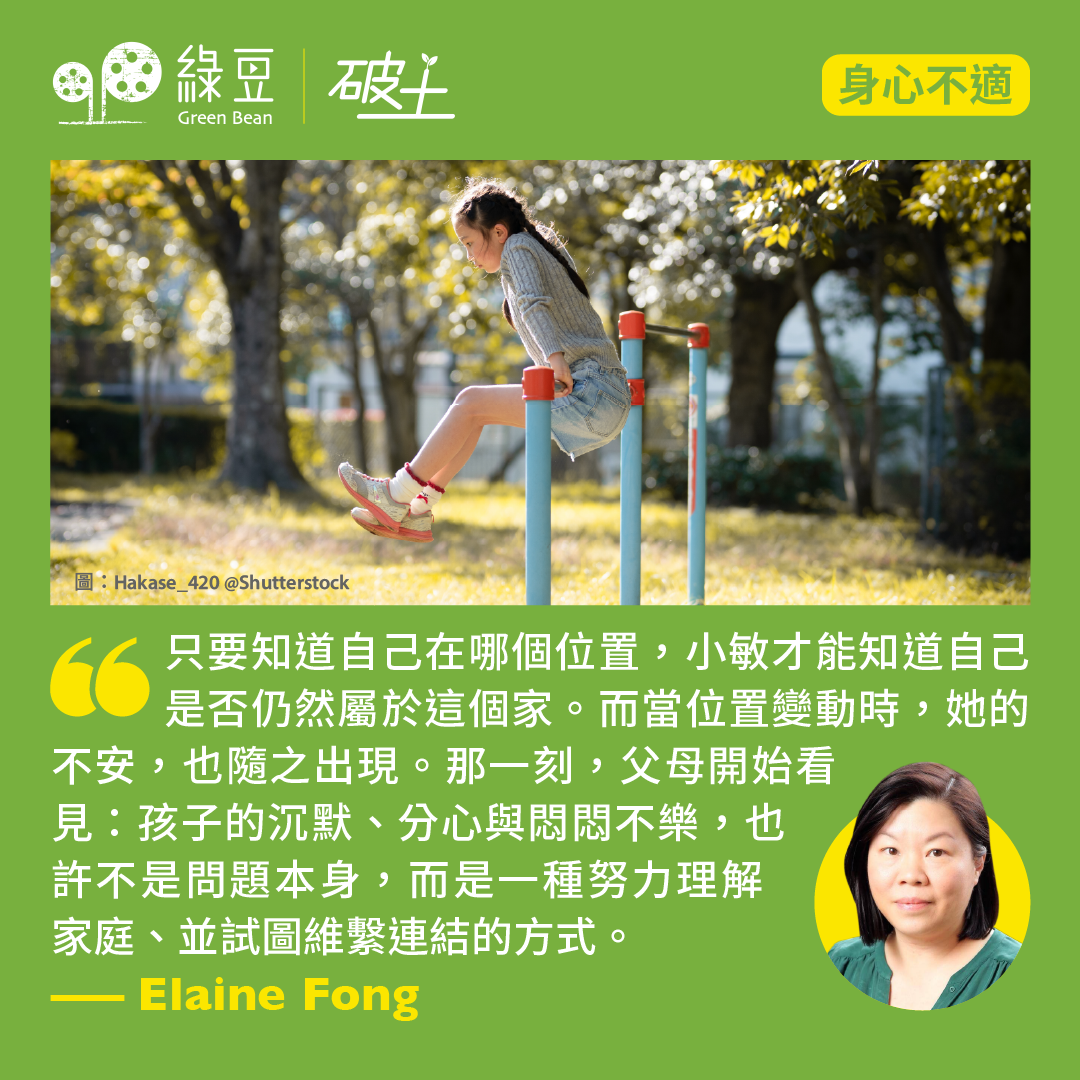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是社會政策議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兩者的分別,在於如何對待少數。移民研究要處理的正正是少數外來者要如何在大社會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自然難免會涉及平等和公平的問題。 簡而言之,平等強調對所有的人相同對待,公平強調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以達至現實上的平等。例如對於要坐輪椅的人,我們的社會不會說「所有人都要走樓梯」才是公平,而是會刻意多花成本設立輪椅專用的通道,讓他們也能在後果來說得到公平。當然,正如本欄過去多次提到,「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差別對待」的原則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要分辨出在哪些時候應該差別對待卻十分困難。雖然法律上常見「受保護階層」(protected class)的概念,列明膚色、宗教、性別、康健、年齡等類別的特殊地位,但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數之不盡的矛盾,告上法庭或要求修法的聲音亦是無日無之。 千萬種差別對待的理由 移民在許多地方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在這問題中當然不能倖免。而更麻煩的事情,是移民社群本身存有巨大的內部差異,同一套邏輯對某一個移民社群有利,對另一個移民社群則可變成不利。大學入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純粹追求平等,那十分簡單,十萬考生回答同一份考試卷,最高分的一百名考生入學,大學入學處除了考生編號之外甚麼都不知道,這樣最少看起來就是完全平等待遇。但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對待,例如有身心缺陷的考生我們會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完成試卷,畢竟他們往往不見得自願的,一般人認同社會有補償的必要。然而一旦我們開始考慮各種「不自願」的缺陷,則出生在一個因為歷史和政治原因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原住民社區,又算不算是一個提供差別對待的理由?如是者,有些社會又產生了「原住民加分」的制度,彌補社會過去的不公。 很明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些做法。當大學入學(或任何需要競爭的機會)不再只考慮冷酷無情的測試和分數,而開始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特別是種族)的時候,就會吵得特別厲害。有些人是原則上反對,有些人則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公平所以不用再考慮。來到移民社群,一方面有移民社群會因為相關政策而得益,但也有不少例外。例如亞裔移民來到歐美社會,父母特別會強迫子女讀書考試,如果大學入學只看考試分數的話便全部都是亞裔學生,大學於是實施配額減少亞裔學生的比例;那麼在亞裔考生的角度出發,則會寧願不要基於族裔的差別對待了。...
前文提到,一般來說中產於移民後被迫向下流動,往往被視為正常現象。畢竟之所謂社會身分,來來就必然嵌入在個別社會當中,無論是專業證照、街頭智慧還是人脈關係,一旦離開了便很可能會隨之失去,要在移居地重新累積。不過,在全球化底下,近年亦不難見到一些逆向現象,移民後還可以保持原來的社會地位,甚至因為移民而開創出新的事業。 各個移民因由 在解釋新現象之前,先說明一點:為什麼有下流風險,不少中產仍然甘心移民。這兒不外乎出於三種情況。第一,是原居地的情況正在變差,包括精神價值或是物質條件,以致潛在的移居者推算就算移民後會向下流動,留下來可能更糟糕,移民實為兩害取其輕。所以對於那些聲稱「多搵幾年錢才移民」的人,到了發現香港經濟明顯轉差的時候,就是考驗是否真正坐言起行的關口。 另一個古今中外常見的理由,就是移民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下一代。因為不想子女要在受限制的環境下成長,寧願犧牲自己的事業也要帶子女移居他方,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中各次移民潮的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按黃子華在《秋前算帳》中的說法,如果沒有下一代,其實我們是不用移民的。 最後,就是移居者本身擁有豐厚金錢資本,所以移民後就算失去本來的專業工作,也無損其社會身分。香港寸金尺土,許多中年的中產人士本身在香港已有物業,如果早兩年趁香港樓市高峰期的時候出售,移民後已基本上高枕無憂,可以過半退休生活,時間拿來料理家務種花養狗。曾經遇過資產豐厚的移英港人選擇做貨倉,只是為了打發時間,還說現在因為上班不用過於動腦筋而十分快樂。如果選擇去一些性價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台北以外的台灣,則實行成本更低。 向上流動機會 不過對於較年輕的移居者,無論是為了自我認同還是有實際的經濟需要,移民後總會希望重拾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點對這一波的移民來說又確有不少可能性。...
按照經典的社會理論,中產在移民後往往會經歷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在這一波移民潮當中,身邊也見到數之不盡的案例。不過與此同時,可能是時代變遷,又或香港移民本身的特質,也遇到不少例外情況,移民後仍然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以前更風生水起。 傳統來說移民後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往往是和工作相關。現代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不是含金鎖匙出世,很多時候都是來自他們的工作;尤其是中產,他們不少都是專業人士,不單收入比較高,在社會上很多時候也較受尊重。移民對他們的衝擊可以十分直接,畢竟甚麼是專業本身就因地而異,香港很吃香的專業例如金融服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沒有需求的,反而某些在香港不被重視的工作如維修通渠,在當地才是真正專業人士。 專業資歷認證 另一個常見的原因,則是專業資歷要靠政府認定,移民後原有的資歷不一定能帶過去,當地很多時候會不予承認。沒有資歷認證,便做不了原本的工作,本來的專業人士要轉做能力錯配的工作,於是工作和社會地位都會下降,亦是移民後向下流動的常見案例。 資歷未能獲認證原因可以有很多:最常見的說法是當地專業有保護主義,不歡迎外來人士爭飯碗。不過這說法可能只是部分事實,後面通常還會有些實際理由。例如在美國,即使是在國內,許多州份的律師資格也不互通,畢竟每個州份的法律都不太一樣,更別說要到別的國家。律師要看法例,但許多專業也是和法律打交道的,醫生和工程師都要知道當地的監管制度才能有效工作,移民後資歷難免無法自動承認。 即使不看法律的部分,各地對專業內容的要求不一樣,有些知識或技能在當地看得很重要,在香港考牌時卻未必有考,也難怪當地要花時間釐清是否合適。又或者有些專業在香港本身也經歷過轉變,以前取得比現在要容易;當地查看過後,不接受某些持有舊資歷的香港申請人也有他們的道理。 當資歷不被承認,那可以怎麼辦?最直接就是重新考牌,但現實上有時還有迴旋的空間。舉個例,駕駛執照在國際間不時會有各種不協調,甲地的駕照和乙地不能互換,但甲地和丙地可以,而丙地又和乙地可以,於是便有人會繞個彎避開本來的資歷阻隔。有些專業資格國際上原來也有類似的情況,也見過有港人移民通過第三地取得移居地的資歷。至於當利用這方法的人越來越多,當地的監管機構會選擇「堵塞漏洞」還是索性直接開方便之門,則很大程度按各行各業的具體環境而定。例如英國就決定開放授予海外教師「合格教師身分」,為許多移英港人教師帶來重執教鞭的希望。...
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
近年到美加澳紐等地的大學參與學術交流活動,不時會聽到主辦單位在開場之前會先做一個「原住民土地確認」(Land Acknowledgement),向參與者說明活動所在地點的歷史。一般的宣言會包括「我們今天相聚的地方是(當地原住民民族)的傳統及未被割讓的領土」等字句,說明今天大家來開會的會場歸根究底是從原住民手上強搶而來的。 這種宣言大約是近十多年來開始流行,用意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對原住民的尊重。有在加拿大的港人組織也在網站上展示類似的宣言,鼓勵赴加港人多認識加拿大原住民的歷史。對於這些做法,有些人認為是對歷史的尊重,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無論是開明派或保守派,都有反對聲音:雖然出發點未必一樣,但都認為這些儀式只是門面功夫,做出來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口惠實不至。 對此,我問過一些當地朋友,卻又未至於完全反感,反而頗肯定其作用。面對白人主流對可見少數族裔的歧視,這些做法起碼可以警剔那些白人優越主義者:別忘記,你們自己也是移民後裔,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並不是你們。 「自古以來」 沒錯,在美加澳紐等移民社會,除了原住民以外,所有人某程度上都是移民或移民後代。因此,所有今天針對新移民的說法,對當地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同樣適用。例如說墨西哥裔移民到了美國之後繼續說西班牙語,建立只說西班牙語的小社區,引來不少批評;但是別忘記美國本身沒有法定語言,那些批評新移民沒有轉用英文的,也不見得自己有學會美洲原住民的語言。如果說擔心移民會取代原有的生活模式,則不得不說白人才是這方面的模範生。在此脈絡下,批評者不是真的關心文化承傳,只不過是害怕自己的主宰地位不保。 也有論者把類似的議論延伸到台灣。過去台灣常有「省籍之爭」,即「本省人」和國共內戰後遷台的「外省人」之間的問題。有評論就認為要把時間尺度拉闊,所謂的「本省人」也是從中國大陸移居來台,只是再早幾百年而已,然後延伸出台灣有七代移民的說法。...
台灣有文學雜誌評選90後作家,有移台港人入圍,評選紀錄當中「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一句,「馴化」一詞引發許多不滿。許多港人論者,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台灣的,都批評說法不尊重留港港人。文學雜誌後來表達歉意,並表示將會在紙本雜誌中發出勘誤與更正啟示。 自移民潮以來,如何描述仍然留在香港的港人一直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題目。有些離港者經常強調「香港已死」,批評留港者沒有看清形勢拒絕離開,一旦香港政府作出甚為荒謬決定便會揶揄一句「留港者值得擁有」,這些說法常常引來留港者的不滿。畢竟不是每個人可選擇離開,離港者如果不相信香港還有未來,又何必還要落井下石?於是又有輿論批評說這些話的離港者只不過是在艱難的生活適應中尋找自我安慰,意圖通過貶低留港者來合理化自己的移民選擇。類似的離港留港之爭,自移民潮以來已不停出現。 另一個類近的面向,是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朋友,見到香港情勢近年的急速逆轉,亦會表達各種類近「香港已死」的慨嘆。畢竟這些朋友都是在外面看香港,甚至本身從來沒有到過香港,相關說法往往流於概括或過於扁平,留港者聽到難免感到有點離地。近來網上常見一般台灣人外遊,擔憂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會否被警察拘捕,引來港人取笑「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高」。接下來就是台港雙方罵戰無限輪迴,這邊說不懂就不要亂散播恐懼,另一邊說蔑視恐懼正正代表走向麻木。 複雜性被濃縮 這次台灣文學雜誌帶來的反響,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爭拗的延伸。最初讀到「馴化」一詞時,坦白說反應並不是很大。有文友查字典說馴化是應該用在動物身上,用來形容港人是侮辱。然而在社會科學的語境,以馴化來形容威權統治下的公民社會不無案例,亦無侮辱之意;即使在文學雜誌中看到,自問也不太感到突兀。當然,每一位讀者的背景都不一樣,相關議題本來就十分敏感,而且早已被附加各種意義,帶來爭議亦不應意外。 當然,在學術世界談馴化,總會帶上一系列的條件和說明:政權意圖馴化社會,不代表社會已成功被政權馴化;馴化有程度之分,而即使表面上被完全馴化的社會,底層仍不難尋找到異議。去歐洲參觀各地的佔領博物館,看到各地在前蘇聯或納粹統治之下,總會有人反抗也會有人妥協,有人選擇慷慨就義也會有人選擇助紂為虐;極端之間還有數之不盡的灰階,不是每一種的沉默都是埋沒良知。當這一系列的複雜性被濃縮成短短的一句說話,能引發的不同解讀和之間的矛盾可想而知。 承認轉變是回應的第一步...
這一代的香港人移民離港,除了極少數未能像一般旅客從機場出境的尋求庇護者之外,大多數都是按正常途徑離開,到達目的地後通過正常途徑申請留下來。不過近年來佔領新聞版面和主導輿論的,往往都是那些自行跨過邊界的「非法移民」。美國有來自中南美洲的,歐洲有來自北非和中東的。他們的情況主導了社會對移民的思考,也連帶影響到社會對其他移民社群的接受程度。 說下去之前,先處理一個問題:所謂「非法移民」的說法,在香港十分普遍,但在歐美社會卻有一定爭議。不少支援移民的團體認為應該用「非正規移民」或「無證移民」等說法,可以讓社會更完整的理解他們的存在,而非僅僅視之為執法問題。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意,例如法庭會認為他們確實是違反了出入境條例,最少在法庭這個場合把他們稱之為「非法移民」,反而更為中性。 順帶一提,移民本身在美國經常被稱之為 Alien ,與公民(citizen)相對。可能因為 Alien 一詞今時今日會讓人想起外星怪物,也有政府機構開始改以「非公民」(noncitizen)為稱呼。以前台灣的居留證是叫...
美國總統大選辯論,一如所料移民議題成為重點的討論項目。不過,出現的方式有點奇怪,甚至成為了辯論後被瘋傳的內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說,在俄亥俄州的春田市,來自海地的移民在偷鄰居的貓狗烤來吃。這件事當然不是事實,但也揭示了移民作為政治議題的一些重要邏輯。 慘劇被當政治工具俄亥俄州是美國的傳統工業州份,曾經一度沒落,近年有重新振興之勢。海地移民聽到春田市有工作機會,口耳相傳紛紛湧至,估計過去數年來了超過一萬人。 他們都是合法移民,努力工作改善生活;不過因為人數真的太多,整個春田市的人口忽然增加了四分之一,形成了各種生活壓力,也出現了居民和移民之間的矛盾。早前一名十一歲兒童於一宗交通意外喪生,海地裔司機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社區矛盾變得更為尖銳。 就在這個時候,傳出「移民偷鄰居的貓狗烤來吃」的傳言,並被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拿來在演說中當作案例,並被特朗普在辯論直播中提出。畢竟事件十分敏感,辯論主持立即澄清當地政府官員已表明並無此事,然而特朗普繼續辯稱「但是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人這樣說」。本來堂堂總統候選人,好像無知路人一樣拿電視上看到的片段當證據已經十分荒唐,何況身為公眾人物在緊張的社會氣氛下為偏見助燃更是不負責任;辯論後春田市收到34宗的炸彈恐嚇,學校被迫改為網上授課。 同為共和黨籍的俄亥俄州州長表示,移民政策是嚴肅問題,他在這方面對拜登政府也有不滿,但認為散播謠言無助解決問題,反而會模糊焦點。他說這時候煽風點火沒有好處,並對特朗普和萬斯一再重覆謊言表示失望,認為他們的言詞傷害了春田市和當地人。最初在社交媒體貼出質疑的網民表示後悔,交通意外中喪生兒童的父母要求政客不要再拿孩子的悲劇當作政治工具。 移民就是原罪春田市的事件發展至今固然可悲,然而移民議題被拿來政治操作卻是長久以來的問題,而且有自己一套的邏輯。 首先,散播謠言的人並不真的關心真相。在萬斯首次拿海地移民做文章之前,當地官員已通知了他謠言並非事實,但他 還是繼續說下去。到了第二天,他又說:「就算可能謠言最後被證明是假的,但你知道什麼是真的?傳染病在上升!」於是當地官員又要再花精力解釋傳染病其實沒有上升。這不是說當地社區沒有問題,人口急升當然會帶來問題,但解決問題要制度配合,然而排外政客明顯只想製造更多矛盾。 因為真相在排外政客面前不重要,只要對方是移民就有原罪,這樣也打破了許多人以為只要「當一個好移民」便可以避開歧視的想法。排外政客聲稱不是反對所有移民,只是反對「非法移民帶來社會負擔」,然而春田市的海地移民是合法而且努力工作,州長還肯定他們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但只要排外政客有機會炒作議題,各種貢獻都可以被瞬間忽視。 不存在的「好移民」想當一個「好移民」?在排外政客的邏輯中,你是永遠沒可能做得到的:你不工作,你就是虛耗社會福利;你努力工作,你就是搶走本地就業機會。你不工作也不拿福利,只靠自己帶來的積蓄過活又如何?抱歉,你的存在就佔了空間,房價上升的責任就要算到你的頭上。真正會被接納的「好移民」是不存在的,那只是排外政客用來騙自己又騙別人的遮醜布,在移民社群中製造分化,以免他們團結起來爭取權益,誰真心相信便是中伏了。 相對於當一個「好移民」,不如當一個「好公民」。關心時事,多理解問題背後的原因,捍衛自身權益,才是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最大的貢獻。 說回春田市,美國輿論界分析,特朗普和萬斯挑起移民議題的後面可能有更深一層的政治計算。首先,他們不見得真的關心邊境問題,因為本來由共和黨眾議員提出增加邊境管制資源的法案,拜登和賀錦麗都同意了,反而是特朗普要求眾議員調頭轉為反對,免得對手有機會在任內得分;而他們樂此不疲的把春田市說成是人間地獄,不理當地共和黨同僚的反對繼續火上加油,很可能是他們不想傳媒注意力轉移到對他們不利的範圍,例如墮胎和醫療保健。換句話說,這個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成為了他們政治操作的犧牲品了。 ( 圖 :Gage Skidmore@ Creative...
這一波移民潮和過往到世界各地旅居的港人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十分刻意強調自己來自香港的身份。而這一點,最少在歐美社會,又明顯是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移民相對應。上篇提到離散港人在歐美遇到當地人用「nihao」來跟他們打招呼時會感到不舒服,反映的正是這種轉變。有些朋友甚至會刻意提醒對方自己來自香港,母語是廣東話,然後再教對方兩句廣東話的髒話來緩和氣氛。 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一直和中國大陸相對應。從《網中人》的阿燦到《表姐,妳好嘢!》中的表姐,香港認同一直建構在「和中國不一樣」的基礎上:香港是現代、聰明、勤奮;中國是落後、死板、懶惰。這個中港之別實際操作上當然一直有轉化,例如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便從貧窮變成暴發戶;在八九民運中,中港差距則被演繹成「香港人是帶領中國走向自由的中國人」;到了近年,本土主義之下則有不少香港人索性宣告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過去港人到了歐美生活,又不會把界線分得那麼清楚。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條界線在歐美社會的處境中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過去很多海外華人來自華南沿岸地區,到達歐美之前也很可能曾經在香港停留,無論生命軌跡到語言與飲食習慣都和港人很相似,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感到很大必要為「海外港人」另樹旗幟。 政治影響力 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浪潮,和隨後的港人移民潮,大幅改寫了港人離港後的身份認同。這一波的移民不少有極為鮮明的政治立場,不單止希望和中國政府劃清界線,也不希望被稱之為「中國人」。本來在日常的英語溝通當中,華人和中國人都會被簡單稱為 Chinese ,但許多港人明顯不接受這個混淆。有港人移民為子女填寫學校表格時,刻意不挑選表格上已有的...
早陣子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則帖文,內容是有網友移民英國後的一些社會觀念有所改變,覺得自己以前想得不夠。結果文章一出,卻被其他網友批評說他已被當地的「錯誤」社會期望所「污染」。從這案例看移民社群中常常出現的「入鄉隨俗」相對「文化承傳」的爭議,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自省機會。 事緣該帖文的作者有一位同樣移民到英國生活的女性朋友,她在一所本地人為主的企業工作,有次遇到一位剛剛生完孩子的同事回來上班,女友人隨口說了一句「你生完孩子後身材恢復得真好」,結果卻得罪了這位同事。隔日,女友人收到人事管理部門通知,警告她不得談論同事體型。帖文作者說,以前在香港都沒有想過,原來讚美一名孕婦生產後「身材恢復得真好」是有問題的;但思前想後,這樣的讚美背後已暗示了身材有好壞之分,而讚美也是評論的一種,即使出於好意但在職場也是應該避免的,認為自己上了一課。 帖文出來後,其他網友在下面議論紛紛。其中不少網友認為歐美社會「左膠」橫行,事事講求「政治正確」,弄得連說句話也要「自我審查」。那位同事感到冒犯,明明只不過是自己過份敏感而已,還要驚動到人事管理部門,根本是小題大做。這些網友認為帖文作者反過來認同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是移民後被「左膠」思想所「荼毒」了。 無時無刻的價值判斷 我們常說移民後應該「入鄉隨俗」,也就是要和當地社會融合。本欄以前已經提過,百分之百的融入在今天的移民研究眼中已無法期望,其一是當地社會不一定歡迎外來人口的融入,其二是甚麼才是社會主流也難以說清。那麼在融合和不融合之間,就有很多的灰色地帶,有時我們不會想得太多,但有時又會帶來很多爭議。 舉個例,乘搭捷運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應該兩人各站一邊還是只站一邊留空另一邊呢?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習慣。在香港,人少的時候會只站一邊,但人多的時候也會兩邊都站;在台灣,我卻發現大家是近乎宗教信仰地只站一邊,就算後面的隊伍排得很長也堅持留空另一邊。我來到台灣,見到台灣人這麼做,當然也是照做。看起來,就是使用方式不同而已,沒甚麼好爭論。但再想一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兩邊都站是較有效率,代表總體利益優先,轉個頭來是假設每個人都重要;只站一邊是犧牲多數人,讓少數人可以更快,轉個頭來是接受自己在當下不一定最重要。 要說扶手電梯的例子,是要說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時無刻都存在價值判斷,雖然我們不一定自覺。身為移民,在新的社會當中無時無刻都在新的價值判斷環境下生活,絕大多數時間都會自動接受,只會在少數時候多加留意甚至掙扎,而這些事情往往都和身份認同相關,也就是「碰到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