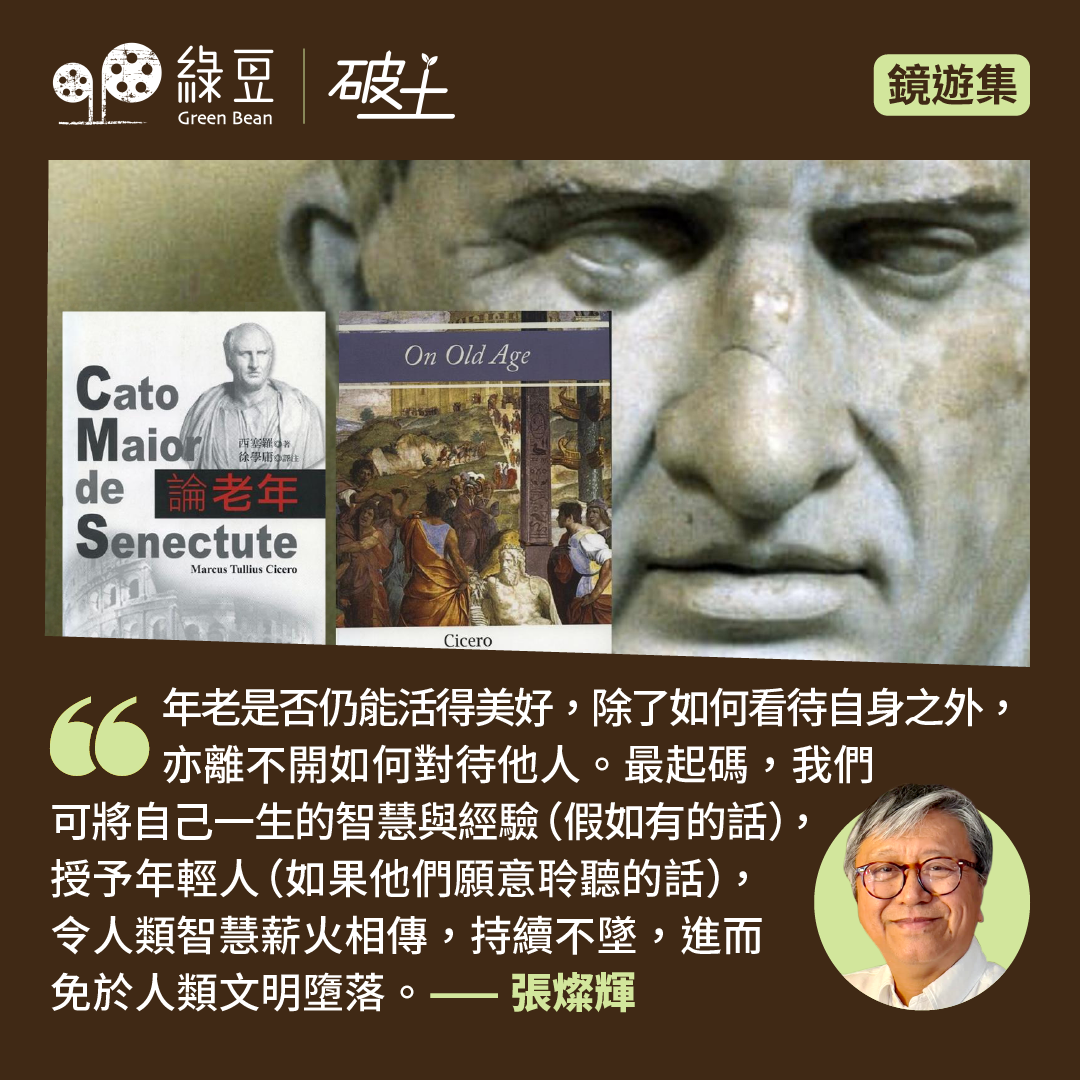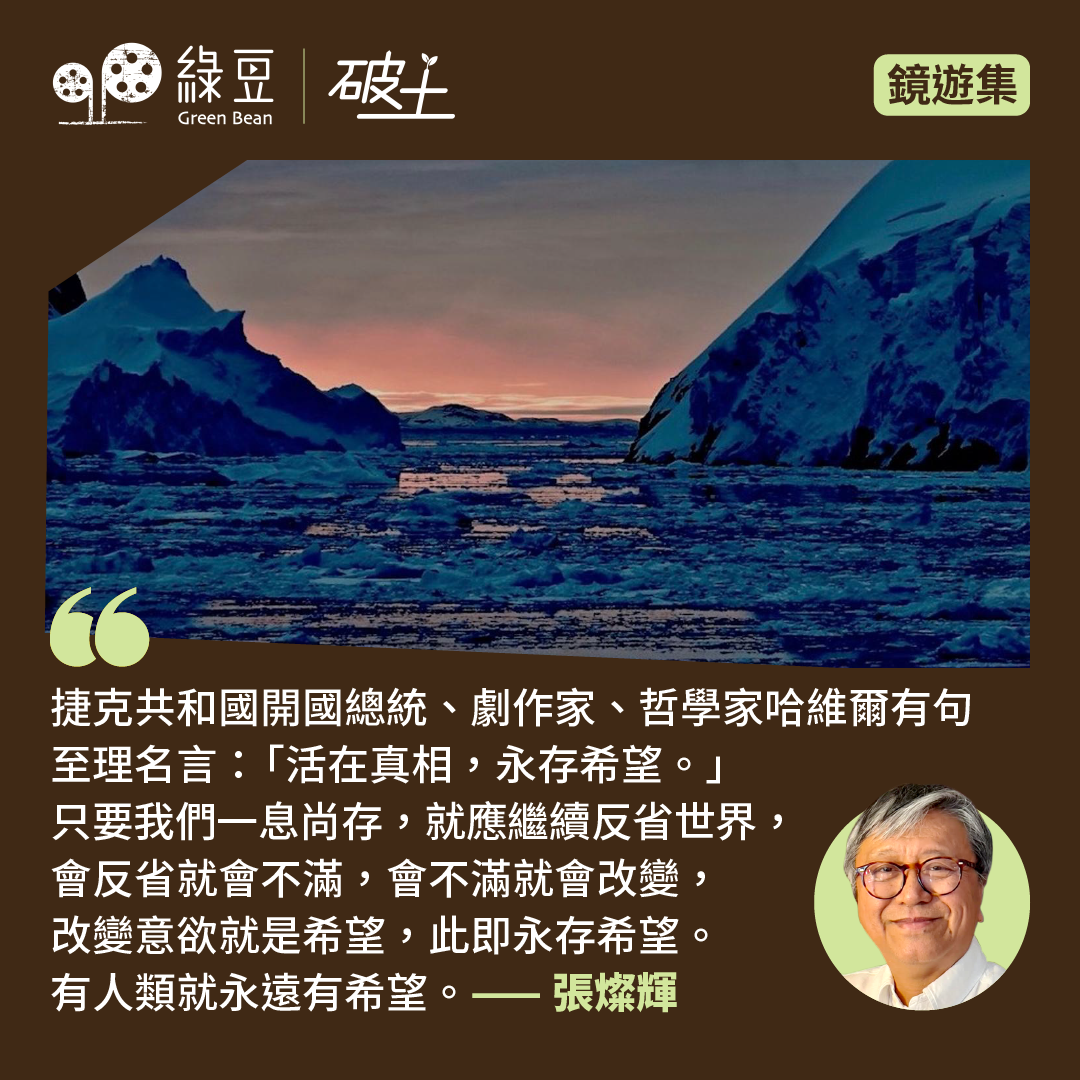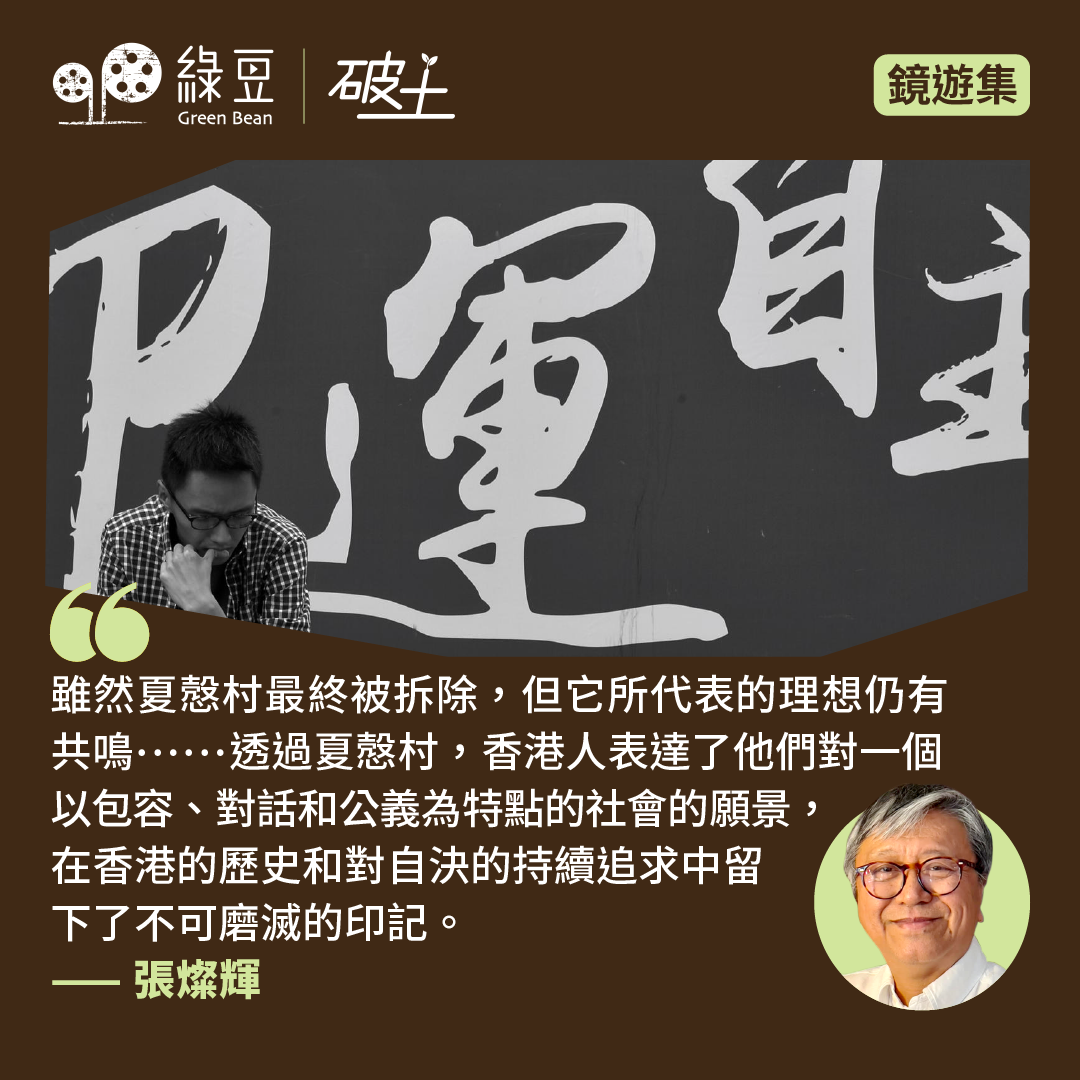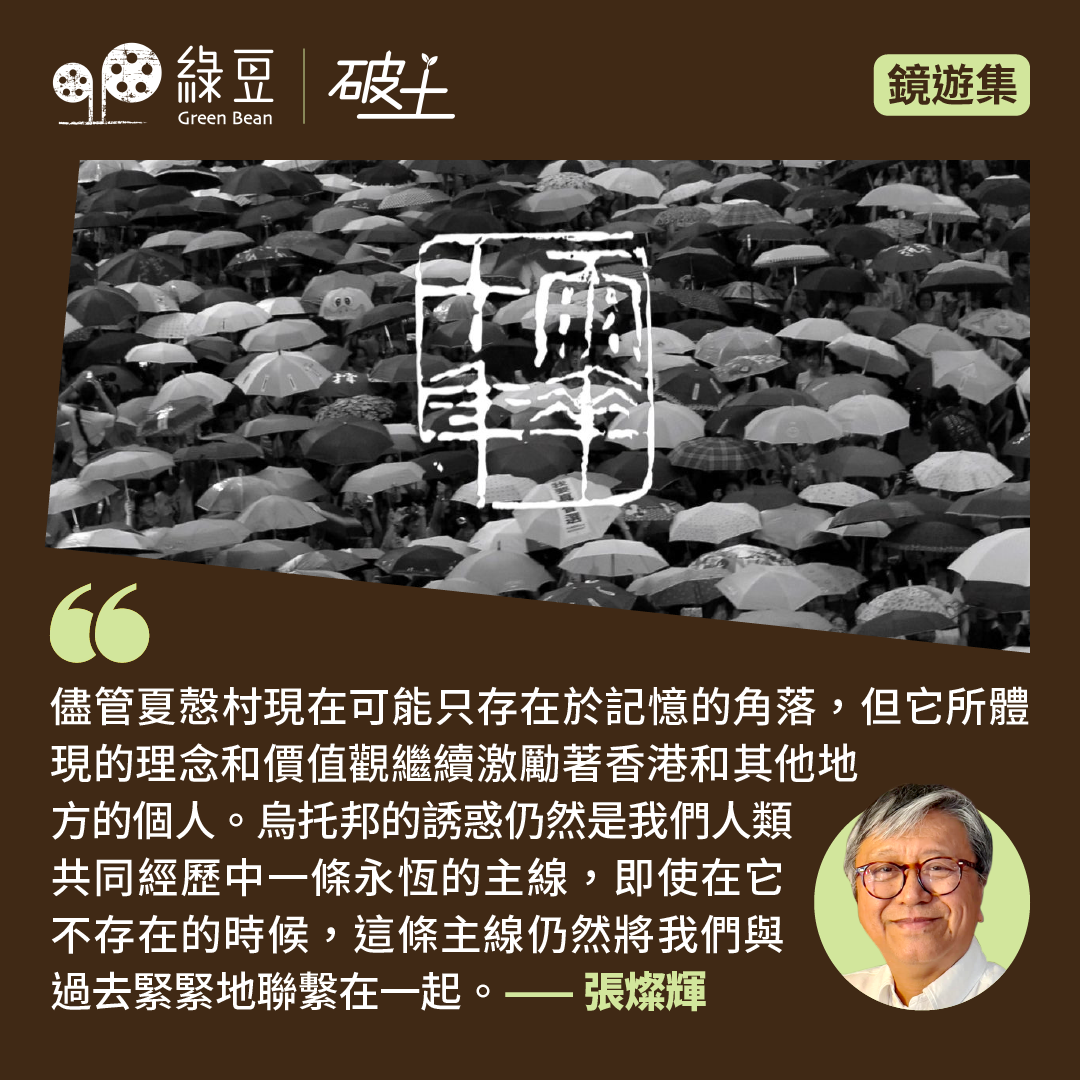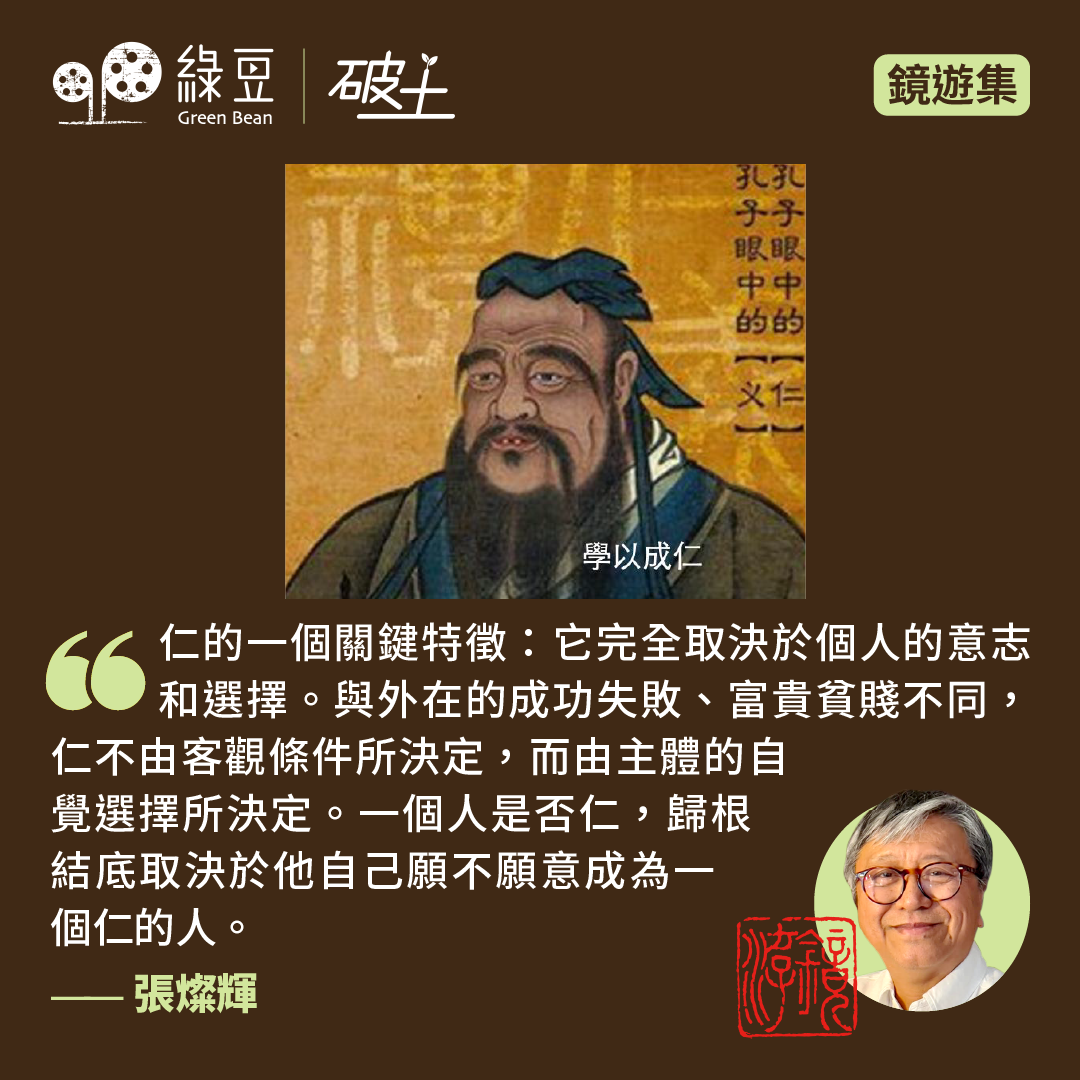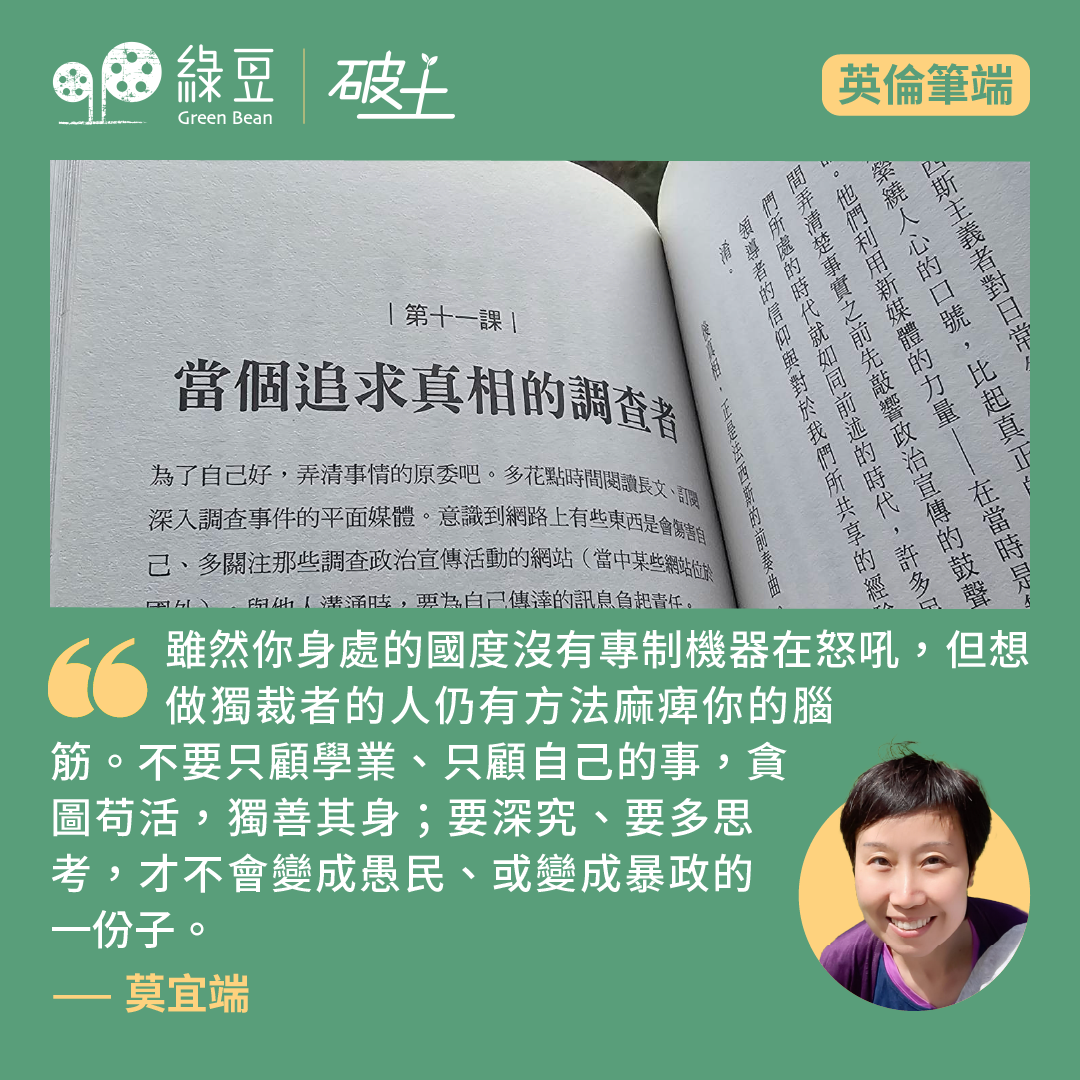哲學必須開始正視年老問題,因為死不去,導致死亡問題彷彿頗遙遠,而年老問題卻變得極逼切。直到20世紀,西方真正處理過年老哲學問題的書籍,僅止兩部:一部是古羅馬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所著《論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44...
既然我們要以知識層面理解希望及烏托邦,將哲學導入希望,則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哲學與希望關係是什麼。正如上述,過去不少哲學家認為「世界為一已完成的封閉實體」,故他們始終以被動沉思而非主動行動的態度,來理解希望,導致理解無法突破既有框架。 布洛赫指出,哲學(philosophy)這個概念本身,已經揭示這些哲學家思想方向有誤。眾所周知,「philosophy」希臘文是「Φιλοσοφία」,「φίλος」(philo)是「愛」(love),「σοφία」(sophia)是「智慧」(wisdom),故「哲學」原意為「愛智慧」。觀此原意,則可知哲學絕不是智慧,而是追求智慧。是以「愛」是種欲望,所以有欲望,實由於尚未得到或達成。因此,愛智慧便是尚未得到智慧,把握智慧,故追求。基於此前提,則哲學不可能是將「視世界為已完成的封閉實體」作思考基礎,此即這些哲學家思考方向所以有誤之由。 愛欲與希望 根據古希臘神話所言,人與神之間最大分別,就在於後者不朽。但柏拉圖卻將此說法扭轉,他說人有一部分可以不朽,就是靈魂,此即靈魂不朽論(immortality of the soul)。何以人類靈魂不朽?因靈魂具備自我昇華能力,可憑藉理性,提高到理念(eidos)層面,而追求如此境界的欲望,就是理性推動力所在。理性使人類一步步昇華,最終擺脫肉體束縛,化為完全精神之存在。凡此,皆由於欲望。...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人文詮釋者代表人物,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其思想固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希望藉此解決人類問題,但他亦非單純共產主義者。二戰後,他流亡東德,長住該地,任教於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為哲學教授;直到一九六一年始返西德,復為圖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名譽教授。 在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似乎已徹底失敗,談論及相信共產主義者日少,甚至仍然以共產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亦完全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極權式資本主義;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背後理想,卻仍相當重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出現,造成種種問題諸如壓逼、剝削、異化(alienation)。在此情形下,無產階級沒法盡其天性,更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由此觀之,馬克思主義可謂人本主義,他極為重視人類尊嚴,在其思想中,人類最重要。可惜,自馬克思主義變成列寧主義起,經歷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乃至於如今習近平思想,以人為本此關鍵已然喪失,所有人的生命及人生,均由國家實施極權統治以牢牢宰制。 烏托邦不會被取代針對如此馬克斯主義脫離馬克思原意的現象,布洛赫主張,應將馬克思主義拉回正軌,重振其以人為本之關鍵部分,但他絕非天真而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他深知隨二戰結束,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加上自由主義盛行,世俗化益甚,以及大家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蘊含極權主義種子所作種種批判,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烏托邦思想已逐漸煙銷雲散。 大家都不再相信人類有能力建立烏托邦,所以都不再討論相關主題,認為毫無意義,白費心機。甚至乎,早在二十世紀初,已然出現反烏托邦思想(Dystopia),此派人不止認為烏托邦毫無意義,且大力批判烏托邦為人類帶來更大災難。然而,相當弔詭之處,在於人類一方面努力忘記烏托邦,另一方面仍孜孜建立烏托邦。試問,如今大家都在努力追求自由、民主、和平、公義、公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此社會不正是烏托邦嗎?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應該具備上述條件,這個「應該」,不正是理想及烏托邦嗎?試問,反烏托邦者,他們可有想過,有何方案可代替烏托邦? 與放棄烏托邦思想或反烏托邦者不同,布洛赫仍堅持烏托邦,但他是位非一般的烏托邦支持者。儘管二千年來,烏托邦似乎不可實現,但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重新探討,認為烏托邦並不會被取代,因為無論人類遭受多少苦難與恐怖,仍不會失去希望,希望內在於所有人,只要我們不滿現狀,希望將來有所改變,它就會成為一股力量,推動我們朝理想前進,而希望正是烏托邦的根本。換言之,烏托邦思想正如同康德式道德,亦內在於人類,不可能消失,雖然它如今似乎一時沉寂。以此為基礎,踏入廿一世紀,我們應重新理解希望。 主動過活以上主張,皆於其最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希臘神話中的泰坦神普羅米修斯(Promētheús)是人類的始祖。眾神居住於奧林匹斯山上,盡情享受,而山下的人類卻如野獸般生活。惟普羅米修斯憐憫人類,將火從天上帶到人間,讓人類免於茹毛飲血和寒冷的侵襲。正因為有了火,人類文明才得以開始。然而,這位帶來幸福的普羅米修斯卻觸怒了宙斯(Zeus),因此受到重罰,被囚禁於高加索山上,日夜遭受鷹啄食肝臟之苦。 同時,人類也遭受了懲罰。宙斯「賜予」人類第一位女性,即第一美女潘朵拉(Pandora)。潘朵拉嫁給了普羅米修斯的弟弟艾匹米修斯(Epimetheus)。普羅米修斯在希臘文中意指「先見之明」,而艾匹米修斯則意指「後見之明」,因此後者以愚笨著稱。普羅米修斯曾警告弟弟,切勿接受神明所賜的任何禮物,但艾匹米修斯不聽兄長的話,接受了第一份贈禮——潘朵拉。 潘朵拉在下嫁時帶來了一個盒子,這個盒子正是享負盛名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艾匹米修斯因好奇盒中所裝之物,便不顧宙斯的警告,直接打開了盒子,結果盒中所有邪惡與災難——痛苦、悲哀、疾病、虛偽、嫉妒、貪婪、殘忍、暴力等,全部被釋放出來。由於這場巨變,開盒者驚慌失措,立刻關上了盒子,卻因此將「希望」鎖在了盒中。在潘朵拉之盒被打開之前,人間並不存在痛苦,人類也不會死亡,那是一個被稱為黃金時代(Golden Age)的時期,但自此之後,人類的境遇愈加惡劣。 什麼是真正的希望 希望被留在盒中,意味著人類仍然保留著希望,但這希望是否必然是正面的呢?尼采(Friedrich...
前言 《論希望》這篇長文是根據我2024年在台灣清華大學課程《烏托邦及其不滿》最後一課編寫而成。這課程廣泛涉足古希臘神話、基督宗教、西方思想家如柏拉圖及湯瑪斯摩爾等、傳統中國文化中探討完美世界、理想社會、烏托邦,以至近世反烏托邦思想。人類追求烏托邦,歸根究柢,實因我們不滿現實,故欲改善世界,而這種「欲」的根源,就是希望。希望正是這篇文章主旨。 文章頗長,要分數篇和讀者分享。 . . ....
在我的作品《異域》的後記中,我開始了對香港所面臨的困境反思探索,特別是通過被稱為夏慤村的浪漫悲劇角度去反省。在這個本來充滿活力的香港,自由逐漸被侵蝕,威權統治肆虐,這段敘事正是歷史的關鍵時刻。在以下段落中,我將討論反修例運動的影響、曾經許諾的「一國兩制」的崩潰,以及香港人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下所經歷的生存危機。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是對被認為是政府越權和試圖箝制香港一直以來的自由的重要呼聲。由於引渡法的修訂建議(許多人擔心這會為大陸的壓迫性司法制度打開大門)激發了這場運動,並在不同人群中獲得了顯著的支持。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在街上團結一致,揮舞橫幅,高呼口號,主張民主和自治。然而,在這股社會熱潮之下,卻隱藏著更深層的不祥預感;這正是不久後將籠罩整個城市的動盪現實的前兆。 反修例運動不僅喚醒了香港居民的公民責任感,也揭示了共產政權野心的殘酷現實。運動一開始只是要求立法改革,很快就演變成更廣泛的爭取人權和維護香港生活方式的行動。抗議揭示了人民的韌性和決心,然而這種反抗也引起了當局的暴力反擊。 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核心原則之一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中英協議提出,1997年回歸後實現。旨在維持香港的獨特身份,同時促進香港重新融入中國。然而,這項安排的現實證明是假象多於實質。圍繞反修例運動所發生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表明,所做的承諾正逐漸被取消。 白色恐怖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起了國際關注,暴露了香港管治框架內的明顯矛盾。中國政府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反映了其鞏固對香港控制的無情欲望,導致市民之前享有的自由受到壓制。《國家安全法》的頒布是這種背叛的縮影,將市民推入一個充滿監視、壓制和恐懼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結構。...
(作者按: 此文原是英文論文 The Tragedy of Harcourt Village,將於本月26日在日本東京大學「雨傘運動十週年紀念會議」宣讀,現翻譯為中文,在《鏡遊集》先刊出。)...
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業師勞思光有異於唐先生,他1955年來港,至1989年受邀於李亦園教授而返台,執教於清華大學;之後往返香港和台灣之間,直到2012年於台北逝世。他在香港生活長達57年。勞先生家庭背景相當顯赫,他祖上勞崇光,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先後出任雲貴及兩廣總督,1860年,代表清廷與英國簽訂《九龍條約》。勞先生父親勞競九,為革命黨人,與蔣介石似乎關係匪淺。因此,勞先生可謂貴族出身,屬於上流社會人士。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勞先生亦跟隨其父赴台。勞先生自始至終,都對於共產黨的專制相當警惕,並不斷反省,故此其時他離開中國,前往台灣,多少亦有不願生活於專制政府治下的因素在內。順理成章,他亦不可能願意在蔣介石政府威權統治下生活。當時台灣仍處於大殺異己,鎮壓民眾之白色恐怖年代,故勞先生於1955年,離開台灣前往香港。 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離開時,他寫下《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六年,就是1949到1955年,在此六年間,他生活於台北與台南,而無論在南還是在北,他只覺得這地方政治壓力太大,所以他必須離開。對於香港,他又作何感想?他認為自己「不是長住香港的人」,而且與唐先生一樣,「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殖民地先天就有問題,是個原罪。似乎當時在避秦南來的知識份子眼中,沒有誰會覺得殖民地是好地方。殖民地就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就是邪惡(evil),這是他們的見解。香港雖然市里井然,街道漂亮,但勞先生不為所動,這個地方對他影響不大。不過,亦與唐先生相同,因為此地允許他自由生活,故其餘一切原罪、邪惡、問題,就瑕不掩瑜了。此外,從另一角度觀察,香港自1842年變成英國殖民地後,影響中國發展極大,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住在香港。孫中山就讀於香港大學醫科,他之所以萌生革命念頭,正因為他身歷目見英國政府治理香港之良。可見香港對現代中國發展,影響何等巨大。正如上文所引述余英時之言,香港不止有自由,還有法治(rule of law),這是最重要。儘管香港沒有民主,但其整套制度,基本上屬於保護群眾,而非保護政府。不過,勞先生當初畢竟認為,香港「雖信美」,「卻非吾土」,故「何足以少留」。當然,勞先生1955年寫此書信時,絕不可能知道,往後57年,他都會留在香港。這基本上與唐先生相同。《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情理皆備,是理解勞先生當時的心境最好的文章。 「家」的看法勞先生出生於西安,在北平長大,後來輾轉去過成都與台北,再來香港。談到成都,則不得不談其《憶巴州》一篇短文。勞先生曾在四川巴州住過一年,他認為此地是他生平居住過最寧靜、寫意、舒適的地方,其餘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在此文章中,勞先生雖未提及,但已隱然透露出他對於流亡與「家」的看法與情懷。在巴州,雖然如是其寧靜、寫意、舒適,但這種寧靜、寫意、舒適,決非現代化大都市那種。他在文中提到,巴州沒有汽車,出入都用滑竿,而在城內都是騎馬,不過通常以步行為主;巴州亦沒有供電,只有由燈草點燃的桐油燈;房屋沒有地板,全部是濕土地。身為世家子弟,又常年居住在西安與北平等名都大都,養尊處優,按道理,勞先生應甚不習慣巴州生活。然而,從其文章可見,並非如此。他在這些不便中,尋找出種種樂趣。例如,沒有汽車,馬匹亦不多,只能以步行為主,他就養成與二三鄰里踏青郊遊的新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勞先生雖處於流亡中,似乎無一處是家,然其隨遇而安的性格,卻使他所在皆是「家」。這與唐先生不同。唐先生流亡到香港,從不以 為家,他一直認為,其家在中國,祖籍四川宜賓,他希望回去,儘管一生都再沒回去。勞先生一生去過不少地方,最後定居於台北市,長眠於宜蘭櫻花陵園。我必須再次強調,勞先生並不覺得任何一處是其家,因而處處可以為暫時的「家」。 痛批香港青年正因為處處是其家,所以對香港問題,勞先生比唐先生有更多關懷。他曾著有《歷史的懲罰》一書,我認為這本書實是勞先生最上乘作品。他對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曾作出最痛切評論:「今日海外最與中國接近,同時知識青年較多的地方,應是香港。我們就香港來看,香港青年很少有願意獻身於政治運動。這自然有思想、環境、生活種種原因。香港是殖民地,一切社會標準都十分不正常。已成熟的人在香港生活,尚不免有迷眩之感;眾青年無論是外來或本地,在這個環境中度過童年,他們的人生觀已受了這個環境雕塑,而成為一種香港型青年。香港型青年最顯著特徵,就是缺乏理想性,缺乏犧牲精神,沒有遠大抱負。就研究學問說,他們不願面對有關文化價值的大問題,而只要學謀生技術;就實際工作來說,他們只要求有較好待遇,以便有較好生活享受。他們不切實感到國家危難,也不明白今日人類無法苟安。他們一味只構造個人小世界。談到政治運動,他們只在職業性或甚商業性考慮下,方有興趣。說到奮鬥犧牲,則他們會笑你是傻瓜。」基於這種看法,則勞先生絕難以置信,何以2014年會有雨傘革命,自然更不可能想像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前景研究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九七回歸問題出現,勞先生思考如何面對香港從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回歸大陸的極權統治。正因如此,所以他在1982年時,創辦「香港前景研究社」。他知道當年英國透過《北京條約》,向清廷租借香港九十九年的大限已到,故想方設法保存香港。勞先生指出,考慮香港問題,必須從實際角度出發,而香港之於中共國,其最大用處,就在於經濟以及現代化,我們應從這裡切入,思考如何保存香港在中共國的位置。不過,他亦深明,在中共國與英國之間,香港人從無置喙餘地,甚至連立足處也沒有。故此,他自始就斷定,一國兩制是騙局,至今其言可謂大驗。所謂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其實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它是藉控制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以成就中共國經濟發展;而讓香港人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只是達成這個目的下,不得已接受之副作用。可是政治控制,卻一步步加強,因而說到底,香港絕不會有真正民主,勞先生早於一九九七年前已明言。他一語道破一國兩制的騙局:「由這兩面看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九七後的香港,除了在經濟方面可能有表面的『繁榮安定『,其他優點皆難保持。尤其在以後,中共當權人士很明確地將香港看成一個『顛覆基地』,又將一切抗拒專政統治的觀念與行動,與所謂外國的『陰謀』混在一起,結果必使香港民意及輿論受到強力壓制。總之,香港九七後只能在中共壓力下勉強苟全,再不能發揮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作用了。」在前景研究社時期,勞先生再三強調香港九七問題必須有香港人參與:「最後,我想總結上面所談各點,說說我認為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前途問題應該作甚麼努力。第一:決定香港前途的權力在中國,但香港居民自有根據事理,表達意見的權利;所以,我認為在香港經濟未嚴重惡化以前,香港居民應當面對問題,形成一種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第二:香港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正面功能,本來是中國當局所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問題』,以及更長遠的香港地位問題等等,了解上仍然有許多隔膜;為了使香港問題獲得一個有益於中港兩方的解決,香港居民應該盡量運用言論,使中國當局對這些問題充分了解。第三:關於最後形成甚麼可行的方案,雖然不是可以由香港人單獨決定的;但香港居民仍然應該主動研討,形成一些草案,並作出實際的推動工作。總之,香港的前途要由香港人主動爭取;香港問題的解決要符合中國與香港雙方的利益。這就是我看香港問題時的主要意見。」很可惜,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當然對勞先生在前景社的一切努力,視如敝屣,毫不在意,香港人始終沒有參加處理自己命運的權利。是以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刊出後,勞先生已經知道維持香港前途的努力已成泡影,前景研究社即時解散。所以中國共產黨答應台灣的一國兩制(而近來馬英九大力附和),若大家相信,若你果真相信,就正如勞先生所說,完全天真與無知。他深知共產黨絕不會放棄任何權力。故此,何以中共如此害怕香港,因為它害怕為香港所顛覆,它永遠視香港為顛覆基地。結果到2019年,就知道中共所害怕者,並非全無道理。最終勞先生離開香港,因為他絕不能生活於專制統治下。 一生都在流亡至於他到台灣教書,正如他自己所說,也只是隨緣,他再次流亡。他一生人都在流亡。勞先生雖然「所在即其家」,然而到頭來,實在沒有家。儘管他在香港五十餘年,亦有結婚生子,但這絕非其理想。1980年代,老師已然諄諄教誨我們,「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共產黨絕不可信。」對於這番話,當時我們好像聽不懂。香港對勞先生很重要,作為大學教授和公共知識人,也盡了責任;在重要時刻敢言批判時事,為香港人在97問題上發問。不過我覺得他最關心的是香港這個城市淪陷後,他失去自由開放的空間思考和寫作。但他並不關心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對香港人自己命運問題也沒有任何建議。他自始至終知道香港人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是以他九七後已離開香港,大部時間獨自在台灣教學生活,回香港只是探望親人和見學生而已。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勞先生一生都在流亡。2012年在台灣祝賀勞先生85壽慶時,也是他辭世的一年。有朋友聽到他一句感慨説話:「一生是苦多於樂。」果真如此,先生漂泊一生,四處可暫時寄居,但無一處真的為家,安身立命之所。( 註 :...
(編按 : 上文提到唐君毅先生1949年避秦南來後,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 ============================== 唐君毅先生認為,為使中國文化重生,故必須重新肯定儒學,這個肯定首先在自由的香港,其後傳到台灣,以及美國,如今講中國文化與哲學,都在這三個地方。論重振中國文化與哲學成就,台灣是否最高,我不無懷疑。但如今台灣,正如過去香港,皆是華人世界中較為自由之地。因此,在台學者可藉此優勢,推動新儒家運動,正如當初唐先生利用香港這個特殊位置,實踐其理想,儘管這個理想與香港本土毫無關係。他似乎沒有思考過,如何運用此思想推動香港文化,因為他認為兩者完全無關。他所思所想,都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對立與融通,他的中國文化,從完全抽離香港此地之普遍意義上出發。 正因如此,《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雖由唐先生起草,並有幾位先生聯署,卻並不完全為當時學者接受,其中反對最力者,莫過於錢穆先生。他堅決不參與,且表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宣言是「在」香港發表,但不是「為」香港而撰寫。在唐先生心中只有大中華,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和空間」。 花果飄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