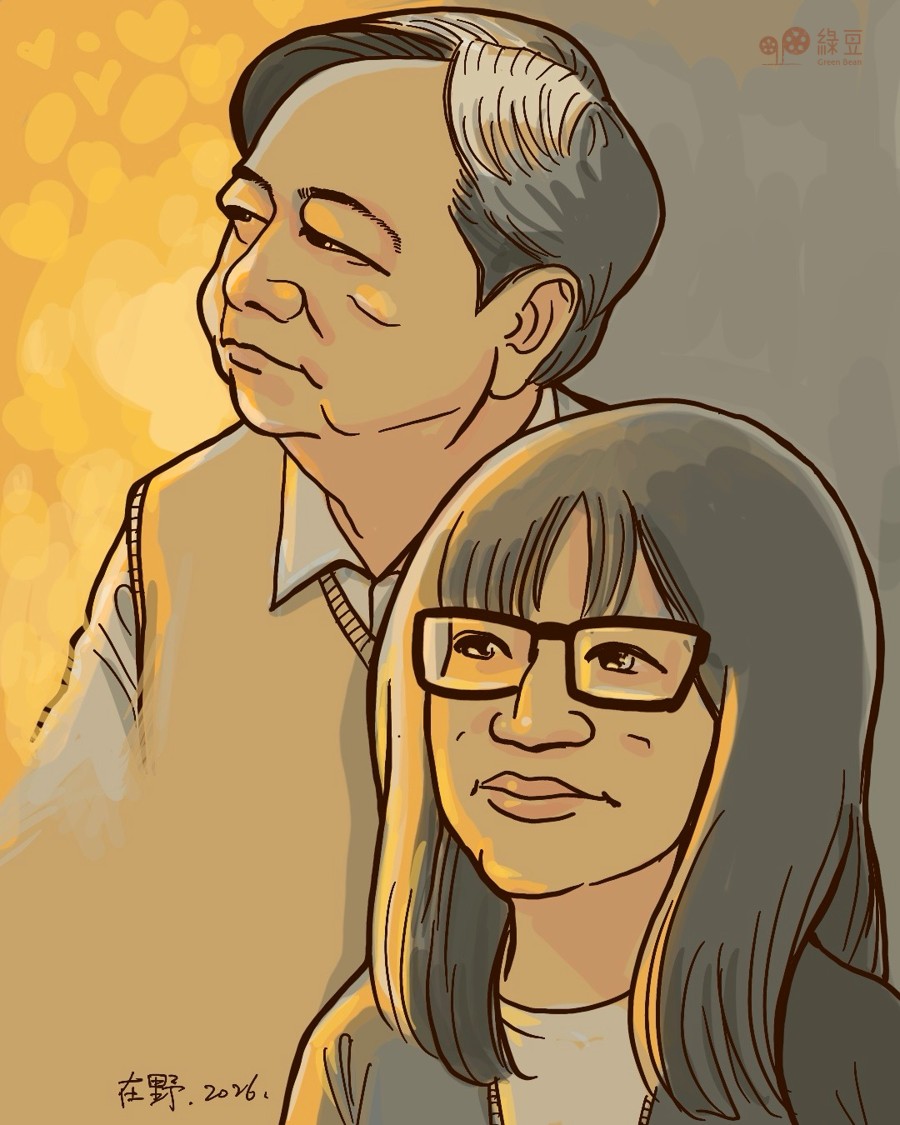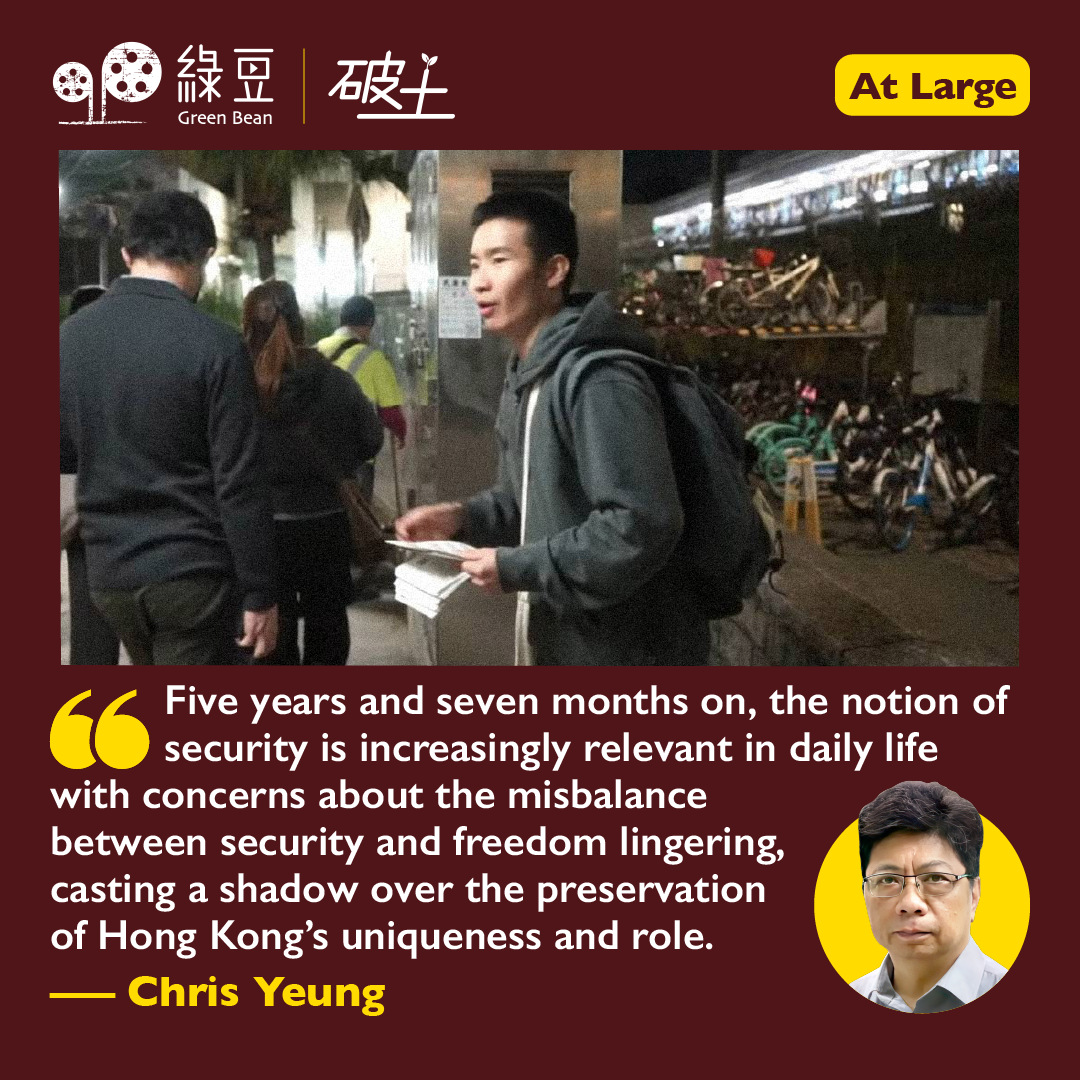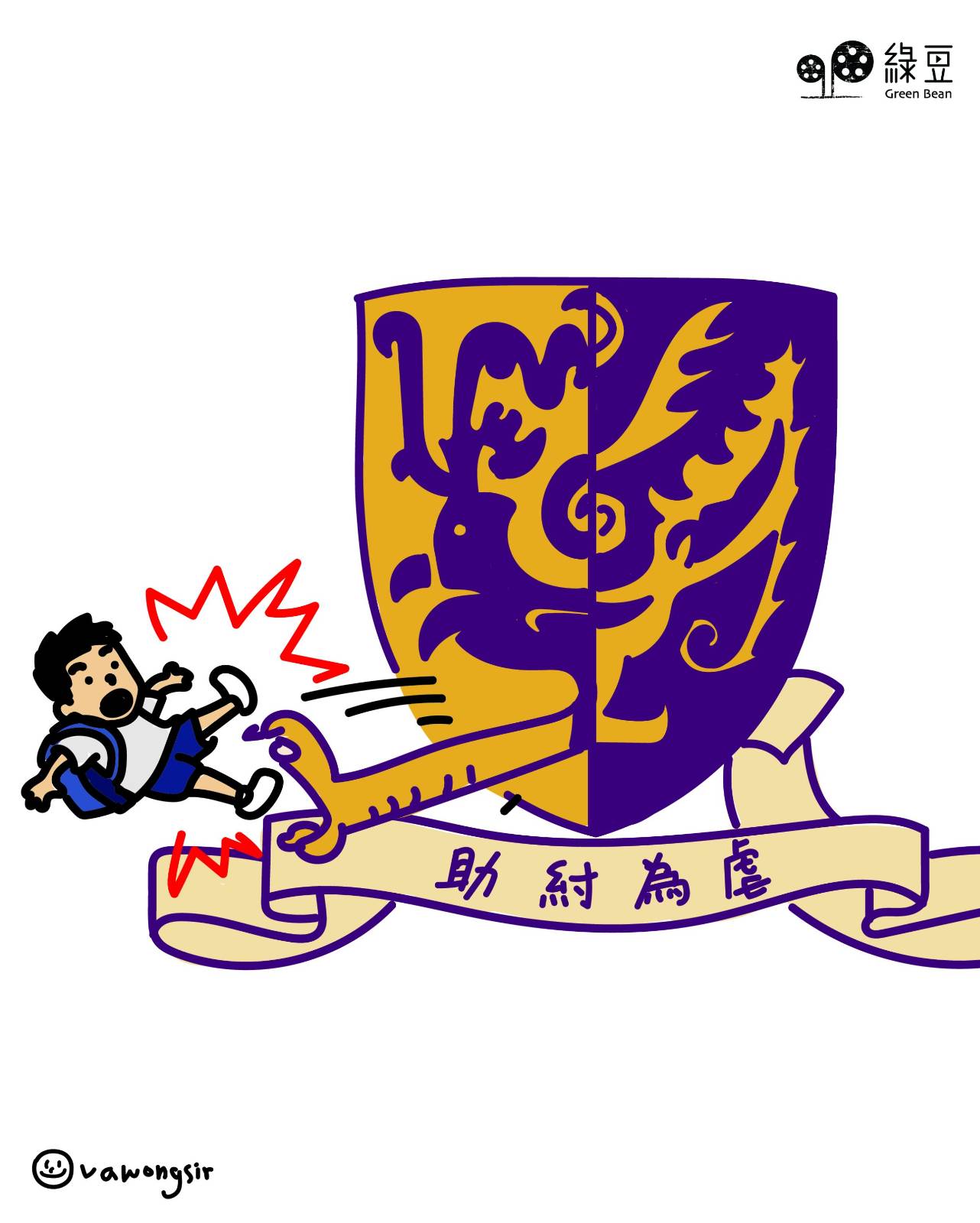《夕陽西下幾時回》- 明慧的回信(三上)——由不可自決的無助變成低俗 | 大埔山人


凌漸:
其實是我要感謝你,世上有許多問題,不得不問,問又如何?不過發發牢騷而已,難得你給我這大半生我從未有過的空間。自大學畢業落入蜘蛛網中,一去何止三十年,多少問題,都付生活中,沉埋蒿萊,我看到堅持認真生活的人,走到最後,問題總比答案還多,直至問者或答者其中一位舉手放棄為止。
八十、九十年代的我,正如你形容的模樣,前途和生命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快轉至千禧年代,無力感蛻變成習慣性失助,更甚者,一種集體感染的一生不可自決,我也不免。想起中六當年的國文老師教過,窮則獨善其身,實行起來,其實是習慣性恐慌抓住所有還能抓住之物。於我是在牀上讀牀下底的藏書,於朋友是在桌上作曲給下面的抽屜欣賞,於鄰居是散盡積蓄換得三百杯酒一晚飲完。隨著兼濟天下的理想越來越不可及,自身之善也很易隨時間變質。
猶太人在集中營前排隊
你在德國許久,不知有沒有人跟你談起這個問題:探討德國人如何以超乎人性的服從和秩序運行集中營的人眾多,卻沒甚麼人探討為何當時的猶太人以超乎想像的服從和秩序進入集中營。
漫長黑暗的納粹時期之中,猶太人的反抗少之又少,每次看到猶太人在集中營前排隊,或死亡行進魚貫的隊形,總覺無名恐懼,我反覆問自己,怎樣的狀態才會在集中營前排隊?一般的解釋是他們不知前面只得死路一條,還以為是去集中營前的中途站,連德國人也不知道,起碼甫戰敗時盟軍問他們如是說。最終解決方案實行至戰敗之間經年,種種蛛絲馬跡顯示,無論德國人或猶太人對於方案甚至集中營皆並非一無所知,就算不知全情,起碼有合理懷疑,瀰漫社會各處,不致於排隊待斃。
最誇張的,是瀰漫集中營裡的平靜,德國人守衛的平靜,猶太人進毒氣室的平靜──凌漸,我想說,撇開似乎早不存在的道德和尊嚴,我看著兩者的表情舉止,竟驚人地相似,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終於可以告訴你,就是那種集體感染的一生不可自決:當習慣性失助去至極致,至生活中所有方面,催眠自己或醒覺到(兩者其實一樣)一生何事也不由自己決定,是減低因道德和尊嚴掃地自然而生的痛苦的最易方法。當然,沒有了痛苦也就沒有了存在感,沒有了滅絕的責任,也沒有了被滅絕的恐懼憤怒,艾希曼如是,他所相對者也如是。
像我如此一生不可自決的人仍得佔大多數,起初如何,明日亦然,還包括那小部分自以為品味高雅風霜高潔的。我看見以文以武摧毀我們的人,皆在我們之中奮起,並非外來,亦非變節投名,就是本來如此,順著風勢起燒而已。我又看見我們之中有人醒覺,越來越多人醒覺,在火場裡負隅頑抗,然後殉難,或如玉碎各散東西,剩下的絕大多數不得不也本能的褪色成瓦回復不可自決的常態,就如剛才發了一場天馬行空的夢。
低俗是一種習慣
兩地何其相似!痛定思痛,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一體兩面,皆社會共業矣,我你皆有份。既然寫信,我且不怕班門弄斧,雖然海德格不免落入納粹之泥沼,他仍曾一針見血指出,我們大部分時間之生活乃無等無聊且無意義的日常,既然大部分人一生至大限來前都幾乎無法超脫日常,我們必須弄清我們面對、經歷的日常是甚麼。在我而言,我概括稱這一切人事為「低俗」。低俗不是具體的人事,不是口味風格,不是文化,而是一種習慣。
食色性也,八卦窺淫閒話廢話亦性也,不一定低俗。倒過來說,行禮如儀、不假思索的行為,對自己除作如此行為以外别無意義的行為,成為一種習慣,甚至成癮,這才為之低俗。所以對低俗無動於衷甚至甘之如飴並非文化或哲學問題,只是久入鮑魚之肆,足履窪者若平之類的習慣問題。
日看大台,夜追網紅,正是習慣成低俗的通例,不過這是主動的低俗,起碼還要伸手去開電視電腦,要用力去追求低俗的圖文影音,如白粉癮起惟有用力爬上樑上做君子。我從來想像不了吊癮者何以大力出神蹟,回溯上去,應是天先降下遍地白粉,然後才有癮君子的,也應是先有能令人落入低俗的環境,才有對低俗的追求者。自小被低俗的內容和表達沒頂,是被動的低俗,幼稚園時開始認識對偉大的園丁感激流涕,到大學時就認為奸妃和爭產的橋段勝過王子的獨白,低俗不能移。見人低俗而不阻止,任由其繼續低俗,如見人煲膠劇而不轉台或熄電視,其低俗的結果自己也將得一起承受。
低俗成為了板蕩黍離之中掙扎的大眾的避風港,習慣給人安定的慰藉,無所意義給人即時的滿足。演變至最終,自己意識所及之人事,會自行被自己的意識低俗化,是下意識還是自動都無所謂,反正就是齊彭殤,齊賢愚,齊善惡。原本對自己有意義的人事都被自己的低俗化所掏空、忘卻,向前還是向後都一樣低俗,加害還是受害都一樣再無意義。
(待續)
▌ 作者簡介
「大埔山人」為張燦輝的學生,一位為日常無聊生活所困卻不願意沉淪其中的讀書人和音樂愛好者,也不想埋首沙堆無視當前政治荒謬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