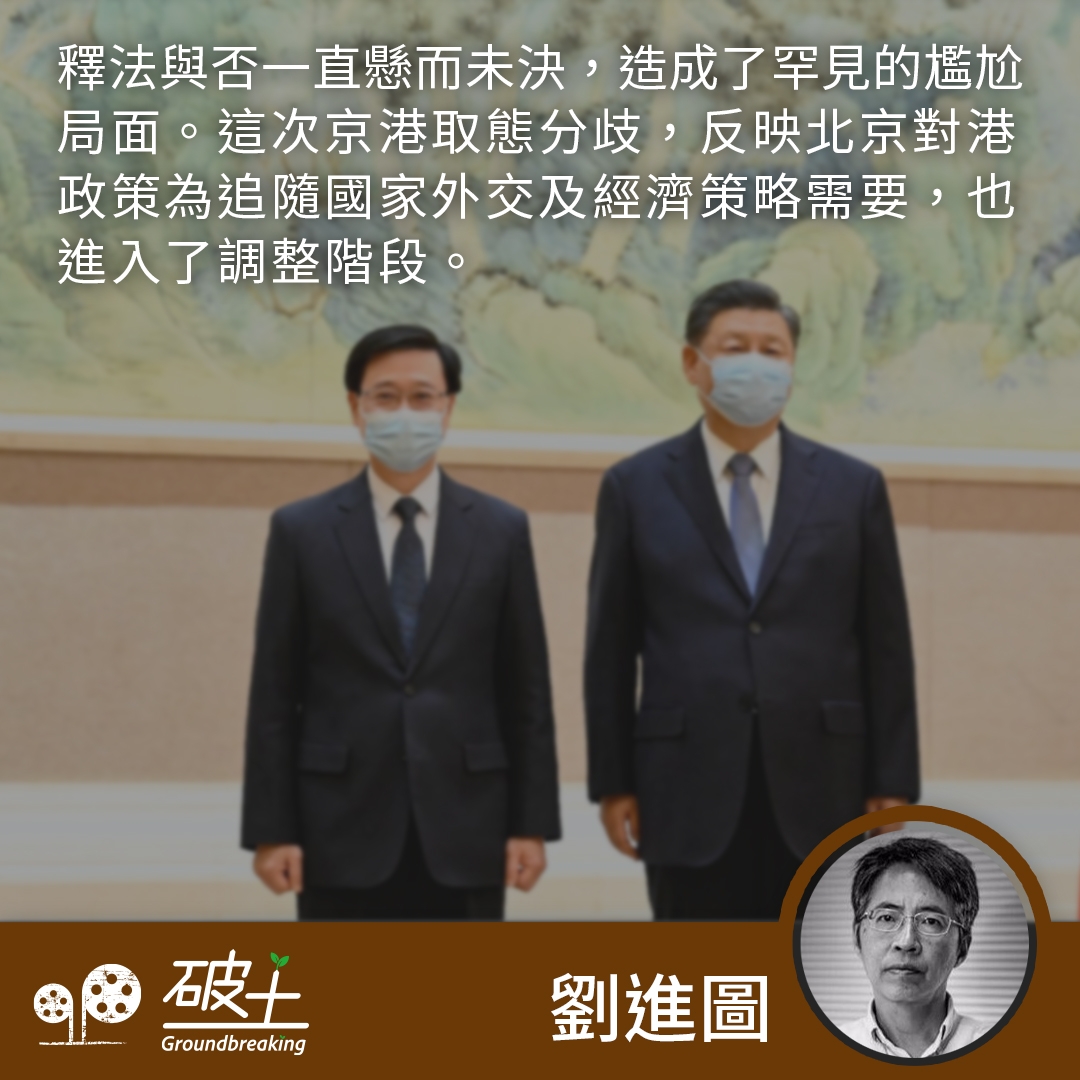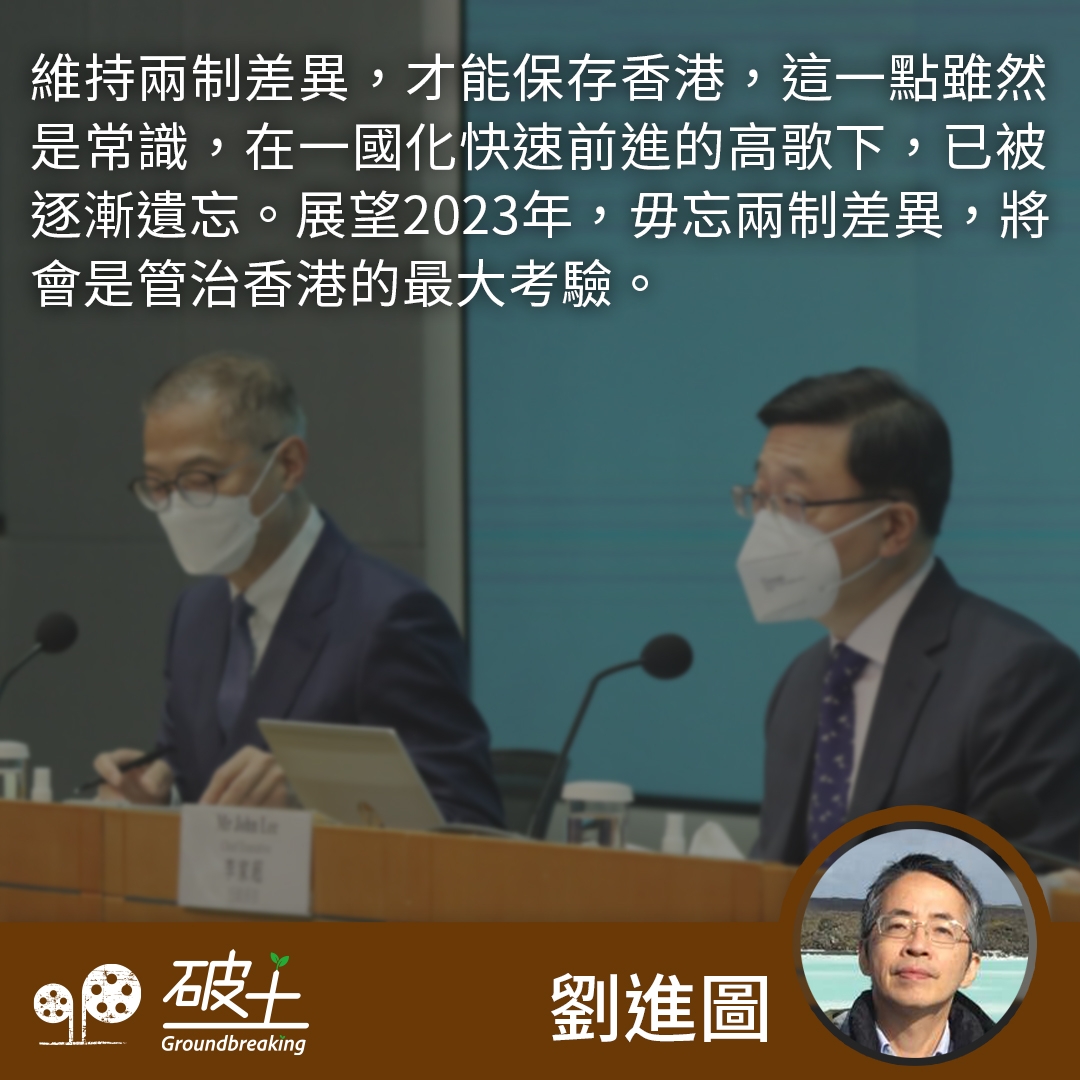日本爭當馬前卒 中國棒打出頭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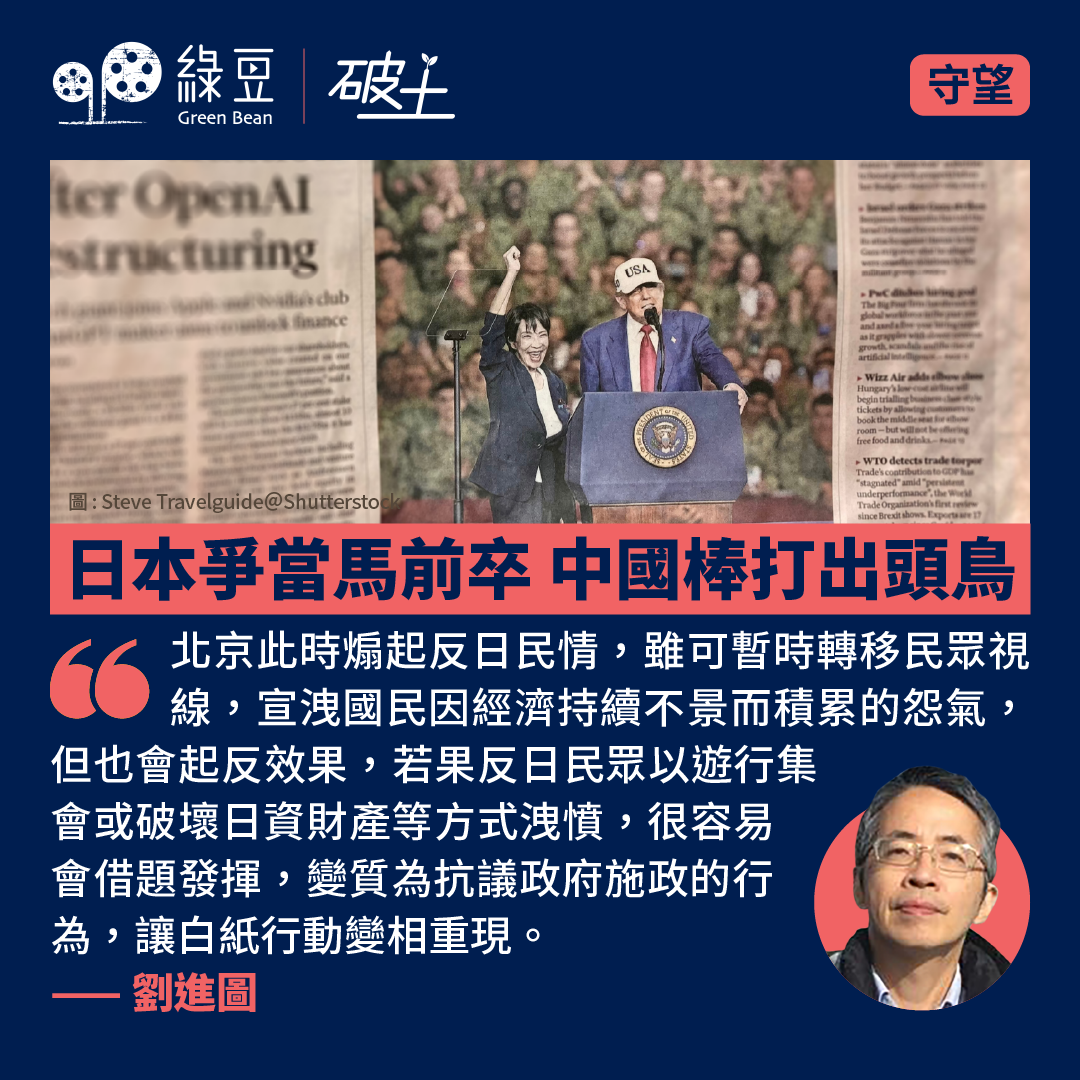
日中關係急劇惡化,日本政府拒絕撤回或修改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日本極可能面臨存亡危機事態」言論。中國除了以狠辣言詞口誅筆伐,挑動國民反日情緒,更發動經濟懲罰,叫停中國觀光客赴日觀光、再度停止進口日本水產;而日本防長則宣布日軍將與美軍在沖繩等地聯合軍演三天。到底日本為何堅持觸怒中國,中國又為何要強硬報復?
沒有澄清降溫
如果說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是一時口誤,無心之失,中國強烈回應,視之為干涉兩岸內政甚至侵略,日本內閣大可以作出澄清,嘗試為事件降溫。畢竟台灣有事牽連日本之說,源於日美安保條約,歷屆日本政府均認為條約覆蓋釣魚台乃至台灣海峽,只是不宣諸於口,避免刺激中國。
日本政府若要降溫,大可把責任推給美國,指美國國會有立法保障台灣,美國若因此介入守護台灣,日本基於日美安保條約不得不協助美國,但美國若不作軍事介入,日本未必會單方面介入台海衝突。
日本政府沒有這樣解說,只是通過外交磋商及對外發言確立高市早苗言論,這個取態顯示,日本政府是經過深思熟慮,明知道會強烈觸怒中國,仍堅持台灣有事即日本面臨危機的立場,把過去一直刻意隱晦模糊的對華軍事策略挑明白,到底為了達成怎樣的政治目的?
不當永遠的歷史罪人
上周本欄已分析過日中關係惡化的經濟背景,指出中國尖端製造業強勢崛起,威脅日本多個重要領域的龍頭企業,導致日本決意借美國與中國脫鈎的契機,加入西方擺脫對中國經濟倚賴行列,加大對中國實行經貿保護措施。今期繼續分析日本修訂對華策略的政治成因。
近日有不少評論指出,高市早苗遭中國尖銳批評,日本隨時失去中國遊客和中國市場,但在國內仍民望高企,民眾普遍支持高市首相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這股民情源於中國幾十年來不斷譴責日本二戰侵略,是歷史罪人,要求日本反省,不要再對鄰國指手劃腳,避免軍國主義復活。
日本民眾本來也接受這個論述,但重複聽這論調幾十年後,對此感到相當厭倦,許多日本人心裡認為,二戰已過去這麼多年,日本早就應該恢復正常國家身分,為什麼仍不斷要以犯罪者兼反省者的委屈身分自居?換言之,高市早苗對華強硬的取態,並不是單單建基於日本右翼的強國擴張意識形態,而是獲得許多中間民眾的支持,日本要爭取做一個正常的大國,不再因二戰侵華對中國卑躬屈膝,這股民意是日本政府敢於觸怒中國的重要政治因素。
要當美東亞地區首席代理人
另一個促使日本修訂對華策略的政治因素,是美中經濟走向脫鈎,東亞地緣政治出現變局,日本有意爭取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首席代理人,藉此成為區內龍頭,替美國出頭辦事,換取美國對日傾注投資、武器和高科技,使日本進身區內第一強國。
這個考慮就像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成為美國頭馬,地位凌駕沙地、卡塔爾等富裕油國,可以憑藉先進軍事力量,橫掃區內敵對勢力。過去日本若要稱雄東亞,首先要過中國這一關,在全球化年代,中國和美國綑綁成利益共同體,日本沒有一絲機會,只能跟南韓、台灣、菲律賓、新加坡等一樣,悄悄躲在美中兩大國身旁,政治上保持低調,盡量開拓美中兩國消費市場,悶聲發大財。
如今,美中合作破裂,美國刻意擺脫對中國倚賴,致力打造排斥中國的西方經濟陣營,日本要在美中之間走平衡鋼索愈來愈難,因為日本追求的是尖端製造和先進科技,這些領域乃是美中矛盾最尖銳之處,日本不可能同時討好美國和中國的,只好作出選擇。既然作了選擇,就不如大步踏前,食盡這樣選擇的好處,成為西方經濟陣營在東亞的門面擔當,把南韓、新加坡和菲律賓等美國小弟拋在後頭。
要取得這個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地位,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用台灣問題挑釁北京,北京愈是強硬回應,日本就愈有理由尋求美國對日本銷售最尖端的軍備,使日本走上重建強大軍隊的道路。與這個巨大的利益誘因相比,中國的觀光遊客消費算得什麼?
對中國政府的考驗
面對日本的挑釁,中國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處理手法,但北京很快就作了抉擇,以最強硬最狠辣的方法回應。那些戰狼上身的外交官員都是聰明人,若沒有摸清最高領導的對日取態,是不會貿然跳出來放狠話的。能夠說出斬掉日本醜陋頭臚這樣的狠話,並且不作補救,還刻意營造對日談判官員蔑視日本來使的新聞圖像,強烈煽動民眾反日情緒。這些表象說明,北京已決定棒打出頭鳥,狠狠教訓日本,警告區內其他親西方國家不要仿效日本。因此,這次中國反擊日本不會輕易落幕,一定要做到讓日本明顯痛楚,才能傳達殺雞儆猴的信息。
不過,正如好些專研中日關係的學者指出,北京此時煽起反日民情,雖可暫時轉移民眾視線,宣洩國民因經濟持續不景而積累的怨氣,但也會起反效果,若果反日民眾以遊行集會或破壞日資財產等方式洩憤,很容易會借題發揮,變質為抗議政府施政的行為,讓白紙行動變相重現。如何有效控制反日民情,對中國各地政府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