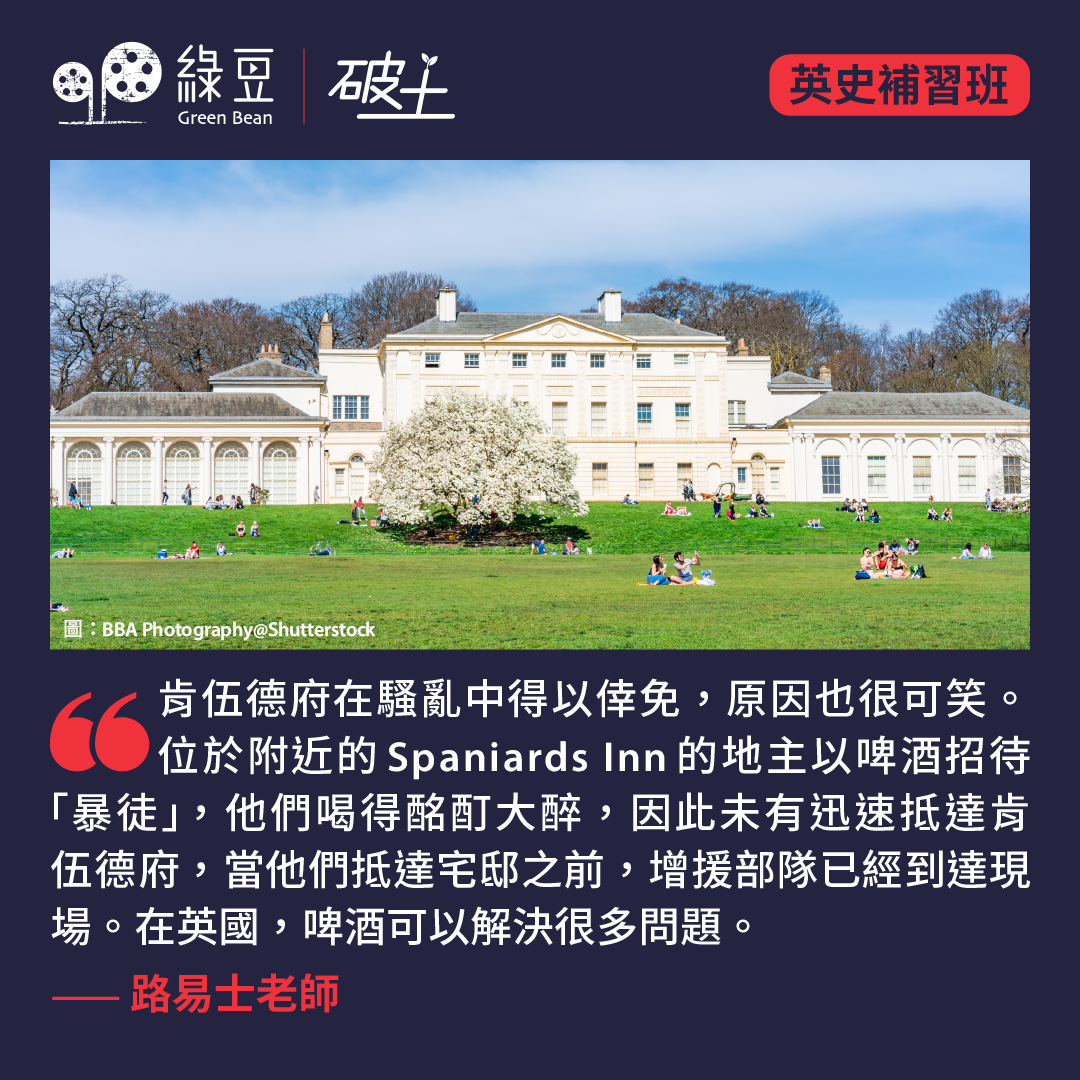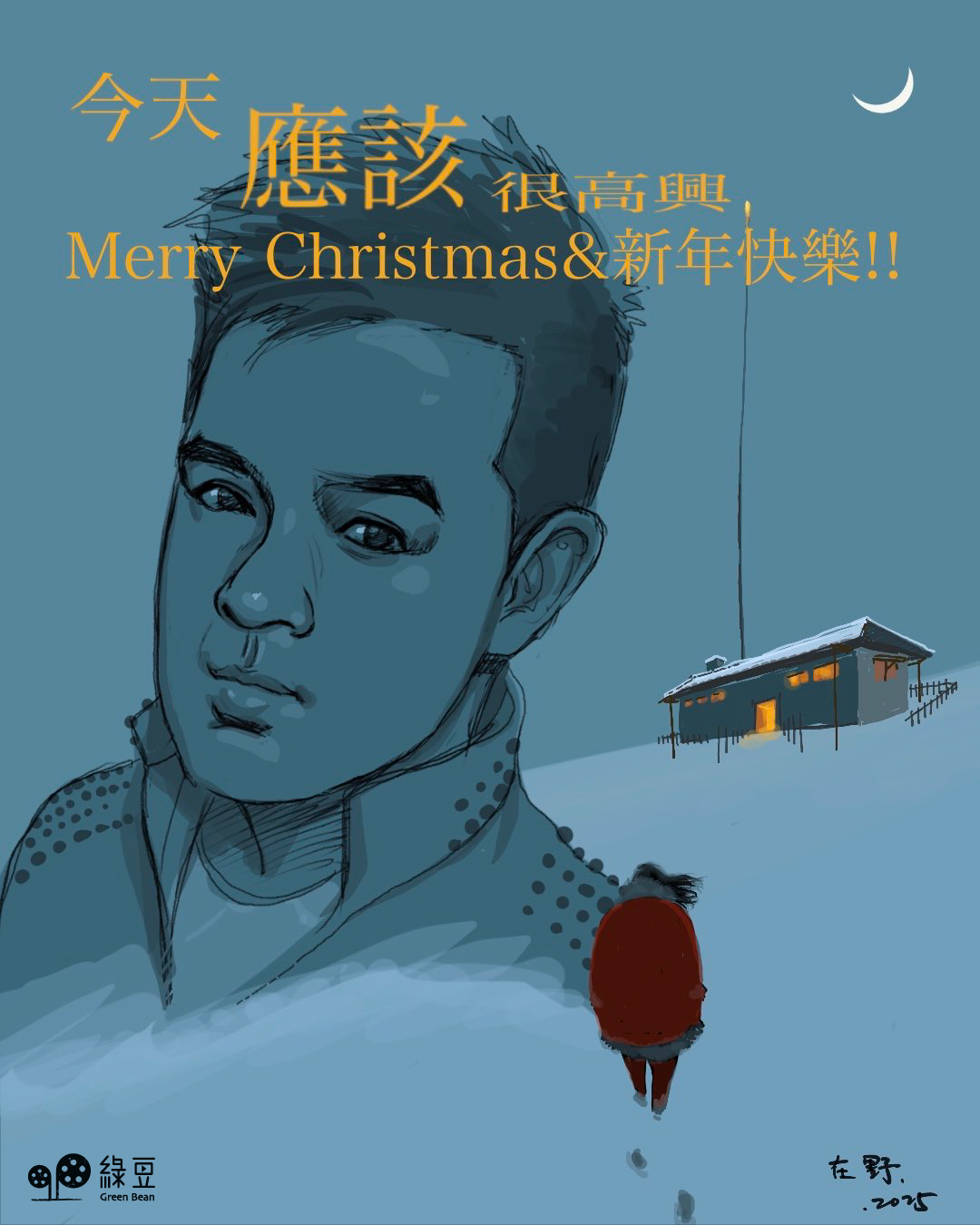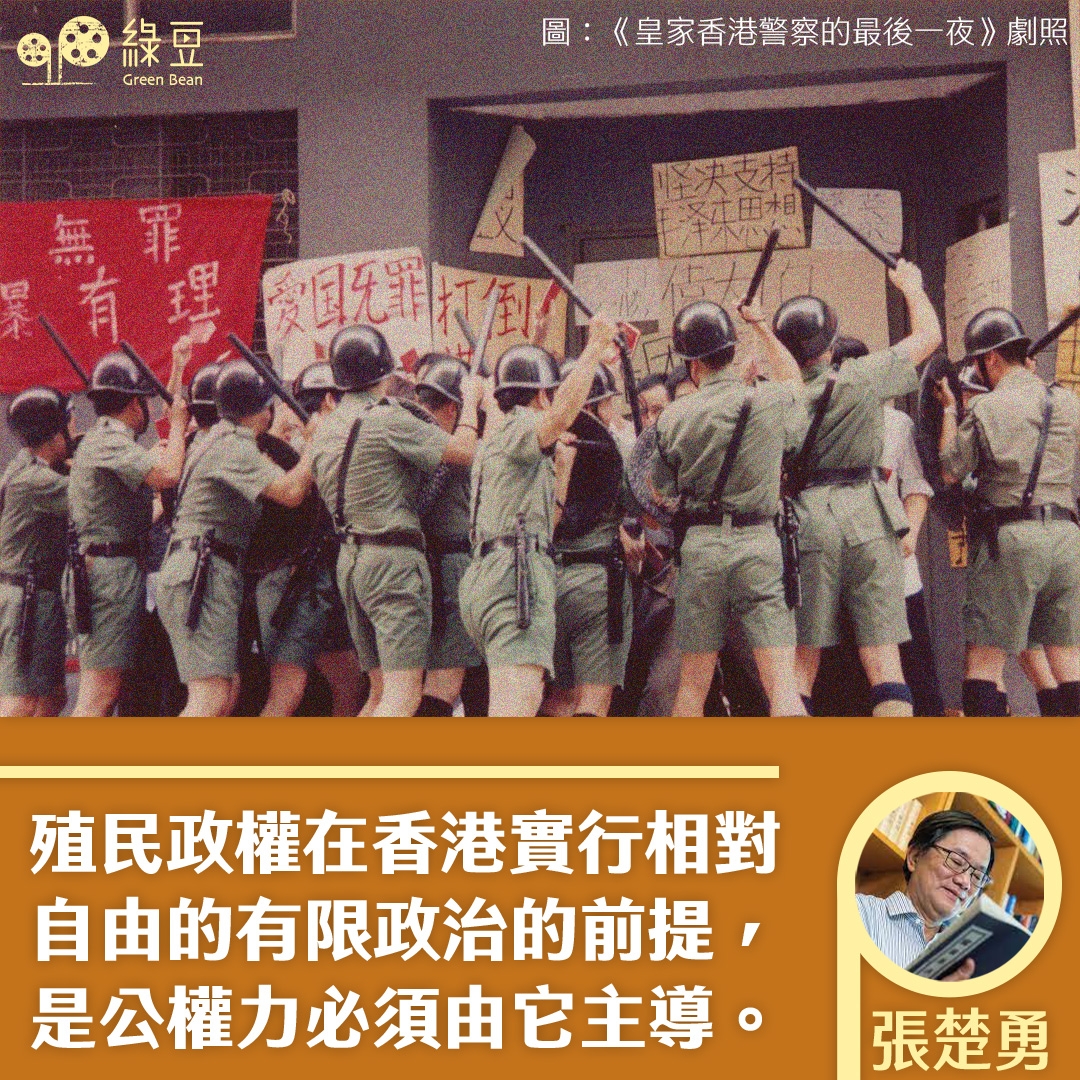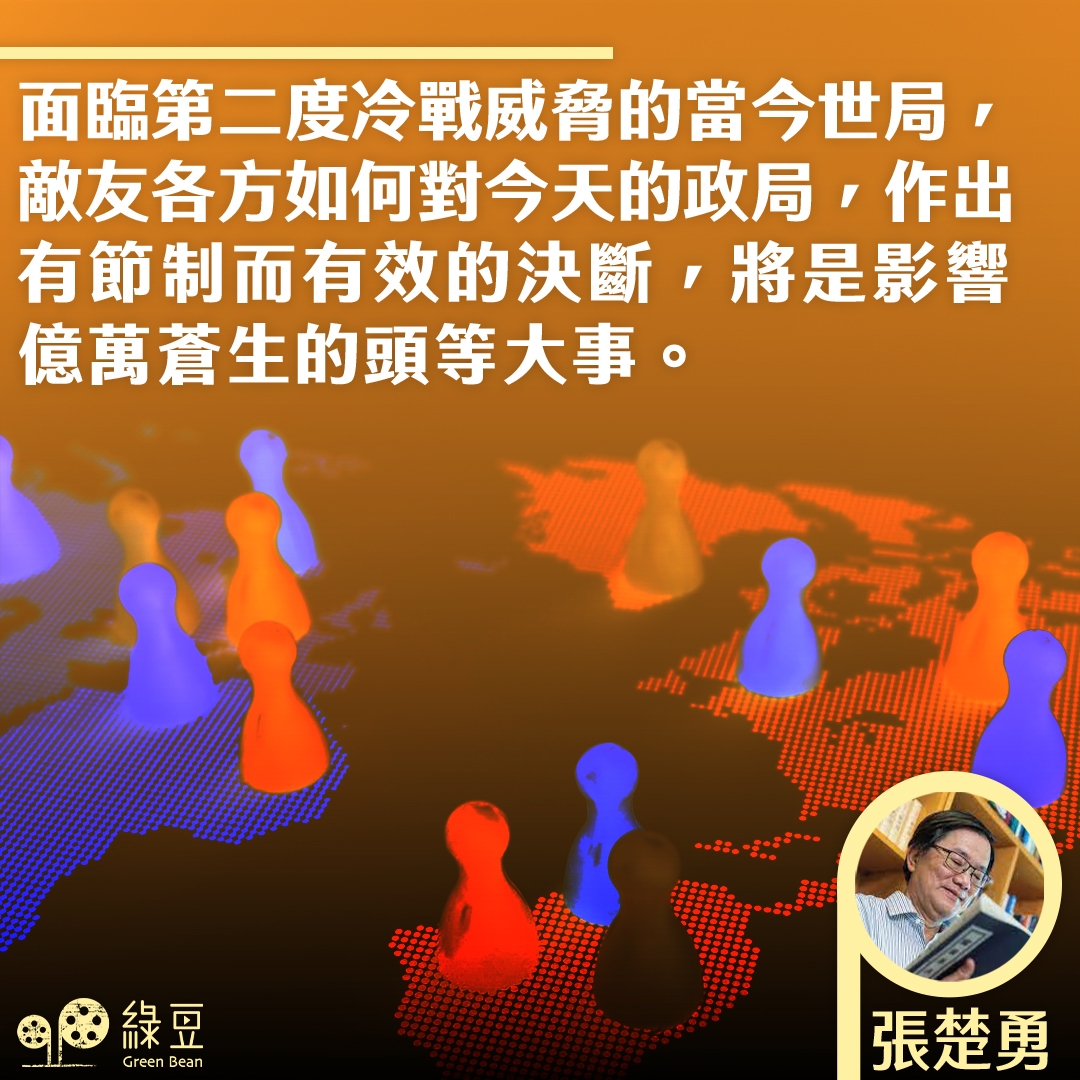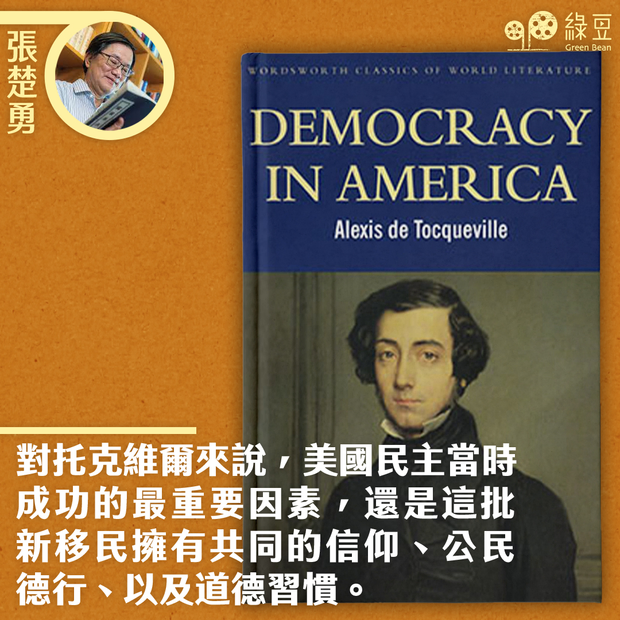治人與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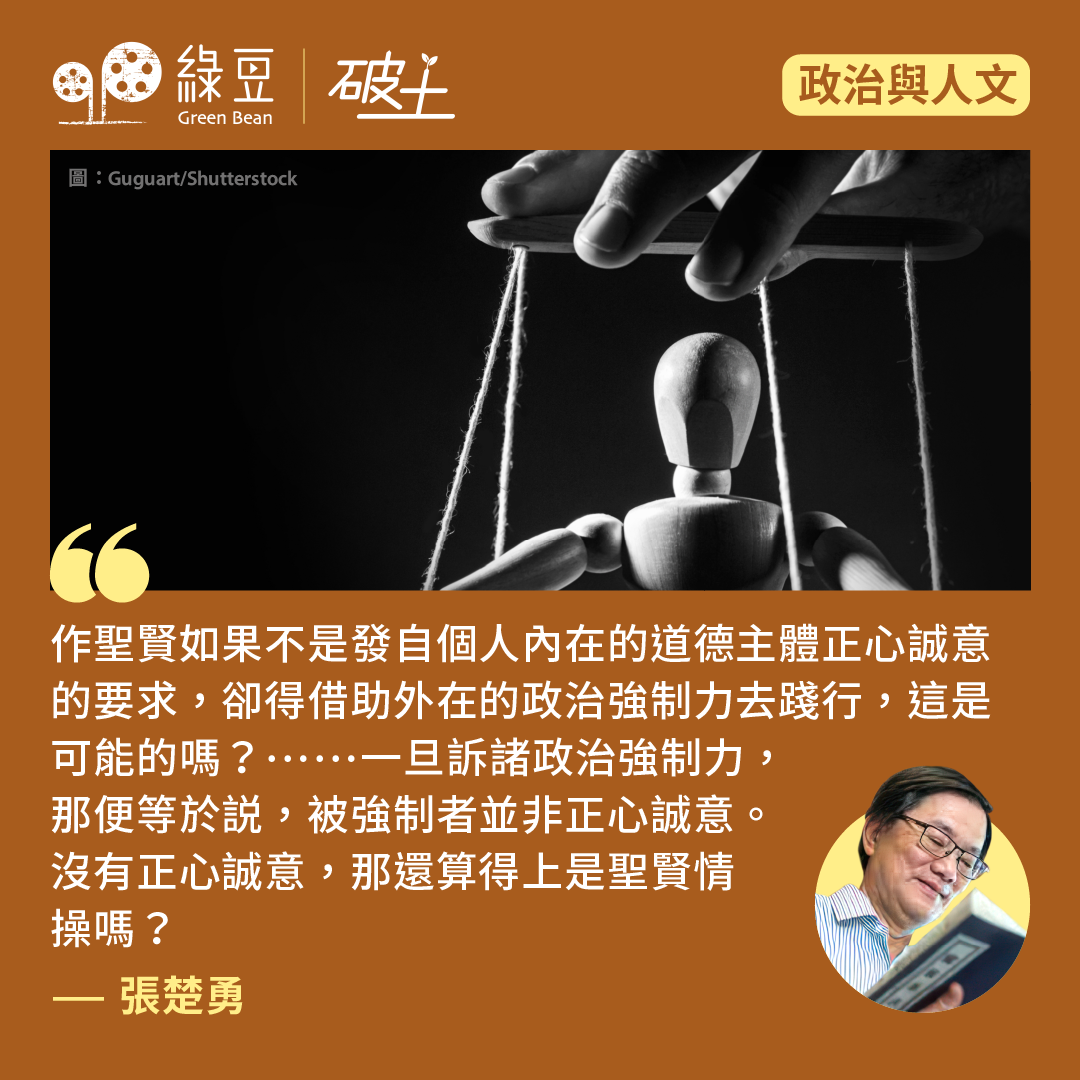
上個月,我在《綠豆》發表的〈修己與治人的關連與區分—徐復觀論儒家與民主人權〉一文中,提到20世紀新儒家徐復觀先生以下一個重要的觀點:
「儒家思想,主要是『規定人的行為的思想』。這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把修己和治人的行為作出區分,其基本用心之一,便是要執政者明白,『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要人人作聖賢,即使是真的,也會成為莫大的罪惡。』」
為甚麽「以政治強制之力」使人民做聖賢會是「莫大的罪惡」呢?我在這篇短文內,將會提出一些看法,並就此對規範行使政治公權的公共道德的性質及相關議題進行思考。
政治強制力與正心誠意
公權是構成人類政治社群並保障該社群存在、發展和有效運作的中樞元素。掌握公權者對政治社群的安危興衰,負有重大的公共責任。如果他們在這方面不稱職,嚴重者將影響政治社群的存亡。公權力要保證有效運作和執行,必須符合嚴謹、公正以及正當的程序,也得大體上為人民所認同和接受。必要時,公權力更得訴諸合法和適切的強制力作為推行的手段,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利益,和維護政治社群的安全法治和秩序等等。
作聖賢,是個人修身的崇高的道德要求。這往往需要慕道者裡外如一地終身不懈的努力去踐行。孔子不是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賢如夫子,也只敢說自己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吧了。再者,個人修身的道德必須重視正心誠意,因為這是發自慕道者個人内在的道德主體的要求。根據這要求化為個人行為後,其所產生的客觀實踐結果是成是敗、是差強人意還是盡善盡美,自然是重要的事。但如果個中缺乏了個人內在道德主體的正心誠意,那有關的行為是否可稱為聖賢行為便頓成疑問。
試想伸出援手拯救將墜於井的孺子的人,如果不是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心裡盤算著孺子家人會否因此而感恩圖報者,其道德情操離聖賢有多遠呢?
作聖賢如果不是發自個人內在的道德主體正心誠意的要求,卻得借助外在的政治強制力去踐行,這是可能的嗎?政治強制力或許能迫使被強制者在外在行為上服從於行使公權者的要求。但外在的強制力如何保證被強制者內心真的是正心誠意、表裡如一呢?個人如果自發地正心誠意努力作聖賢,那又何須訴諸政治的強制力呢?一旦訴諸政治強制力,那便等於説,被強制者並非正心誠意。沒有正心誠意,那還算得上是聖賢情操嗎?「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要人人作聖賢」顯然是自相矛盾和不會成事的一種荒謬的政治規範。
莫大的罪惡
在政治上強行推動不可能達致的目標,很可能會為國邦和蒼生帶來傷害 (例如強制力使人失去自由),也難免會導致不少負面的後果 (例如浪費公共資源)。更有甚者,這樣做也就是在政治社群中迫著人們去實踐表裡不如一的虛偽道德。不管如何努力也達不到的公共政策的目標,執政者假若執意要通過公權強制力不斷迫使人民繼續去做,這在政治上和人心上,都是最腐敗的事,因此也就是「莫大的罪惡」。
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規範個人的社會行為,極其量只能規範到人的外在行為。「齊之以刑」,有效者也許會做到「民免而無耻」。但「有耻且格」不是強制得出來的。「齊之以禮」因此只能是君子教化和移風易俗的理想,這並不應屬於公權強制力的範疇。其成敗與否,也不是公權強制力所能保障的。
當然,行使公權不一定都要訴諸政治強制力的。但如果我上述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話,強制公權力便只應限定於規範人的外在行為之上。假若人們 (例如極權政治 totalitarian politics 下的執政者)用之試圖規範人的道德動機和意圖,這往往會造成民既不能「免」,社群又「無耻」無「格」的罪惡後果。
首要的政治責任
基於以上的考慮,德國思想家韋伯 (Max Weber) 在談到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時,他反覆強調掌公權者必須首要遵從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這一主張,我認為是很有見地的看法。英國哲學家漢普希爾 (Stuart Hampshire)在他的〈公德和私德〉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 一文中甚至說,有能力大規模改變蒼生命運的掌公權者不單止是責任重大,他們得負上與個人道德考量不盡相同,卻在公共道德範疇內不得不負上的獨特重大責任。
掌公權者在公德範疇內最重大的道德考量,當然是對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負責。掌公權者如何才算是對人民負上政治責任呢?
由於政治決策者是通過運用公權賦予他們的權力來籌謀公益的,而權力的有效運用往往免不了要牽涉政治上的強制力作為保障,因此,審慎而認真地對待政治的任務,以及對公權力的適切行使便是至為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公權力的運用得著重於實效成果,而非單靠良好的意圖,因為行使得當的公權力是有可能促成大眾受惠的社會後果出現,但卻無法保證人民都有聖賢的意圖或情操。
換言之,掌公權者的首要政治責任,是盡最大努力去促進、維護和保障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以及維持讓以上的努力可以長治久安地持續下去的內外政治環境。
當然,對於社群中的個人成聖成賢的追尋、父慈子孝的關係、相敬如賓的夫妻、君子之交的朋友等個人道德考量,掌公權者大可歡迎甚至鼓勵。但相對於掌公權者的公德責任倫理,上述的個人道德考量是次要的。公德責任倫理的考量必須佔優先地位。
支持公德責任倫理在掌公權者應佔有優先性的理由,除了是因為公權保證不了個人修身的聖賢情操外,還因為公德責任倫理事關芸芸眾蒼生。運用公權保障公益努力的成敗,影響的並非只是個人,而是社群中的所有人。社群公益不保,個人福祉和利益的追尋也變得失去保障。正如上文所說,審慎而認真地對待政治的任務,以及對公權力的適切行使是至為重要。在這議題上,有些論者甚至認為,在政治領域上,假如遇到公德責任倫理和個人意圖倫理產生矛盾時,掌公權者為了前者而犧牲後者也應是在所不惜的。這方面最有份量的論者大概是文藝復興年代佛羅倫斯的思想政治家馬基雅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他的論點,至今還深具影響力。
政治上的管治問題
促進、維護和保障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及其內外政治環境,是必須講求實效和實際結果的。就像在戰爭中,能取勝的將領和軍隊,才是有價值的。行使公權和制定及推行公共政策,其好壞標準繫於該政策是否能實效地為人民公益在可行範圍內帶來最良好的結果。於此,負責任的公權者必須有根有據、實事求是地去制定政策目標,衡量相關風險,並提出能落實達成目標的可行方案。如果當中不得不牽涉上政治強制之力,那便得要有方法把強制力的深度和廣度,限制在最小範圍和影響之內。這些都是責任倫理對公權者的要求和規範。
孔子曾經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在社群中有紛爭和不同意見便可能有訴訟。聽訟便是通過公平的程序就有關的紛爭和分歧作出裁決,判斷誰是誰非。而有關的判決,在執行上也難免有強制力的介入。當然,公正的訴訟極其量只能保障程序的公正。但程序的公正卻並不一定保證實質的公正。最好的法官和最公正的訴訟程序,在現實上還是不能排取冤枉好人或讓壞人消遙法外的。在這一點上,聖人和凡人同樣是免不了的。
但孔子接著那「必也使無訟乎!」的喟歎,卻沒有在政治上提出一個現實上可以落實無訟的方案。尤有甚者,無訟的社會更意味著是一個沒有爭執、不需要訴訟的社會。如果真的是這樣,政治已被和諧或一致所取代,因此更毋須在社群中訴諸政治上的強制力。如果是這樣,政治也許已不復需要了。在人人都是自發自律的君子社會中,當個個都是自治者時,那裡還需要治人!但現實的社會,真的已是這樣了嗎?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管治問題,掌公權者還是得面對的。
孔子這個嘆喟,似乎是指向一個很高遠,但卻是非政治的、人類崇高的至善式理想。如果我們把政治強制力強行伸延去規範人類的道德意圖,正如上文所說,那是容易變成為危險的暴政。但如果由於政治現實和制度的不完美,我們便以至善高遠的道德要求作為政治社群行為規範的根本,這樣做不單容易讓政治流於空談,同時也容易讓人不經意的把對掌公權者的責任倫理的要求遺忘了。如果公權執政者遺忘了責任倫理的優先性,對蒼生而言,那同樣是危險的事。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