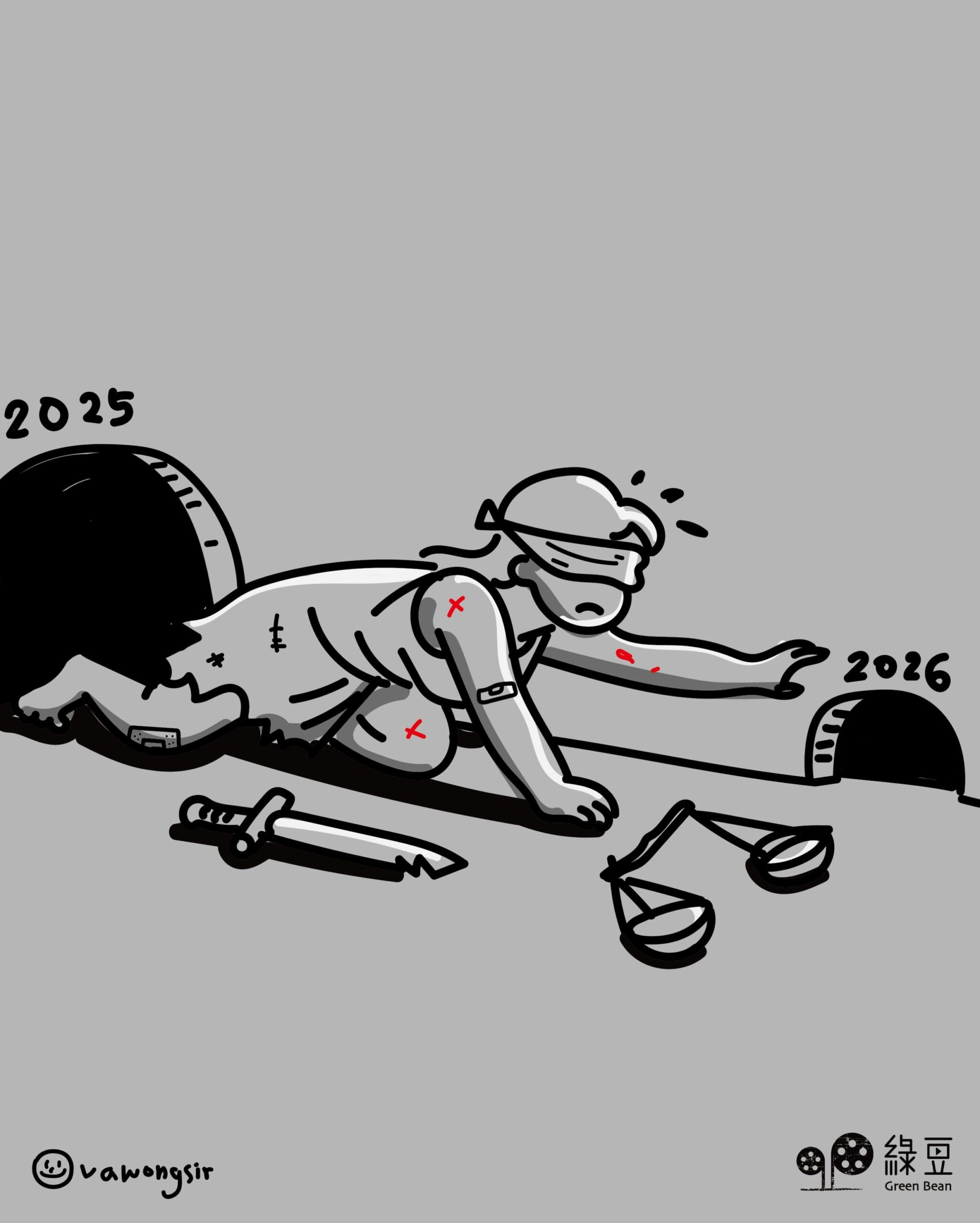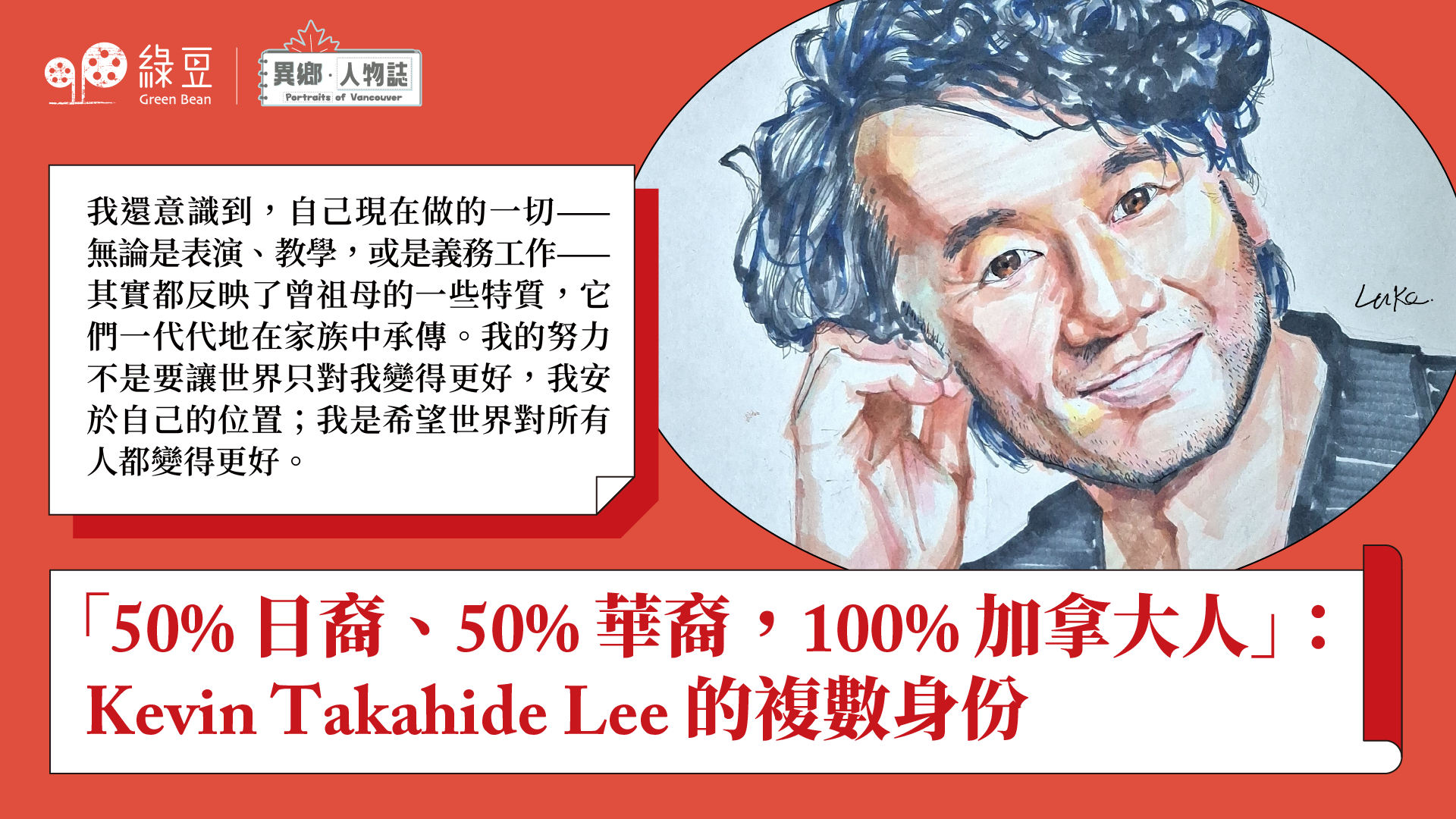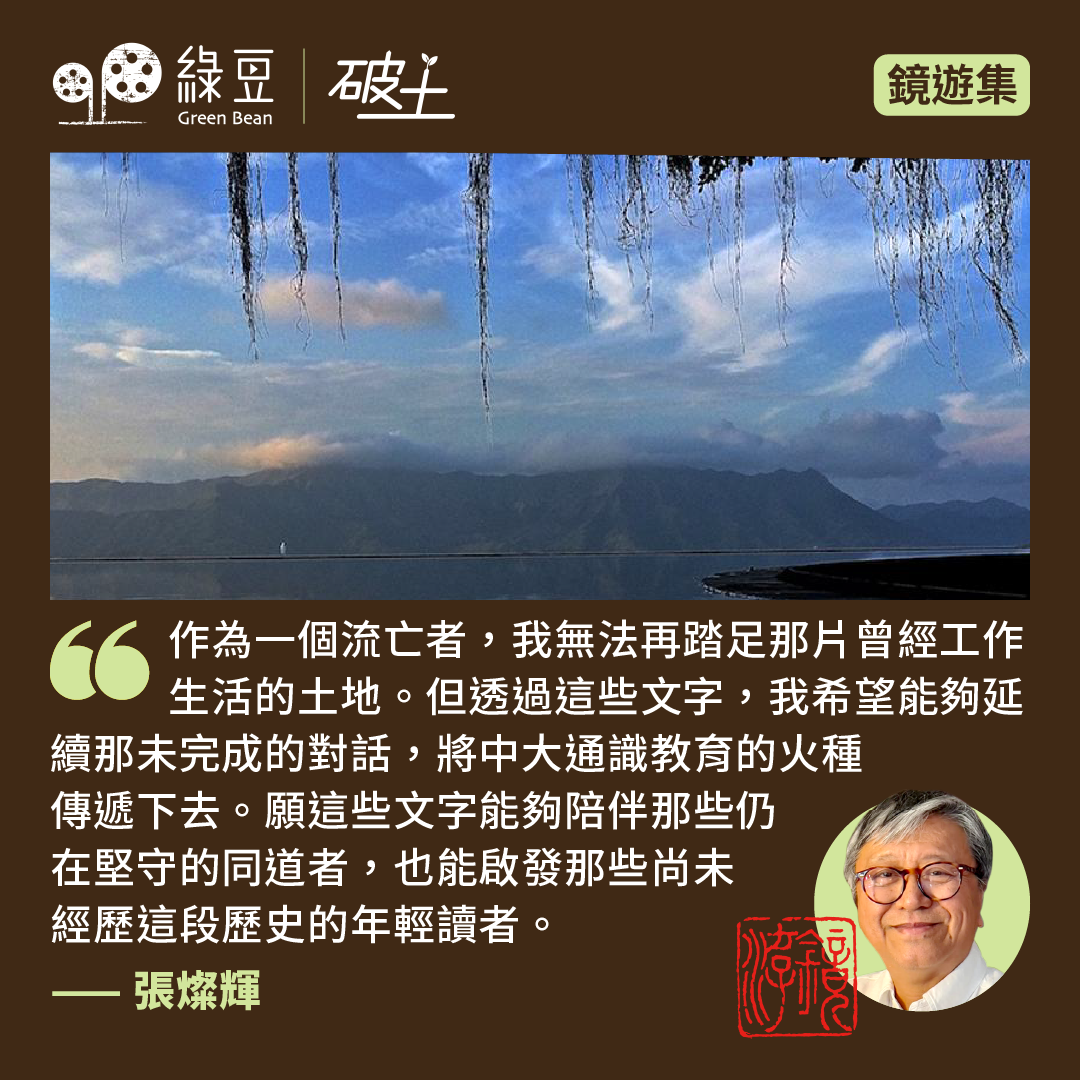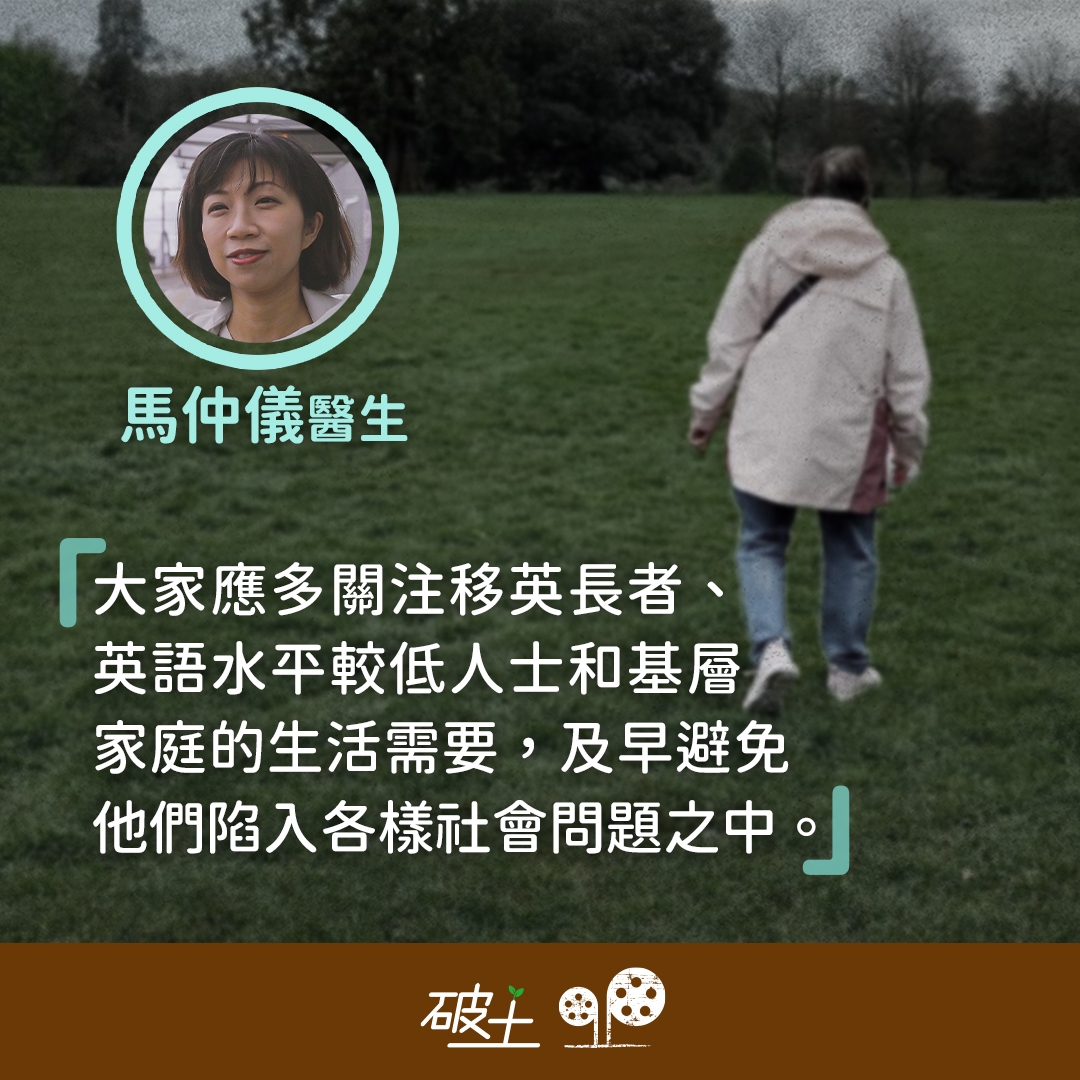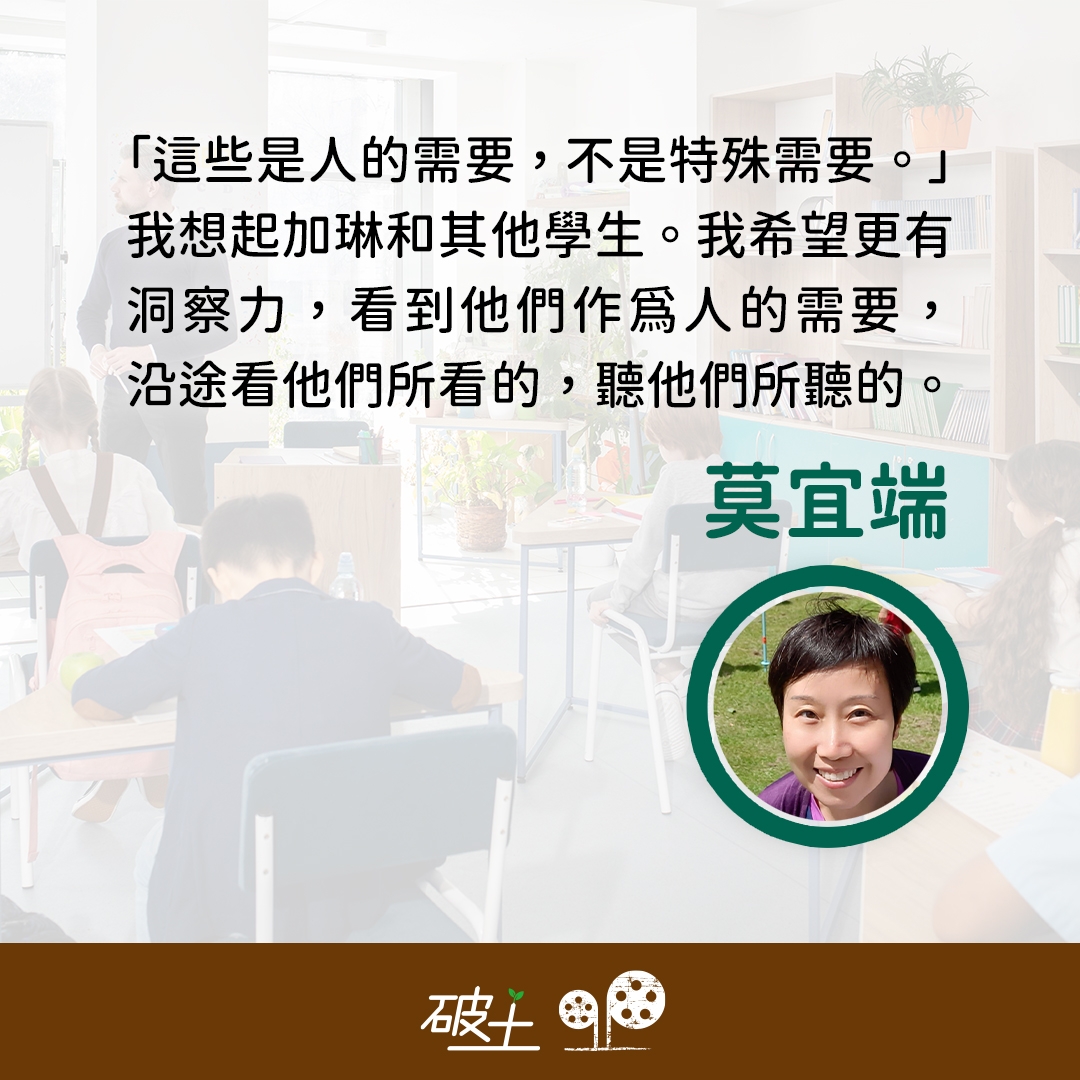現今世代旅行意義的深度反思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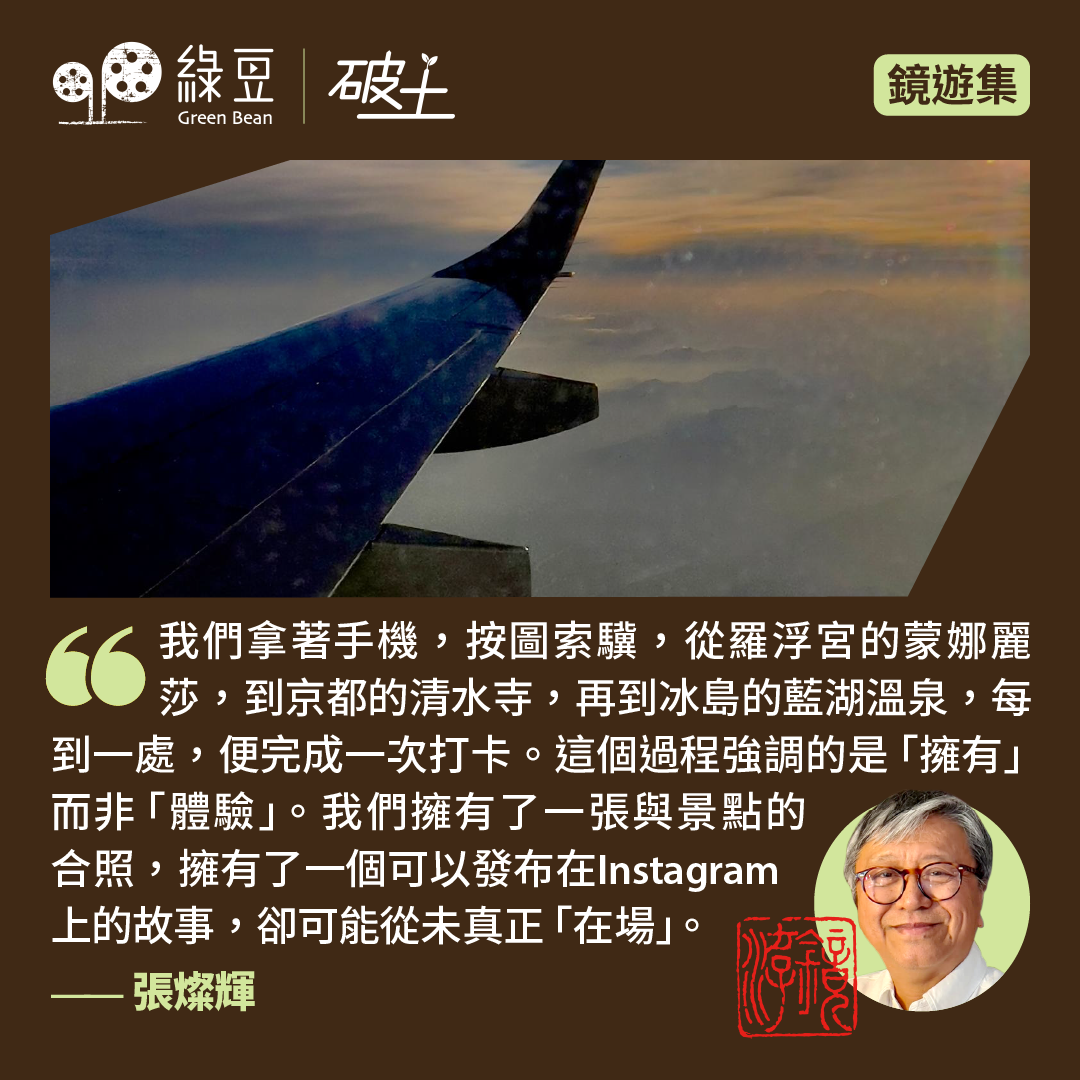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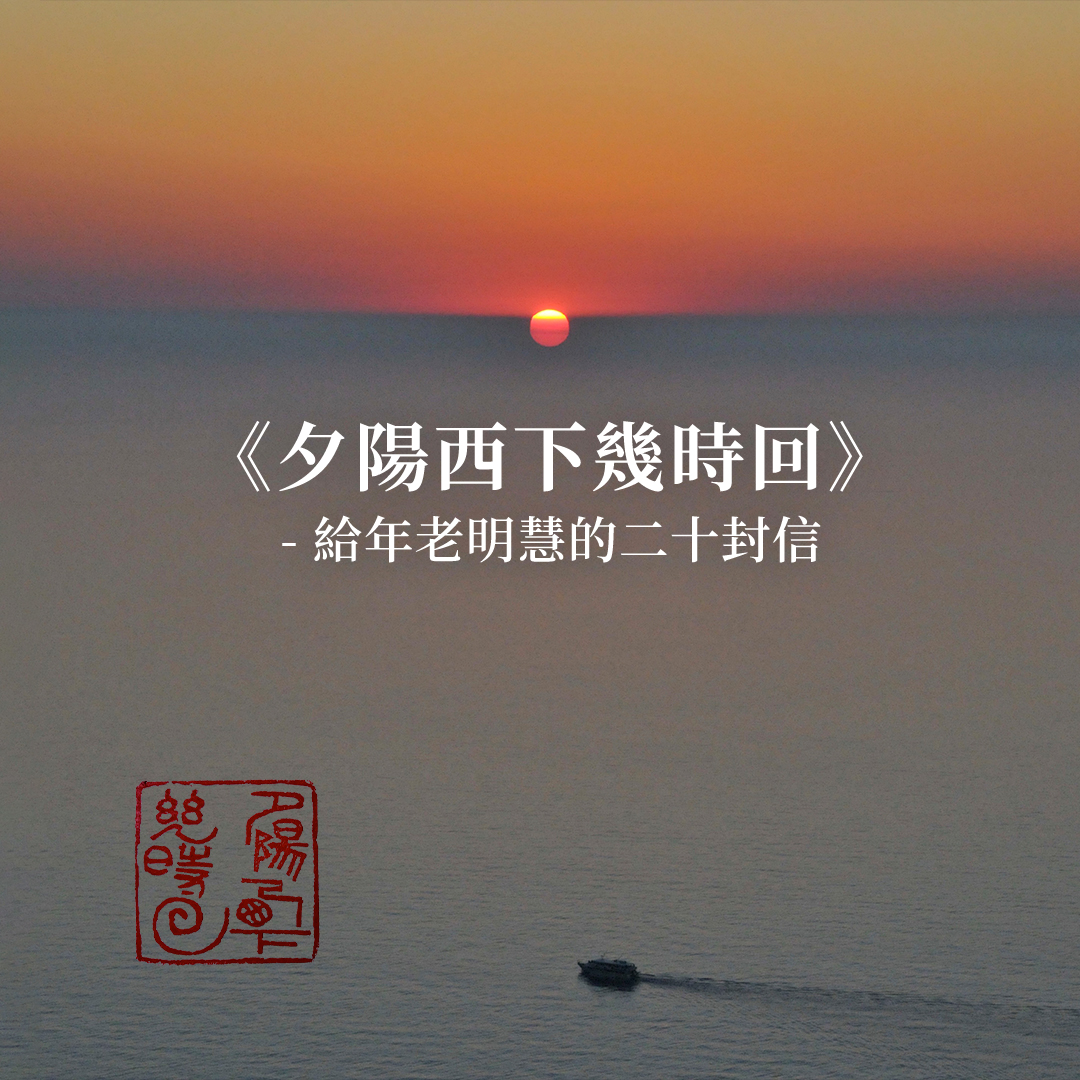
第十七封信 17.1
明慧,
「暑假期間,你有什麼安排?去旅行?意大利還是冰島?」
每當聽到這樣的問題,我總是忍不住思考:相信你肯定去了不少地方旅行,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去旅行,旅行的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當今這個資訊爆炸、消費至上的時代,顯得格外迫切而深刻。
然而,在這條被消費主義鋪平的道路之外,旅行存在著另一條更有意義,也更為深刻的道路,這條路通往旅行的古老核心: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姿態,一場艱難而必要的自我反省,一次從個人狹隘與無知中的解放,以及最終,一份對他者與他者文化的深沉尊重。
現代旅行的景觀化困境
現代旅行的本質,在很多層面上,已蛻變為一種「有組織的觀看」。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中精闢地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真實的生活已被景觀(spectacle)所取代。「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已轉化為一種再現。」這句話完美地概括了現代觀光業的運作邏輯。
明慧,你是否也察覺到了這種轉變?今日的旅行,其流程與購買任何商品並無二致。我們在網路上瀏覽「產品目錄」(旅遊網站),被精美的圖片與誘人的文案吸引,比較「性價比」(機票與酒店價格),最終「下單購買」一個旅遊套餐。目的地被塑造成一個待消費的物件,其複雜的歷史、社會紋理與日常生活被簡化為一系列「必看景點」、「必吃美食」與「必買伴手禮」。
這種消費模式深刻地影響了旅行者的心態。旅行不再是探索未知的過程,而成了一次「清單式」的任務執行。我們拿著手機,按圖索驥,從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到京都的清水寺,再到冰島的藍湖溫泉,每到一處,便完成一次打卡。這個過程強調的是「擁有」而非「體驗」。我們擁有了一張與景點的合照,擁有了一個可以發布在Instagram上的故事,卻可能從未真正「在場」。我們觀看了風景,卻未曾與之對話。這種旅行的滿足感,源於完成消費行為的快感,而非源於與世界產生深刻連結的喜悅。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代的旅行經驗往往被「觀光凝視」所主導。這種凝視將觀者導向異於日常生活的景觀,使他們對視覺要素更敏感,並常透過照片等方式將景色「客體化」以便複製。我們成了視覺的奴隸,用鏡頭框住世界,卻失去了用心靈感受世界的能力。
舞台真實與虛假事件的迷霧
親愛的明慧,你是否曾經在旅行中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失落?彷彿所見所聞都帶著一層虛假的光澤,讓人難以觸及真實?這正是學者們所說的「舞台真實」現象。大眾旅遊體系常將遊客包圍在舞台真實中,使其體驗到的多是膚淺的「虛假事件」(pseudo-events),而非真正的「後台」真實。這些虛假事件精心設計,目的是滿足遊客對「真實性」的渴望,卻又不讓他們真正接觸到可能令人不適或複雜的現實。於是,我們看到的威尼斯是去除了垃圾與貧困的威尼斯,我們體驗的巴黎是沒有社會問題的巴黎,我們遇見的當地人都是為了旅遊業而存在的友善面孔。這種經過篩選和美化的現實,雖然令人愉悦,卻讓我們與真實的世界愈行愈遠。
人們對旅行目的地的想像與期待常受旅遊廣告、媒體資訊影響,這些資訊往往經過簡化和篩選,只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導致實際體驗與期望產生落差。當我們懷著電影《好想有嫁期》(Under the Tuscan Sun)的浪漫幻想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卻發現現實中的托斯卡尼也有交通堵塞、商業化的景點和疲憊的當地人時,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落差?
旅行的三重境界
中國文化對旅行有著獨特而深刻的理解。在漢語的語境中,「旅行」包含了三個不同的層次:「旅遊」(觀光娛樂)、「行遊」(非觀光娛樂)和「神遊」(精神旅行、想像旅行、網路旅行和生死之旅)。其中,「遊」是中國旅行文化的關鍵與核心概念。
這種三重境界的劃分,為我們理解旅行的本質提供了珍貴的視角。
「旅遊」是最表層的,以休閒娛樂為目的,這也是當今主流旅遊業所專注的層面;「行遊」則更深一層,它不以娛樂為唯一目的,而是帶著某種使命感或求知慾的移動;而「神遊」則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它超越了物理空間的限制,通過精神的力量實現真正的「旅行」。
明慧,當你下次踏上旅程時,不妨問問自己:我正在進行的是哪一種「遊」?我是在消費景點,還是在與世界對話?我是在逃避現實,還是在尋求更深層的理解?
邊界的穿越與自我的重構
學者Eric Leed將旅行定義為「任何穿越重要邊界的行為」,並強調旅行與「經驗」(experience)緊密相關,認為旅行是改變旅行者自身的「典範『經驗』」模式。這個定義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旅行不僅僅是地理位置的改變,更是心理和精神邊界的突破。
當我們身處一個語言不通、文化陌生的環境,所有熟悉的社會角色與身份標籤(如職業、家庭地位)都被暫時剝離。我們不再是某某公司的經理,或某某人的子女,而僅僅是一個「異鄉人」(The Stranger)。這種身份的懸置,迫使我們直面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是誰?」在這種孤獨與疏離感中,我們反而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一種可以重新選擇、重新定義自我的自由。旅行,因此成為一場存在主義式的冒險,它將我們拋入未知,迫使我們思考存在的意義,並在找尋方向的過程中,完成一次艱難的自我創造。
這種邊界的穿越,不僅發生在地理空間中,也發生在時間維度裡。當我們走進一座古老的廢墟,我們實際上是在穿越時間的邊界。旅行者探訪廢墟,透過古老殘骸反思生命的有限性與虛空,從中獲得慰藉。廢墟象徵時間的無限,提醒人類在時間面前的渺小,並能激發崇高而沉重的感受。
好奇心與虛榮心的複雜糾葛
明慧,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旅行動機中的複雜性。驅使我們踏上旅程的,往往不僅僅是純粹的好奇心,還可能包含著虛榮心的成分。
這種心態導致了幾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地方的物化。當一個地方被視為「光景」時,它就不再是一個有生命、有歷史、有當地居民日常悲歡的所在,而退化成一個滿足遊客視覺慾望的背景板。當地居民的生活被展演化,他們的家園成為遊客的遊樂場。
這種物化過程,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暴力。它將活生生的社會現實簡化為可消費的符號,將複雜的文化傳統降格為旅遊商品。當我們在麗江古城拍照時,我們看到的是經過商業化包裝的「納西文化」,還是真正的納西族人的生活?當我們在台北夜市品嚐「正宗台式料理」時,我們體驗到的是台灣的飲食文化,還是為了迎合遊客口味而調整的商業產品?
遊客與旅人的根本差異
遊客消費地方,旅人融入地方。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旅行態度。遊客將地方視為服務於自己的商品,他們關心的是能從中「得到」什麼。旅人則嘗試將自己視為地方的暫時居民,他們關心的是如何與地方產生連結,如何以一種更負責任、更少侵擾的方式參與其中。
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行為上,更體現在心態和價值觀上。遊客往往帶著征服者的姿態,希望將異文化納入自己既有的認知框架中,一旦遇到不符合期待的情況,就會感到失望或憤怒。而旅人則保持著學習者的謙遜,願意調整自己的視角,接受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和啟發。
例如,一個習慣了精確時間觀念的德國人,到了拉丁美洲,可能會對那裡悠閒的生活節奏感到困惑甚至惱怒。但如果他能放下批判,嘗試去理解這種「慢」背後的社會文化邏輯——或許是更注重人際關係,而非商業效率——他就有可能從一種單一的時間觀中解放出來。他會明白,鐘錶上的時間,只是衡量世界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
現代度假制度的歷史反思
要理解當代旅行的困境,我們必須回溯到現代 度假制度的起源。現代的「 度假」是晚近的產物,始於貴族的「壯遊」,後因工業革命、公共假日的立法和交通發展,普及至大眾。然而,假期的增多不代表人們更懂得「閒」,過度追求效率反而使休閒變得匆忙。這種歷史背景解釋了為什麼現代人的旅行往往充滿了焦慮和匆忙。我們將工業社會的效率邏輯帶入了旅行,試圖在有限的假期中「maximizing」我們的體驗。於是,我們制定詳細的行程表,計算每個景點的停留時間,用「性價比」來衡量旅行的價值。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與旅行的本質相矛盾。
真正的旅行需要的是時間的餘裕,需要的是無目的的漫遊,需要的是與偶然相遇的開放性。但現代 度假制度給我們的卻是被切割成標準單位的「休閒時間」,我們必須在這些被量化的時間片段中,完成對世界的「體驗」。
中國傳統旅行智慧的當代價值
面對現代旅行的種種困境,中國傳統的旅行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他們的旅行往往不是為了娛樂或炫耀,而是為了修身養性,為了與天地自然建立更深層的連結。
他們懂得「神遊」的妙處,知道真正的旅行不一定需要身體的移動。莊子的「逍遙遊」、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蘇軾的「赤壁賦」,這些都是精神旅行的經典範例。他們告訴我們,旅行的終極目標不是到達某個地點,而是達到某種精神狀態。
這種傳統智慧對當代人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旅行是一種內在的修養,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即使我們身處熟悉的環境中,只要保持著開放和好奇的心態,我們同樣可以經歷深刻的「旅行」體驗。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