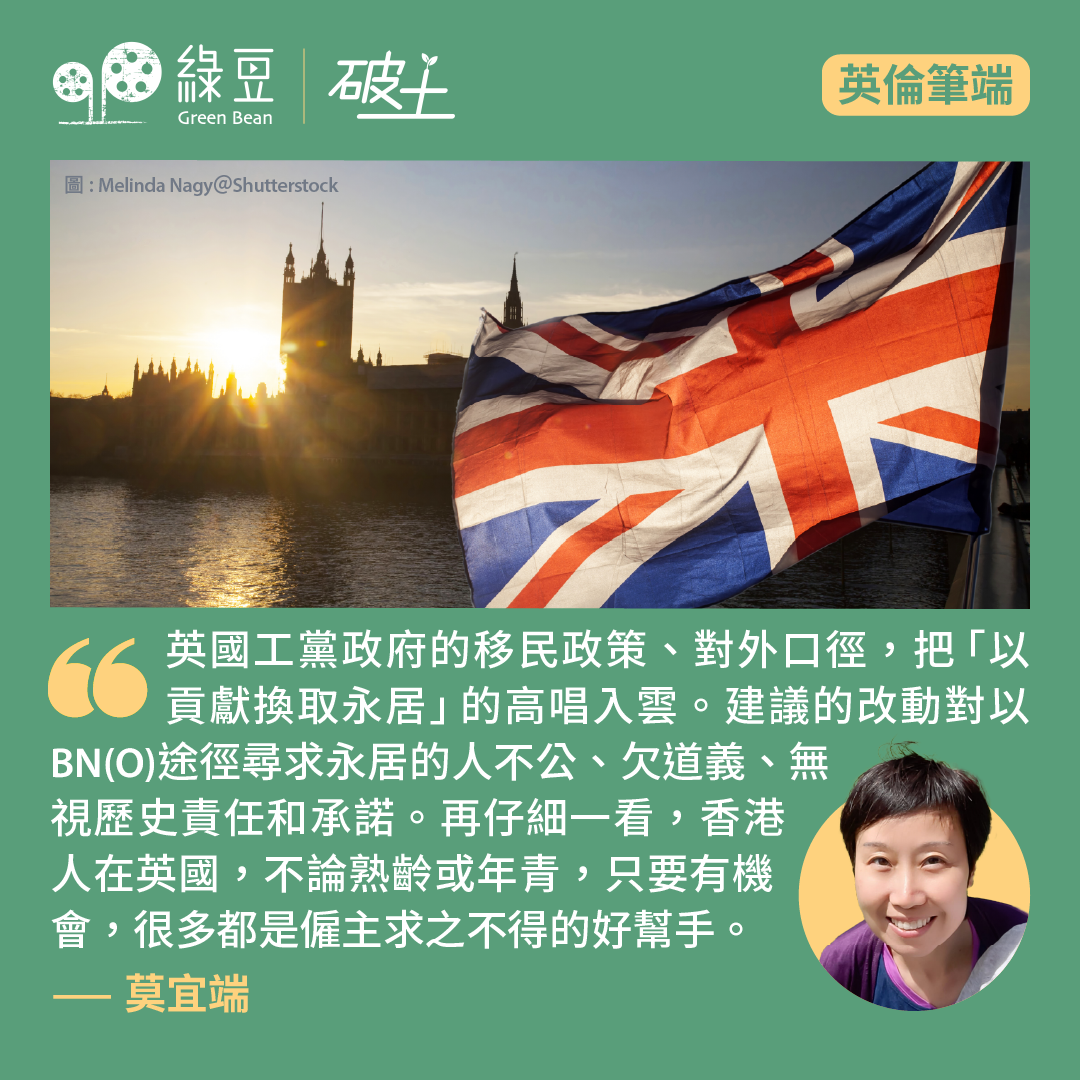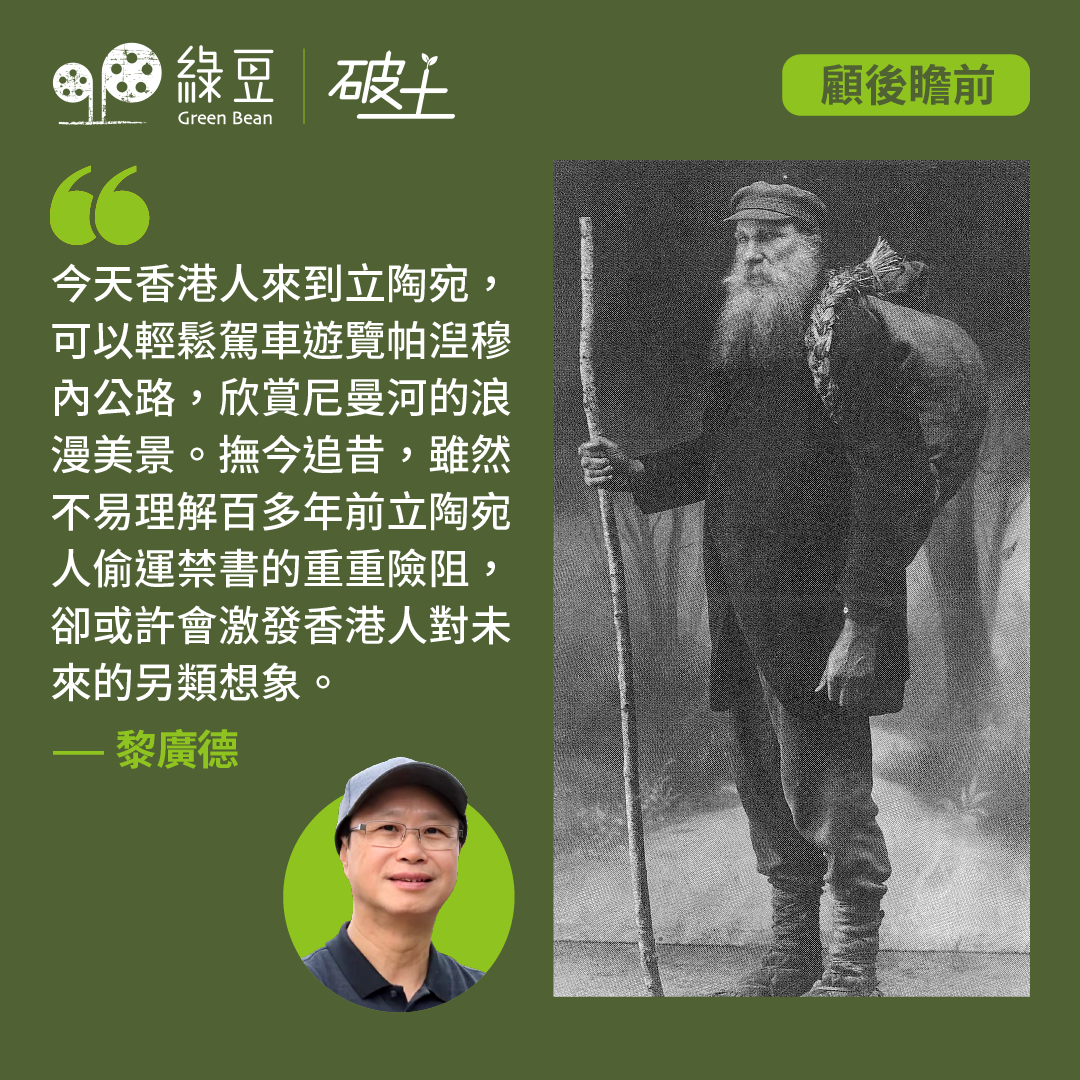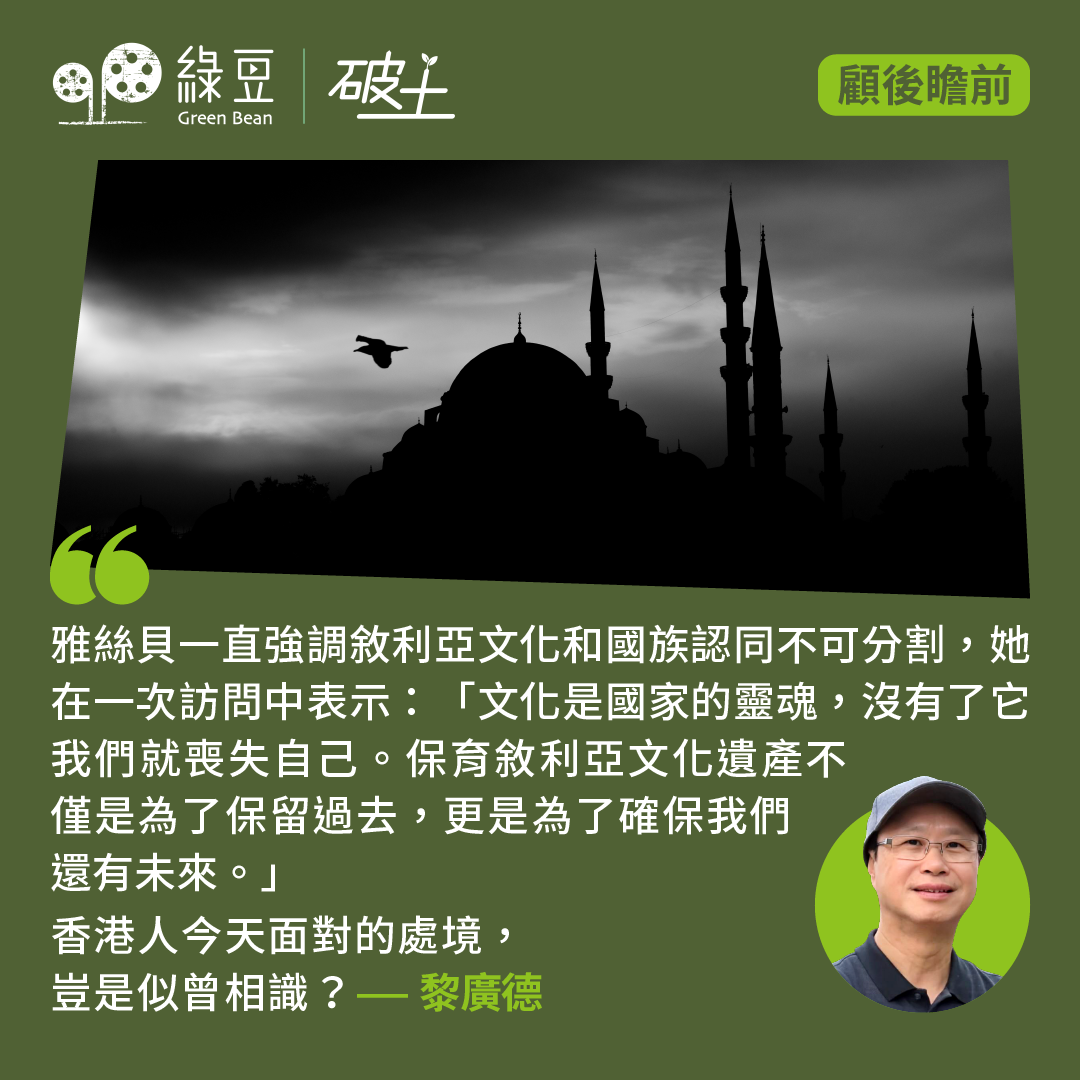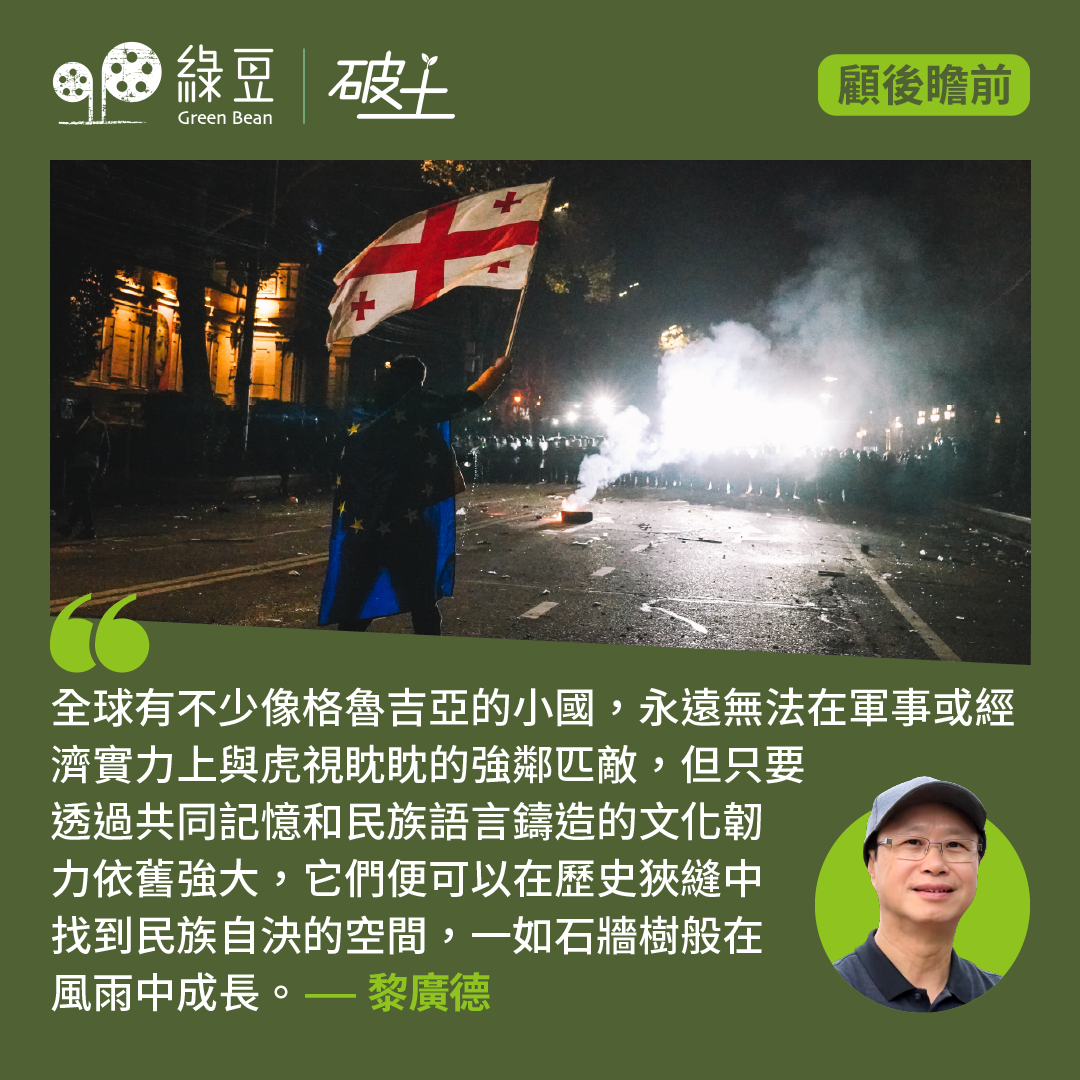從難民到議員 :庫爾德人示範離散族群在地參政的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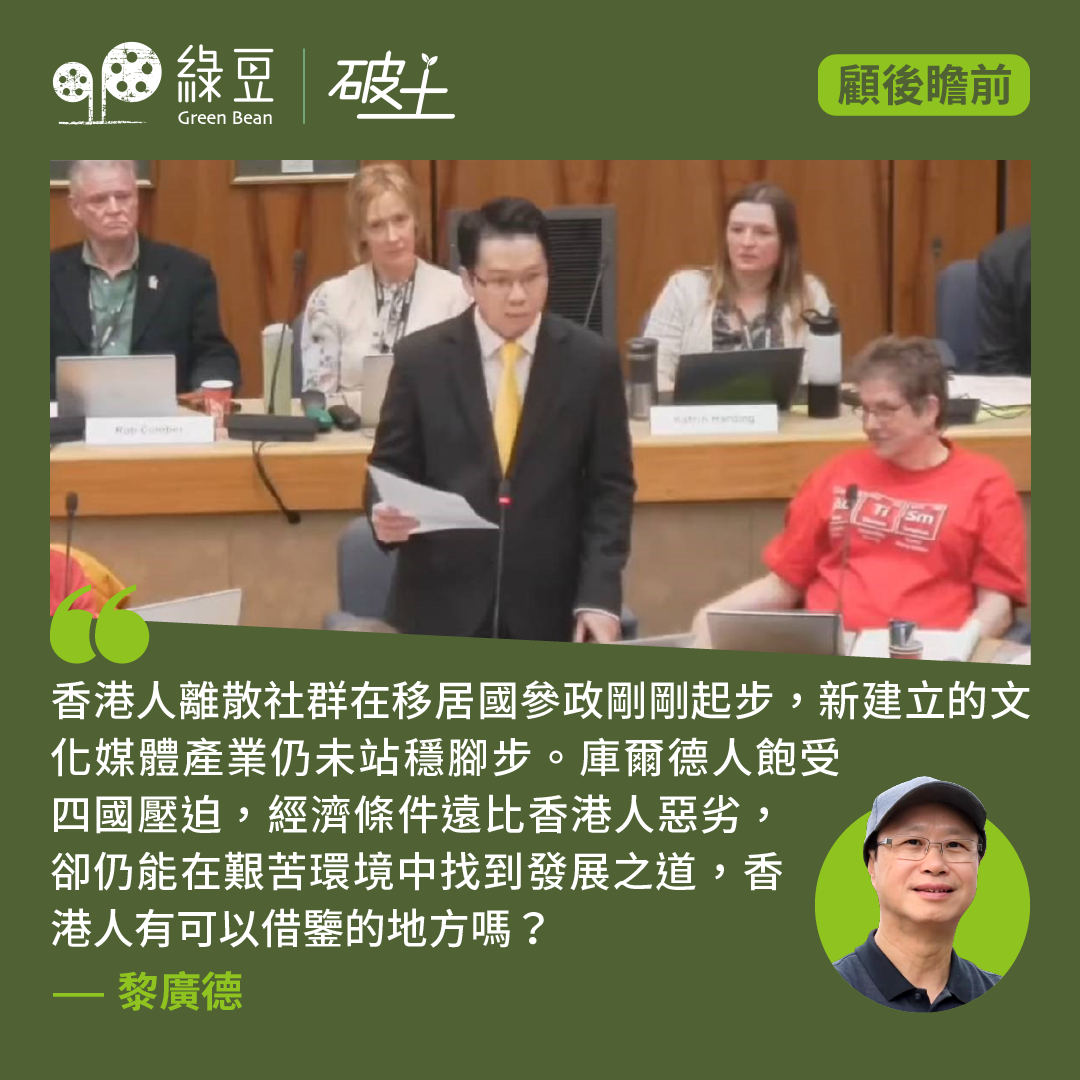
最近居英港人群起反對中國準備在倫敦興建超級大使館,去年當選為Wokingham 地區議會議員的吳兆康提出動議,他在所屬的自由民主黨支持下,地區議會通過決議,正式致函英國副首相加入反對行列。雖然執政工黨議員並不支持決議,但這可說是首次由香港人議員在英國政治體制內就離散港人關注的議題打響第一炮。
究竟離散族群在移居地參政,是否有助該族群的在地發展和文化傳承?或許可以參考一個堪稱四面受敵的族群 —— 庫爾德人在歐洲參政的正反經驗。
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擁有過千年歷史,到了16世紀逐步形成獨特的民族語言,屬於印伊語糸的一個分支。庫爾德人的居住地—— 庫爾德斯坦,自中世紀起被奧圖曼和波斯帝國統治。奧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解體,曾經在1920年訂立的條約中協議成立庫爾德國,但協議最終並沒有執行,以至庫爾德斯坦被四個國家瓜分 —— 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令庫爾德人成為當地的弱勢民族。
庫爾德的總人口估計有三千五百萬,包括逾150萬人離散海外,當中以移居德國的最多,約一百萬人,而在英國和瑞典估計各有近十萬人。雖然庫爾德人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四個國家分別發起自治和獨立運動,但一直飽受壓迫,有反抗團體被標籤為恐怖組織,亦曾經被當地政府禁止使用庫爾德語。所以庫爾德人分布海外的離散社群一直肩負文化傳承的重任,通過語言學校、音樂藝術、文化活動等種種途徑,在移居地讓下一代堅持國族認同。
離散社群中的兩類人才
在庫爾德離散社群中有兩類人才對庫爾德的未來發展特別顯眼:一類是在移居地參政的政治人,另一類是在移居地建立文化媒體的企業家。
根據粗略統計,過去20年當選全國議會和地方議會的庫爾德議員,在德國和瑞典各有七位、在英國有四位、在歐洲議會也有三位。這些庫爾德議員分布在不同的政治勢力 (但極右政黨除外),例如在德國既有議員屬右翼的基督民主黨,亦有屬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在英國則有議員屬保守黨,亦有屬工黨及蘇格蘭國家黨。但無論這些議員屬於那個政黨,他們都有兩個共通點:其一是關注庫爾德人在原居地面對的政治打壓,其二是在移居地政府中倡議人權議題、多元文化和包容的難民政策。
「跨國公民」意識
在庫爾德民族的共同記憶中,有一個特大事件可與中國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相提並論。1988年3月16日,伊拉克空軍使用芥子氣和沙林毒氣襲擊庫爾德斯坦地區的哈拉卜賈鎮(Halabja),導致近五千人死亡和一萬人受傷, 是歷史上針對平民的最大規模化學武器襲擊。
由於伊拉克當時被視為對抗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的堡壘,受到西方國家、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所以大屠殺發生後大部分國家都不願意高調譴責。但分布各地的庫爾德裔議員和公民團體鍥而不捨要求國際社會徹查事件,最終伊拉克刑事法庭在 2010年對哈拉卜賈大屠殺的最高指揮官阿里哈桑.馬吉德判處死刑、歐洲議會在2012年定性該場大屠殺為種族滅絕事件、英國國會在2013年就此舉行正式辯論。從這場事件的後續發展足以看到庫爾德裔議員發揮的關鍵作用,亦說明了倡議工作必須持之以恆才奏效。
庫爾德裔議員的身份帶有強烈的「跨國公民」意識,因此他們必須在關注原居地議題的同時站穩移居國的利益立場,但兩者衝突有時在所難免。例如瑞典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申請加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土耳其一直從中作梗,原因是瑞典的少數黨政府在2021年上台和往後執政,都一直倚靠一位曾經身為伊朗庫爾德戰士的獨立議員Amineh Kakabaveh 的支持,所以瑞典一直執行親庫爾德路線,而這正是土耳其的大忌。
由此可見,在離散族群的期望和移居國的整體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和取捨,正是對「跨國公民」議員的最大挑戰。試想吳兆康若果份屬執政工黨,他的影響力或許更大,但取捨會否更加艱難?
多年來移居海外的庫爾德人與近幾年離港的香港人有一點共通之處:無論個體自視為移民、難民、避秦者或流亡者,他們都屬於因原居地社會衝突而催生的離散族群,所以政治參與度特別高漲,而在衝突期間的共同經歷和集體記憶,就變成了建立族群認同的養份。
離流媒體的角色
庫爾德流亡歐洲的知識分子當中,有不少人為了保存國族身份認同而創立文化媒體產業,包括報章、社區電台、電視台、出版社和網上媒體,例如以德國作為基地的庫爾德語日報Yeni Ozgur Politika 以及覆蓋英國丶比利時、法國和丹麥的電視台MED TV。這些企業並不倚賴政府資助,但多年來的摸索已讓他們掌握到可持續的商業運作模式,例如開拓本地市場廣告收入,利用餐館或廣告公司等賺錢企業的盈利補貼社區項目運作,善用義工參與補貼營運成本。
本來散居於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四國的庫爾德人處境本身就大有不同,但由於這些文化產業的跨國性質和善用數碼科技,反而增強了身處四國的庫爾德人和離散族群之間的國族意識,以及催生了更有活力的庫爾德文化產品,這些發展令當權者始料不及,亦印證了離散文化媒體的重要角色。
香港人離散社群在移居國參政剛剛起步,新建立的文化媒體產業仍未站穩腳步。庫爾德人飽受四國壓迫,經濟條件遠比香港人惡劣,卻仍能在艱苦環境中找到發展之道,香港人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嗎?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