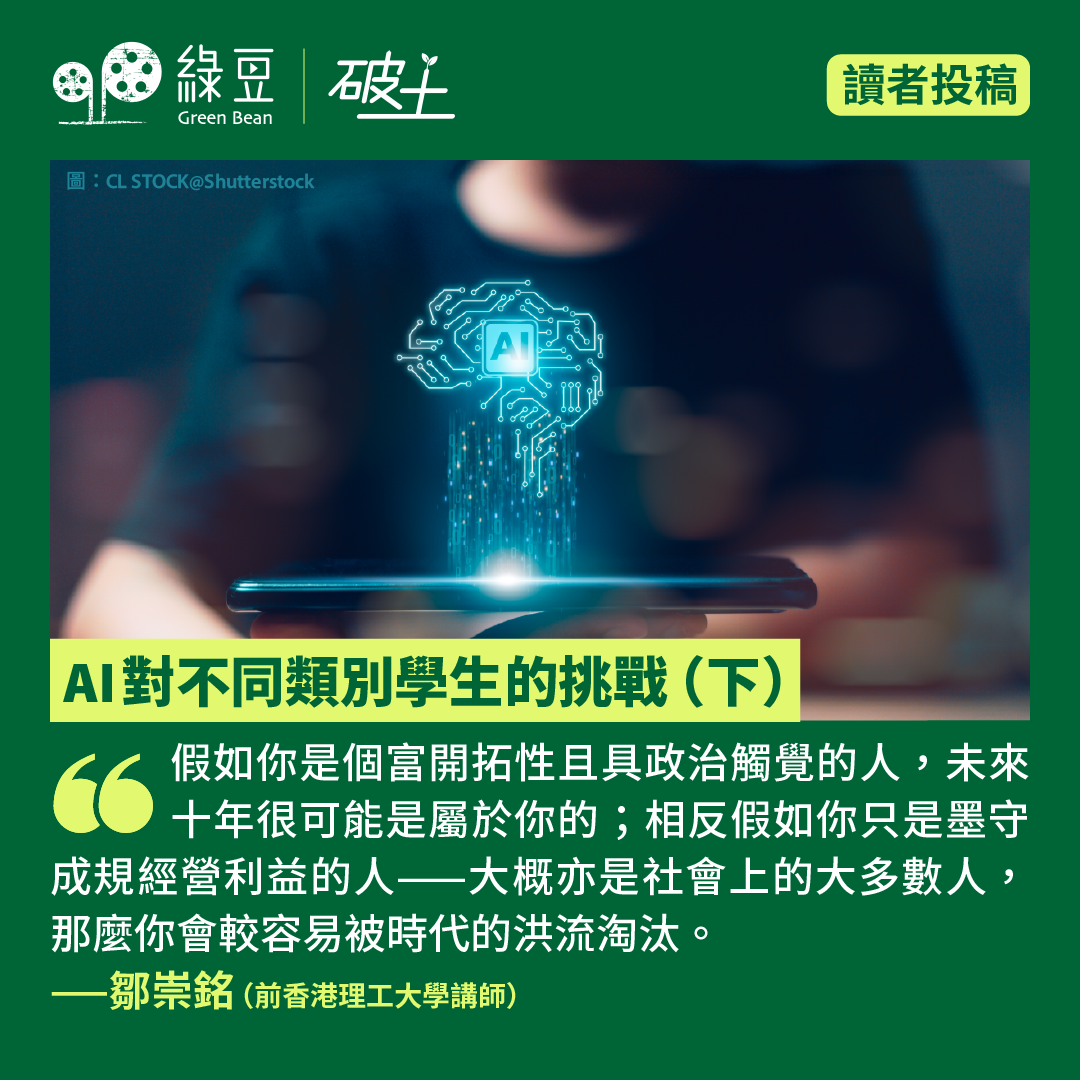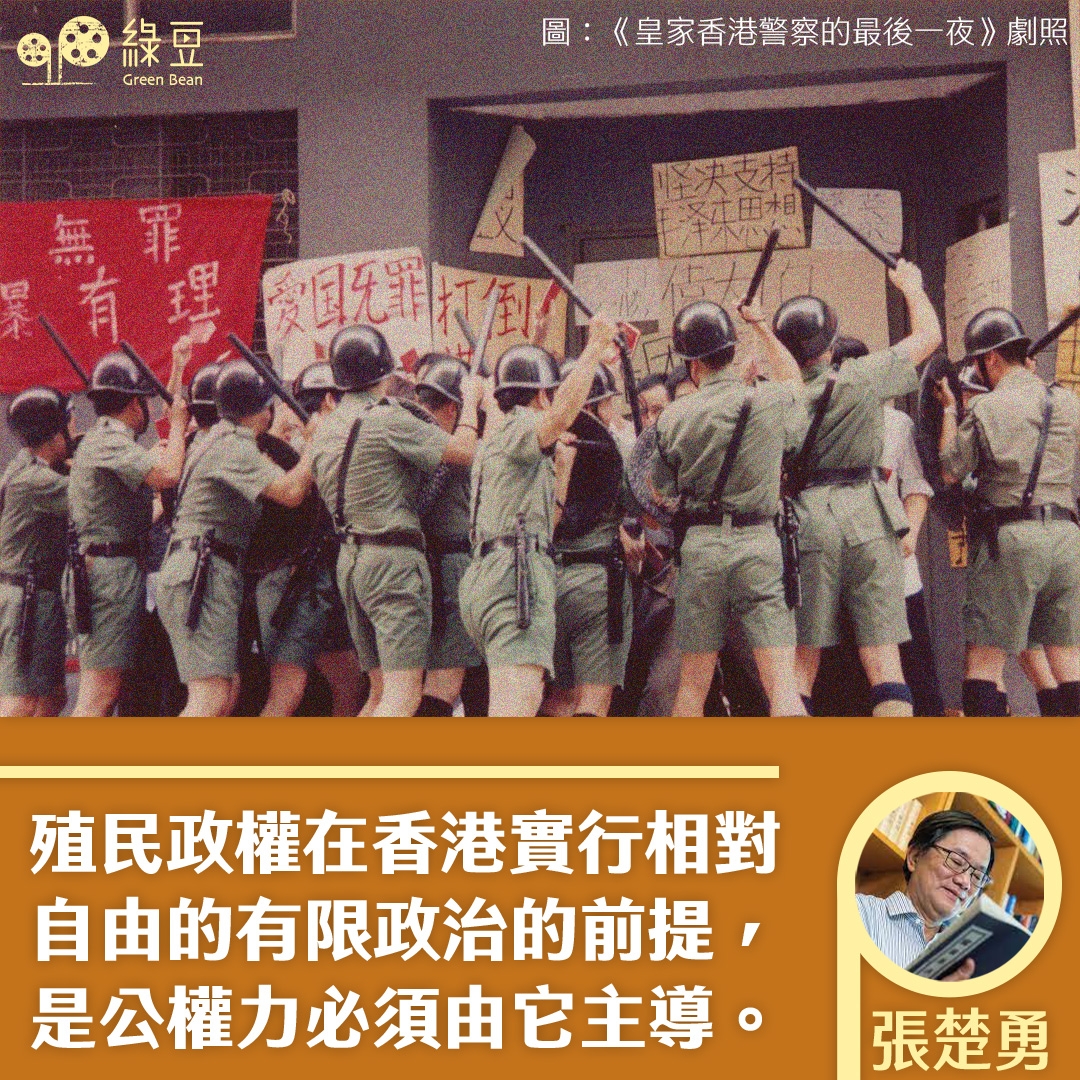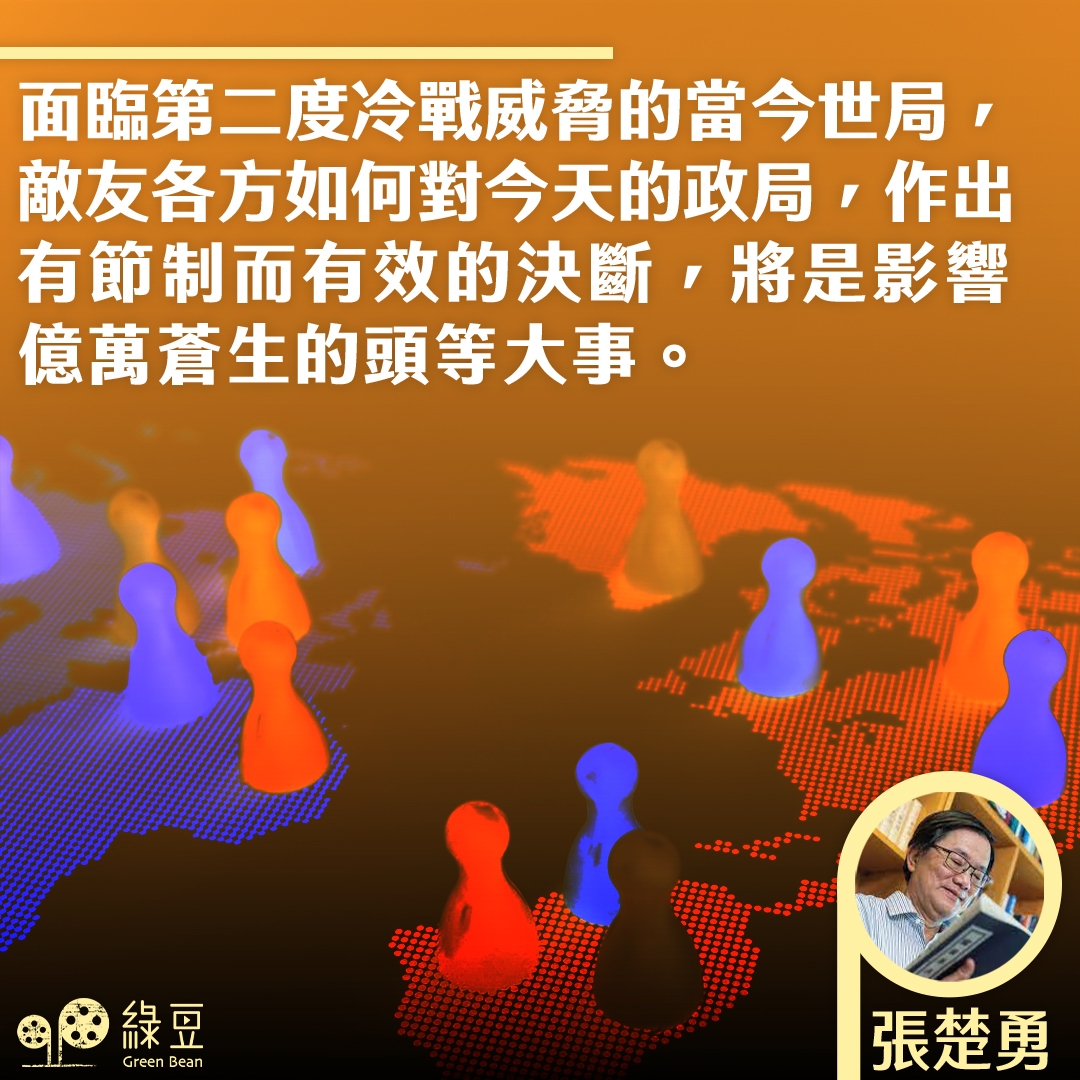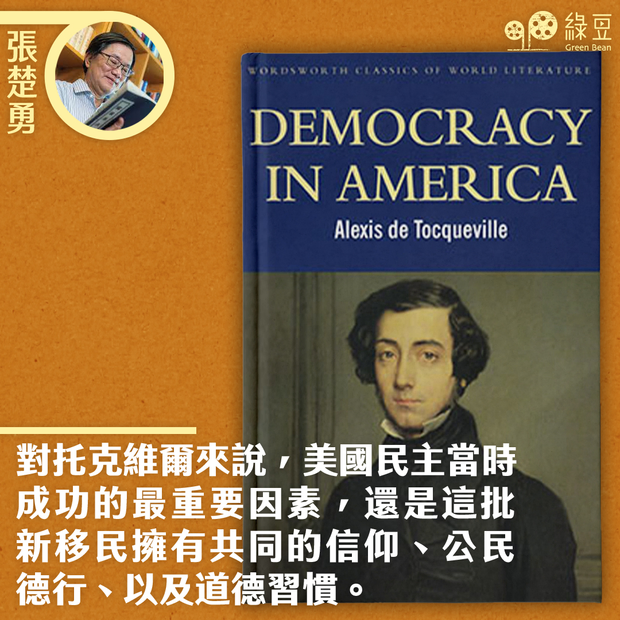讀鄂蘭思考現代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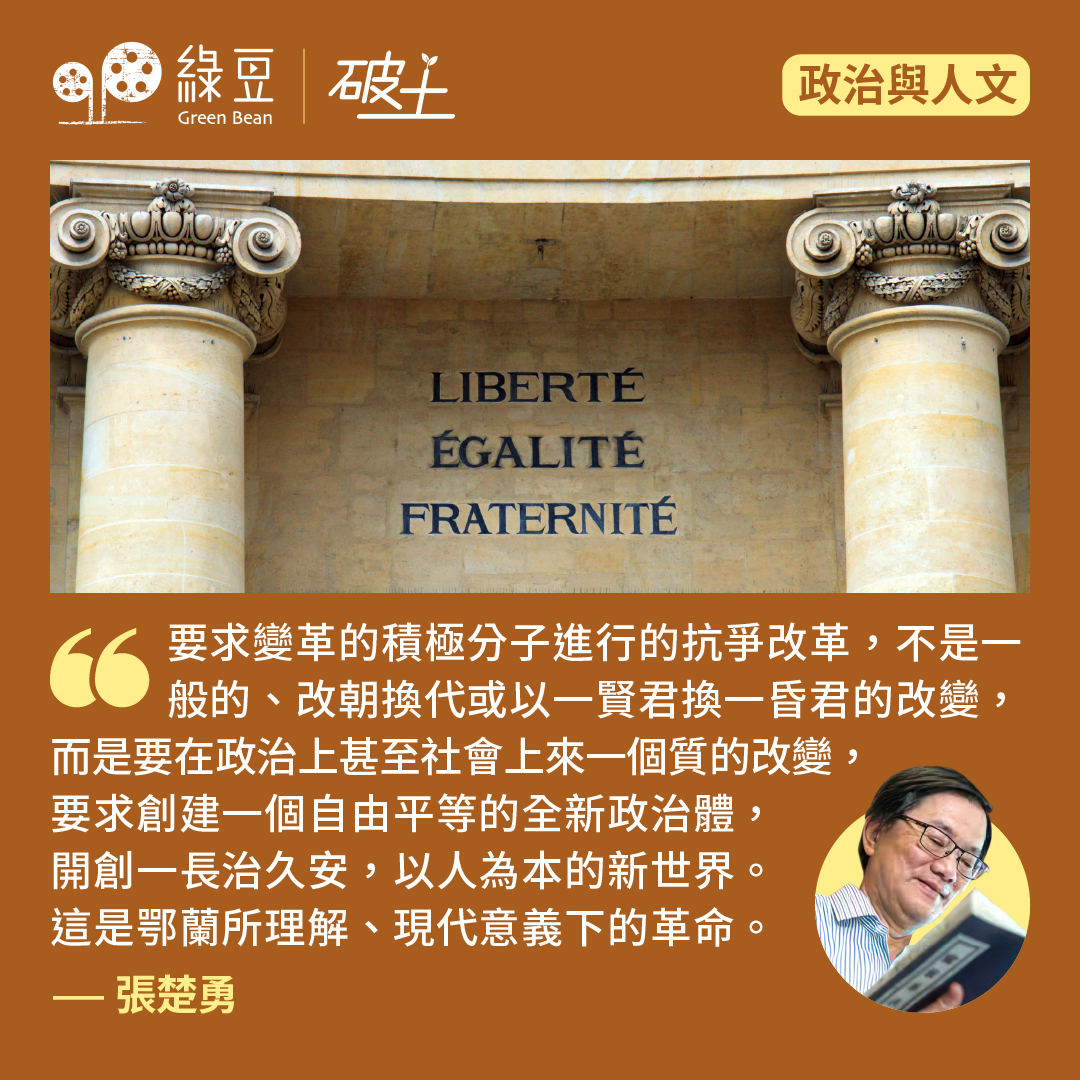
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當中,最能啟發我的其中一位。
她對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思考、對二戰後針對納粹戰犯審訊的分析、對權力/力量、權威、暴力的探究、對獨裁統治下個人的道德責任的反省等等,都是學富五車,深具原創洞見和鞭辟入裡的傑作。她那些充滿抽象哲理的著作,例如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的系統反思、對思考活動尋根問底的討論、以及對康德三大批判中的判斷 (judgment)批判的政治哲理含意的見解,都是一流的學問工夫。
兩本超越時空的著作
每當我面對困惑複雜的政治世局時,閱讀鄂蘭都能幫助我整理自己的思緒,並從中學習如何更好地思考政治。近日我重讀了她的《論革命》(On Revolution) 和 《共和國的危機》(Crises of the Republic)。這兩部著作雖然發表於上世紀60至70年代,但對當下世界激進政治的冒升等現象,以及對像美國這共和大國目前面對的危機,還是很有啟發性。我想,深刻的思辨,總是超越時空的。
在《論革命》一書中,鄂蘭分析了戰爭和革命的不同性質,辨解了革命為什麼不是傳統政治上的造反和起義。她也詳盡的比較了18世紀美國立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異同,並試圖拷問何解法國大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會變得愈演愈烈,不但吞噬了革命的「兒女」,更褪變成恐怖統治或暴政;相反,美國獨立戰爭既成功地發起抗英革命,並完成革命的初心,創建了自由分權的憲政共和國。
至於在《共和國的危機》一書,鄂蘭批評二戰後美國自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以來,好幾任總統逐步歪離憲法,在沒有國會授權下,在越南進行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鄂蘭指責歷屆聯邦政府的領袖,在長時間以來,通過一個蓋一個的系統謊言,為其在戰場上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說項。當政府機密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部分被傳媒揭發後,人們對政府及政客的信任產生了重大危機,恐怕政界中那習以為常的謊言政治,已對憲政共和體制造成嚴重的損害。
鄂蘭在書中又提到公民抗命這個在法治社會出現的政治抗爭現象,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抗民已不是個人的不服從問題。公開以非暴力方式的抗命者也不是一般的罪犯,而是有清楚政治或法律理念、有組織的重要少數派。這少數派對當時主導公權的民主多數持嚴重的不同意見,要通過公民抗命的方式來改變社會或政治決策。鄂蘭雖然同意公民抗命的做法與法律有抵觸,但卻是民主社會內防止多數人暴政的一種抗爭行動,與美國立國精神很有呼應的地方。
《共和國的危機》也分析到上世紀60年代席捲全球多處的美國學生運動。鄂蘭認為,大學生們是本著道德理念對社會既得利益建制和結構上的不公進行抗爭的。他們在運動中體會到政治力量(power)是通過參與者那共同挺身而出、以一呼百應式的公開集體行動所形成。這種公民參與體現出憲政共和國的活力,也反映了政治自由的保障來自於這種政治力量。
這政治力量擴展了公民參與的自由和公共政治空間,但卻並非是解決所有社會民生問題的萬應靈丹。學生運動隨後愈發產生暴力傾向,代表了運動逐步失去了一呼百應的自發政治力量,變得僵化和意識形態化。鄂蘭認為,暴力進場正反咉了政治力量的退場。學生其後試圖把追尋學問的校園變成是鬥爭場所,實際上是自毁長城的做法。
鄂蘭的現代政治觀
鄂蘭厲害之處,是她雖然是在探討過去或當下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她的分析背後所呈現的理據和觀念架構,在理論上卻很有普遍意義,因此很能加深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並可以以此來協助我們分析其他類似的政治經驗。
在這篇短文的餘下篇幅,我希望能把鄂蘭在論革命和論共和國的危機時背後所呈現的現代政治觀整理出來,以了解古今政治觀的不同,並探討現代政治的性質和假設,以及這種政治觀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表現如何,及其遇上的挑戰和困難。
革命的中心觀念
鄂蘭在討論「Revolution」這個政治現象時,她的一個重大的判斷,就是Revolution是個現代的現象。在現代之前(也就是17、18世紀之前) 「Revolution」是沒有的,其性質和造反以及起義(legitimate uprising)都不一樣。華文一般用「革命」來翻譯「Revolution」這個概念,但如果鄂蘭的說法是站得住腳的話,那麼,中國夏末商初的「成湯革命」儘管有說法認為是「順乎天,應乎人」的天命轉移,卻不是鄂蘭所說的「Revolution」。同理,孟子所說的誅一民賊或匹夫,未聞刺君也的對暴政的合理反抗,也不能算是現代政治意義下的革命。
那麽,現代政治意義下革命的現代性在哪裡呢?鄂蘭認為,革命的中心觀念是創建自由,即創建一個政治體,以保證有空間讓自由可以出現。
當然,在過去幾千年人類的政治文明史上,古希臘城邦中的公民在相當時間內是享有自由,並能在政治上自主地參與公共事務,平等地共同商議決定城邦的命運和決策。因此,古希臘人認為是他們把政治關係 (相對於當時流行的主奴關係為主的體制)帶進人類文明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說人是政治動物,正是指出,要能是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政治關係、有份自主地參與決定社群的公共命運的自由民,才是完完整整的人,並以此來區別於奴隸,以及沒有政治平等的關係、沒資格、機會或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和決策的人。
但是,現代的政治自由的假設和古希臘城邦的自由有一個關鍵性的分別,那就是前者在理念上是普世的,適用於每一個人的,後者卻只適用於城邦內的自由民。城邦內外的其他人,包括奴隸、外方人、婦女等都不適用。換言之,為推翻暴政或解放人民的現代革命並非只是為了奪取政權或改朝換代,而是為了創建一個保障所有公民的權利和政治自由的政治體。
鄂蘭認為,這種普世式的自由和政治平等關係觀念的出現,是建基於現代人逐漸發展出一種看法,認為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差序等级格局,並非是天理或神授的,更不是內在於人間世的秩序之內,而是可以和理應改變的。當然,這種改變的社會和歷史脈絡複雜漫長,在這裡不能細說。但其結果是,現代人愈來愈不接受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差序,甚至認為貧窮不應是必然存在,而是可以消除的。政治上也不應問出身或貴賤,人人理應有權利和自由參與,並相信通過人為的努力,是可以改變社會甚至世界。
上述的發展,自然是離不開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科學和技術的長促發展,逐步取代宗教和傳統的神聖權威,讓政治和道德社會事務愈趨世俗化的後果。當這種現代觀念變得愈來愈普遍之後,到了17、18世紀,當一些地方的政治社會條件因某些的矛盾或導防線引發大規模的改革訴求和運動後,這些要求變革的積極分子進行的抗爭改革,便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或以一賢君換一昏君的改變,而是要在政治上甚至社會上來一個質的改變,要求創建一個自由平等的全新政治體,尋求一個能夠解放人們政治社會上的枷鎖,開創一長治久安,以人為本的新世界。正是這樣的一種政治運動和抗爭,成為了鄂蘭所理解的、現代意義下的革命。
自然,政治理念上的假設和內涵,跟現實的政治實踐和經歷總有種種不同程度的差距。理念上指向的目標及其理解的性質,在現實政治中總有不少落差甚至脫軌變形。但自1688年英國出現的光榮革命、1776年美洲的建國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至中國的辛亥和共產革命等等,都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用上述的現代政治意義下的革命觀去理解。
社會如何避免專政?
這種現代的政治觀,自有其打動人心的深遠而普世的理想。但當所有人都有權參與政治和作出集體而強制性政策時,一旦群體中出現分歧甚至分裂時,那該如何解決這些經常出現的矛盾?如果盧梭(Rousseau)式的公意 (general will)難以形成,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分權足夠化解邦國内的根本政治矛盾嗎?假若兩者都不奏效,社會如何避免專政?
當神聖和傳統權威不再能支撑政治和社會上的差序格局,有什麼權威在這世俗化的現代性中能為憲政共和作出絕對的保證呢?現代政治上的絕對神聖不再,是否就是類近尼采(Nietzsche)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在,若不是一切都變成相對,是否一些人便得扮演上帝的神聖絕對角色?現代革命實踐中不時會出現造神運動,或者革命者在過程中反被革命吞噬,成為了現行反革命,是否反映了現代政治中的世俗化帶來的兩難?
當差序格局被認為是人的互動行為的結果後,是否代表了在理性和科技的協助下,人便可以通過政治行動隨心所欲的解決所有社會經濟民生上的差序?政治參與向全體民眾開放,自然是擴大了公共空間和加強了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但政治決策是集體強制性的行為,是否適合全方位地應用於解決所有社會經濟民生問題,以滿足不同的個人或社群的個別需要,委實是個十分存疑的問題。
我不敢說我上述對鄂蘭思想背後勾畫出的現代政治觀念的理解一定是準確,這觀念期盼的理想及其在理念中和實踐上碰到的挑戰和困難,肯定比我上文所羅列的要多。但通過閱讀鄂蘭的著作,我想我們既加深了對現代政治認識之餘,也對人類在人間世經歷到的機遇和困境,有了不同層次的體會。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