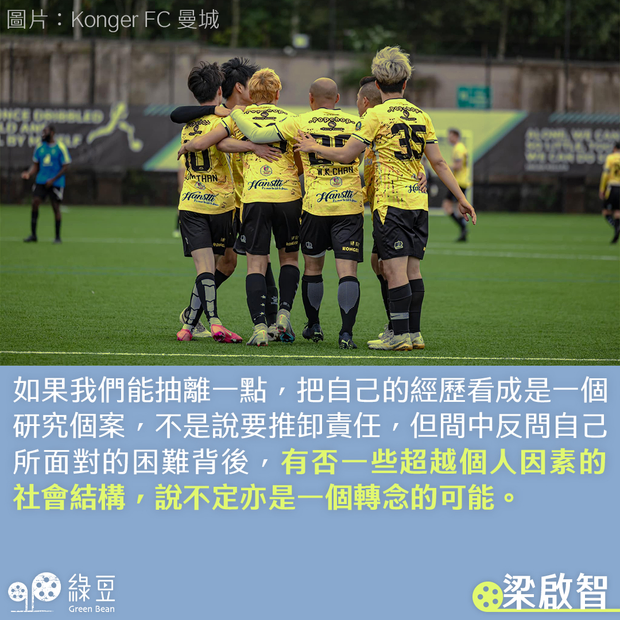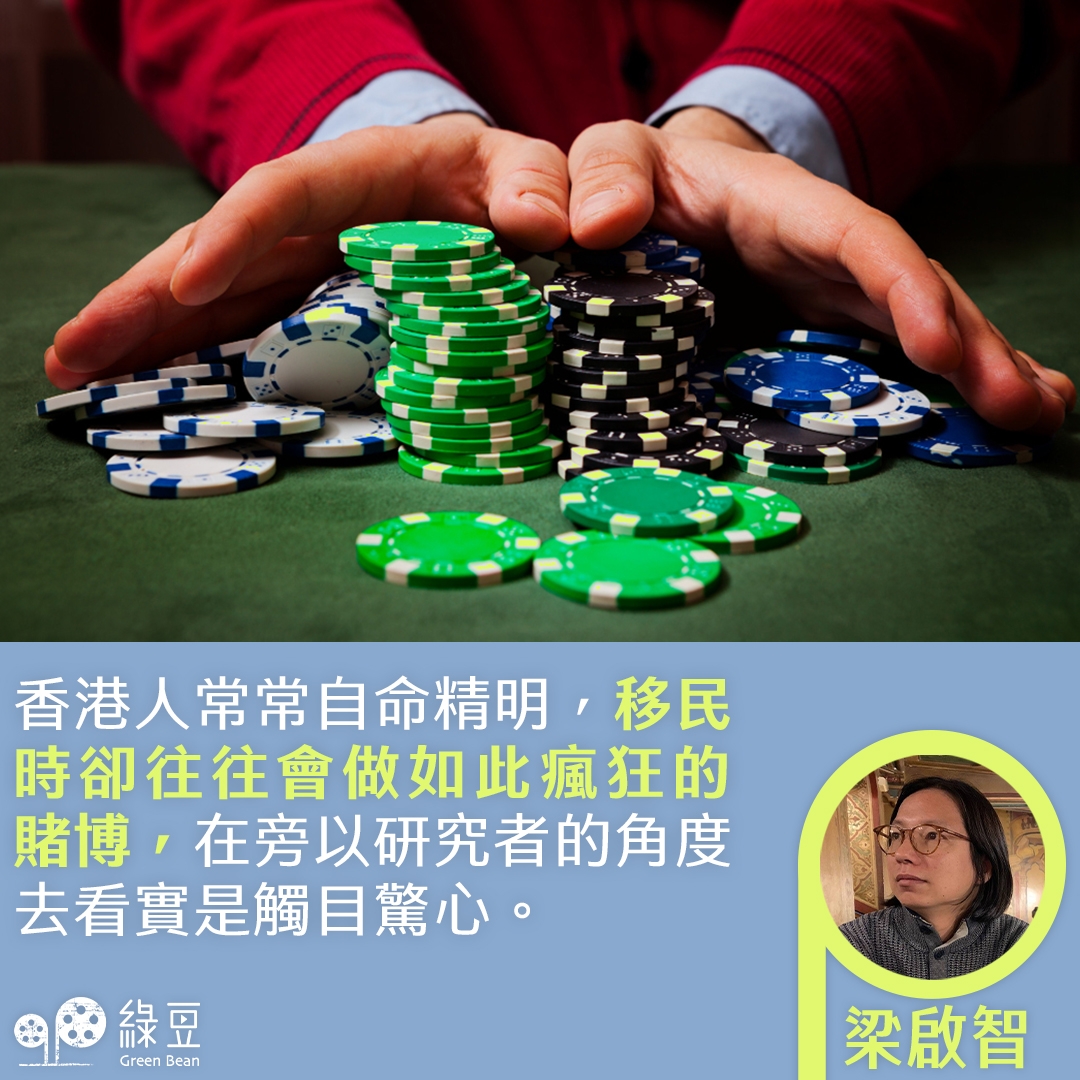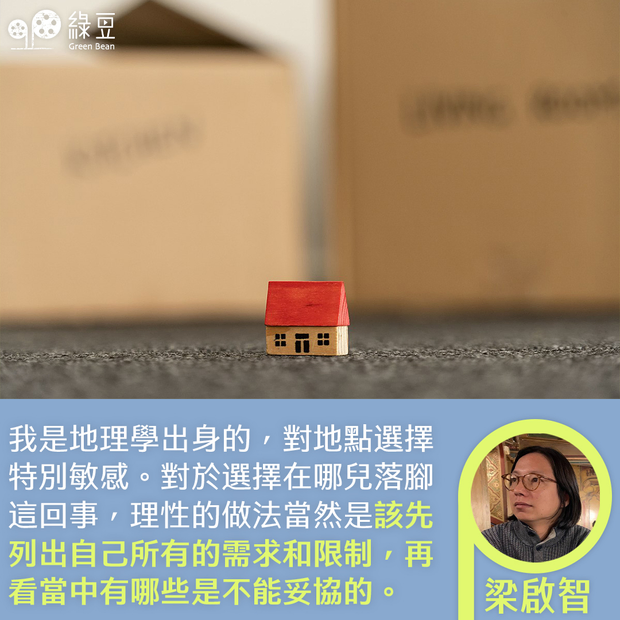國安疑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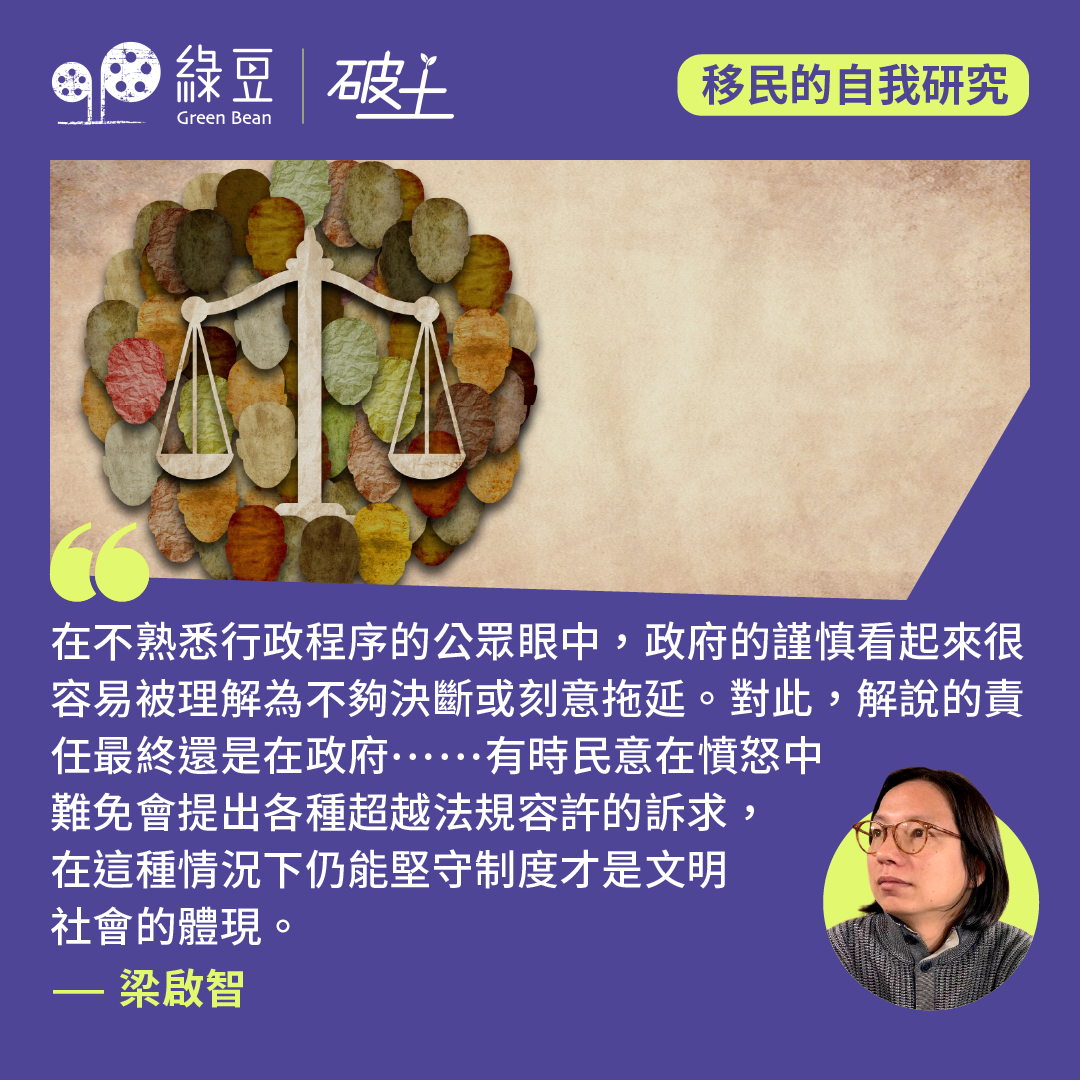
近日台灣移民署因應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鼓吹武力統一,取消其居留許可並限令離境。這宗新聞對許多港人移民來說大概會覺得是事不關己,如果不是幸災樂禍的話。然而細想之下,港人移民其實也是時候想想如何應對針對移民社群的疑慮;在台港人固然要想,到其他地方的亦不見得可以免疫。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沒有限制,危害社會的言論在各地都會被明文禁止。不過言論自由的界線,和許多社會規範一樣,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移民在此的第一重困難,自然是對紅線的掌握。這點對港人移民同樣適用。有些港人在香港的時候自恃是多數,習慣各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不自知,移民到了因為經歷過種族撕裂而對相關言論特別敏感的社會,如果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套然後聲稱當地的要求是「玻璃心」,則未免沒有入鄉隨俗。見到一些港人移民在歐美社會因為歧視言論而遇到麻煩,還要反過來指責當地是「左膠國家」,只好慶幸不是人人會讀中文,否則惹當地人討厭的程度只怕和上述的台灣案例相距不遠。
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
當然,台灣的案例還有其特殊性:移民的原居地政權或移民所代表的群體,和當地的主流社會衝突,以致移民本身被視為潛在的疑慮對象。在台港人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感受至深。2019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過許多「撐香港」的言論,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運作的介入日深,台灣政府難以再把香港和中國大陸作差別對待,港人移台無論是政策或執行上亦出現不少波折。
成為被疑慮的對象,過程不一定很有道理,要作辯解往往亦不容易。早兩年有不少港人因為「國安疑慮」而定居台灣遭拒,其中不少個案的解說相當無厘頭,例如在公立大學短暫工作也成為拒簽原因;雖然這些案例後來被監察院查明,原來只是移民署「為爭訟便利」而沒有詳細說明所有原因,例如投資移民本身的個案問題,但在港人社群中帶來的誤解和傷害已難挽回。
面對衝突,移民本身固然應當尊重當地社會的紅線,凡事有所分寸。與此同時,政府若要把紅線變成政策,主管機關的解釋必須有理有節,不作過度干預。近日台灣的案例得到輿論普遍認同,皆因台灣政府這次劃出的紅線十分清晰:談統談獨都可以,但不能「鼓吹戰爭」,並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為此原則背書。換句話說,政府表明不是要針對個別移民社群,也不是要針對思想,而是「鼓吹戰爭」此一特定行為,也就是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界線普遍輿論認為適度合理,相關案例在此也是證據確鑿,沒有冤枉好人。
反過來說,當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不一,被針對者難免會感到不服氣。例如當移台港人發現自己被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卻見到退休軍官將領能到中國大陸出席統戰活動,不免懷疑所謂對國安疑慮的重視到底是真是假。相對來說,早前賴清德總統提出檢討港人移台政策,是放在十七條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因應策略中提出,港人移民並非唯一針對的對象,就未有引起相關政策研究者的普遍反彈。
堅守制度才是文明社會的體現
最怕的情況,是政府以「危害社會安定」或「國家安全」為由趕絕移民,執行過程中橫衝直撞不講程序不問法治,只為贏取民粹狂熱的掌聲,後果就會十分嚴重。在太平洋的另一面,新任美國政府大張旗鼓遣返移民,最近就有前往中美洲的航班在法官下令掉頭後仍然拒絕返航,引發輿論譁然。無論你如何看待移民問題,認為該從寬還是從緊,最後總得依法辦事,不能執法者聲稱在執法卻本身也不守法。政府不認同法院決定,可以上訴,卻不可以不執行。很不幸,這次美國政府沒有承認錯誤,總統特朗普卻反過來攻擊法官,憲制危機進一步加深。
政府做事和個人做事不同,一定要所有細節都準備充分才可以行動;畢竟萬一動起來後才發現錯漏,賠上公信力的後果無可估量。政府疏忽可引發的社會危害,有時恐怕比本身要解決的問題還要大。最起碼,商人不會想在一個不可預測的政策環境下投資,而經濟活動可是各種社會生活之本。港人移民本身也要面對各種入境政策不確定性,不可能以為能在任意莽為的政府面前獨善其身。
反過來,在不熟悉行政程序的公眾眼中,政府的謹慎看起來很容易被理解為不夠決斷或刻意拖延。對此,解說的責任最終還是在政府,畢竟公眾不可能都熟悉所有法律條文和原則。有時民意在憤怒中難免會提出各種超越法規容許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堅守制度才是文明社會的體現。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