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作為生命之反省:從生死愛欲到幸福烏托邦 (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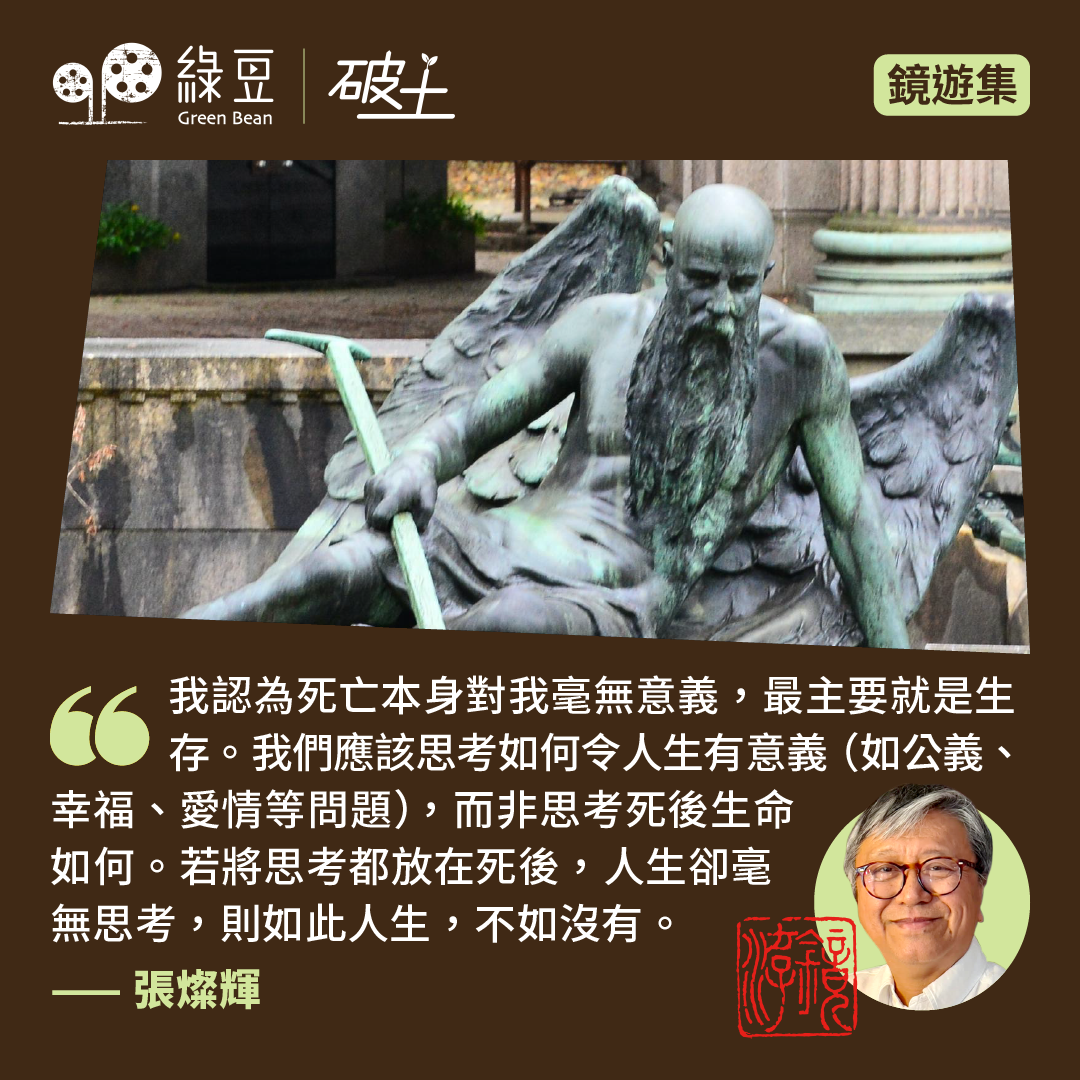
哲學與人生問題
2021年,我曾出版《為人之學:人文、哲學與通識教育》一書,當中講述我如何看待哲學教育及通識教育。我從哲學與生命角度切入,發現通識中心甚少有課程觸及這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以哲學思辨生命,並非單純講述自身故事,而是如何運用學問,探討及解決自身所面對人生問題。必須注意,運用學問並不代表你必須讀通康德或亞里士多德等人博大精深的學術巨著,你大可完全不明白他們的學術思想,不過卻要學習他們如何看待生命的方式。出於以上想法,因此將生命哲學放入通識教育範疇,作為實踐自身教育理念的基石。
正如上述,我們要向眾哲學家學習,如何看待生命。但他們所講的問題絕非具體問題,而是若干人類必然會遇到的共同問題,並尋求普遍意義的解決方法。就我自身能力所及,將眾多人類必會遇到的共同問題中的五種,納入講學範圍,後來遂發展成「死亡與不朽」、「愛情哲學」、「性與文化」、「幸福論」、以及「烏托邦思想」五門科目。以下我逐一講解這些科目的內容與意義。
五個人生共同問題
死亡與不朽,乃人生最重要、亦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基督教徒強調,信耶穌,得永生。然而,何謂永生?何謂不朽?柏拉圖講靈魂不朽(immortality of the soul)與耶穌所謂肉身復活(resurrection of the body)有何分別?凡此種種,當我們面對生命與死亡時,實無可避免,必須處理。
人生另一主要問題就是愛情哲學。試問誰不渴望愛情?然而,何謂愛?何謂情?將「愛」與「情」化作人生經驗,該如何處理?表面上大家都在談情說愛,但若問他們何謂愛情,被問者大抵皆無言以對。華夏文明本無「我愛你」的概念,在座各位可否於1900年前任何一部古籍中覓得此三字?起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找到。為何在我們的傳統中,並沒有任何概念可對應「I Love You」等外語?為何華人都不會說我愛你?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西方人與東方人認知「愛」這個概念完全不同。佛家視「愛」與「貪」「欲」「渴」等為同義詞,為十二因緣之八。呂洞賓稱 「愛」是「色身日益長成,貪淫等心已開,而生種種愛欲」,但「尚未實愛欲之境也」。由於愛欲「尚未實」(填滿),故需要拿取、爭取、求取,亦即十二因緣之九,「取」。「取」是「色身強壯,愛欲日盛,而馳求恣取色聲香味觸等以實愛欲之境也」。由此可見,佛家的「愛」,與西方人「我愛你」之「愛」的內涵完全不同。華夏文明則以「情」代「愛」,例如我與你有情。以「情」代「愛」其實頗為奇怪,因為「情」並非動詞。然則,我們又應如何理解這個問題,以及上述種種問題?為此,愛情哲學這門課得以確立。愛情問題,西方人談得極多,而以雅正中文寫作者則似乎甚少論及,即使近數十年亦然。
與「愛」「情」必然相連者,就是性事 (sexuality)。談及「性」,世人常嗤之以鼻,避而不談。然而,誰與「性」無關?在座每位聽眾,包括本人,誰非誕生自「性」之中?如無父母性行為則無我們,此豈非自然之理?出生後,又每個人都會有兩種「性」,一則性別,二則性向。因此,我們每個存在都是「性」的存在,所謂「sexuality」,絕非單純與性行為有關,其內涵比流俗所理解的複雜深奧得多。「性」與文化也有莫大關係,這事實也常為世人忽略。我認為大家必須理解此等問題,故開設性與文化這門課。
以上所談種種問題,死亡、不朽、愛情、性,凡此種種,都可歸結為「欲」與「不欲」,而我們所欲者,往往又與幸福及快樂相連。問題是,何謂幸福?
何謂快樂?正如愛情,幸福快樂似乎很易理解,但當我們果真深究時,被問者大抵亦是無辭以對,或說來模糊不清。幸福問題涉及烏托邦問題,我將在別處另行詳言,在此我只簡略交待。
亞里士多德著述極多,當中兩部最重要的即《尼各馬可倫理學》(Ethica Nicomachea)與《政治學》(Politica)。前者主要為幸福下定義,講述我們如何達到「心靈豐富發展」(eudaimonia),從而獲得幸福。除自身心靈發展外,亞里士多德亦指出,社會環境良劣亦構成每個人是否幸福的主要條件,相關探討則體現於《政治學》裡。這種思想與我們華夏文明,尤其道家一派思想,有所不同。譬如莊子認為,所謂逍遙,就是與他人毫無關係,獨善其身,換言之,逍遙建基於自在之上。正由於此一異同,故我斷言,古華夏並無烏托邦思想,因為烏托邦是必須將個人幸福置於社會條件內。
環環相扣
以上種種問題,我認為乃人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誰能離開生死愛欲?誰不希望幸福?故圍繞以上主題而生出這幾門課。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獨立的問題,更不是單純哲學問題,而是環環相扣。譬如愛情問題,它牽涉到東西方文化異同的比較,且必須透過跨學科研究,從不同角度切入,如文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能捕捉其全貌。當然,追根究柢,愛情問題最終仍回歸於人類存在問題。因此,探討這些原本就是來自實際人生的問題,即使要以學科方式處理,都不能以尋常學科看待。
人生問題不是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問題,人生問題就是人自身存在的問題。人生或生命乃一整體,並非如學科般被切割成零碎狀態,因此,即使是以學科方式探討人生問題,也不能強行將其歸於某學科下,以單一角度觀察,否則不可能掌握到人生問題。現代大學教育太習慣將所有學問變成各式專門學科,但這種情況必須在人生問題面前終止,人生問題絕不能以如此違反人性與生命的方法探討。以處理生命問題為目標,用學科方式與一眾學生共同探討,思考如何將其變成應用哲學,在中文大學可算是一大嘗試。
儘管我在開設這幾門課的方法上,有異於現代大學教育慣常做法,但仍遵守若干基本原則。譬如,我們課堂上的探討仍需要學術理論支持,而非無根漫談。要以學術方式探討,則第一步依然離不開讀書。為此,我寫了好幾本書,如針對生死問題,則有《悟死共生:死亡之哲學反思》一書。
有生便有死
如前面所說,我的哲學從死亡開始。死亡本身是否荒謬(absurd)?如果死亡本身是荒謬,它如何被思考?應如何看待死亡?死生有何分別?凡此種種,我們從自身處境出發,共同思索探討。香港人很奇怪,極懼怕死亡,但凡與死有關,莫不忌諱。若有人死,他們會婉轉用「走」、「去」、「逝」等代替「死」,連與「死」諧音的「四」亦不能講。若大家到過香港,仔細觀察會發覺頗多建築物都沒有第「四」層樓,尤其十四樓,因為「十四」在廣東話中,與「實死」諧音,意謂一定會死亡。身邊人都諱言死,我卻不禁問:既然死亡絕不可能逃避,為何我們要害怕與諱言?難道你們希望不死嗎?破除害怕死亡的迷思後,我們便必須追問,為何會有死亡?死亡,並非因為絕症或不健康,而是基於極簡單的理由:有生便有死。
這個看法我是從海德格所著《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一書習得。他指出,切勿以為死亡自外於生命,事實上,生命即包含死亡,每個存在本身就已有死亡在內。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但在海德格而言,卻是「未知死,焉知生。」正好與孔子相反。由這種生中有死的觀念裡,我們便可以知道,死亡並非人生盡頭,而就是人生一部分。若持此觀念,則我們自可坦然面對死亡在任何時刻突然來臨,以及死亡必然會來臨。正如上述,「何時應該死」這個問題並不成立,因為海德格說,我們出生當刻就已經可以死去,生就是死的根本原因,無生則無死。
當然,我知道,所有宗教都輕視此看法,因為他們主張死亡並非盡頭,而是另一生命之始,基督教如是,佛教如是。但我們不妨想像,如生命是終而復始,死後轉生,則生命將成何種狀態?如果真有永生與天堂,永生所寓居的天堂又是何等光景?大家若讀過文藝復興巨擘但丁(Dante Alighieri)所著《神曲》(Divina Commedia),其描述的地獄、煉獄、天堂,則大概可知基督教的天堂是何種模樣。簡言之,天堂光亮無比,所有人都不需要上班、吃飯、 睡覺,只須終日高唱聖詩,以歌頌上帝,捨此以外,別無其他。天堂完全由永生這個理念撐起,實我們人類生命全部投射的結果。各宗教均宣稱死後世界如何,單憑此一事實,即可知死後世界不過是死前世界所構想而來。若果真有永生與輪迴,我們根本不需要處理生死問題,反正死後自然會於別處再生。
海德格分析死亡時,明確表示他反對基督教義所主張的永生。因為人類若能永生,則對於生命本身,又該如何面對及描述?故此我說悟死共生,生命就是我們唯一能理解之事物。諱言死亡者,往往認為談論死亡乃屬悲觀之舉,但我認為,諱言死亡,妄想永生者,才是真正悲觀,而且無知。人不可能永生。
藉死亡反省人生
有生所以有死,因此我們思考死亡,其實是反省人生。無人知道死為何物,狀態如何,它只是生的極限(ultimate limited)。伊比鳩魯嘗言,當生之時,仍然未死;當死之後,已無意義。我們不能知道何謂死,實由於所謂知道,乃預設我們有身體,而這個身體有感覺。如果沒有感覺,則所談皆虛,毫無意義,故說死後無意義。由於死後無意義,所以我們思考死亡問題的意義不在於死亡,而在生命,在人生,在反省生命與人生。若你明白何謂「藉思考死亡以反省人生」,則自然會明白,人類所以怕死並非懼怕死亡本身,而在於不知死亡為何狀態,死後光景如何,是否會受懲罰,甚至愁子憂孫,擔心他們貧餒飢寒。總言之,就絕非死亡本身。

哲學給我機會將死亡問題逐漸思考清楚,而我這個思考,始自柏拉圖。眾所周知,化死亡為哲學問題的第一人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在其申辯中明言,死亡不過兩個可能:第一,猶如無夢睡覺般;第二,如前往他處(註一)。若是前者,實在不錯;若是後者則更妙。若我死後可前往他處,而該處聚滿荷馬等古希臘先賢及我諸位已逝親朋,可與他們日夕相對,酣飲暢談,何其快哉。如果真有此地我也想去。問題是,我不認為有這個地方,亦不敢奢求。基於以上想法,我認為死亡本身對我毫無意義,最主要就是生存。我們應該思考如何令人生有意義(如公義、幸福、愛情等問題),而非思考死後生命如何。若將思考都放在死後,人生卻毫無思考,則如此人生,不如沒有。
最後,我再次強調,死亡本身無意義,死亡而有意義者,在於藉思考死亡以反省人生。
註一 :
柏拉圖在《自辯》(Apology)一文有詳細記載,見該書40C-41C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