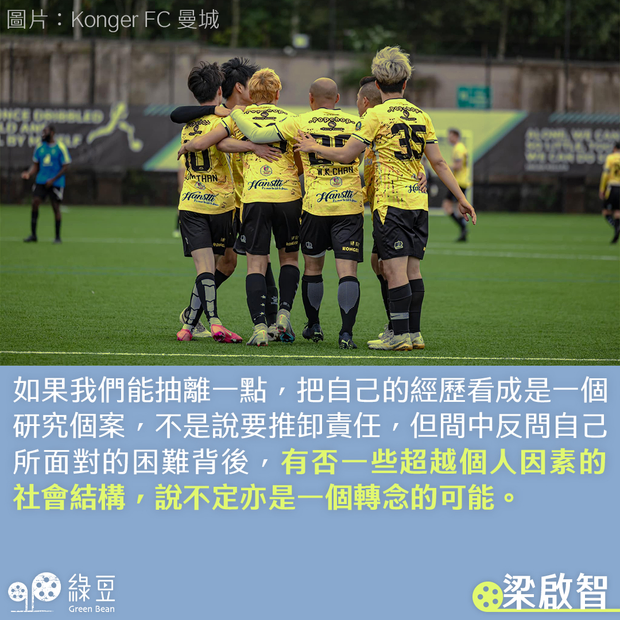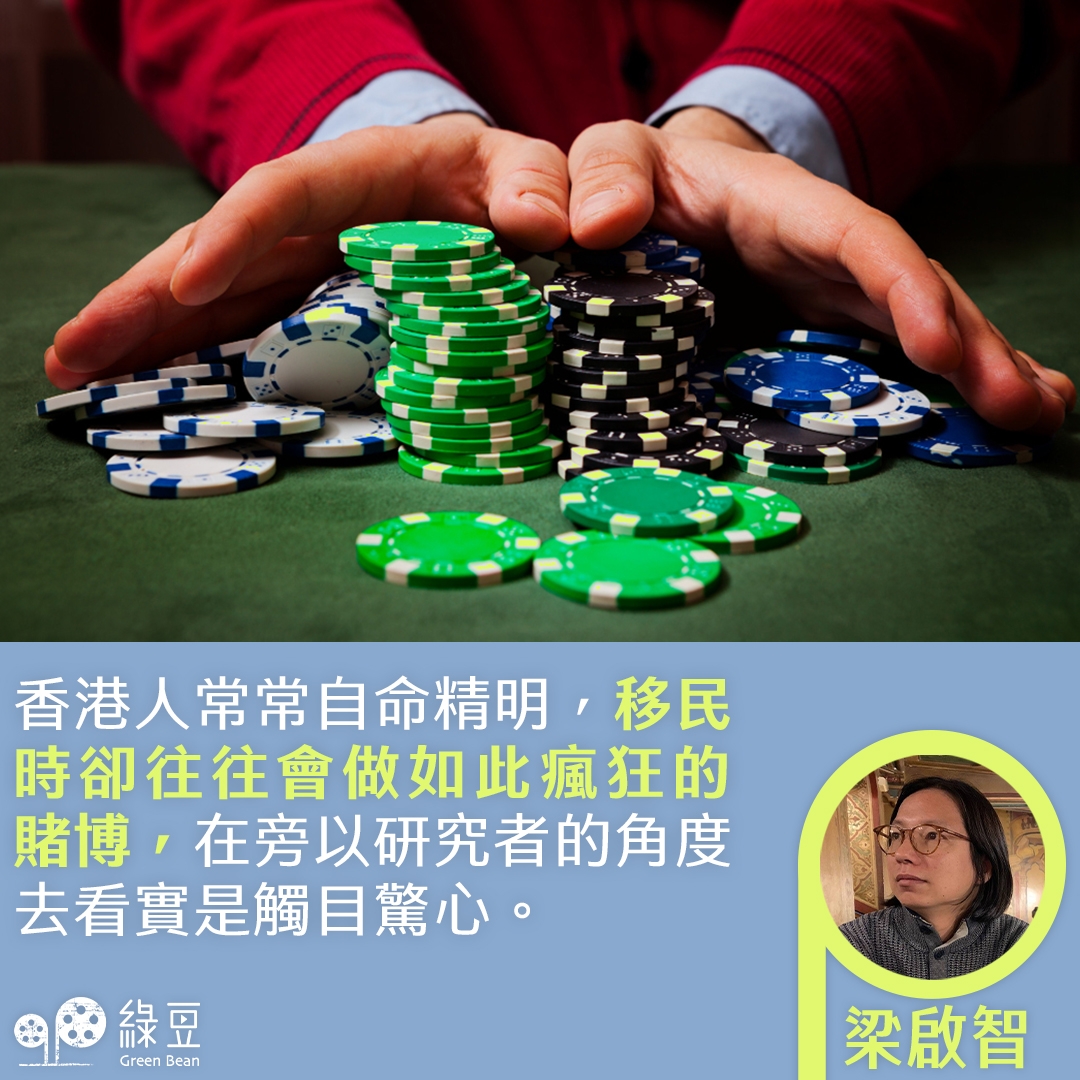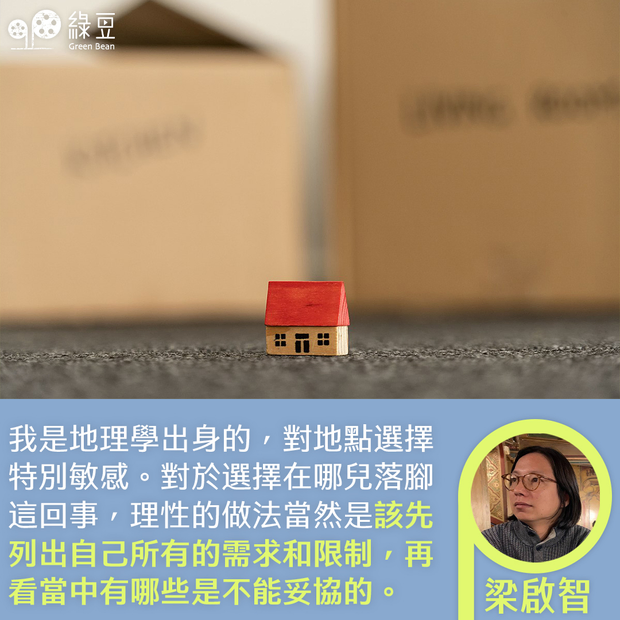香港的死亡與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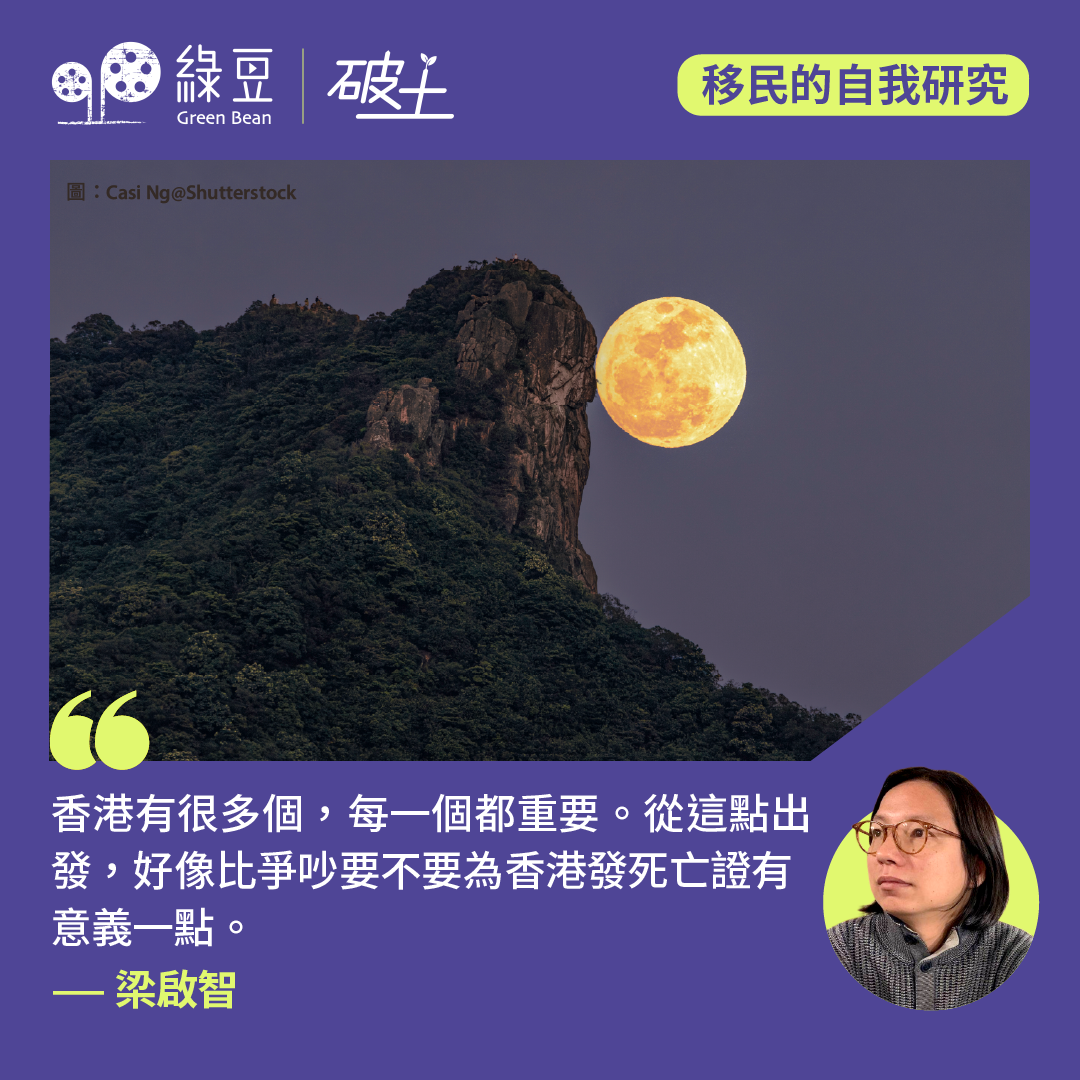
每隔一段時間,離散港人社群好像都會爭吵一次「香港已死」這題目。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覺得這議題重要,畢竟它關係到社群本身的角色,例如各種對承傳香港文化和價值的想像。不過要討論香港到底是否已死,又或離散港人社群到底要承傳什麼,難免必先回答香港本身是或不是什麼。然而回頭再想,關於香港本質的爭議在離散港人這概念出現之前已經有過不止一次。如果把每次爭論都算進去,香港可能已經「死」了很多次,又或者已經輪迴轉世了很多次。
離散港人如持有「香港已死」的觀點,後面不少都預設了香港必然要有某些內容或特質,這個香港才有「資格」被稱為「香港」,否則就是虛有其表,行屍走肉。同一邏輯下,也聽過不少離散港人聲稱「要離開香港才能當香港人」,後面也是假設了香港不止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實踐。
「什麼是香港」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香港是什麼」向來是一條難解的問題,並在九七前後出現過好幾波的爭論。這些爭論往往是在香港面對挑戰的時刻出現,因為大家很擔心香港正在消失,所以覺得很有需要定義清楚「什麼是香港」,讓我們得以釐清要捍衛的是什麼,要排除的又是什麼。
例如2010年以來的本土思潮,當中有一些比較教條主義的訴求,曾經聲稱只有在香港出生的(甚至是只有在九七前的香港出生的)人方可被稱為是香港人。當然,這說法很快受到質疑,因為不少著名的本土思潮領袖,本身也是九七後在中國大陸出身,後來才移居到香港。
於是又有另一種聲音認為香港代表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社會價值,例如法治精神和公民參與,要認同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才算是香港人。問題又來了:以前的選舉有最少四成選民會投票給不太捍衛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的政黨,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在香港的歷史也不是那麼長,不少最少要在1970年代之後才普及,那難道在此之前的香港就不是香港?更別說在「虛擬自由主義」的審視下,這些價值恐怕本來都甚為無根和脆弱,以此作為香港價值的標準是否有點兒戲?
過往的論述
類似的問題,我們可以一直回頭數。在利東街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一系列保育運動,同樣是追尋某種意義下的香港特色。但當香港的意義被本質化為某種建築風格以至飲食習慣,說蛋撻奶茶就是香港,就連組織這些抗爭運動的組織者也不同意。在此之前又有2004年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出自由民主等多項原則;但正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講自由民主,類似的價值宣言往往只變成各自解讀。
繼續追上去,還有九七前一系列來自「夾縫論」和「北進殖民主義」的反省。當時香港正處於九七前自大自卑混合體的狂熱狀態,這邊要移民那邊又唱《我至叻》。當時的學術界同樣對各種意圖定義香港的嘗試提出質疑,其中不少和「香港已死」相關的疑問經歷多次輪迴後仍然歷久不衰。例如每當有人鼓吹香港人一定要懂廣東話,就會有人反問廣東話在香港的主流地位其實在香港歷史當中出現得並不見得很早,而且也靠排擠其他本土語言而達成。九七前的案例就有匯豐銀行的電視廣告通過漁民講述「香港故事」,研究者發現廣告公司本來想找真正的漁民配音,卻發現水上人演繹的對白根本普羅大眾都聽不懂。何謂「正宗」從來是個神話。
香港從來多元善變
來到今天,我們又要在「香港已死」之下翻炒一次「何謂香港」這條問題。我並不是說這問題因為問過所以就不用再問,畢竟每次的回答都有其時代背景。不過回顧這條問題的反覆再現,我想我們還是必須記得:香港從來多元善變。
而這點對離散港人社群又有兩重意義。
第一,離散港人社群或對「何謂香港」有自己的執着,但永遠不能取代香港本體。我們仍然有七百萬人活在一個叫香港的地方,他們仍在書寫香港故事。離散港人社群或可協助承載一些暫時在香港境內無法承載的人和事,但我們不應該輕易界定改變了的那個香港就不再是香港,只有離散港人社群承載的那個才是「真香港」。
第二,離散港人社群自己也有自己的挑戰,留港者的香港在改變中的同時,離散者的社群同樣也在改變中,兩者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恆靜止的,過於強調保存「舊香港」會窒礙離散社群自身的發展。
香港有很多個,每一個都重要。從這點出發,好像比爭吵要不要為香港發死亡證有意義一點。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