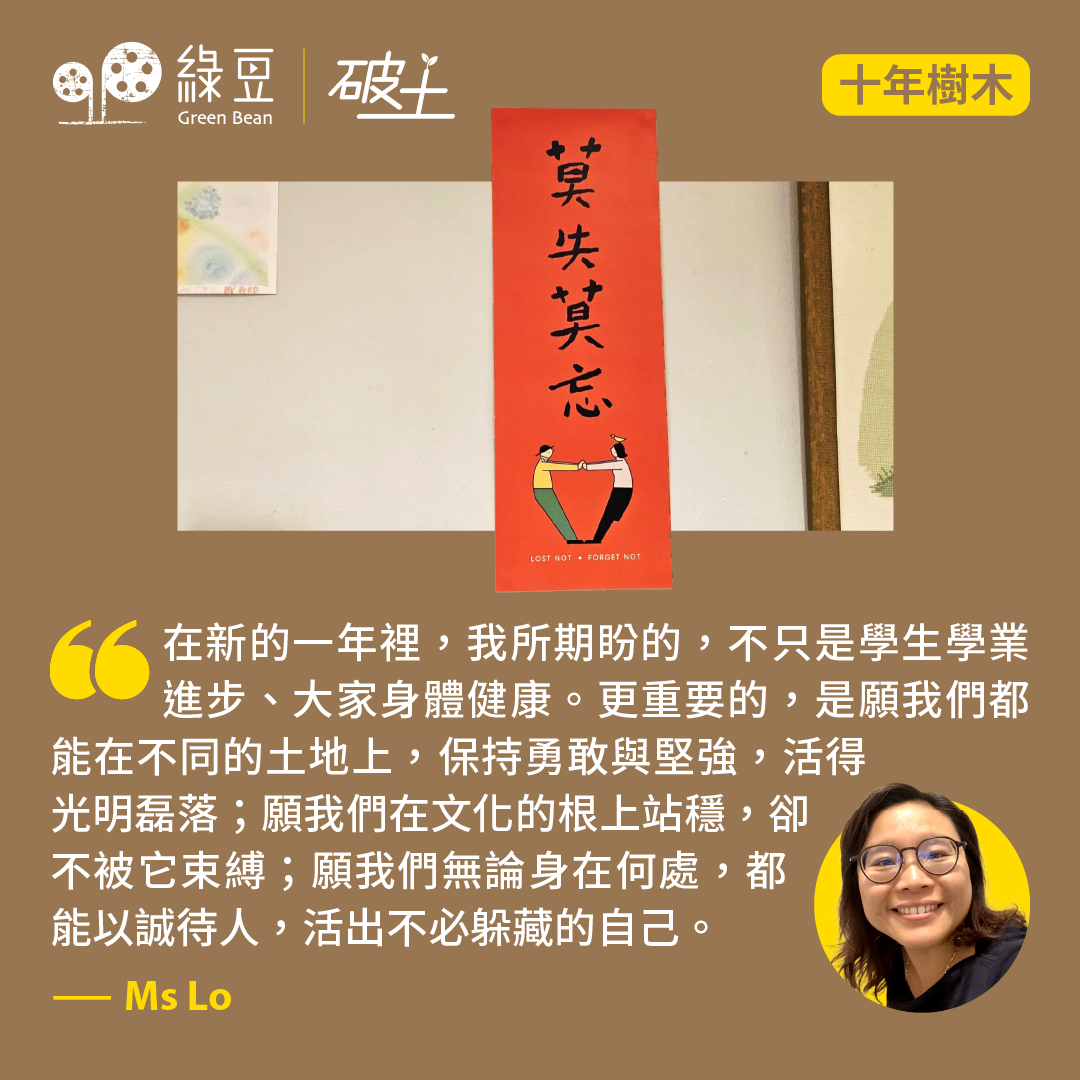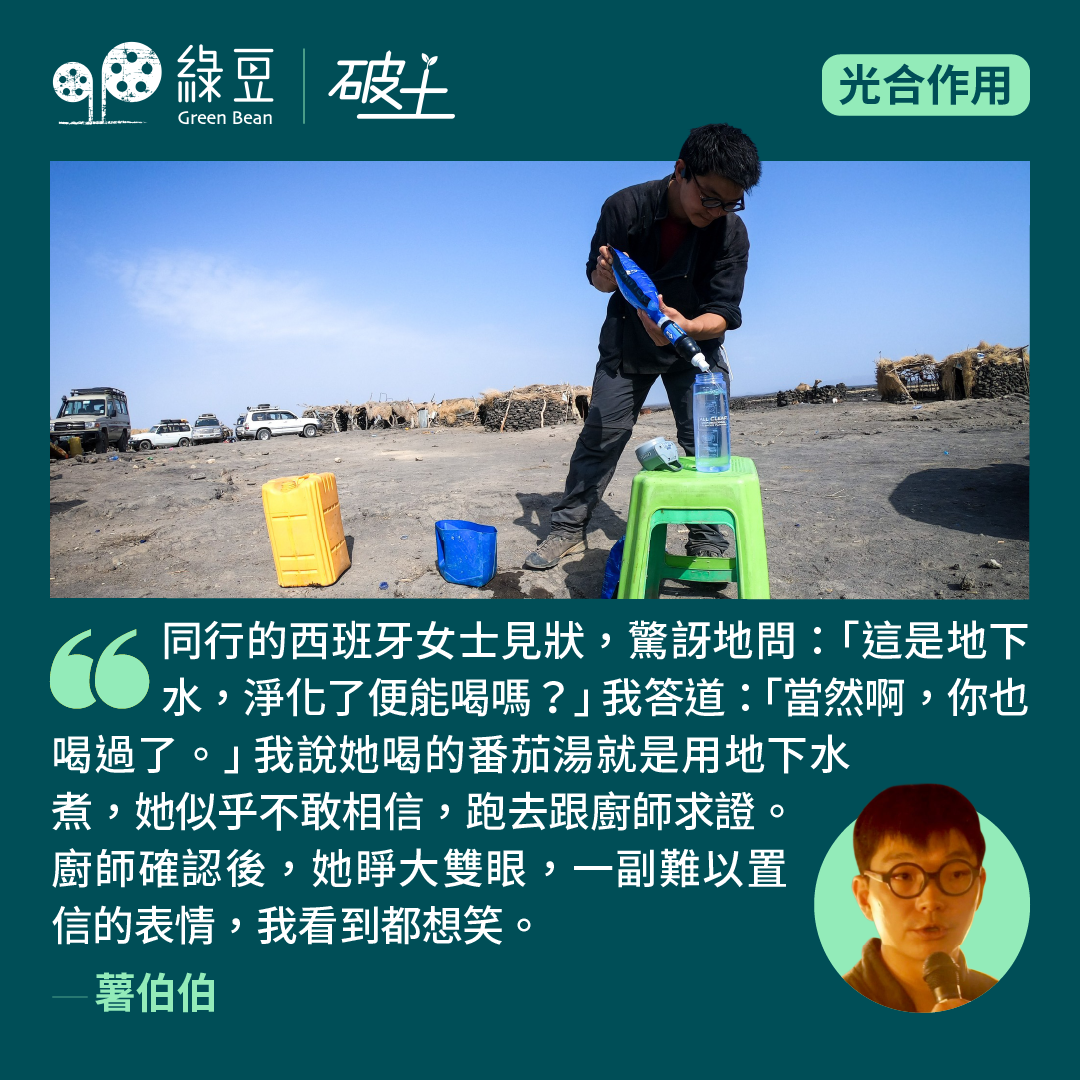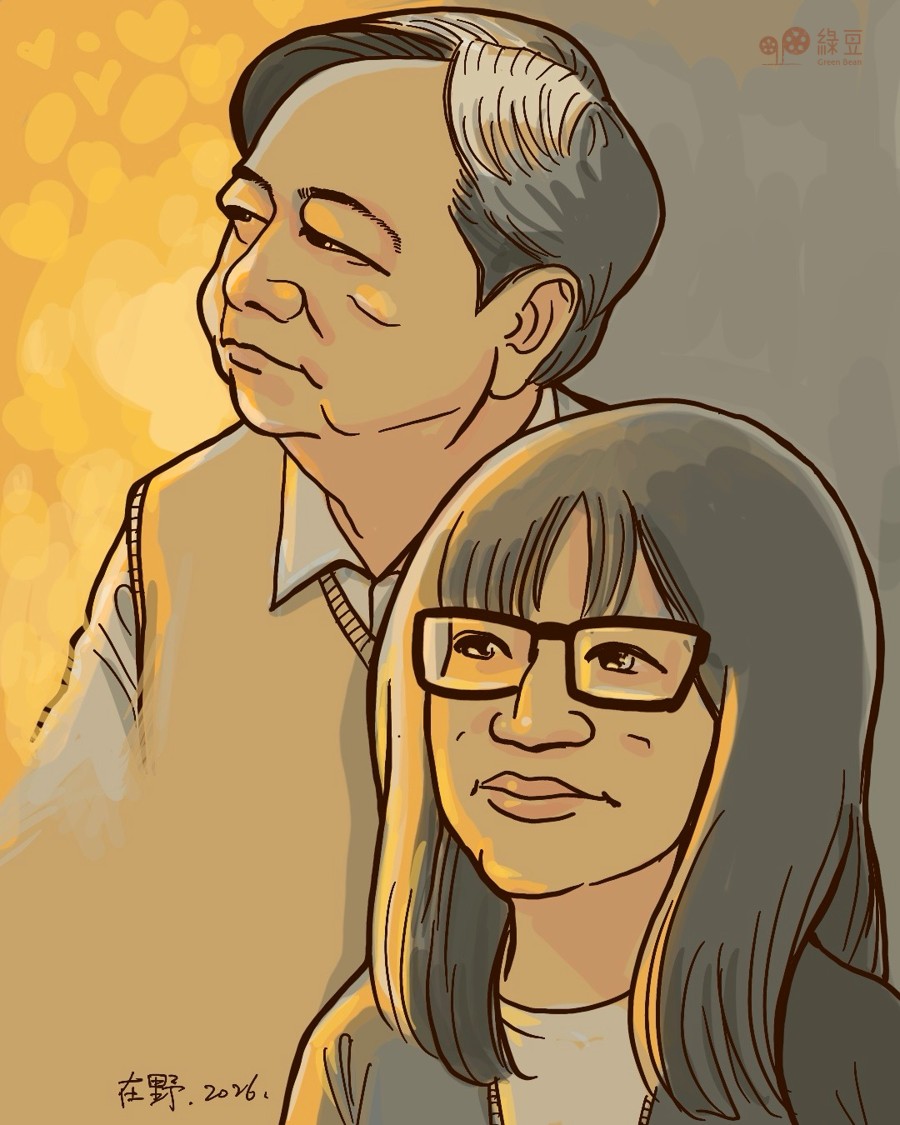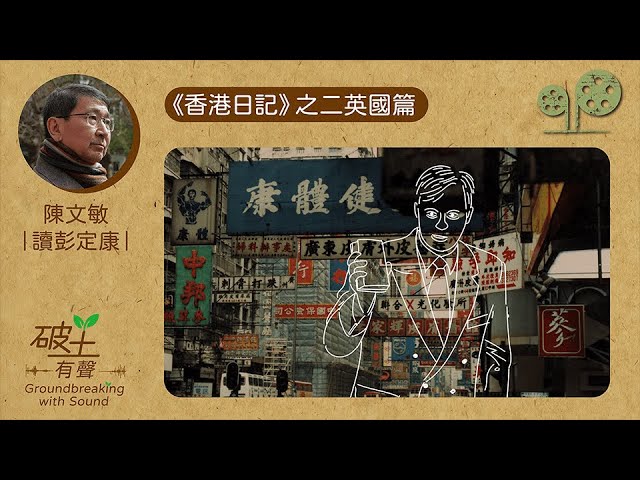跨越以巴衝突:冒死相傳的文化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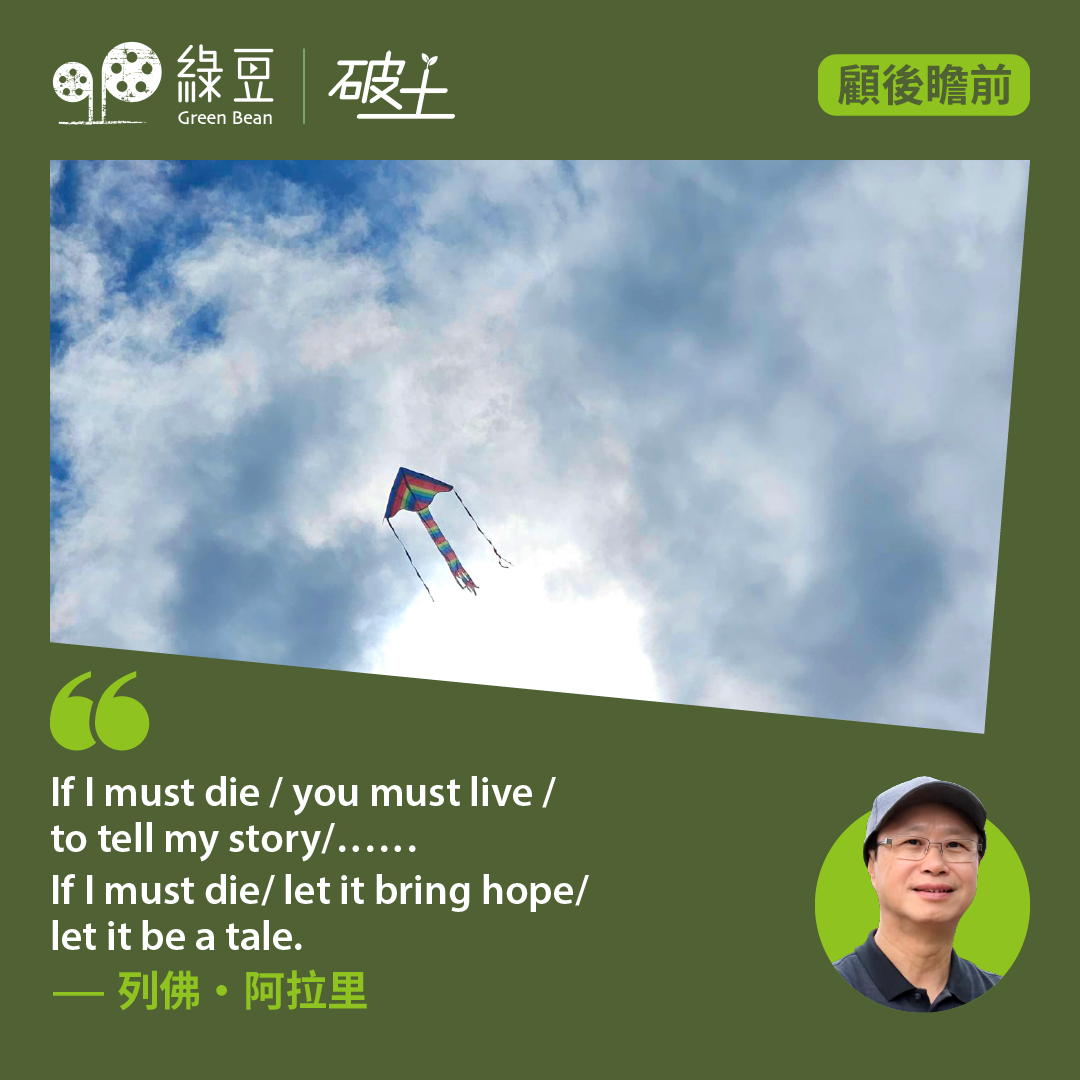
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延續逾七十年,自 2023年10月哈瑪斯襲擊以色列以來, 以色列揮軍進入加沙快近兩年。截至2025年7月, 國際組織估計已有超過六萬名巴勒斯坦人喪生。8月22日,聯合國綜合糧食安全機構發表報告,確認加沙城內的51萬居民正面臨最嚴重級別的人為飢荒;預計到2026年6月 ,13萬名兒童將會因營養不良瀕臨死亡。
因應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的指控,國際刑事法庭在2024年11月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拘捕令。國際社會要求停火與停止限運糧食的呼聲一浪接一浪,從聯合國決議、人權組織聲明、 全球各地大型示威, 到法英加澳等傳統盟友公開宣布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均令以色列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
即使背後有美國政府,以色列社會內部亦面臨嚴重撕裂。2025年8月4日 ,逾600名以色列退役情報官員及軍事將領聯署公開信,認為哈馬斯組織已非對以色列的生存威脅,呼籲美國總統特朗普促使內塔利亞胡立刻結束軍事行動。國內數十萬市民持續上街集會要求停火救回人質,與右翼政府主張擴大加沙軍事行動和西岸殖民計劃,矛盾越演越烈。
沒有人希望軍事衝突成為常態,為了民族生存,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 都要面對根本的困局:如何在戰爭與壓迫之下,讓民族記憶不被仇恨掩沒?如何把渴求和平共存的普世價值不被扭曲地傳承給下一代?這場文化戰線上的掙扎,不但關乎歷史真相 ,更是尋求和解必須跨越的關鍵課題。
在拷問人性的歷史現場,有兩個名字值得銘記——以色列歷史學者以蘭・班柏 (Ilan Pappé),和巴勒斯坦詩人、作家列佛・阿拉里( Refaat Alareer)。他們來自對立的民族,卻為了文化承傳走上同樣艱難的道路。
沒有真相,就沒有未來
以蘭・班柏 1954 年在海法出生,父母是從納粹德國逃亡來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這樣的家庭背景,使他對「流亡」與「離散」有著與生俱來的理解。
年輕時的班柏曾是以色列建制內的歷史學者,畢業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並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方向原本與眾多同儕並無二致,但在接觸以色列檔案館釋出的 1948 年戰爭文件後,他開始質疑官方歷史敘事。檔案揭示了大量涉及巴勒斯坦村莊被摧毀、居民被驅逐的紀錄,這使他直面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以色列的建立,伴隨著大規模的強制驅逐與暴力。
他在2006年將這些研究整理成著作《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揭露1948 年的「大災難」 Nakba 是一場計劃周密的種族清洗。他寫道:「沒有 Nakba,就沒有以色列;但沒有真相,就沒有未來。」 雖然這部著作是令他獲頒2024年「英國中東研究學會」 成就獎的主因,但當時在以色列國內引發激烈反彈。
班柏遭受同僚孤立, 極右組織把他標籤為叛徒 ,家人接到死亡恐嚇。他因為支持一個學生發表有關1948年在Tantura 約二百名巴勒斯坦村民被屠殺的研究論文,被海法大學排擠,最終於 2007 年離開以色列,前往英國流亡。他在雅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擔任教授,繼續對以巴歷史的批判性研究,陸續出版《有關以色列的十項迷思》等著作,並倡議「 單一國家方案 」——即構建一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平等、多元、共存的民主國家,而非兩國分治的方案。
班柏的勇氣在於他並非局外人,而是來自主流社會的少數良知學者。他曾直言:「 拒絕承認就無法和解, 你不能夠否認製造衝突的罪行但又要求和平。」
誰來說我們的故事?
如果班柏選擇流亡是對信念的堅持,那麼列佛・阿拉里選擇留下, 則是對生命的賭注。
阿拉里出生於 1979 年的加沙城,自幼在戰火中成長,中小學時常在轟炸後走過瓦礫去上課;大學時,他主修英語文學,因為他深信只有掌握世界語言,才能讓加沙的故事傳出去。
他在加沙伊斯蘭大學完成學位,後來遠赴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攻讀博士,專研英國文學與殖民敘事。那段歲月給了他相對平靜的生活,他曾收到留任的邀請,原本可在海外開展安穩的學術生涯。
然而,他毅然回到加沙,因為「如果我們都走了,誰來說我們的故事?」
回到加沙後,他成為伊斯蘭大學的英語教授,同時投身寫作與文化運動。他其中一項重要成就是共同創立 “We Are Not Numbers”,培養年輕一代用英語書寫自身故事。他對學生說:「你們不是死亡名單上的一串數字,而是有臉孔、有靈魂的人。」這句話成為整個計劃的精神。
他的課堂常在斷電的燭光下進行,有時甚至轉移到避難所。他教孩子們讀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 和莎士比亞文學: 「我教莎士比亞是因為在加沙這地方『to be or not to be』不是憑空詰問,而是日常現實。」
2023年12月6日, 他往姐姐家中避難 ,卻與兄姐及四名姨甥一同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他死前幾天發表的最後一首詩《If I Must Die》,成為加沙的文化遺囑:
If I must die/ you must live / to tell my story/……
If I must die/ let it bring hope/ let it be a tale.
他的喪生令巴勒斯坦損失了一位知行合一的詩人,但在國際社會又能泛起多少漣漪?
個人犧牲為下一代燃點希望
班柏和阿拉里,兩人站在民族對立的兩端,卻同樣選擇了拒絕沉默的道路 ,堅持用知識捍衛真相,為下一代以身作則。前者揭露自己國家隱藏的暗黑歷史,後者則在廢墟中教育孩子書寫未來。他們的命運迥異:一個被迫流亡,一個以身殉道,但信念始終如一。
在強權和炮火面前,班柏和阿拉里的人文關懷猶如風中弱燭。但無論是在加沙或任何受極權壓迫的城市 , 儘管統治者不惜以煽動仇恨鞏固權力, 以國家安全之名大開殺戒, 卻仍然無法阻擋不屈的心靈,用筆桿守護記憶 ,用個人犧牲為下一代燃點希望。
或許你慨嘆面對悲劇無能為力,這些苦難與香港人有何相干? 相信最有資格解答的人是剛從香港啟程前往加沙的歐耀佳醫生,這是他第四次到加沙進行人道醫療工作。 由於局勢緊張,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把這趟行程從過往每次六周縮短至四周, 8月25日加沙Nasser 醫院遇襲已知有20人死亡 ,包括五名記者 。願歐醫生平安。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