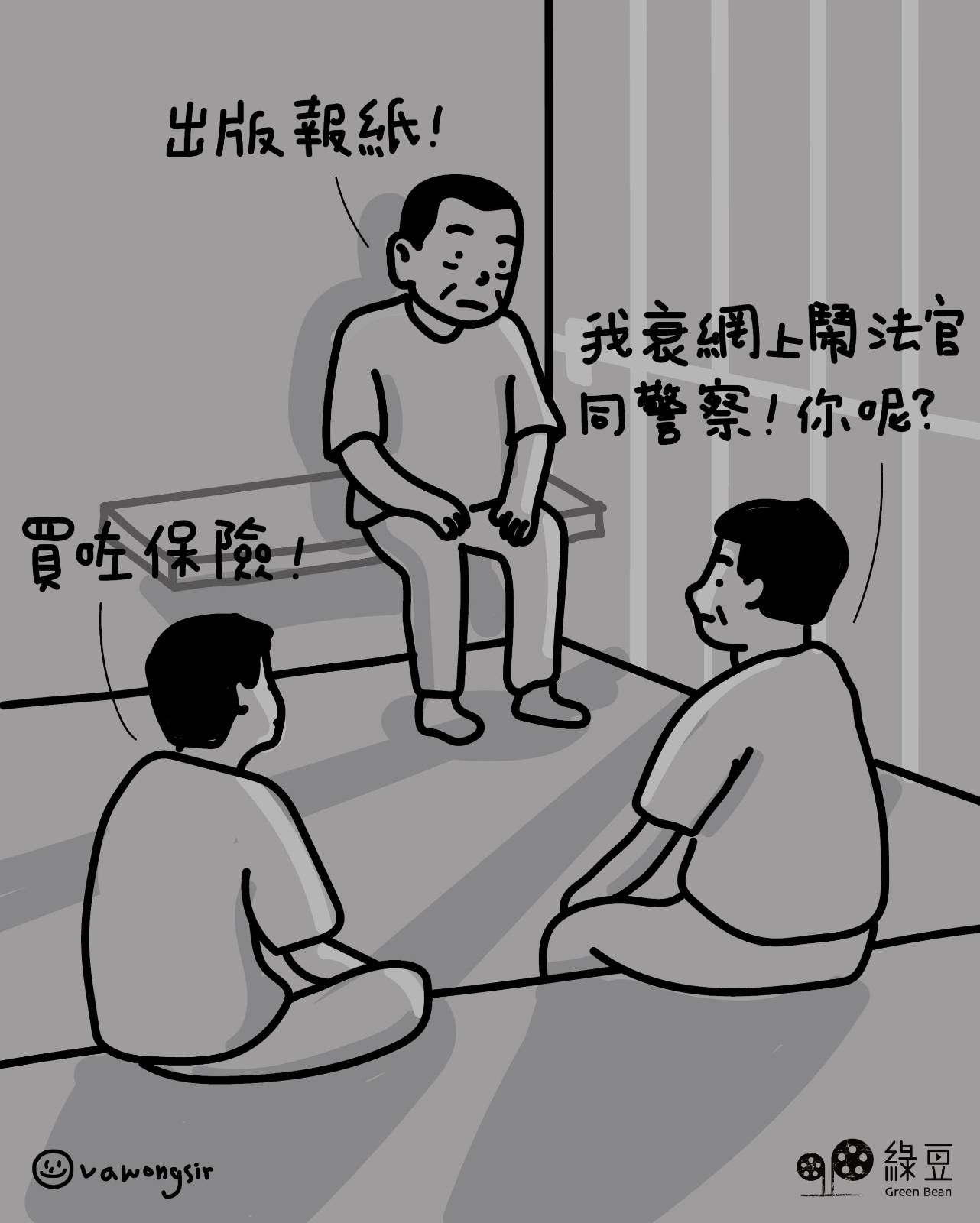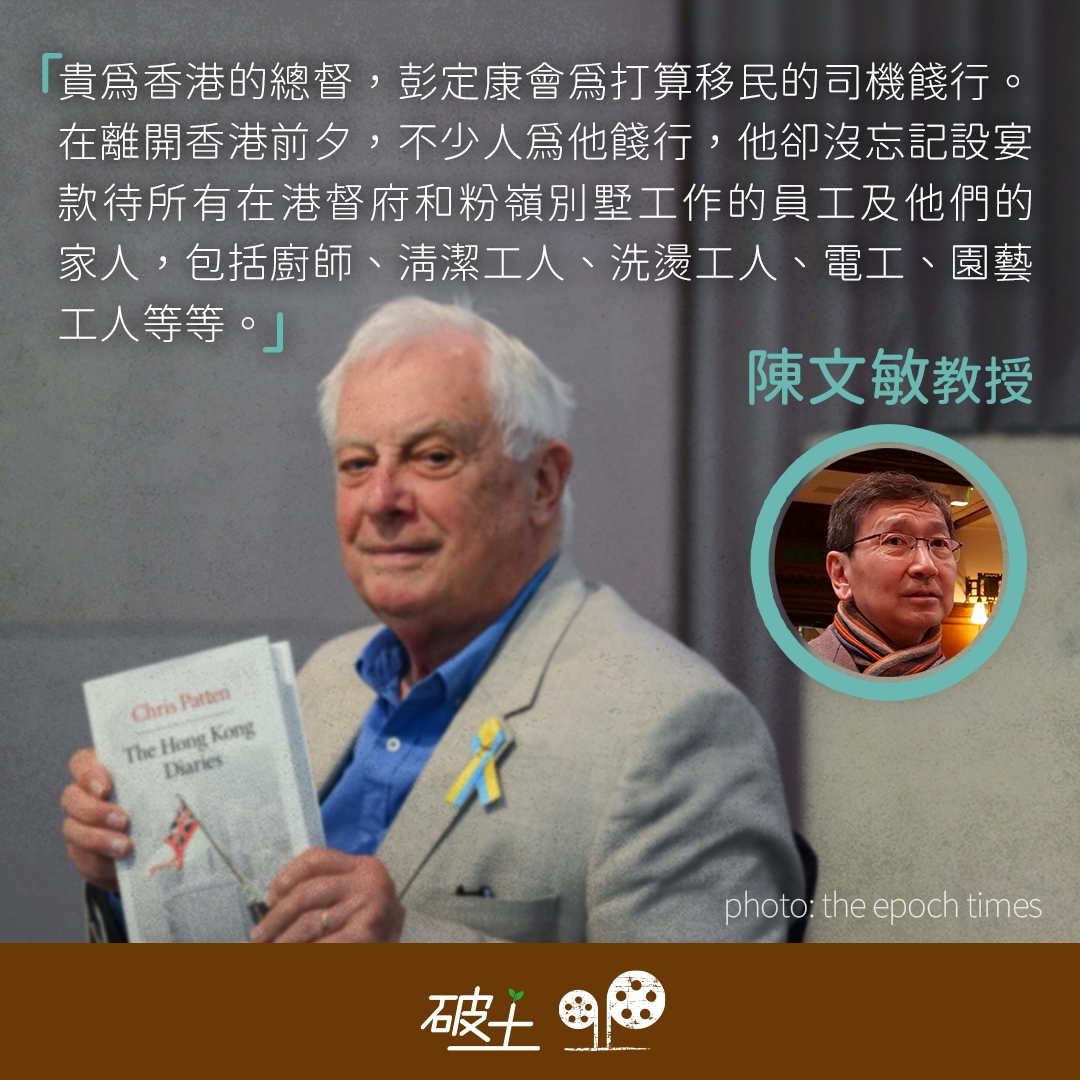評立場案(二)——滲入個人政治取向的裁決

(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一連四天連載)
沒有客觀理據還只是不同意見?
涉案的17篇中,7篇是人物專訪,1篇被裁定為新聞報道,其餘的是博客文章。法院裁定當中11篇文章具煽動意圖,包括兩篇人物專訪及9篇博客文章。17篇文章都是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發表,在分辨為何某些文章具煽動意圖或不具備煽動意圖,判詞顯示,當中帶有不少主觀和法官個人政治取向的成分。
有別於敍事論文,人物專訪不該只是抽離地敍述受訪者的生平或經歴;一篇好的人物專訪,是要將受訪者的性格、情感、特質、主張和個人經歷立體和鮮明地呈現於讀者眼前。嚴肅的學者、拘謹的官員、活潑的年輕人、油滑的政客、滿腔熱血的理想主義者,憤世嫉俗的抗爭者,他們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經歷,令他們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方式、語言和態度,好的人物專訪就是要將這些特徵和性格忠實地呈現出來。
一樣的專訪 不同的結果
鄒家成在專訪中談到要宣揚香港民族主義、提倡香港共同體等概念,又指香港已進入革命的階段。法院認為這並不構成煽動,因為專訪中有更多篇幅論及他對泛民的不滿[1]。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若言論是意圖挑起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那麼為何同時批評泛民的言論便會不構成煽動?
羅冠聰在專訪中提及自己主張外國制裁中港官員、狙擊訪歐的中國外交部長等[2];許智峯則談到讓他可以高調地與香港政府「打仗」,並希望能在海外以打國際線維生,他概括地提及一些行動計劃,包括與其他外逃者如何分工[3];梁頌恆則表示他希望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共識去支持香港時,向他們爭取金融系統上的制裁,亦希望為97後出生沒有BNO的人爭取救生艇計劃,及支持正流亡英國的前英國領事館職員鄭文傑,在英國成立「影子議會」的計劃。他提出只有兩個國家才能有兩個制度,亦表示不相信中共之下的地方會有民主的制度,甚至直接指中共不是honest player[4]。法院認為這些言論只是表達他們的政治理念或心路歷程,並沒有進一步鼓勵他人跟從他們的想法,所以不具有煽動意圖。
相反地,何桂藍也是在表達她的政治信念,闡述她為何是抗爭派,為何她認為攬炒是一條出路,指出「攬炒消極還是積極,取決於你看到的香港是不是真實的香港。」[5]但她的專訪卻被裁定為具煽動意圖。從言論的內容看,她的主張和其他受訪者的言論並沒有甚麼本質上的分別,都是在表達一種政治理念,亦提及一些行動和計劃。她認為那些不同意攬炒的人只是因為「他們還未察覺他們只是生活在極權之下⋯ 香港是完全沒有自由、不能正常生活的地方。」[6]這是她為自己的政治理念作辯解,還是煽動他人去跟隨她的政治理念?任何政治信念的表達,總會有點嘗試説服其他人接受講者的主張的傾向,兩者之間只有一線之差,如何界定亦會帶有不少主觀的成分。
法官認為她「極度仇恨、厭惡及藐視中央和特區政府」[7],甚至指她參加初選簽署了《墨落無悔》聲明,便認定「毫無疑問,她在煽惑他人試圖不循合法途徑促使改變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叛離」[8],但當時初選才剛開始,大部分人仍認為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作為逼使特首回應訴求等的手段是合乎《基本法》的,「初選案」的判決在差不多四年後才作出,法官如何能斷言在當地的她作出煽動的意圖已是「毫無疑問」?
這裡並非贊成攬炒的政治主張,而只是指出作為編輯,如何界定那些是紅線以內可以刊登的文章,那些是紅線以外的煽動性言論?幾篇專訪的內容相近,表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這同時表達了受訪者的性格。媒體應該忠實地呈現受訪者是一個怎樣的人,還只是平面地去敘述受訪者的主張或經驗?不同的編輯或媒體可能有不同的處理,社會不會亦不應期望所有媒體均用同一方法作出報導。這亦是為何普通法要求具有煽動暴力或破壞公共秩序的意圖的言論才能構成煽動,因為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最少有較客觀和清晰的界線可以跟從。
滲入法官個人政治理念
判詞滲入法官的個人政治理念,在處理博客文章便更明顯,將沒有客觀事實根據的評論,與法官不同意文章作者的意見兩者混淆。例如陳沛敏的文章,[9]她以三件事例包括「譚得志案」批評警方濫權,法院指她所引述的兩件事例和「譚得志案」完全不同,亦沒有披露譚得志是在屢犯並多次被警告無效後才被拘捕,但這是沒有客觀事實基礎,還是只是法官不同意她提出的客觀事實基礎和立論?
區家麟一篇批評國安法的文章,批評國安法適用範圍過寬,指定法官令人質疑法官的獨立和公正、保釋條款及不使用陪審團審訊的安排容許執法機構濫權。[10]法院指他沒有考慮原訟法庭在「唐英傑案」的意見、實施國安法的需要及西方民主國家不設陪審團的安排,從而認為批評沒有任何客觀事實基礎,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構成煽動意圖。
然而,以往已有不少學者在海內外的學術期刊,提出相類似的批評,甚至認為在「唐英傑案」中,對法院謂指定法官並不影響司法獨立這說法表示質疑,尤其是當任命和不延續指定法官的任命完全沒有透明度,難以令人對不延續任命會否基於政治理由感到憂慮。
至於指原訟法庭在「唐英傑案」中指出在《港區國安法》下,保釋申請不涉及有罪假設之説,則更加令人摸不著頭:原訟法庭的説法是基於法庭當時認為《港區國安法》的保釋條款並沒有改變普通法獲保釋的假定或提高保釋的門檻,其後李運騰法官批准黎智英保釋外出,也是基於這個理解,但這判決其後被終審法院推翻,黎智英的保釋亦只是曇花一現,隨著終審法院的判決而被法院撤銷。黎智英至今已被囚超過三年,案件仍在審訊階段,法院指區家麟「對《港區國安法》作出的控訴,除了投訴外,沒有任何實質的理據」,[11]實在難以理解。
再者,提出政治評論是否應以法律學者的標準來衡量?即使評論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也只能説評論欠缺周詳考慮或有所偏頗,但卻不是沒有客觀基礎。至於説區家麟批評律政司追殺政敵絕不手軟,法院指覆核刑期和上訴,本來就是香港法律的一部,但這視乎這些程序是怎樣應用,法院的推論是基於這些見解沒有客觀事實基礎,還只是法院不同意他的見解?
同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羅冠聰另一篇批評「47人初選案」的保釋聆訊安排,[12]通宵達旦的聆訊令部分被告體力不支暈倒,並批評檢控為荒謬和濫用權力。法院以文章發表近四年後的「初選案」的判決,指批評檢控沒有客觀事實基礎,但相關的時間不是文章發表的時間,當時不少人仍認為初選並不違法,而不是以四年後的發展來支持四年前的文章沒有客觀事實基礎的論述?至於保釋聆訊的安排,法院並無指出安排的敍述有誤,而只是解釋因該案涉及被告的人數眾多,法庭有須要延長開庭時間以盡快處理,而控辯各方亦沒有就出席時間作出申請。法官絕對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評論,但不同意見為何一下子會變成作者的評論沒有客觀事實基礎?
社會背景和司法認知
法官用了頗大篇幅描述當時的社會環境,並多次引用司法認知確立事件,從而推論社會仍然很不穩定。司法認知是在訴訟中確立事實的一種方法,它容許法院毋須任何證據,便接受一些廣為人知的事實。司法認知只局限於一些不具爭議的客觀事實,例如太陽是從東邊升起、農曆新年在香港是公眾假期等,但一分鐘是很短的時間卻不是司法認知的範圍。一分鐘是長是短得視乎環境情況,朋友歡聚,一分鐘是很短的時間,但當你趕赴考試但交通非常擠塞,一分鐘可以有如一年那麼長!
同樣地,當法官認為憑司法認知可以肯定, 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被不同派別人士宣傳為政見的公投」,[13]這便值得商榷,因為這是一個結論多於事實,即使是事實也可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事實,不是司法認知的範圍。
在判詞中,法官以司法認知引入大量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作出推論案發時的社會背景。當中引用司法認知的次數之多,實屬相當罕見,所作的推論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餘地。
事實裁斷還是個人政見?
首先,涉案的17篇文章,發表的時間跨越約18個月,而法官在推論當時的社會背景,更從2014年推論至2021年,時間長達七年。這段期間,香港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法官引入的事情確實曾經發生,但選取那些事件用作推論,卻存在不少主觀價值取向。第二,在一般的審訊,法院的工作是裁斷事實,透過雙方提供的證據,去斷定與爭議相關的事實,這種斷定事實的工作一般是較具體的。法庭較少要對一整個時代的社會環境作出裁斷,這是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學者的專長。涉及的時間愈長,涉及的事件愈複雜,推論便會愈具爭議,亦便無可避免會滲入不少主觀的個人政見或取態。判詞用了大量篇幅談涉案的社會背景,但這部分,與其説是法官對事實的裁斷,更多的是表達法官對當時的社會事件的個人政見。
例如在談到參與612衝擊立法會事件的示威者的特徵,法官作出這樣的推論:
本席相信,當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等發表時,這些曾參與佔領或雨傘運動的人正在或快將進入大學讀書,是最早期接觸這些論述的人。雨傘運動5年後,這群人的本土主義理念看來更為堅固;他們追求政治訴求的手段亦深受台灣太陽花學運影響,趨向採用激進及非和平的手段。[14]
雨傘運動的影響,有不少學者已曾著書立説,太陽花運動對香港青年或雨傘運動的影響亦各家各説,法官指這些示威者是最早期接觸到香港民族論的人士,但這推論似乎只是基於香港民族論是在他們進入大學或將要進入大學時出版,這種推論的基礎十分稀疏。香港民族論最初只是在港大學苑刊登的幾篇文章,示威者當中有多少人看過香港民族論?對此並沒有任何證據,更遑論如何受它影響。
判詞提到不少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觀念,例如本土主義,民粹主義等,但只是粗疏的將這些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判詞沒有分析香港民族論的內容,但卻將民族自決等同本土主義,本土主義等同香港獨立,亦等同支持使用暴力和激進行動,這些概念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的關係亦錯綜複雜,不同的學者也會有不同的推論。法官這些推論,似是政見多於事實,而且是頗具爭議的政見。
法官繼而指出,即使在該投票選舉前發生示威者將活人縱火,及中大和理大的暴亂,但抗爭者派別依然大勝。法官從而推論,「到了這個階段,情況已經改變,一切立場先行,目的至上,手段可以不理。本席肯定,民粹年代當時已降臨香港。」[15]法官可以就已獲證明的事實作出推論,但這些推論必須是唯一的合理和不可抗拒的推論。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泛民大獲全勝是事實,但是否所有獲選的泛民人士都是支持暴力的抗爭者?泛民大勝這個事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法官所指的騷亂事件,和抗爭派獲大量市民支持有甚麼關係?法官的推論是合理和不可抗拒的推論,還是法官的個人政治意見?
以司法認知引入社會事件,當中已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從這些選擇性的事件再作一些社會性和政治性的的推論,便難免滲入不少主觀的政治價值和取向,然後以此來審視相關文章,法院便可能不自覺地採納了某些立場或角度作出審視。只要是文章的用詞稍為尖鋭,批評觸及警察、國安法、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便很容易被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煽動言論。
含糊的煽動罪被終院裁定合憲
法院在這方面著墨不多,主要是因為上訴法庭在「譚得志案」已就此問題作出裁決,認為煽動罪並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中的法律確定性的原則。而由於法例已列有建設性的評論的答辯,煽動罪已經在保護國家安全和保障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這觀點已獲終審法院認可,終審法院在「譚得志案」就這一點拒絕批出上訴許可。
終審法院的判決是令人失望的,煽動罪在整個普通法世界均備受批評,不少地區的判例均嘗試以司法解釋收窄該罪行的定義,多個國家的法律改革委員會均曾對此罪行作深入研究,並建議收窄或廢除該罪行。譚得志的違憲上訴理據,是假設終審法院認為煽動罪不需證明具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在這基礎上煽動罪是否仍然符合《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這宗案件本來可讓終審法院有機會詳細審視大量的海內外的判例和經驗,法院的判決亦會對新的煽動罪的合憲性作出啟示,因為新的煽動罪,正明文列出該煽動罪並不須要證明具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可惜,面對這極其重大和關乎公眾的法律問題,終審法院卻連上訴申請也不批准,判詞中對這麼重要的合憲爭議只有簡略的解釋,甚至予人有點匆匆了事的印象,判詞缺乏詳細和深入的討論,更沒有考慮大量普通法地區的案例,這樣的處理實在令人失望。我在另一篇文章作了這樣的結論:[16]
2024年初,政府將原來的煽動罪納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明文規定不用證明具煽動暴力或擾亂公安的意圖。終審法院的判決,意味新的煽動罪,不受憲法挑戰,判決給人有點旨在封殺日後對新的煽動罪提出質疑的訴訟。判詞亦流露法院偏向採納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觀點,對極廣闊的國家安全的定義照單全收的取態。法院只着眼於2019年的暴亂,卻忽略了在處理憲制問題的時候,法院需要同時考慮,當社會遠離暴亂之後,嚴苛的法例和模糊的執法空間對言論自由的打擊。嚴峻含糊的法例一旦被裁定為合憲,法院監察政府執行這些法律的空間便被大大削減,而合憲的判詞便往往成為法院對威權政府的背書。
註:
[1] 見判詞,第283段。
[2] 見判詞,第304段。
[3] 見判詞,第318-319段。
[4] 見判詞,第324-325段。
[5] 見判詞,第278段。
[6] 見判詞,第278段。
[7] 見判詞,第271段。
[8] 見判詞,第276段。
[9] 判詞,第291-299段。
[10] 判詞,第337-339段。
[11] 判詞,第346段。
[12] 判詞,第352-355段。
[13] 判詞,第231段。
[14] 判詞,第222段。
[15] 判詞,第231段。
[16] 「評譚得志上訴許可案」,綠豆海外隨筆,2024年8月30日: https://greenbean.media/評譚得志上訴許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