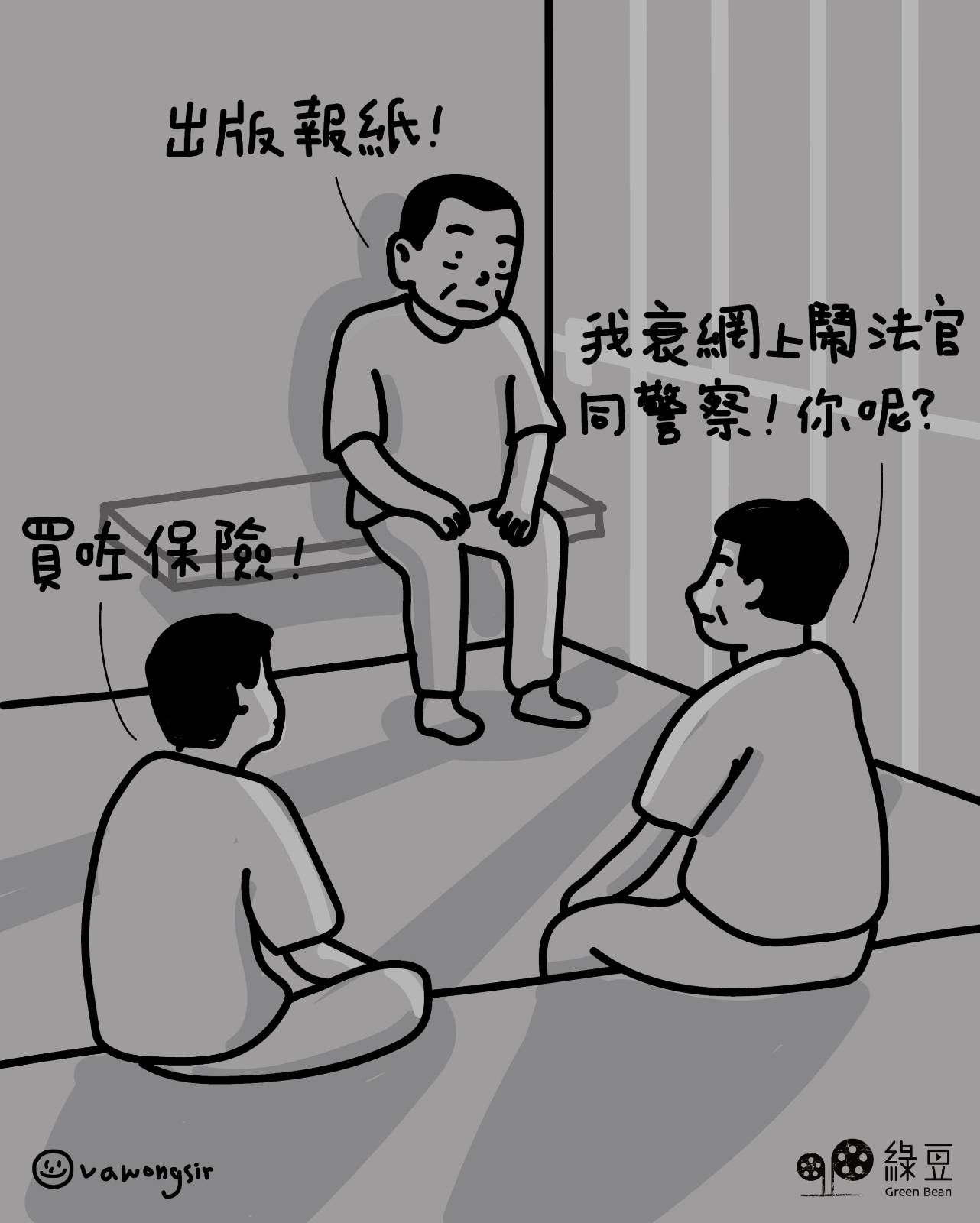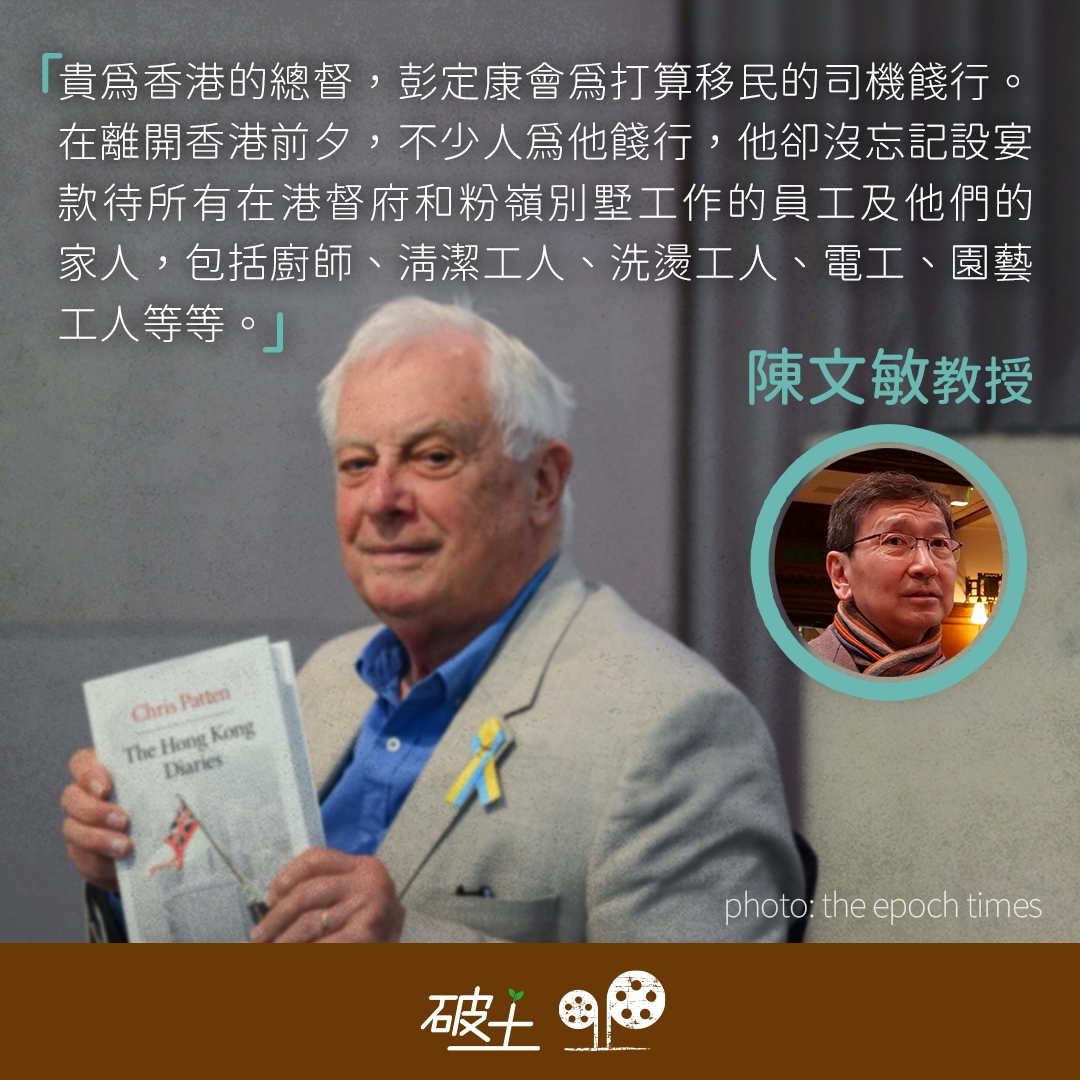評立場案(一)——法院怎樣裁定刊物具煽動意圖?

(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裁定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判煽動罪成,法院的裁決令香港本已脆弱的新聞自由雪上加霜。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確的地方。本文將一連四天連載陳教授就判詞及判刑的分析。)
本案的煽動罪是根據《刑事罪行條例》提出,這控罪已於2023年被《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新控罪所取締。案件審訊前後歷時接近兩年,區域法院於2024年8月29裁定,涉案的17篇文章當中,有11篇屬於煽動刊物,指這些文章指罵政府和法院,但卻無客觀理據。鑒於香港當時仍然有很多不穩定因素,這些文章會挑起市民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憎恨,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危險。三名被告被裁定認同這些刊物的觀點,並具煽動意圖合謀發布這些煽動刊物。[1]
怎樣裁定刊物具煽動意圖?
什麼是具煽動意圖的言論?法例的定義相當空泛,包括任何引起市民對政府或司法制度的憎恨或藐視、或市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但卻不包括目的在矯正政府決策或決定,和法院判決的錯誤或缺點的建設性評論。法院認為,文章是否具煽動性,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一併考慮,並指出這建設性評論的答辯並不適用於無客觀事實基礎、意圖嚴重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權威等的言論。
這裡涉及四個法律問題:第一,煽動意圖是否須有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第二,煽動刊物是否須要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和實際的風險? 第三,就建設性的評論,如何分辨沒有客觀事實基礎的評論與不被接受的意見?第四,煽動罪是否符合《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
普通法要求煽動罪須具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但區域法院在「羊村案」[2]及上訴法庭在「譚得志 (快必)案」[3]均裁定,香港的煽動罪是根據香港本地的情況而非普通法訂立,故普通法的要求和案例並不適用,並裁定香港的煽動罪並不須要具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在「譚得志案」已就這一點批出上訴許可,並安排在2025年1月審理。於是,這個問題的最終判決,要留待終審法院明年的裁決。
由於上訴法院在「譚得志案」已就這問題作出裁決,而上訴法庭的判決對區域法院有約束力,故法院在「立場案」中,就這一點的裁決要跟從上訴法庭的判決是對的。不過,區域法院在判詞中仍花了不少篇幅,指出即使沒有上訴法庭的判決,法院也會達致相同的結論。
煽動罪的權威定義
早前我在一篇評論「譚得志案」的文章中指出[4],翻查香港的立法歷史,港府在1938年訂立的煽動罪的條文,其實是以英國外交部所制定的《煽動法範本》為基礎 ,這解釋了為何大部分普通法地區的煽動罪的條文均大同小異。香港當年引入煽動罪是基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但條文卻是抄襲英國的《煽動法範本》,而英國的《煽動法範本》則是基於普通法的規定。律政司在立法局引入該條例草案時,亦以附表清楚説明該罪行是基於普通法,故普通法的要求依然適用。
法院在判詞中對我的觀點作出回應。第一,法院同意1938年的條例是基於英國的《煽動法範本》,《範本》採納了普通法對煽動罪的定義,而普通法對煽動罪的權威定義可見於Stephen’s Digest of Criminal Law之內[5]。但法院強調,律政司於法案附表只是説煽動罪的定義是「非常緊貼」(very closely)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亦即是並非完全相同。第二,法院跟著比較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和煽動罪的條文,指出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包括「煽動他人觸犯任何擾亂和平的罪行」(to incite any person to commit any crime in disturbance of the peace),但這一項並沒有納入煽動罪的條文內,從而推論立法原意是刻意排除煽動暴力和破壞公共秩序的意圖於煽動罪的定義。
法院這理據有幾點值得商榷:首先,法官的論點建基於法例的煽動罪只是「非常緊貼」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但律政司已於附表內列出相異之處,例如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並不包括誘使軍人不忠,若果還有其他差異,律政司沒理由不在附表內一併提出。第二,Stephen’s Digest 只是對普通法的論述,要確定普通法的定義,還是要從判例推敲。當年的法院在著名的案例R v Burns 中確認Stephen’s Digest 的權威性,並同意它的定義準確表達了普通法的定義,[6]但該判例所引述的定義,並不包括「煽動他人觸犯任何擾亂和平的罪行」這一項。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委員會其後指出,這一項是後來的版本加進去,而並非當時普通法的一部分[7]。
第三,即使這一項是Stephen’s Digest 的定義,它只是説,「煽動他人觸犯任何擾亂和平的罪行」是其中一項煽動意圖,和其他煽動意圖並列,令單純鼓吹暴力亦可構成煽動[8],但這並不表示其他煽動意圖便不須要意圖煽動暴力或破壞公共秩序。換言之,若言論只是煽動市民對政府的憎恨,這仍未構成煽動罪,還要言論是意圖煽動暴力或破壞公共秩序才足以入罪,必須兩者兼備才能構成煽動罪。亦即是説,即使煽動他人觸犯任何擾亂和平的罪是普通法下其中一項煽動意圖,這和煽動罪須要有意圖煽動暴力或破壞公共秩序並無衝突,前者是煽動所意圖的其中一種結果,後者則是煽動所意圖的手段。這亦符合Sir James Stephen在另一本著作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中所指,沒有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便難以構成煽動罪行。[9]
大量普通法案例
普通法有大量案例指出,煽動罪必須具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加拿大最高法院在著名的Boucher 案中便作出權威性的論述[10]。該案涉及宗教組織耶和華見證人發出的單張,當中強烈指責警方、公職人員及羅馬天主教會,指責他們逼害其組織的成員,神職人員更不當地影響法院和司法公正,令法院對他們不公。
最高法院在判案時指出,「煽動罪必須建基於針對英皇或政府架構的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單單只有煽動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之間的惡感和仇視並不足夠。而且在這方面不單要有煽動暴力的意圖,而是這些暴力或破壞社會秩序的目的是要擾亂已確立的政府權力。」 (The seditious intention upon which a prosecution for the seditious libel must be founded is an intention to incite violence or to create public disturbance or disorder against His Majesty or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Proof of an intention to promote feelings of ill-will and hostility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of subjects does not alone establish a seditious intention. Not only must there be proof of incitement to violence in this connection, but it must be violence or defiance for the purpose of disturbing constituted authority.)
普通法的要求,是有鑑於煽動罪的定義空泛,容易被政權濫用。2011年,印度著名政治漫畫家Trivedi公開發表了一系列諷刺政府貪污的卡通,他其後被控煽動罪,指他意圖引起對政府的憎恨或藐視。首席法官在判詞中強調,不論評論多麼尖銳,措辭多麼強烈,只要不會導致擾亂公眾秩序,便不屬於煽動行為。[11]在另一宗案件中,印度最高法院指出,法例所針對的危險不能是遙不可及或具爭議的(remote, conjectural or far-fetched),而必須是相關言論引起的直接和緊密的後果。[12]
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均有相類似的判例。新西蘭法律改革委員會引述 Sir Kenneth Keith的研究,指出在政局動盪的時候,幾乎任何對政府的嚴厲批評均會被視為意圖引起對政府的憎恨和藐視,煽動罪往往用來懲罰對政府政策作出批評的人士,而非用於維護公衆安全。愛爾蘭和澳洲的法律改革委員會亦先後達致相類似的結論,指煽動罪會受到政治氣候的強烈影響,很多時候是用來打壓政治異見分子。普通法要求有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正是要減低煽動罪被利用為打壓異己的工具。在大部分普通法地區,煽動罪已被廢除或收緊。[13]
這些考慮同樣適用於香港。近日在一宗來自千里達的上訴判案,樞密院審視了普通法不同地區就煽動罪的判決和發展,以及當代人權法的發展,認為煽動罪必須具煽動暴力或破壞公眾秩序的意圖,並推翻樞密院在1940年的一宗判決,而這宗1940年的判決,正是過往香港法院認為香港的煽動罪毋須具備該等意圖的依據[14]。換言之,作為普通法法域之一的香港,普通法的發展及《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的要求,均會對煽動罪這條在海外備受批評的法例的詮釋有所限制。可惜,法院並沒有考慮這些判例和發展。
總括而言,法院在「立場案」就這一點的附加理據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法院受制於上訴法庭的判決則無可厚非。無論如何,這方面的爭論,要留待明年終審法院在「譚得志案」的判決才有分曉。
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風險
煽動罪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那要求煽動的言論要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的風險,而非只是理論性或影響極微的風險,這似乎是一個顯然易見的立論,也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道理[15]。
加拿大和南非的最高法院均曾指出,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或憎恨,並不一定等如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的風險[16]。例如在民主國家,很多時執政黨可能只是以些微票數當選,這意味有為數不少的選民不支持或不滿執政政府,但這並不表示國家安全便會面對實際的風險。
法院並不同意這觀點,認為當言論被評定為具煽動意圖,法院必然已經考慮相關的實際情況,視為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破壞,須要制止。況且,所指意圖須是意圖「嚴重」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的合法性或權威,而聽眾是否被煽動言論所挑動並沒有關係。法院因而裁定,只要相關的言論或刊物被裁定為具有《刑事罪行條例》第9(1)條的煽動意圖,便毋須另外再考慮言論是否構成實際國家安全風險[17]。
這個論點的弔詭之處,在於一方面法院認為煽動言論必須「嚴重」破壞特區政府的合法性或權威,從而構成對國安全的實際風險,但另一方面則認爲當相關言論被評定為具煽動意圖,便可被視為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破壞。
可是,實際風險和潛在破壞是完全不同的尺度,一個人在街上叫叫口號,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破壞,但對國家安全會構成甚麼真正和實際的風險?即使批評沒有客觀基礎,甚至構成藐視法庭,但表達不滿和不信任是否便等同意圖引起市民對司法或政府的憎恨,從而對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
法院強調煽動意圖必須「嚴重」損害政府威信,但在應用這規定時,法院的重點放在相關言論是否意圖引起市民對司法或政府的憎恨,「嚴重」這要求好像消失了;實際風險則變成「潛在風險」!法院的判決將煽動罪的門檻大大降低,這從法院如何應用這法律原則於本案中便清晰可見,只要有潛在風險便可入罪,所謂「嚴重」破壞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已變成空洞的口號。
註:
[1] HKSAR v Best Pencil (Hong Kong) Ltd [2024] HKDC 1430 (以下簡稱「判詞」)。
[2] HKSAR v Lai Man Ling [2022] HKDC 981.
[3] HKSAR v Tam Tak Chi [2024] HKCA 231.
[4] 陳文敏:評譚得志案,綠豆,2024年3月15日 (https://greenbean.media/%E8%A9%95%E8%AD%9A%E5%BE%97%E5%BF%97%E6%A1%88/)
[5] 見判詞第170段。
[6] (1886) 16 Cox C C 355 at 360.
[7] “Codific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Treason, Sedition and Allied Offences”, The Law Commiss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Working Paper No 72 (London, HMSO, 1977), paras 69-72 and footnote 103.
[8] 這亦解釋了1970年對煽動罪的修訂,令鼓吹暴力本身已構成煽動意圖。這修訂相信是針對67暴動時一些單純鼓吹暴力,但並沒意圖引起公眾對政府或司法機關的憎恨或藐視的行為。
[9] (1883), vol II, pp 375, 381.
[10] Boucher v R [1951] SCR 265, at 283, per Kervin J
[11] Free Press of Namibia (Pty) Ltd v Cabinet for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South West Africa [1987] 4 All SA 63 (SWA), at 73, per Levy J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wp-content/uploads/2017/09/The-Free-Press-of-Namibia-v-SWA-Namibia.pdf)
[12] S Rangarajan v P Jagjivan Ram [1989] 2 SCC 574 (“The anticipated danger should not be remote, conjectural or far-fetched. It should have proximate and direct nexus with the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should be intrinsically dangero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In other words, the expression should be inseparably locked up with the action contemplated like the equivalent of a ‘spark in a powder keg’.”)
[13] 詳見筆者:”Seditious Publication: The Village of the Sheep Case” (2023) 53(1) Hong Kong Law Journal 65
[14] Fei Yi Ming v The Crown (1952) 36 HKLR 133.
[15] 見 Henry Litton, “The Case of the Wolf and the Sheep in Hong Kong (Pearls and Irritations”, HKU Legal Scholarship Blog, Dec 17, 2022 (https://researchblog.law.hku.hk/2022/12/henry-litton-on-case-of-wolf-and-sheep.html)
[16] Boucher v R [1951] 2 DLR 369; Free Press of Namibia (Pty) Ltd v Cabinet for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South West Africa [1987] 4 All SA 63 (SWA), at 73, per Levy J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wp-content/uploads/2017/09/The-Free-Press-of-Namibia-v-SWA-Namibia.pdf)
[17] 判詞,第175-176段。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