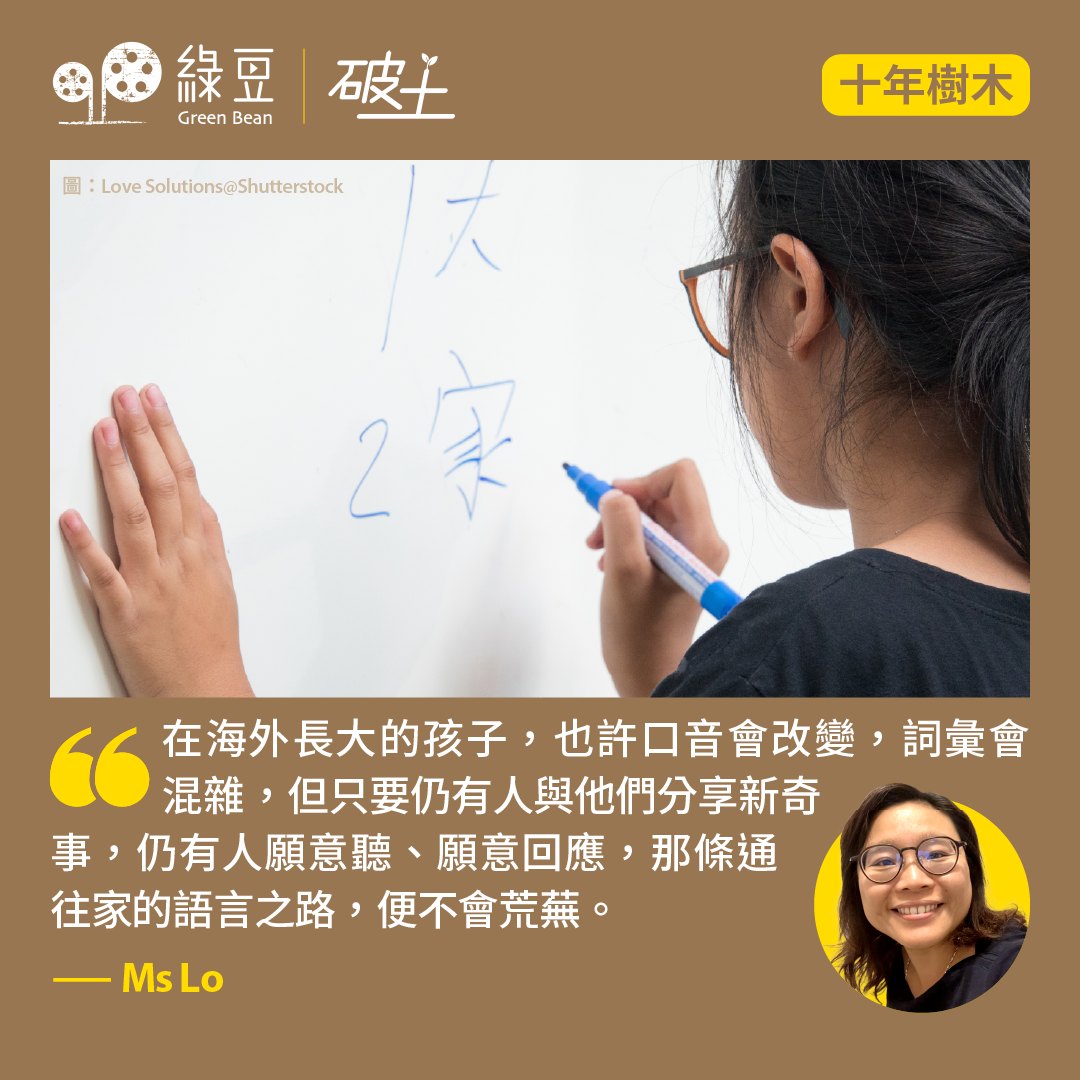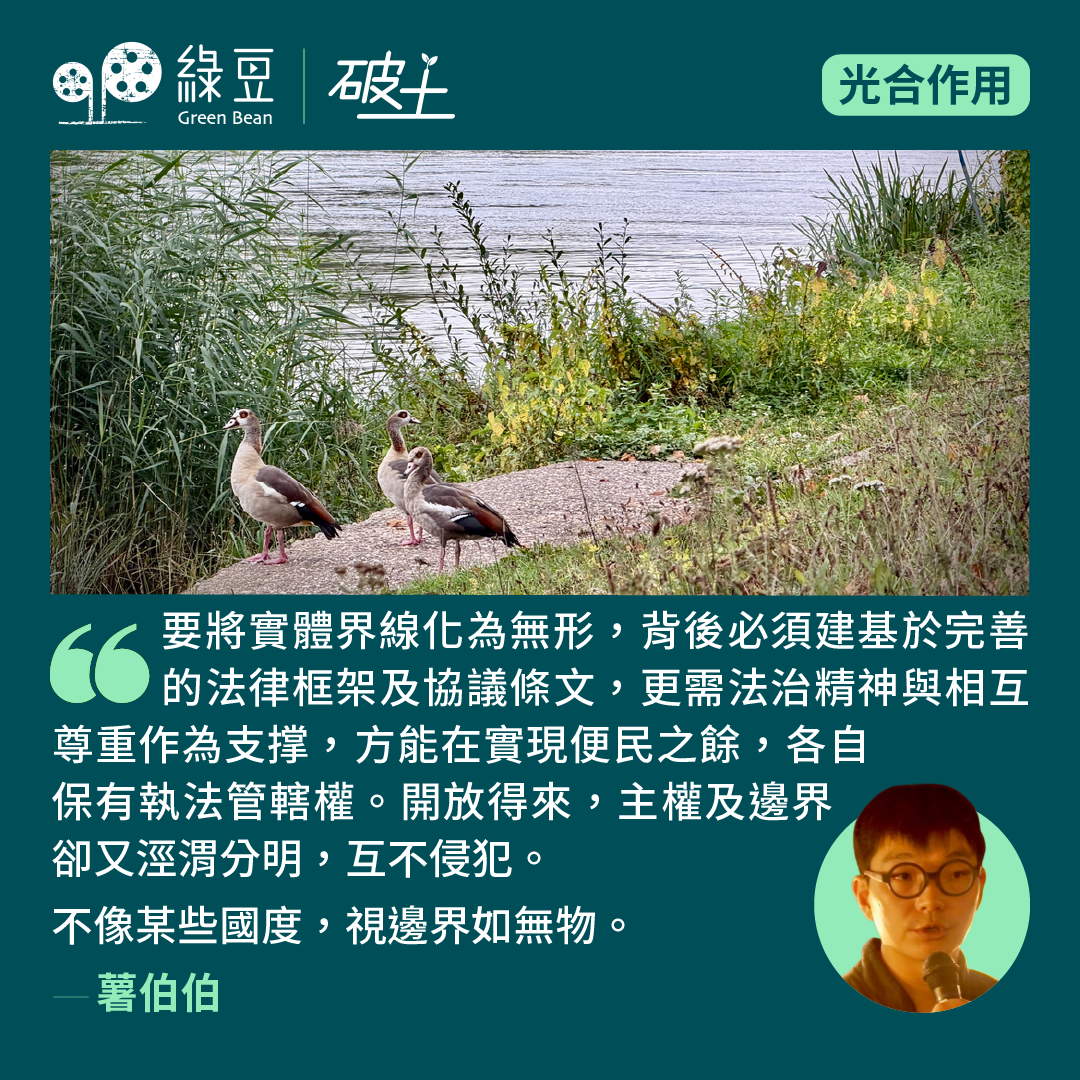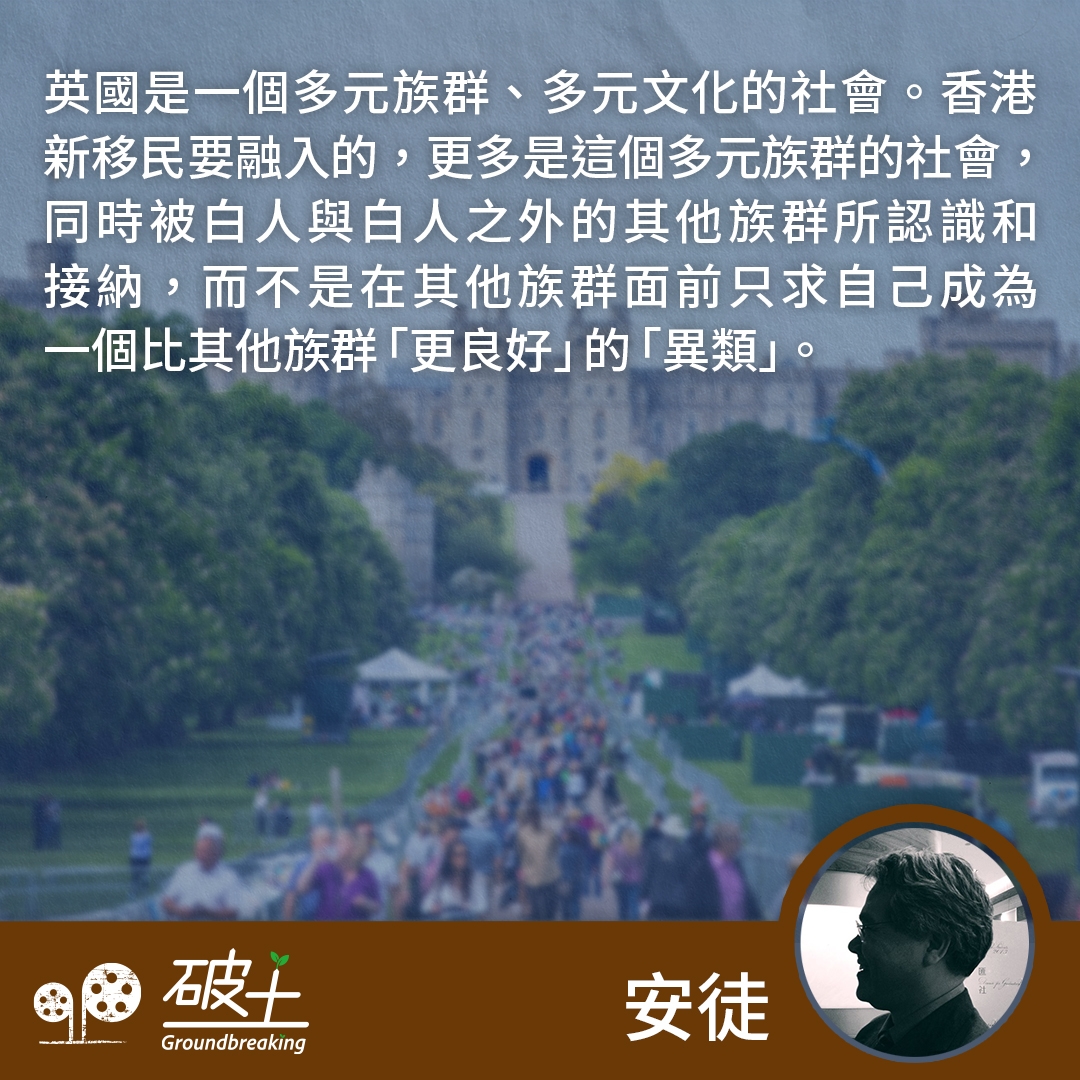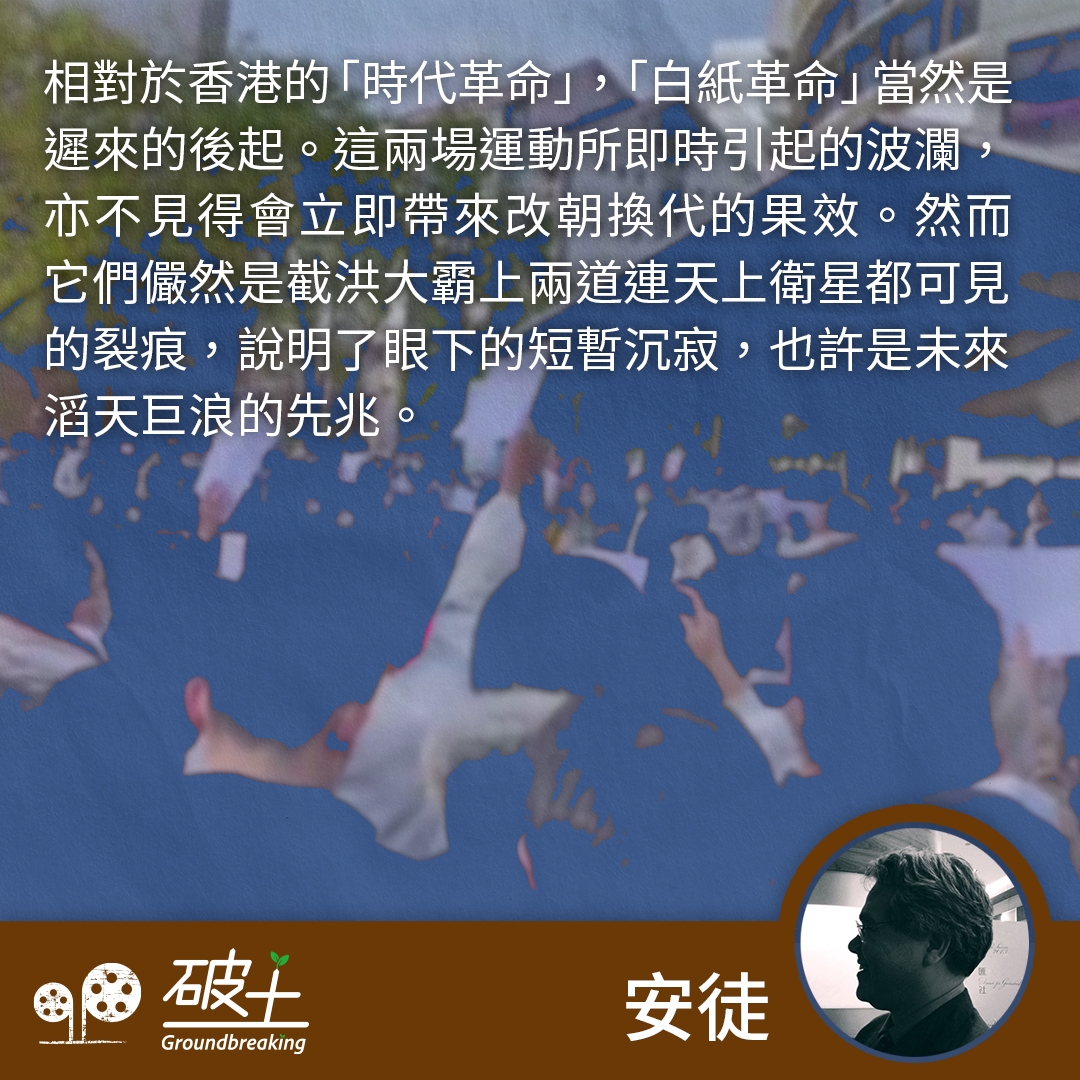英國罷工浪潮與港人意識的轉變

英國的罷工浪潮持續擴散,影響愈來愈大。各地區的不同行業,都有工人進行或醞釀着罷工,當中尤以持續了好幾個月的鐵路和運輸工人罷工,對生活的影響尤為顯著,社會上也議論紛紛。幾年來移居英國的香港新移民,對於罷工也有不同的立場,甚至出現各種爭論。
反對罷工的人因為罷工帶來不便,有各種怨氣和牢騷,指責工人不應為了自己的薪金福利,發動罷工而影響大眾。這種意見當然是香港人所熟悉的,因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大多數香港人對工人權益的漠視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爭論中,相當部分的港人是抱「不反對」甚至支持的態度。他們認為無論怎樣,工人為了爭取自身的權益而「罷工」是無可厚非的,畢竟訴諸「工業行動」是英國確認的一種民權,作為新移民的香港人更應包容了解。
平情而論,這種觀點說不上是對這番罷工的同情甚至理解,因為事實上大多數香港新移民對於英國複雜的勞資關係,這個國家勞工運動的歷史傳統,其實少有確切的認識。對於鐵路運輸工人這輪罷工的具體訴求,也大都不甚了了,所以無法產生真正的「理解」或「同情」。然而,就著應該如何面對「罷工」這事,不少來自香港的評論聲音,都著眼於與一種言論商榷,這種言論把「罷工」妖魔化為純粹自私的行為。這種「撐罷工」的聲音甚至以是否對「罷工」採寬容態度,作為香港移民是否真正能「融入」英國生活,了解英國的自由民主文化的標尺——如果「依然」對於英國竟出現罷工而大驚小怪,那不如「返香港」繼續做「港豬」吧了!
將英國工人罷工引伸到移民能否融入的問題,以致是否繼續是「港豬」的討論,當然是超越了一般的「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爭議,反而更多地表露出,罷工議題是緊扣著香港人身份認同在當下的掙扎。因為目前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絕大部分是因2019年那場運動而來的,所以他們實在無法抽離於那場運動的經驗,去面對當下在英國出現的罷工。
香港人要「返工」
想當年抗爭運動中形成了「和勇不分」的態勢,街頭的示威集會與勇武抗爭交替出場,把運動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抗爭者先後號召「三罷」,因為他們終於認識到,街頭激進示威已無法「升級」,而最「和理非」但卻又最有力的抵抗,正是全民可以參與的「罷工」、「罷市」和「罷課」。可是,「三罷」最終無法接上街頭勇武的棒,雖然中大和理大的勇武對抗是運動的「高潮」,但它們並沒有觸發大規模的「罷工」。這突顯出香港人生活的最優先選擇仍然是「返工」,運動也因此遇上了它最致命的發展瓶頸。
社會上長期缺少對「罷工」的積極態度和正當評價,使人們無法習得「罷工」的組織方法和動員技巧,也欠缺對參與罷工者所可能要承擔的風險和代價作出支援準備。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各方面的民權意識都不斷進步,但香港還是承襲著殖民社會的保守與反動,和資本家擁有鉅大影響力的遺緒。這導致在社會危機總爆發之時,社會力量面臨一場對決,但民間也只能夠匯聚力量參與街頭示威,實踐以肉體犧牲以明志,召喚社會同情共感,但遠未有足夠的條件和力度,去讓全民參與和當權者的對決。長期欠缺「經濟性罷工」去為「政治性罷工」作心理、文化以致組織上的準備,決定了2019年大型社會運動的終局——雖然它仍能在期後的醫護界為防疫問題而舉行的罷工中,留下局部成功的事迹。
當然,究竟「經濟性罷工」是否「政治性罷工」出現的前提,後者是不是前者的更高級、更成熟階段等等,都是勞工運動史上一直爭議不休的問題。上世紀之初,德國勞工運動界曾經熱烈討論過一個名為「總罷工」的構想,大意是指一場總的對決。既然是一次最後對決,「總罷工」需要長久準備,需由大量規模細小的「經濟性罷工」累積條件,加強工會組織,然後建立一個龐大的工會系統去精心協作和領導,「總罷工」才能付諸實行。但它一旦付諸行動,社會根本制度和政權的轉換就有可能實現。
對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
「總罷工」雖然首先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首先倡議,但後來上面這一套想法是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主流所持守的一套。可是,當俄國1905年促使沙皇讓權,成立國家杜馬(國會)的革命發生之後,知名的社會運動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就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發掘出「自發性罷工」的潛力,它們毋須按工會領導所構想的高度集中組織來領導。她認為這些「自發性罷工」對於社會動員和人民對權利的覺醒一樣有重要作用,而「經濟性罷工」和「政治性罷工」也不存在著誰先誰後,誰要作為誰的前提的問題,因為有時「政治性罷工」也可以倒過來促進工人加入勞工運動,在具體權益問題上參與「經濟性罷工」。
香港2019年所曾出現的「三罷」呼召,顯然是屬於「政治性罷工」的一種,甚至可以和當年德國及國際勞工運動所思考過的「總罷工」相提並論,只是「三罷」的呼召雖然和1989年支聯會等提出過的「三罷」有某種歷史連續性,但和「總罷工」相比,就顯示了它缺乏深刻的理論反思和研究。在兩個「三罷」口號出現的三十年之間,香港人對「罷工」權利和重要性的認識,進展其實極為緩慢,顯見1989年之後香港民主運動逐漸發展,但它未能打破香港人對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
可是,2019年的運動所留下來的並沒有被如此輕忽,雖然現在香港並沒有重現大型社會運動的氣候,但觀乎香港移英社群對英國本地「罷工」愈見包容,足見這轉變其實相當顯著。這更加可以在理論上印證,「政治性罷工」的經驗足可以成為人們更能接納「經濟性罷工」的基礎。
所謂「港豬文化」指的並不只是只管「食玩瞓」的生活態度,也包括了甚麼是權利,如何構成集體,怎樣看待「集體行動」等的認識。如果2019年前的香港最終極的「維穩」方程式,是全方位地排斥「罷工權利」,污名化「集體行動」,那由香港抗爭的(挫傷)經驗「讀入」(read in)英國的「罷工」事件,證明的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內涵正在發生變化,而非僅僅是是否「融入」英國社會的問題。它更說明了2019年運動的效應仍在延續當中,改寫着香港人的主體性。
▌[安徒行傳]作者簡介
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