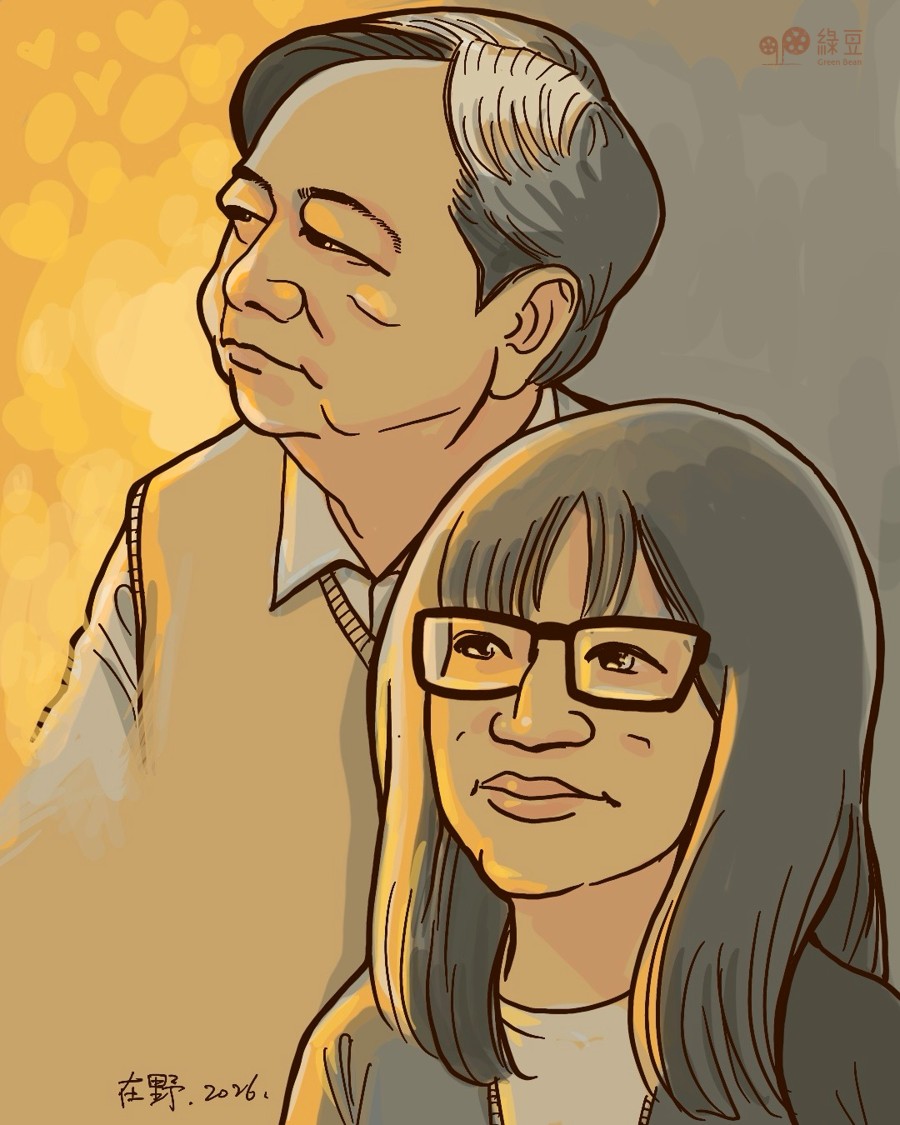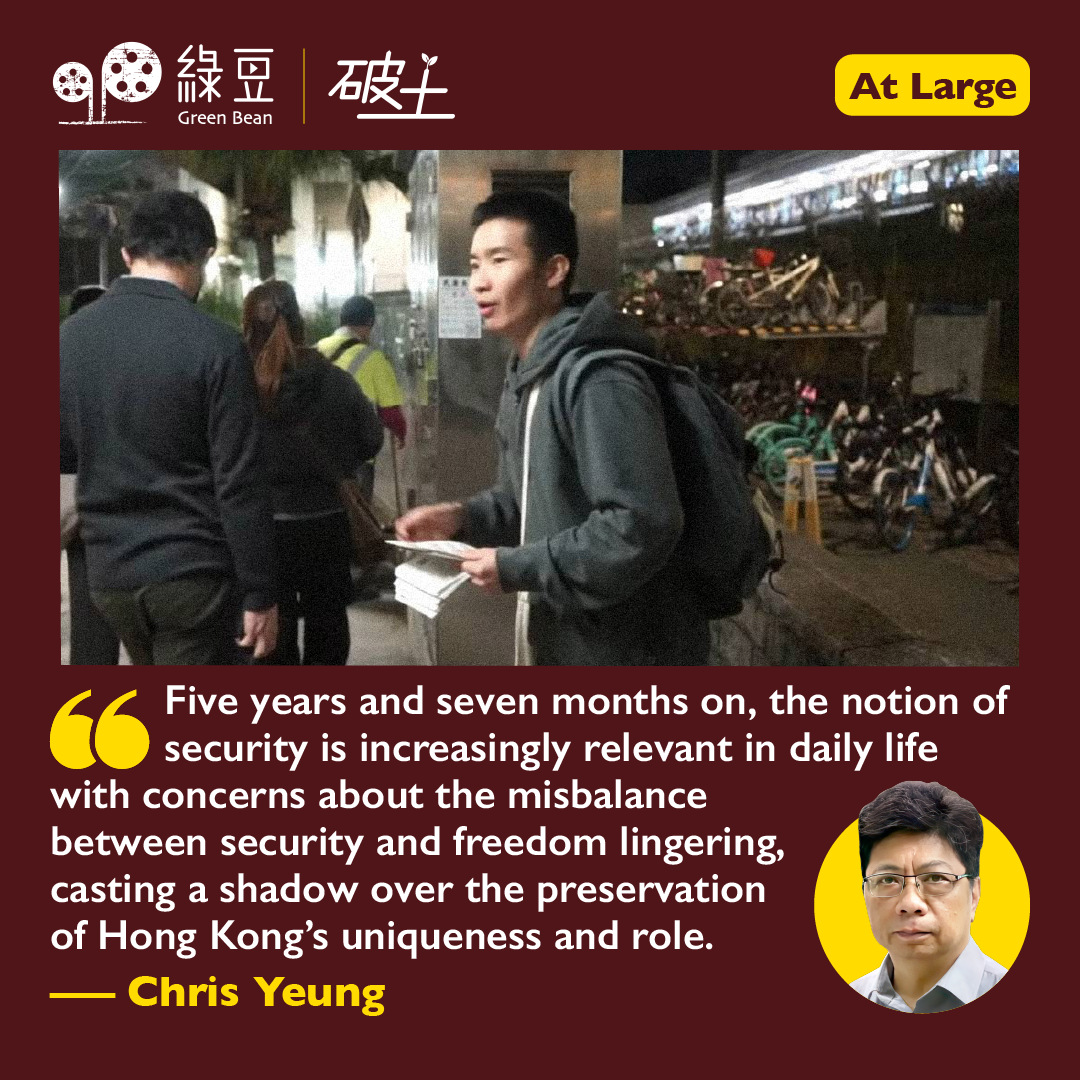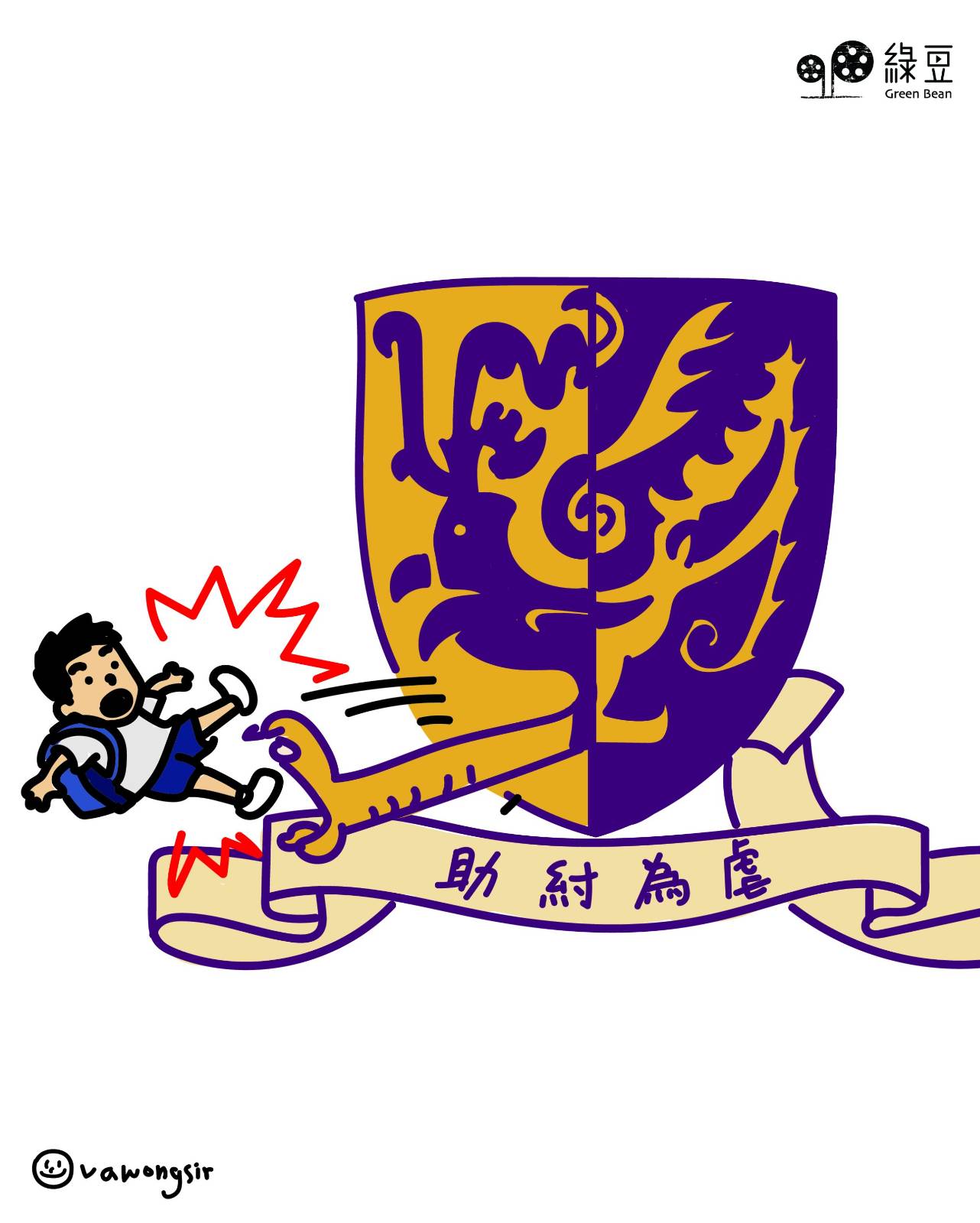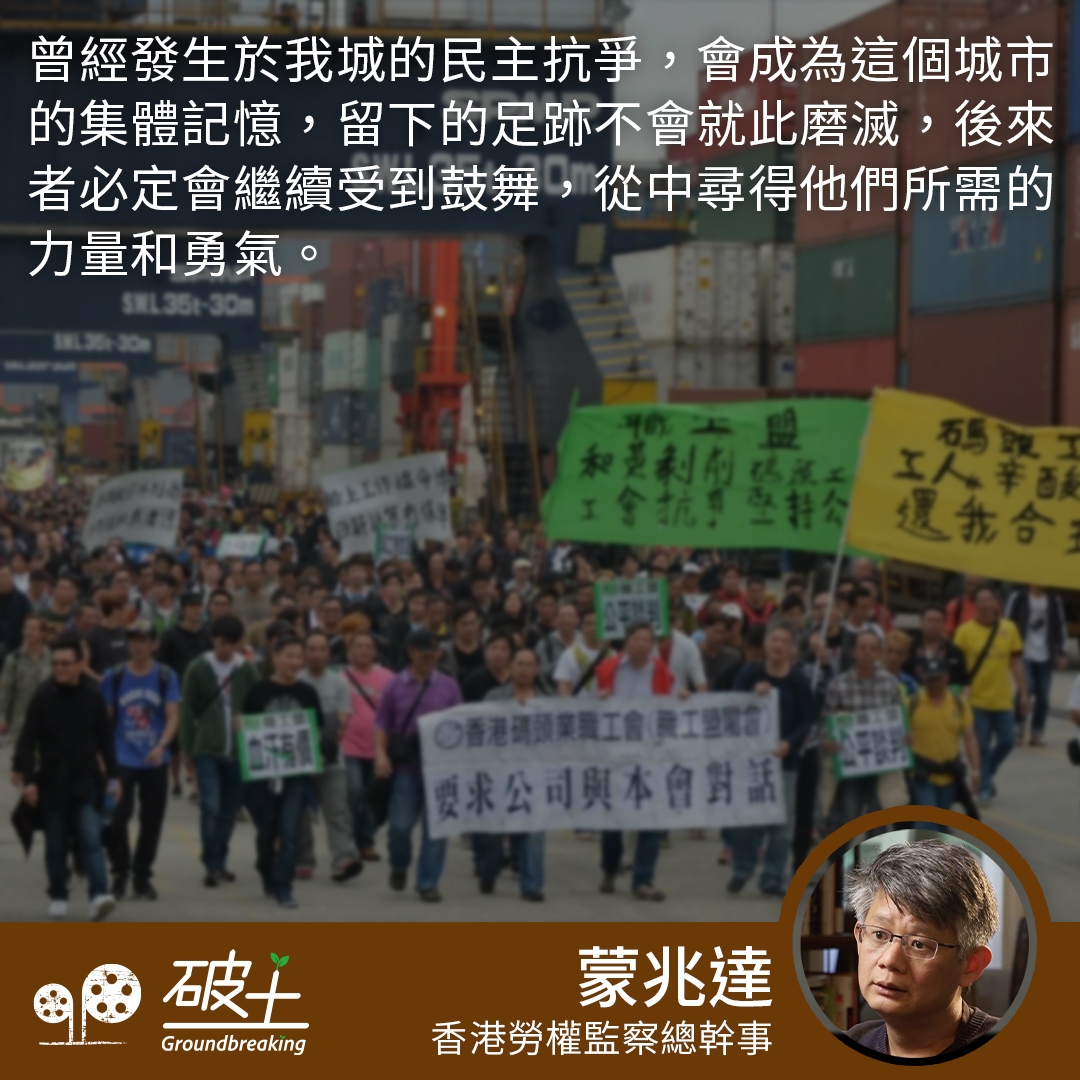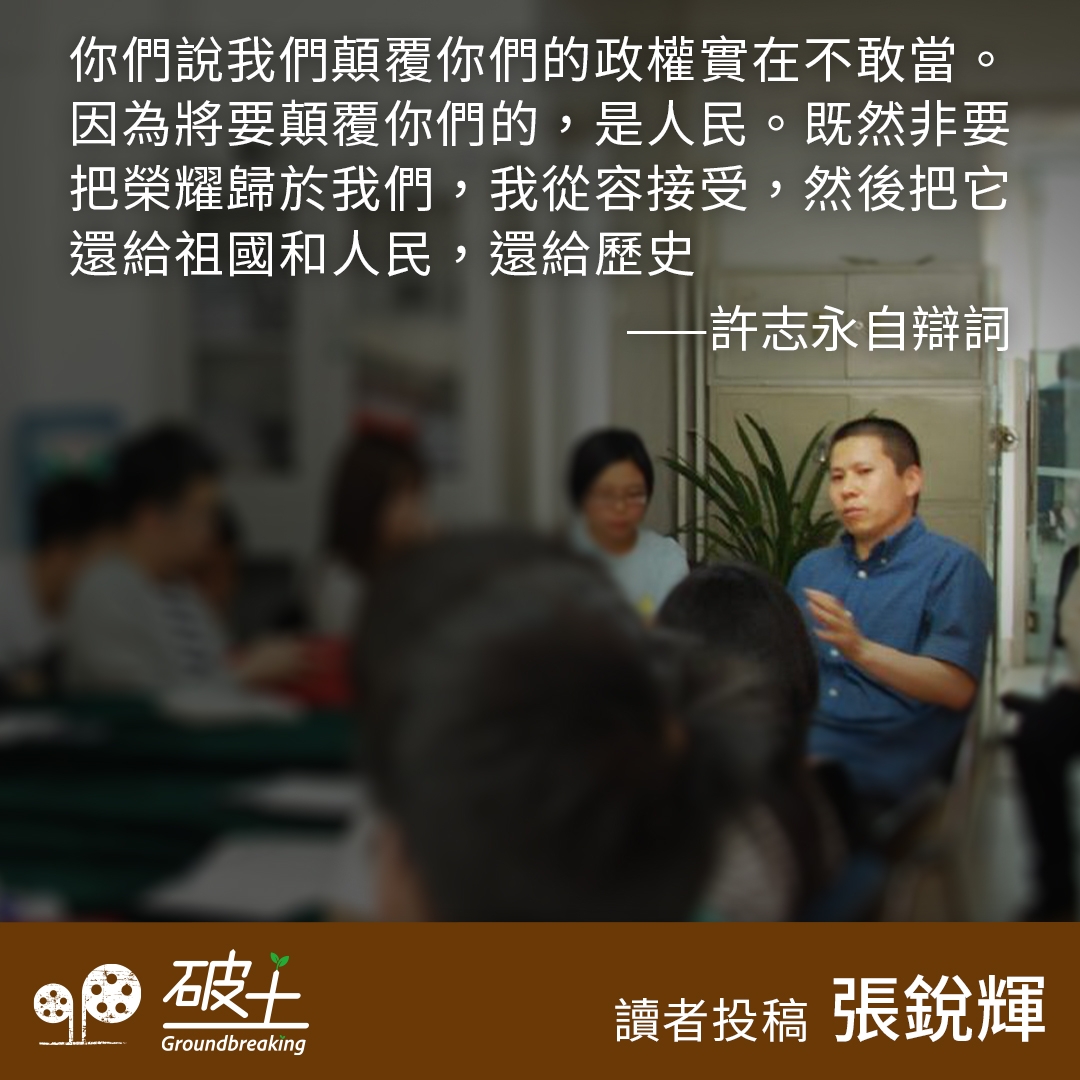立場新聞案與網絡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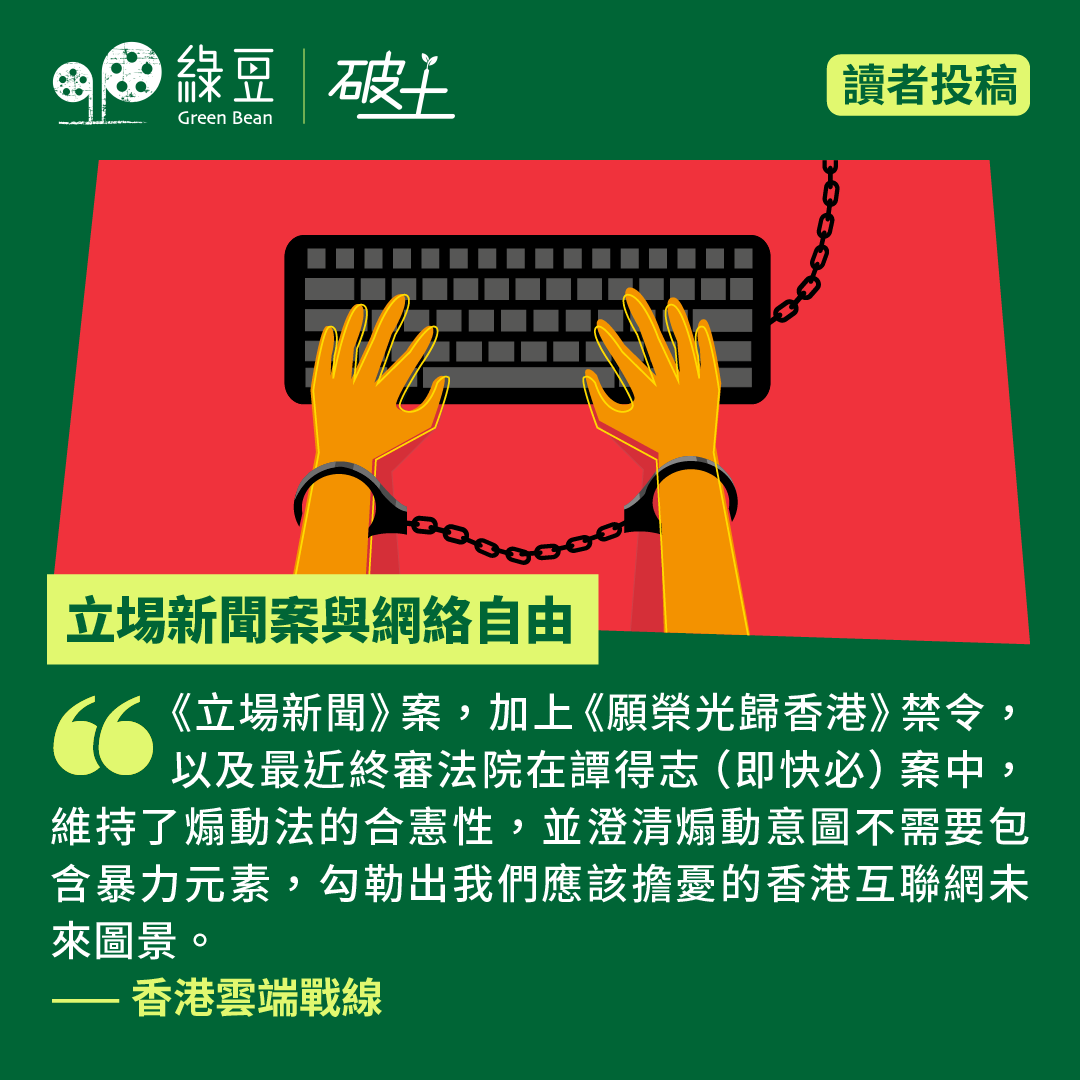
(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左中右各方讀者意見分享。)
2024年9月,《立場新聞》案件塵埃落定,兩位編輯被裁定煽動罪名成立,原因是他們允許在《立場新聞》上發表了一系列被認定為煽動性的專欄文章。
為什麼起訴編輯而不是逮捕專欄作者呢?事實上,大多數專欄作者要麼已經入獄,要麼流亡海外。《立場新聞》案件特別針對編輯和新聞機構的責任。
此案是否會對香港的新聞自由產生寒蟬效應,引發了人們的疑問。例如,《明報》曾致信提醒其專欄作者「遵守法律」。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表示,鑑於大家已在進行自我審查,該案可能不會產生強烈影響。然而,我們認為,《立場新聞》案件可能對新聞自由,甚至互聯網自由產生重大影響。
社交媒體平台的責任?
為什麼這樣說呢?畢竟,傳統上,新聞出版商和互聯網平台在法律上被視為不同的實體。傳統新聞出版商由新聞編輯擔任守門人,負責決定哪些內容可以發表,哪些不能。相比之下,互聯網平台,包括社交媒體,則是平台,通常不在發布前控制或審查內容,而是在發布後進行管理。
但這裡有一個思考實驗:如果被認定為煽動性的《立場新聞》文章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重新發布,會怎樣?鑑於《立場新聞》的編輯被判有罪,那麼社交媒體平台是否也要承擔責任?如果政府向平台發出請求,要求刪除這些文章,或要求提供用戶數據,平台會配合嗎?要找到答案,我們可以考慮《立場新聞》案件中的論點。
互聯網平台可能會辯稱,他們與新聞出版商不同,沒有編輯流程。但這一論點站不住腳,因為《立場新聞》的裁決明確表示,意圖並不重要。此外,當將算法納入考量時,互聯網平台是否具有編輯流程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算法被用來決定您的資訊流中出現什麼,向您推薦什麼。在香港,互聯網平台因其算法而被追究責任的案例並非沒有法律先例:2018年,香港法院在楊受成訴谷歌案中裁定,互聯網平台對谷歌(Google)自動完成搜索關鍵字負有責任。
互聯網平台還可能辯稱,考慮到在熱門互聯網平台上共享和發布的內容數量龐大,相關文章的數量微不足道。《立場新聞》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在發布的超過20,000篇文章中,只有11篇被指控具有煽動性,應該考慮整個新聞平台的情況。但控方成功地說服法院,文章的數量並不重要。相反,控方認為17篇文章應被視為煽動性,法院認定其中11篇是煽動性的,這足以定罪出版商。
也許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法官接納控方的說法,意圖並不重要,出版商在允許發表有問題的文章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魯莽(recklessness)就足夠了。互聯網平台需要做什麼才能避免被視為魯莽從而承擔責任?在收到香港當局的請求後,刪除有問題的內容是否足夠,還是甚至需要在沒有政府提示的情況下主動監控可能具有攻擊性的內容?
香港互聯網未來圖景
也許當今香港當局最強大的工具是《國家安全法》。根據相關法例的第43條,如果他們認為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信息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當局有權要求平台刪除內容。
這一切對香港的互聯網自由意味著什麼?我們認為,《立場新聞》案提出了超越新聞自由的問題,我們需要開始思考它如何影響互聯網平台在香港的運作。
我們已經看到,谷歌遵守了香港當局的禁令,限制網民瀏覽《願榮光歸香港》的影片。我們還看到了此案的寒蟬效應:在谷歌決定遵守禁令後,各音樂發行商要求串流媒體平台刪除該歌曲,以避免承擔責任。《立場新聞》案,加上《願榮光歸香港》禁令,以及最近終審法院在譚得志(即快必)案中,維持了煽動法的合憲性,並澄清煽動意圖不需要包含暴力元素,勾勒出我們應該擔憂的香港互聯網未來圖景。
乍看之下,香港的互聯網現在似乎仍然相對自由,特別是與中國內地的互聯網相比,但自我審查的陰影已不斷伸展。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合理預期,當香港當局向互聯網平台發出審查請求時,這些平台可能會限制在香港的存取,甚至會直接將內容下架。這似乎已經成為今天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代價」,而這個代價,互聯網平台似乎已經接受,甚至願意支付。我們只能希望我們是錯的。
不久之前,互聯網平台曾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以保護香港的互聯網自由──他們宣布,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暫停處理來自香港政府的所有用戶數據請求。我們可以對平台的動機持懷疑態度,但事實上,他們有時候確實會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只能希望,當香港政府再次向他們發出審查請求時,他們仍能展現出當年同樣的道德勇氣。
( 圖 : 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