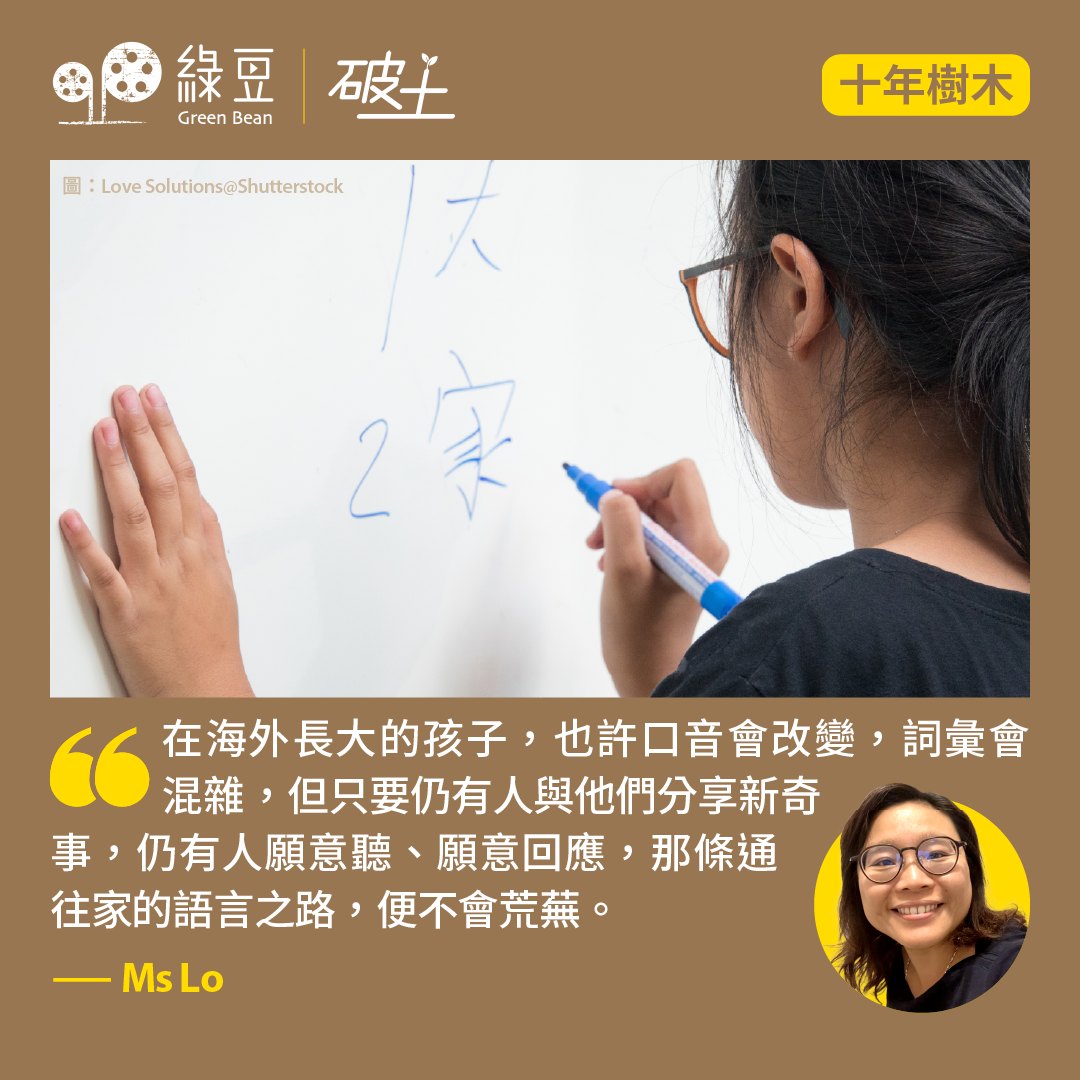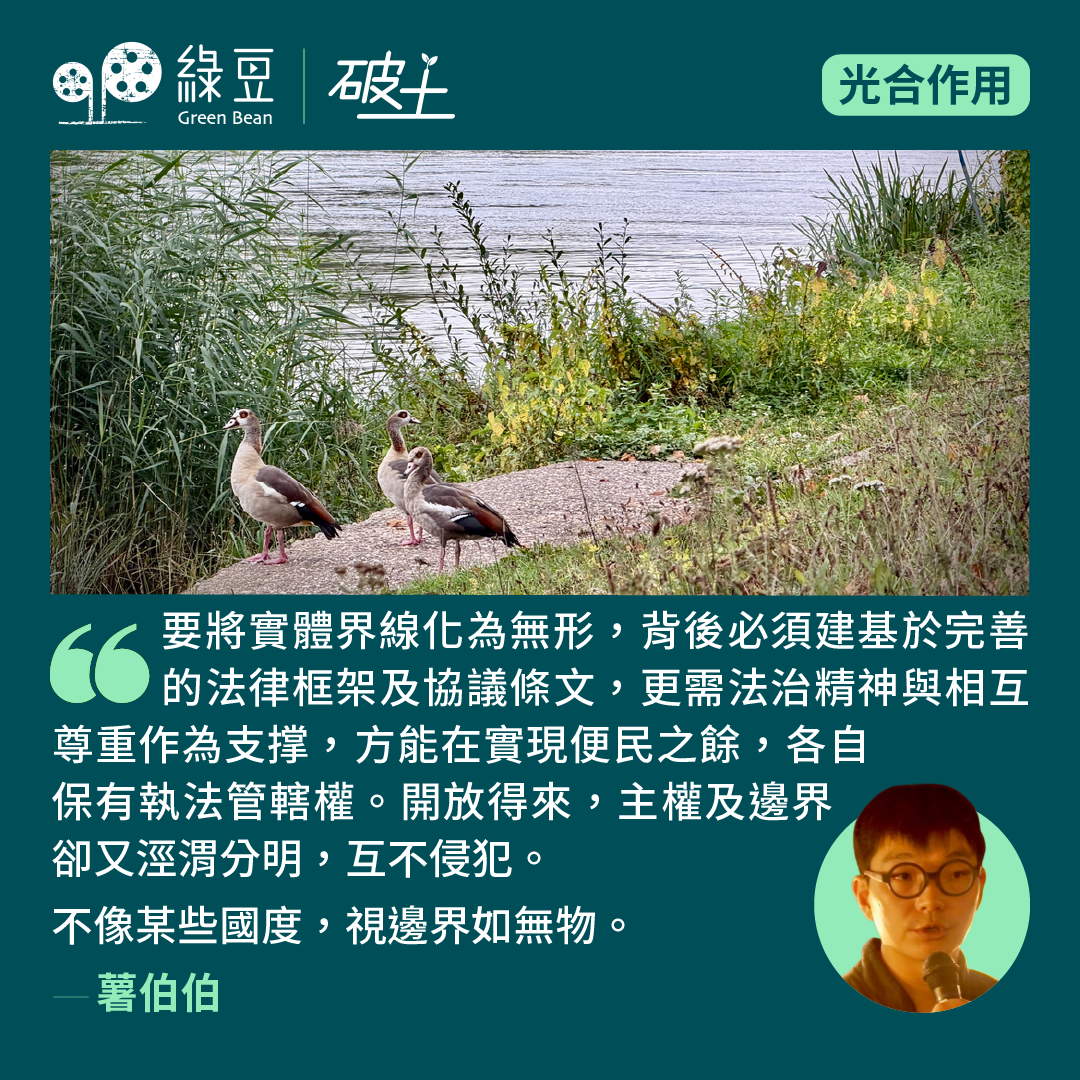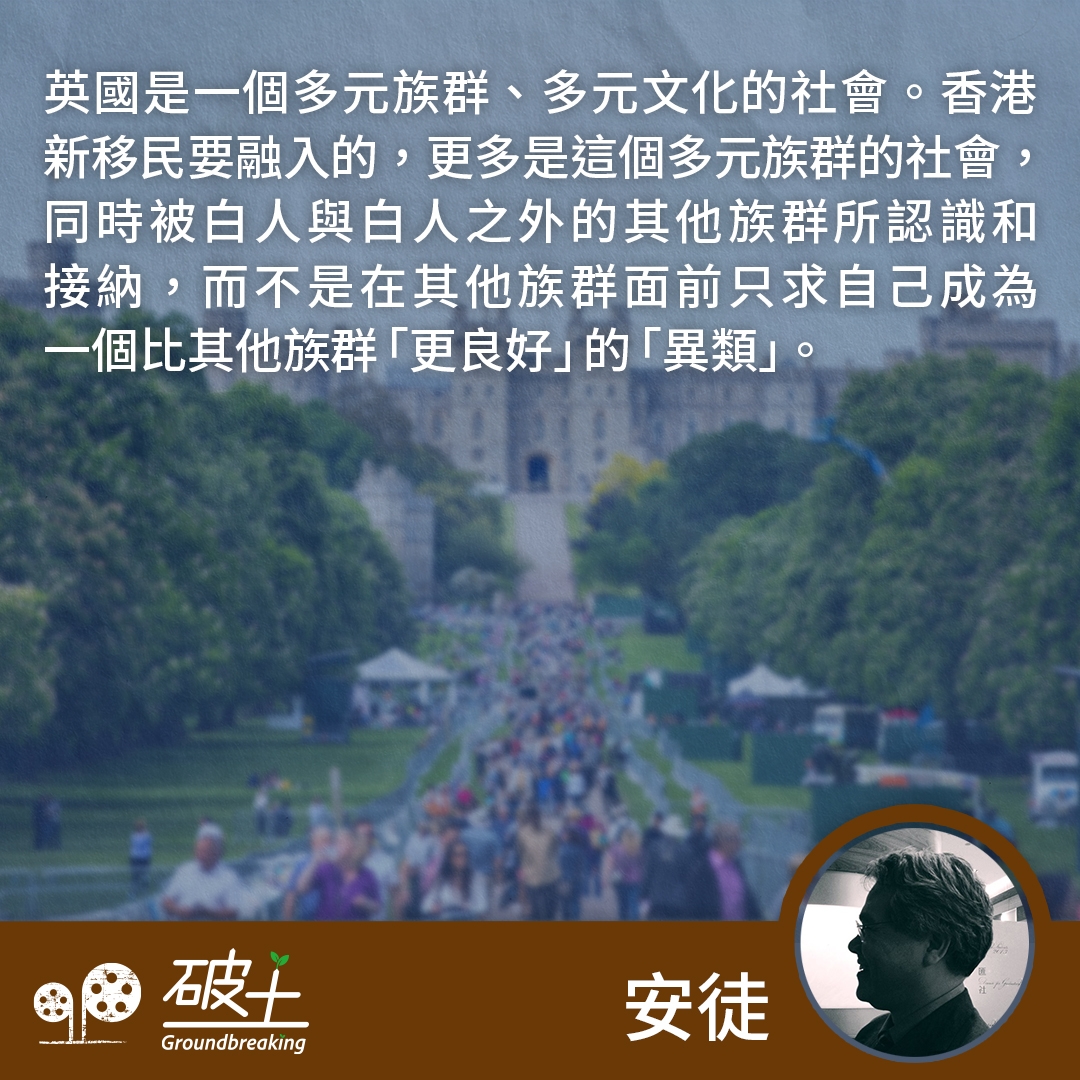白紙革命的時代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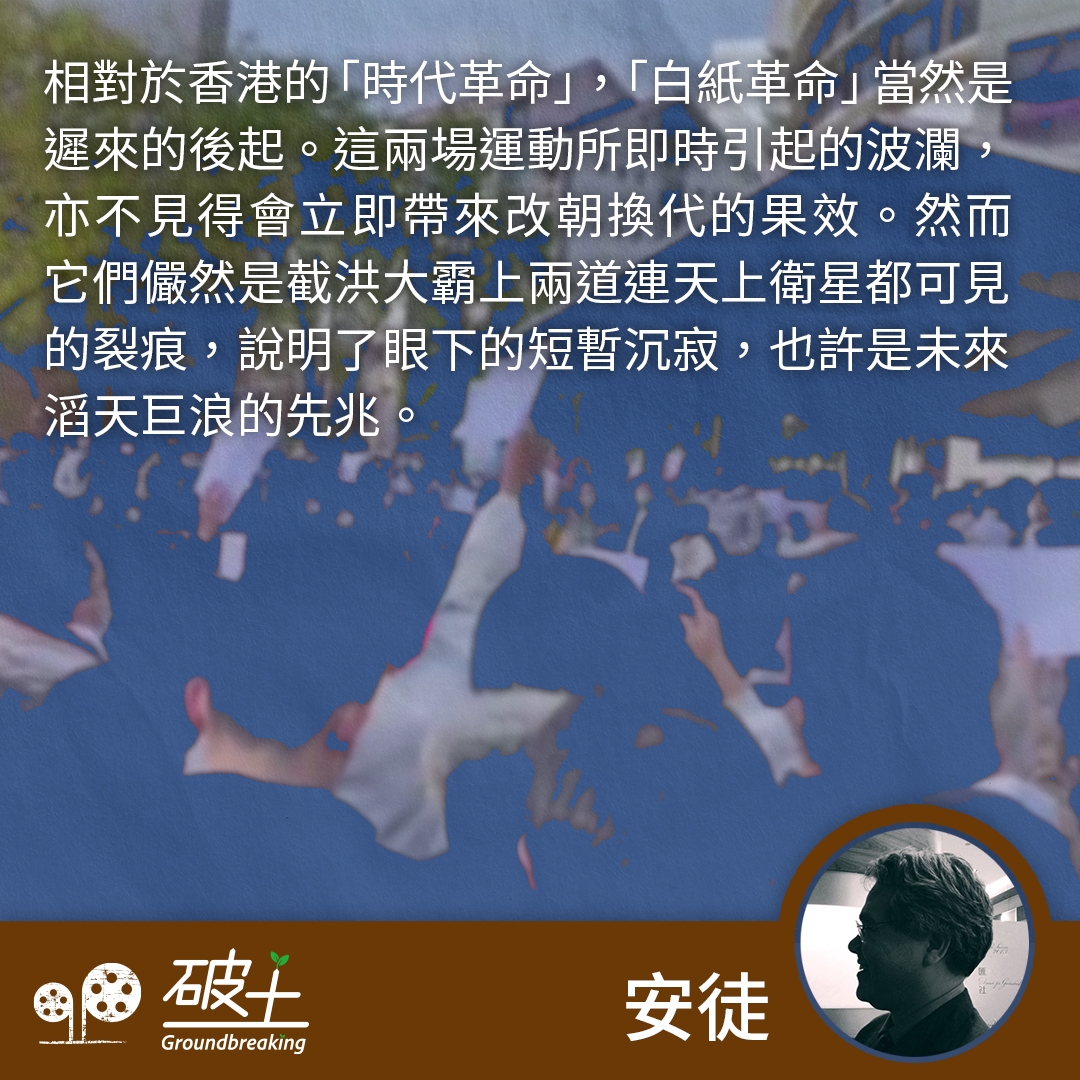
中共二十大剛剛「勝利」閉幕,中國大陸卻接連爆發罕見的抗議示威浪潮。各地群眾不單自發衝擊防疫的設施和關卡,與「大白」們發生肢體衝突,騷動紛起。鄭州更發生富士康工人的反抗,繼後全國多家大學的學生亦互經串連,掀起三十多年來未見的學生運動,帶頭以高舉白紙作為抗議方式。更加有不少地方,抗議者高叫「不自由,毋寧死」,「習近平下台」等口號。連香港也有不少內地來港的學生走出來參與抗議活動,一改過去他們都只是一班盲目愛國的「小粉紅」形象。這連串抗議活動,被稱為「白紙革命」。
如此一幅民怨沸騰,烽烟四起的圖像,當非剛好完成永續執政大計的習近平所樂見。然而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中共竟然只敢私下抓捕勇敢發聲的參與者,卻未見嚴辭反擊,高調壓下這股「反動逆流」,反而急急在各地取消早前嚴苛的「清零」防疫措施,似乎是不想高調地將事情繼續鬧大,不想給人「強力鎮壓」的印象。
一時之間,香港高官鄧炳強的嚴防「顏色革命」論反成孤家寡人之調,趙立堅在外交部新聞發報會上長達數十秒的無言以對,竟成鄧炳強最妙的和音。
這種不言退讓的「退讓」底下, 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但叫停清零政策的目標,似乎已稍見「成功爭取」。雖然中共執政地位絲毫未損,習近平依然可以自我陶醉於他當「人民領袖」的幻覺,但是中共今次懾於群眾壓力而作出戰略退卻,無疑是為日後的民間抗爭打開了一扇窗。
抗議浪潮帶前所未有政治色彩
其實,把中國民眾都想像成心甘情願馴服於現狀的奴民,基本上是一種錯覺,甚至是為了維穩而刻意散播的假像。因為根據中國社科院自己公佈的數字,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徘徊在數萬甚至十數萬之間。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還持續上升,一直至2014年才開始在加大的維穩措施下下降。這些措施包括限制NGO的活動,抓捕維權律師,嚴打上訪,煽動「小粉紅」型的民族主義等。今次「白紙革命」的爆發,一方面是承繼和擴大了這股內部不斷積壓的群眾不滿,但另一方面卻萌生出重要的新意義。
其中最突出的是,今次抗議浪潮以跨族群、跨地域、甚至跨階級的方式爆發,而不是過去那種個案形式的抗爭。再者,大城市爆發了集體的公民行動,這些行動直接以人權、自由、民主及公民身份的概念,為抗爭帶來前所未有政治性。當中甚至出現了挑戰地區居民組織在防疫工作上濫用公權力,這雖然尚不是全面的體制改革訴求,但已經說明中共過去十年發展出來的社區「網格化」管控,不但無法消弭,反而加深了人民的不滿。另外,雖然各地學生明顯有串連的舉動,但行動毋須領袖,沒有「大台」,更沒有談判代表,極似香港2019年的「如水」運動。
中共剛愎自用令民心生變
雖然有一些香港人對於大陸人當年反對抗爭,支持官方鎮壓「黑暴」耿耿於懷,冷言「你哋都有今日」,可是亦見有大陸人聲稱後悔當日的態度,於今方知自由、民言、人權之可貴,覺今是而昨非。究其實,又有多少人真正既是今日的抗爭者,又是三年前真的嘲笑過香港人的「小粉紅」?還是當年他們只是怯於時勢,想支持香港又不敢發聲?
事實上,中共這三年剛愎自用的防疫政策,所引起的經濟動蘯和社會衝擊十分巨大,在民心民情的領域產生了質的轉變絕不奇怪。昔日可以盲目地愛國,三年後也可以呼喊習近平下台,皆因「清零暴政」幾乎把每個人都當成專政對象。當你肉身感受過專政權力的任意欺凌,方知人的基本權利可貴,又怎能再自我陶醉於「制度優越」的意識形態迷湯?
昔日中共的統治,靠的鼓動群眾的「革命熱情」,人們信仰只要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可以實現烏托邦式的未來。文革悲劇打破了幻象,暴露了極權統治的殘酷現實。鄧小平就以改革開放,分享經濟發展紅利來穩住人心。青年學生希望政治改革能夠齊頭並進,可是中共專政本色不變,釀成六四悲劇。中共於是放棄舊式極權主義的老套路,不再問「姓資姓社」,讓人們加深迷醉於消費主義,政治上自我麻醉,容讓專政繼續,充分實現哈維爾所言的「後極權主義」。
在「後極權主義」之後
中國式「後極權主義」只要求人們服從於「大國崛起」的美麗謊言,默認中共以「威權治國」。可是,新冠疫情打破了「後極權主義」的既有秩序。皆因習近平好大喜功,以為單憑黨人意志就可以消滅病毒,不惜犧牲人們的生命安全,破壞社會信任,顛倒生產運作,終於再次暴露出極權主義統治的野蠻本性。
於是,「小粉紅」型的新一代可以對當年的「大躍進」 無感,但對中共今日的「防疫大躍進」的荒謬卻不能無動於衷。因為「美麗新世界」的謊言被戮破後,人們即見「1984」的真實慘狀。在「後極權主義」之後,原來是更為可怕的「數碼—生物極權主義」(digital-bio. Totalitarianism)。
相對於香港的「時代革命」,「白紙革命」當然是遲來的後起。這兩場運動所即時引起的波瀾,亦不見得會立即帶來改朝換代的果效。然而它們儼然是截洪大霸上兩道連天上衛星都可見的裂痕,說明了眼下的短暫沉寂,也許是未來滔天巨浪的先兆。
▌[安徒行傳]作者簡介
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