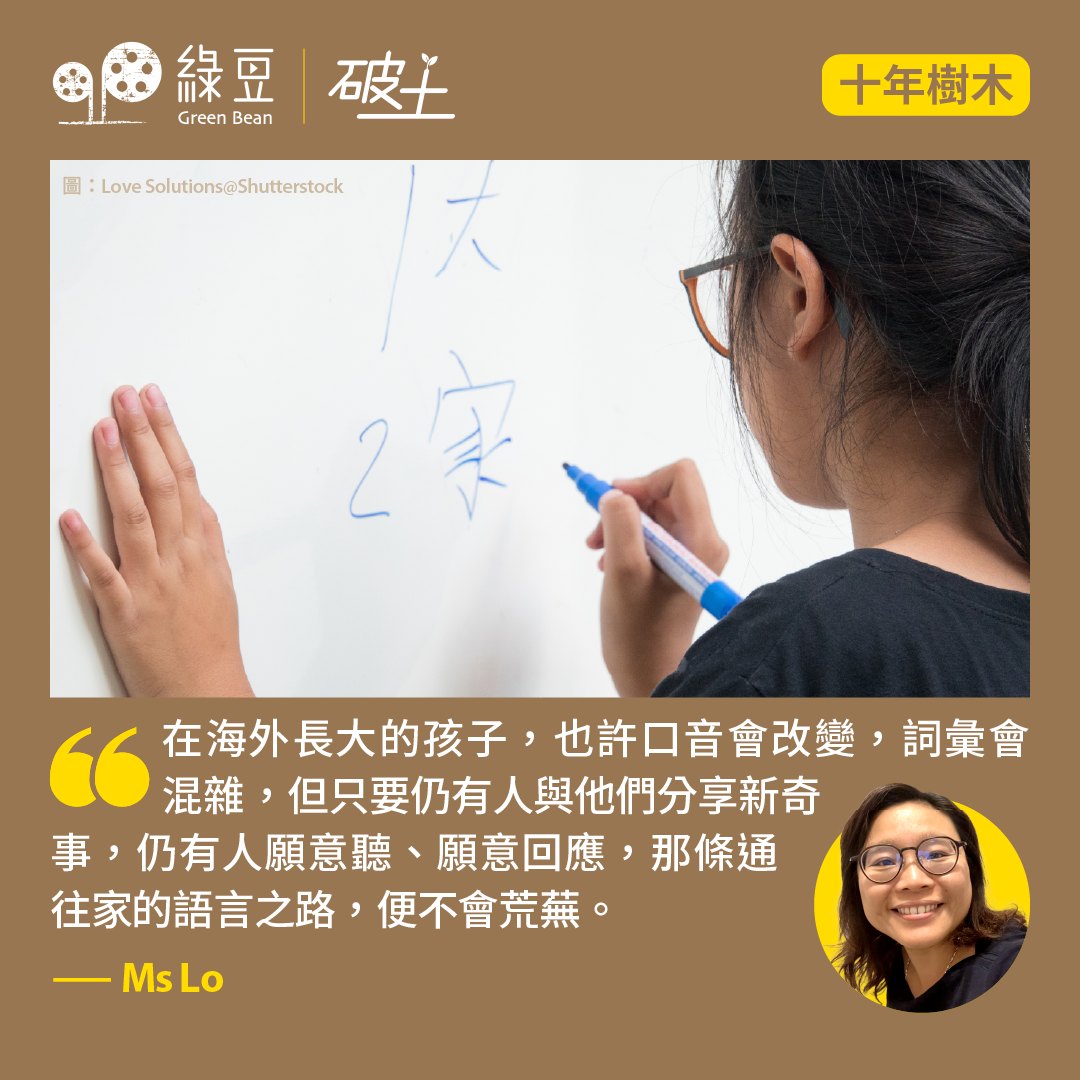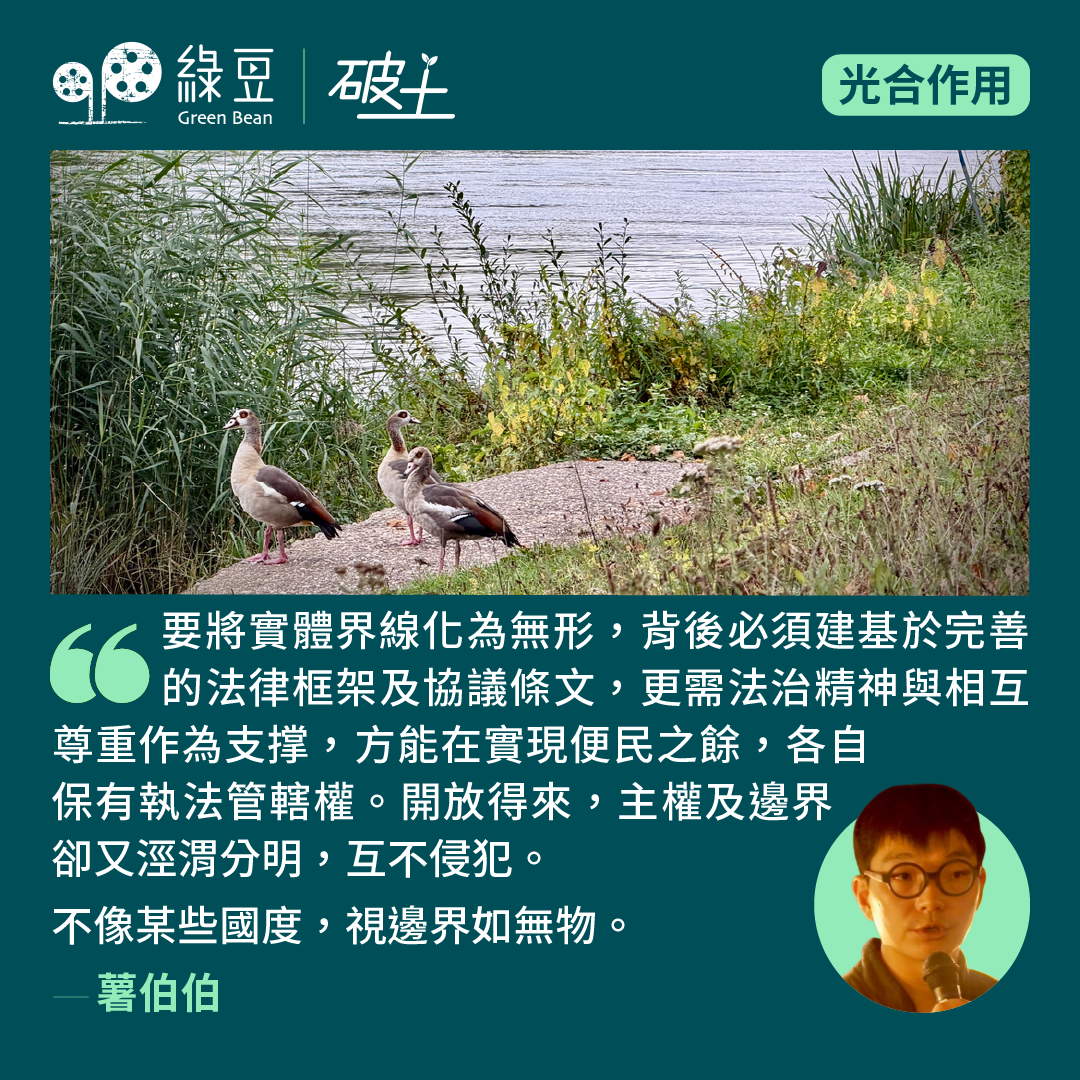物於物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這年頭的移民浪潮,不少人離開自己的故鄉,搬到另一個國度。搬家,從來都是一個重新面對自己生活,去與捨的過程。
但如若在你離開時只能帶上一個盒子,你又會放進甚麼?
在我離開香港之時,我只能帶上35KG的行李。收拾行李那晚,我一邊擔心著警察隨時上門敲門,一邊站在28吋行李箱前躊躇不已。對於流亡是怎樣的一回事,我毫無概念,只感到這兩個字重重壓在心頭。我惟有將這當作是一次長遊,或出於港人愛旅遊的特性,才成功逼使自己本能似的把衣服和日用品收拾好。唯獨這一次,我深知是一趟一去不返的旅程。
很快我就把半個行李箱填滿,我繼而環視屋內四周,看著那年生日他給我送上的乾花、第一次獨遊蒙古時買下的棋盤、在深水埗某間二手小店找到的古董檯燈。這些我都沒可能帶上,但同時亦留不下,因為在我離開後,家的租約亦會隨之中斷。在無預兆和迫切的逃離中,獨居的我沒有時間與空間安置這些物品——這代表著我要將行李以外的全屋家品分置給朋友,甚或捨棄。
「分身家」
很多東西還可以再買,但盛載記憶的物品不可復有。於是,我從衣櫃底取出多年的「寶物盒」,把友人寫給我的卡、明信片和寶麗萊全都塞進行李箱。敏感的資料,我點起火逐張逐張銷毀,最傳統的方法最安全。我還以為這只會是在黑社會電影中出現的情節。其餘的家品,我貼上了一張張memo紙,上頭寫上不同朋友的名字,望為珍重之物找到新的主人。
帶走的還包括獄中友人們寫的信件。如此一別,隔著國家與高牆的距離,我不知再見會是多少年以後,信件會是我們僅剩的連結。我甚至害怕萬一自己在出境時被捕,信件會被連帶充公,而漏夜把信件一頁一頁複印,只帶上複印本。看著信上的筆跡,不禁慨嘆這年在朋友陸續入獄之後,一直替他們處理退租和整理物品等後續事,我還常在探監時故作輕鬆地向他們笑言,在「分家產」的過程中我取得了甚麼戰利品。當初從他們家裏拿到的,現在又將連同我屋內的一切被「分身家」,實在唏噓。
擁有的不是人與物
那晚絕望與孤獨感彌漫整屋,我似是在回顧自己出生至今走過的痕跡。我整夜沒睡,一直收拾至清晨的陽光灑進屋內。貼滿整屋的粉色memo紙,隨著窗外吹來的風飄揚,一陣蒼涼。最後,我把床頭的毛公仔用一層層保鮮紙包裹(公仔也要防疫😷),決定抱著它上機,作我流亡路上唯一的陪伴。

萬般帶不走,我跟曾努力累積的一切告別。25年的人生,濃縮成一個行李箱。移民,或還有新的生活可期待;流亡,卻不知去向何處,看不見未來。離開後的一段時間,我只感到事業、朋友、愛情、物品,什麼都留不住,喪失了生活的所有。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一場突如其來的斷捨離,也讓我領悟了我們擁有的從來都不是一件物與人,而是與那人那物共處的時間。當你全然投入,你就全然擁有。曾在香港歷過的每個偶然與剎那,讓我擁有了一個記憶豐盛的世界,在無常中成心中的永恆。
▌[尋庇護]作者簡介
過著流亡生活、前景未明的在英尋求政治庇護者或他們的過來人,透過綠豆的破土——這塊自由土壤發聲,以專欄「尋庇護」講述自身的故事、申請政治庇護時遇到的種種程序上、生活上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