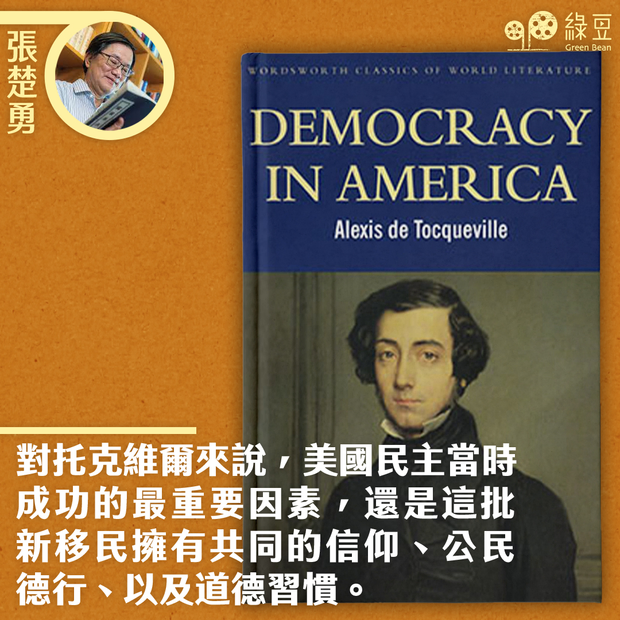為什麼服從政府?—-David Hume論原初契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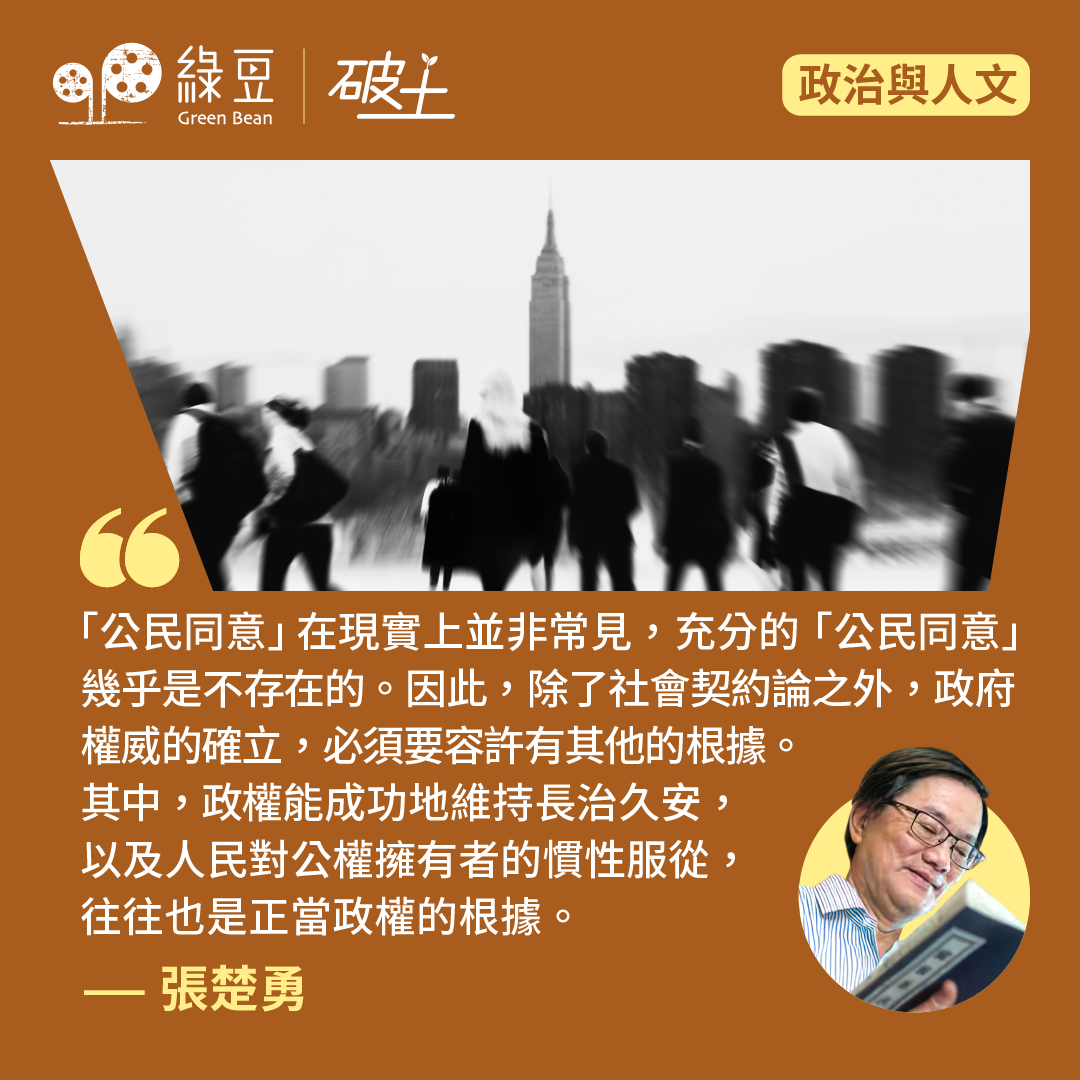
現代政治的一個主流論述,是政權的正當性得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
「公民同意」的理據,簡要說來是這樣的。政府之所以有權作出強制性的集體決定,例如立法、制定政策、推行政令,是因為政治社群中的個人,為了有穩定的秩序,讓大家和平共存,便得在社會上實施集體而共同的規範使大家遵行,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等無政府狀態。大家因此同意,放棄部分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並推舉一些人有權去行使公權,掌管公職,以便公正地保障社群各成員的安全和促進社群的福祉,制定法律和規範性措施,以應付集體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社會契約論
根據這種看法,正當政權的建立,正是從這基礎引伸出來的。社群中的每一個成員據此同意服從政府為集體所作的決定,並承認其權威和公權力。我們一般稱這種說法為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把政權的公權力及其權威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但是,假如政府未能履行社會契約中的要求,公正地保障公民的安全、生命、財產、權利等等,公民便沒有義務繼續服從政府,嚴重者公民更有反抗的權利,革掉暴政的命。
社會契約論處理的根本政治課題是多樣而繁複的。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論述更是博大精深,是任何想認真了解現代政治的學人必須好好地去鑽研。我這篇短文,自然無法對這些課題和論述觸及於萬一。
有留意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發展的讀者大概都知道,與社會契約論有關的幾位最重要的經典理論家,是英國的Thomas Hobbes和John Locke,以及法國的Jean-Jacques Rousseau。不少論者認為,這理論開啟了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因為人類政治的重點,從此由集體轉向個人,以個人同意、權利、自由等為公權力和政治權威正當性的根據,取代了以前的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也把優良管治的要求,從追求至善的社會,轉移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從而開創了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的格局。
「公民同意」是否必須?
對於社會契約論中「公民同意」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批評,也許可以簡述如下:假如政權能有效地為政治社群帶來穩定和秩序,使各成員和平共存,遵守共同的規範,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的無政府狀態,那麼,「公民同意」是否必須的呢?就算「公民同意」在正當政權的建立中是可取的,但「公民同意」是否唯一的正當政權的根據?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看看18世紀蘇格蘭的重要思想家David Hume在他的名著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關於原初契約〉) 一文是怎樣論說的。
Hume在討論社會契約論時提到,如果說政權的起源,是來自先民同意的一份原初契約,要在歷史上和紀錄中找出這份契約來證明此論說的有效性,大概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份契約幾乎肯定地是遍尋不獲。但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社會契約論是完全不合理。相反,Hume認為,如果從人的本性來進行思考,基於在初民的時代,個人不論就其體力還是智能而言,大家的差距實是很少,甚至可以說是接近平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任由個人不受限制地行使其與生俱來的自由,以滿足其欲求,人與人之間便很容易紛爭不斷,難以形成穩定的社群;沒有有效而穩定的社群力量,個人的安全和自由便缺乏有力的保障。因此,人們如果基於上述考量組織起社群,並同意服從於一個共同的政治權威,願意放棄個人部分與生俱來的自由,遵從政治權威制定的法律和指令,以保障個人的安全和維持社會穏妥的秩序,並以此作為公權力的正當性及其管轄範圍的根據,這種說法在現實上並非不可能,在理論上也並非沒有道理。
習慣了長治久安
不過,Hume同時指出,上述的「公民同意」論是不完備的。當政府在紛爭或衝突中遇到不服從者的時候,它往往得訴諸集體的強制力以消弭這些不服從或選擇抵抗到底的力量,否則,有序和依法管治的政府便難以確立。如果後者不能建立,紛亂的政治是容納不了多少「公民同意」的成分的。但是,到了相對有序和依法管治的社會因為種種機遇和因由得以形成,並且能持續不斷時,人民也許已因為習慣了長治久安而逐漸慣性地服從政府的管治,使其正當性和公民同意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
因此,政府權威的建立和維持,往往涉及到人們對有效政府和長治久安的需求,以及人民在這種情況下的習慣性服從。因此,社會契約論中的「公民同意」,對Hume來說,並非是政權正當性的唯一可取或不可或缺的根據,在現實上甚至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根據。
現實上並非常見
Hume認為就是退一步說,假如世上真的有所謂原初契約的話,先民的同意也不能更不應自動轉移到今天的公民身上。Hume指出,從已知的紀錄來看,歷史上世界大部分的政權在建立之初,往往不是由征服所得,便是由篡奪而來,有些時候甚至是兩者兼備。如果這些政權成功地延續下來,人民多習慣性地服從政府並承認穩定政權下帶來的長治久安的好處。就是在一些後來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其先前的歷史,不少也離不開征服或篡奪。另外,實行選舉的政權,其政治和社會精英在當中所佔的主導地位和影響,跟嚴格而充分的「公民同意」還是距離很遠,何况就算是這些政權,也是不容許敵對勢力存在的。
Hume提出以上的質疑和補充,並非是要完全否定「公民同意」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根據。他的觀點是:「公民同意」在現實上並非常見,充分的「公民同意」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除了社會契約論之外,政府權威的確立,必須要容許有其他的根據。其中,政權能成功地維持長治久安,以及人民對公權擁有者的慣性服從,往往也是正當政權的根據。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