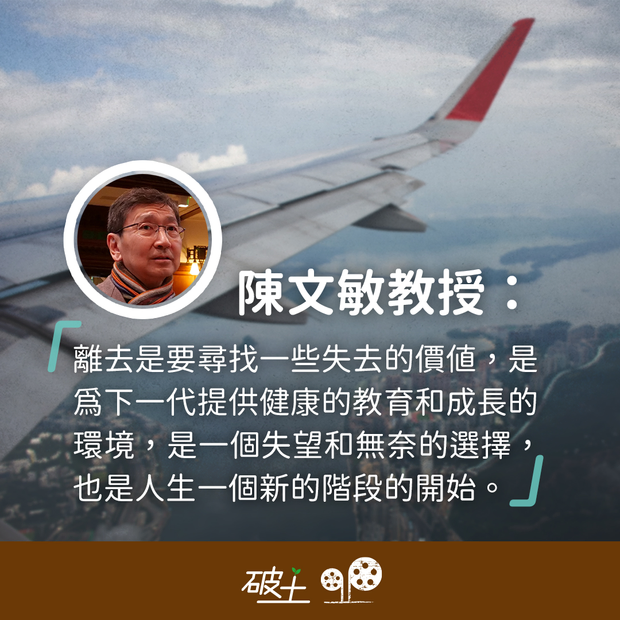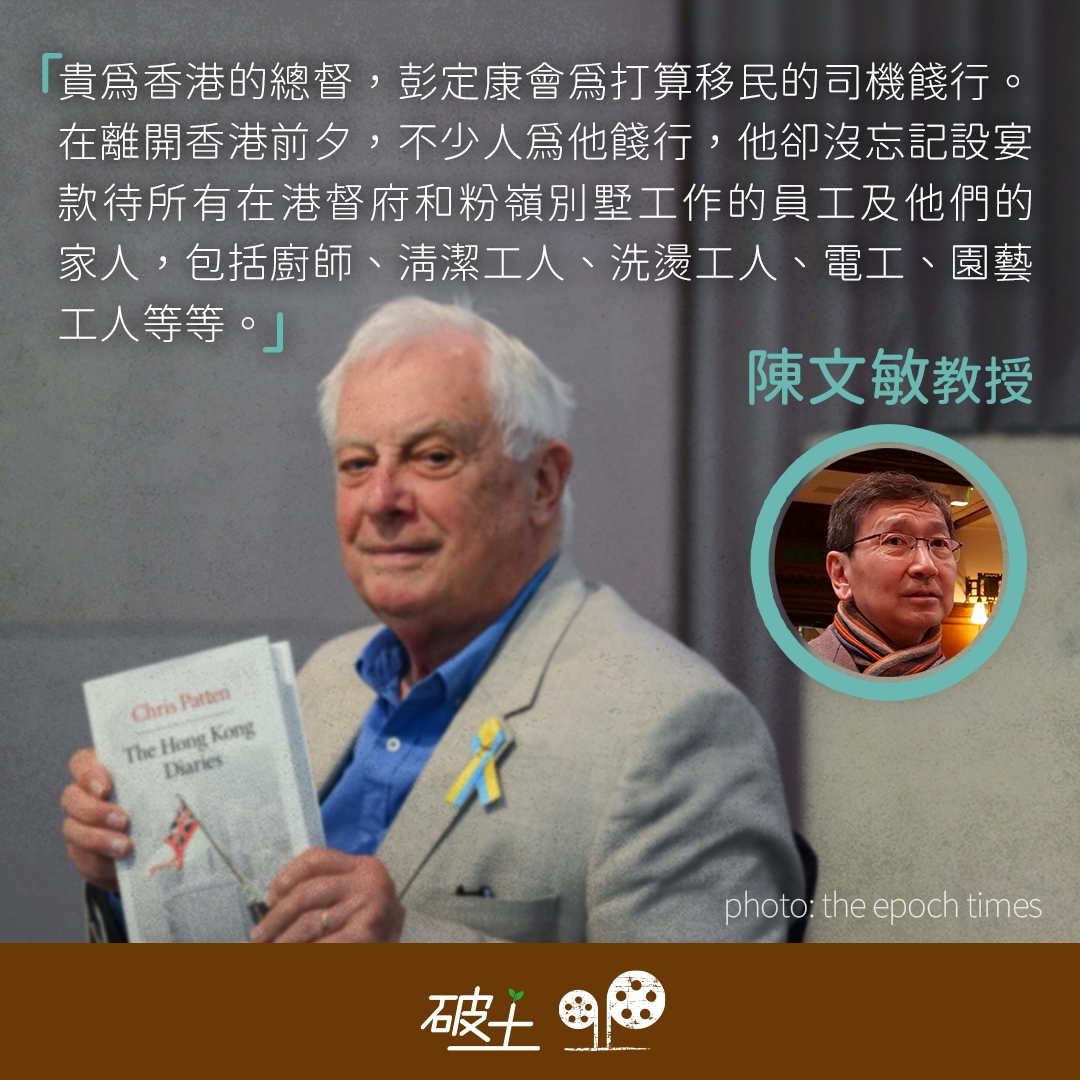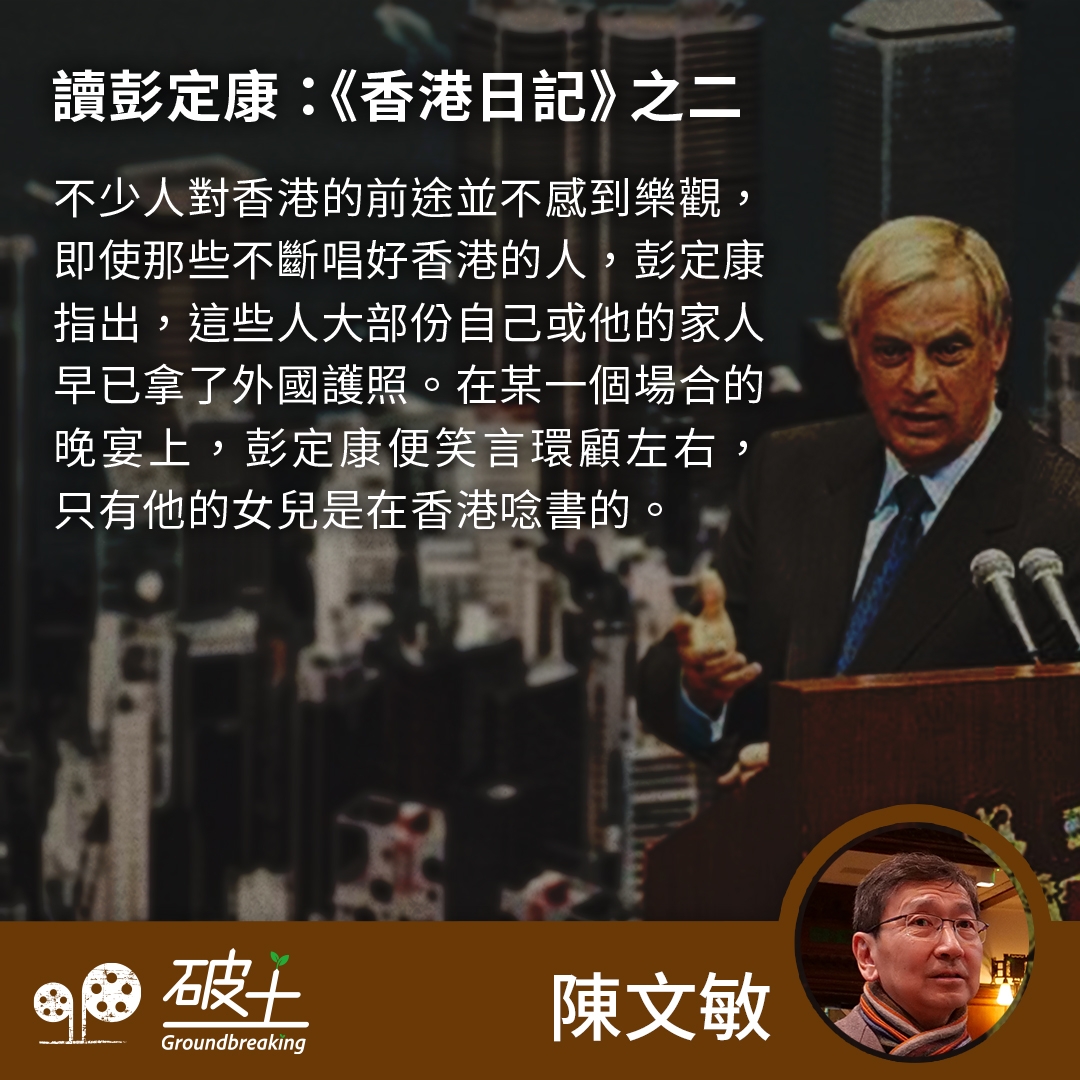從林卓廷廉署案看法院對法律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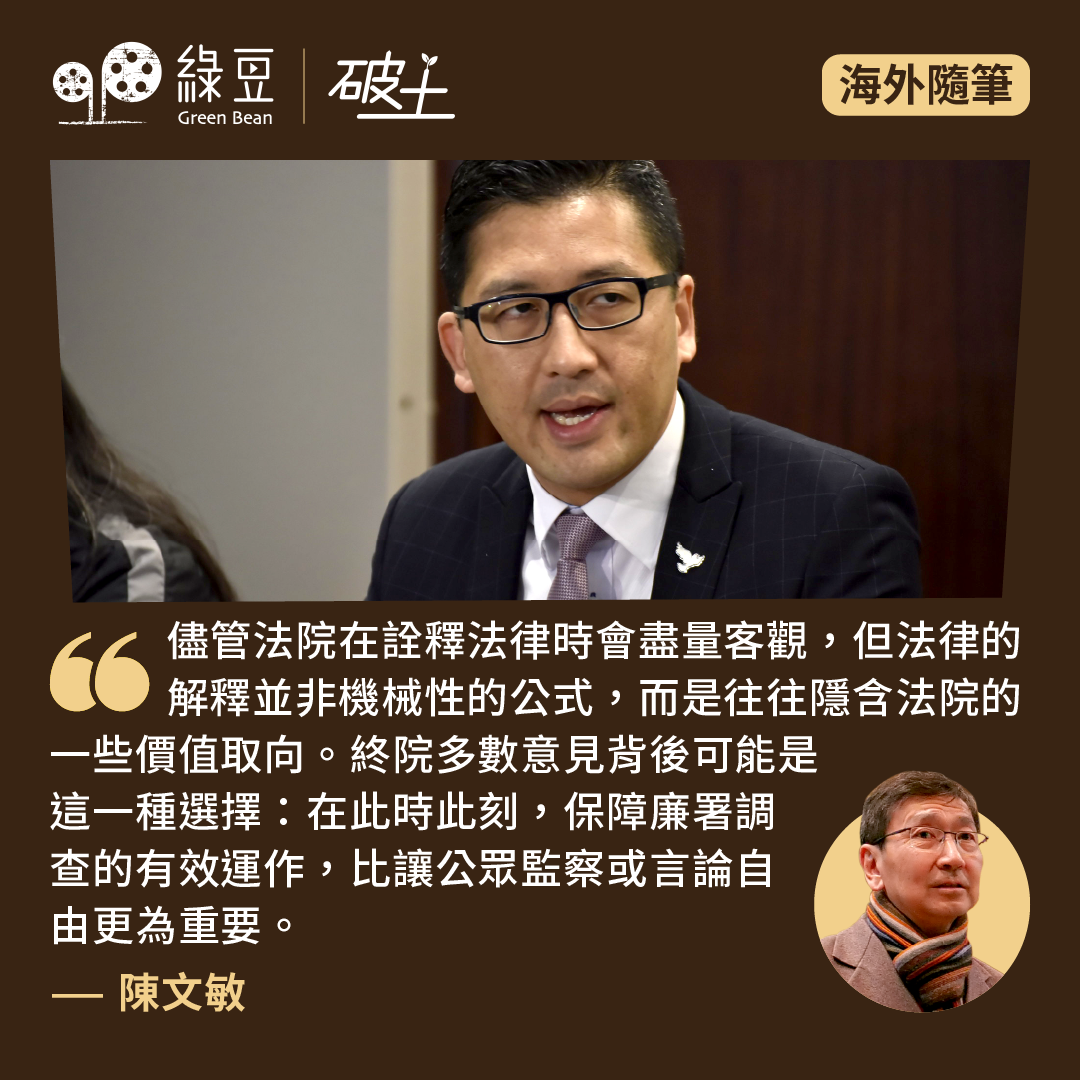
制定一條法律條文時總會有一定的目的,法院在詮釋法律的時候,一方面要體現立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偏離文字的意思。當然,理想的情況是文字準確表達了立法的目的,然而,若因為種種原因,文字未能完全表達或涵蓋立法的目的,那麼法院應該尊重文字,即使這意味立法的目的未能完全實現?還是以立法的目的為依據,勉強詮釋甚至扭曲文字的意思來迎合立法的目的?
前者可能被批評為僵化和造成法律漏洞,後者則可能混淆司法和立法的角色。這裏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兩者之間的分界可能模糊不清,而如何取捨和平衡,亦往往反映了一些基本價值的取向。
近日林卓廷披露廉署調查警司一案[1],便正好反映兩者之間的角力。林卓廷因向公眾披露廉署正就警司游乃強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作出調查而遭起訴,該案的焦點是《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條禁止披露的內容是廉署的任何調查,還只是廉署就該條例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的調查?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原審裁判官裁定林罪成;上訴時高院推翻裁決,認為林披露的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故沒觸犯法例;律政司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於四月初以3比2多數裁定林罪成,維持裁判法院的判罪和四個月的監禁。
《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條
《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條禁止向受調查人士或公眾透露廉署的調查,禁止披露的內容,包括該受調者人士正受調者的事實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而向公眾作出披露,則還包括披露受調查人士的身分。條例的目的是保障廉署調查的效能,不會讓受調查人士獲悉而銷毀相關證據,以及保障受調查人士的聲譽,不會在調查完結前受到不利的報道。
由於案件取決於對第30(1) 條的解釋,讓我們先看看這條文的內容:
「30. 披露受調查人身分等資料的罪行
(1) 任何明知或懷疑正有調查就任何被指稱或懷疑已犯的第II部所訂罪行而進行的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 ——
(a) 該項調查的目標之人( 受調查人 )披露他是該項調查的目標此一事實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或
(b) 公眾、部分公眾或任何特定人士披露該受調查人的身分或該受調查人正受調查的事實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1年。」
林被控的是第30(1)(b)的罪行,該條禁止披露「受調查人」的身分、他正受調查的事實及他被調查的細節,那誰是「受調查人」?第30(1)(a)條界定「受調查人」是「該項調查」的目標之人。那「該項調查」又是指甚麼調查?第30(1)條便説明,「該項調查」乃指就「任何被指或懷疑已犯的第II部所訂罪行」而進行的調查,第二部分主要是涉及貪污賄賂的罪行。
終審法院的判決
法院少數意見認為,就條文用語而言,條例是相當清楚,法例並非禁止披露任何調查,而是特定指向「該項」調查,明顯只是禁止披露一項針對第二部分的罪行的調查。少數意見同意,被告可以直接或間接披露該項調查,披露的方式甚至可以是點頭示意或以眼神確認,但這無損對條文的解釋,即必須有證據證明被告曾以任何方式披露涉及第二部分所定罪行的調查,而非任何調查。由於林沒有披露任何涉及第二部分的罪行的調查,故判林無罪。
少數意見並不認為條文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即使可以有另一解讀,由於涉及人身自由,法院應該採納較狹窄的詮釋。
多數意見則強調立法的目的是保障廉署調查不受妨礙,貪污賄賂案有別於其他罪行,一般沒有明顯的受害人,行賄與受賄者均犯法,故難有證人出來指證,證據亦多隱藏或較易銷毀,故廉署的調查必須不動聲色,以免打草驚蛇,保密至為重要。條例應從維護這目的出發,雖然少數意見的解讀有理,但這並非唯一的解讀。
多數意見強調,這條例分別禁止披露調查這一「事實」和該項調查的「細節」,後者包括涉及的控罪,故前者應被視為廉署的任何調查。這詮釋較能反映立法的目的,廉署調查的權力遠不止第二部分所列的罪行,多數意見看不到為何針對第二部分的罪行的調查會受保密的保障,但其他罪行例如賄選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調查則不受保密的保障,因而認為披露任何廉署的調查均被禁止。
聽過兩方面的理據,你認為那一方的理據較具説服力?
分析
普通法談到立法原意時,這原意不是指行政長官、律政司或立法會議員的主觀意願,而是客觀地從條文的文字、上文下理、立法的背景等推敲出來的目的。立法會有責任將立法的目的清楚地顯示於條例內。於是,若條文的文字無法支持某種落實立法原意的詮釋,法院只能指出該漏洞,讓行政和立法機關日後跟進。法院若強行將法例延伸,便很容易變成立法機關而非進行司法解釋。這也是普通法和社會主義法制的一大分別,後者以政策為指導,條文的限制相對脆弱,司法或行政機關往往可以以政策目的為依歸,扭曲甚或改變法律條文的意思。
當然,法律亦需要有一定的彈性,以處理千變萬化的實際情況,例如濫用電腦是一項罪行,但十多年前對電腦的概念,和今天手提電話甚至一隻智能手錶也可以是一部電腦時,法院對電腦的解釋亦可能需要與時並進。但正如上述,當條文淸晰時,法院能夠擴展法律條文的空間相對狹窄,但當條文的文字含糊的時候,法院釋法的空間便大大擴闊。
這是多數意見和少數意見的最大分歧。少數意見認為條文清楚不過,沒有可作其他解釋的空間。多數意見不能否認少數意見的解讀,但若要落實條文的目的,多數意見必須能夠在條文內找到另一個解讀,當法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讀,法院才有空間以立法原意來選擇認為合適的解讀。
多數意見的困難
於是,問題是多數意見的解讀能否站得住腳?多數意見面對幾個困難:
第一,即使法院將調查的「事實」和調查的「細節」分開處理,但這仍不能擺脫從條例的行文中,不論是調查這一事實或其具體細節,仍然是指向一項就條例第二部分所列的罪行的調查。
第二,多數意見的解釋沒將行為和意圖一併考量,條例規定被告需明知或懷疑正有就第二部分所訂罪行而進行的調查。廉署可以調查不同類型的案件,若條例禁止披露廉署的任何調查,那意圖應該是明知或懷疑廉署正進行調查,而毋須將意圖局限於第二部分的罪行。按多數意見所採納的詮釋,這較狹窄的意圖便毫無意義;甚至令保障廉署的任何調查這原意無法完全落實,因為若被告不知或沒理由懷疑相關的調查是涉及第二部分所訂的罪行,披露仍不犯法。
第三,1996年修訂加入這較狹窄的意圖的立法原意,正是為收窄這一條的適用範圍。在1970年訂立這條例時,當時的條文清楚禁止披露某人正遭廉署調查他被指或被懷疑觸犯這條例所訂的罪行的調查 (the subject of an investigation in respect of an offence alleged or suspect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him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fact that he is subject to such an investigation or any details of such investigation)[2]。
促致修例的《明報》案
在1994年5月一次公開的土地拍賣會上,多名地產商涉嫌聯手壓價,涉及的地產商的身分和當日在拍賣會內的行為,傳媒均作了詳細報道。事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廉署接獲投訴後展開調查,並嘗試接觸當日各報館包括《明報》派駐會場採訪的記者。翌日《明報》報道廉署就拍賣一事展開調查,報道並沒披露任何調查的細節,但廉署其後向《明報》及三名總編輯提出檢控,指他們違反第30(1)條。[3]
《明報》提出兩項答辯,第一是該條例禁止向受調查人作出披露,故條例的前設是廉署已鎖定標的人物進行調查,而當時廉署只是進行初步調查,並無任何目標對象。第二是條例的範圍過於廣闊,即使廉署調查的並非《防止賄賂條例》下的罪行,但由於傳媒無法知䁱廉署在調查甚麼罪行,故這一條等如令傳媒不敢報道任何涉及廉署的調查,甚至當調查涉及濫權的情況,故違反《人權法案》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障。
裁判法院同意這兩點,但單以違反《人權法案》為由而判被告毋須答辯。上訴法庭推翻裁判法院的決定,認為若廉署的調查並非《防止賄賂條例》內的罪行,披露便不屬犯法[4]。《明報》繼而向倫敦樞密院提出終極上訴,樞密院同意第30條並不違反《人權法案》,並認為將保密的責任局限於該條例下的罪行並無不妥[5],但樞密院同意裁判法院的意見,條例只有在有目標人物才能適用,判《明報》上訴得直,撤銷控罪。
換言之,上訴庭和樞密院均確認,第30條只適用於保障廉署就《防止賄賂條例》下的罪行的調查,這保密的保障並不伸延至其他罪行的調查。
1996年,立法會修訂第30條,確認這一條只適用於《防止賄賂條例》第二部分的罪行,並加入被告的意圖,即被告必須明知或懷疑廉署正在調查第二部分的罪行。這修訂成為今天的條文,而修訂的目的是收窄而非放寛第30條的範圍。更加清楚的是草案委員會在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中指出,在修例期間廉署曾要求將保障範圍擴展至廉署的任何調查,但草案委員會並不同意。[6]
海外法官的處理
終審法院批評上訴時高等法院不恰當地考慮立法過程中的辯論。立法原意是一個客觀和抽象的概念,而非個別議員的立法原意,故立法會個別議員的發言或辯論不能用作詮釋法律條文的依據,這是行之已久的原則。但法案委員會的報告是代表整體立法會的意見,具一定的參考價值,尤其是當多數意見所選擇的詮䆁和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相衝突時,這個詮釋還是否屬立法原意便值得商確。
多數意見只是籠統地指立法原意是保障廉署調查,而沒細心考慮立法的背景和草案委員會的報告。當四位常任法官以二比二持相反意見時,最後的決定便落於海外法官身上,他同意其中一方的意見令其成為多數意見,這決定本身是值得尊重的,但他對少數意見所提出修訂法案的立法原意只是一兩句輕輕帶過,沒有深入考慮,這處理是較令人失望的。
第四,退一步而言,假若兩項詮釋均屬可能,由於涉及刑事罪行,法院一般應該採納較狹窄的詮釋。多數意見認為這只是一般原則,一切還視乎立法的目的,這又返回立法原意的問題。即使如此,立法原意是否清晰排除較狹窄的詮釋?
價值取向的選擇
儘管法院在詮釋法律時會盡量客觀,但法律的解釋並非機械性的公式,而是往往隱含法院的一些價值取向。終院多數意見背後可能是這一種選擇:在此時此刻,保障廉署調查的有效運作,比讓公眾監察或言論自由更為重要。少數意見的選擇是當涉及人身自由時,公眾須知曉法律的限制才能守法,若刑法的範圍不清楚,那法院便需肩負保障個人權利的責任,而非牽強地詮釋法例來填補法律漏洞,那是立法會而非法院的責任。少數意見較切合文字意思,亦對人身自由有較大保障。若因此而出現漏洞,應該由立法機關修例填補漏洞。多數意見的詮釋則顯得有點牽強,亦未能完全落實所謂的立法原意。若要扭曲文字的意思以體現立法的原意,司法和立法的界線便會顯得模糊。
(文章部分內容曾於《明報》「法政隨筆」專欄發表,見「法律詮釋」,《明報》,2025年4月9日)
( 圖 : 獨立媒體 )
[1] HKSAR v Lam Cheuk Ting [2025] HKCFA 7.
[2] Section 30(1) reads:
“Any person who, without lawful authority or reasonable excuse, discloses to any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an investigation in respect of an offence alleged or suspect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him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fact that he is subject to such an investigation or any details of such investigation, or discloses to any other person either the identity of any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such an investigation or any details of such an investigatio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one year.” (my emphasis)
[3] Attorney General v Ming Pao Newspaper Ltd [1996] AC 907.
[4] HKSAR v Lam Cheuk Ting [2024] 5 HKLRD 198, paras 43-44.
[5] “The fact that disclosure of investigations into other offences is not so severely restricted does not re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1) disproportionate or unnecessary.”: Attorney General v Ming Pao Newspaper Ltd [1996] AC 907 at 920.
[6] https://legco.primo.exh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5LEGCO_INST:LEGCO/1218831850006976, 引述於 [2025] 5 HKLRD 198, para 61.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名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