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了,還能做什麼?》—— 年老哲學導論1

(作者按:本文根據2024年7月31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演講,由鄭栢芳同學筆錄編寫,經作者修訂而成。文章頗長,故分三篇刊出。原文頗多註釋,因篇幅問題,在此省略。)
這篇的主題為「年老」(ageing),而非「老年」(old age)。
「ageing 」是個過程,英文的「ageing」亦有「變化」與「成熟」之意,而不專指年老。大部分人都以為,「ageing」簡單不過,甚至根本稱不上問題。
「ageing」與生命密不可分,同榮共枯,自出生至死亡,皆處於「ageing」這個過程,不論你兩歲、三十歲、九十歲,都在「ageing」之中。但是,今日所討論的「ageing」課題,雖然亦含有「成熟」與「變化」之意,但主要是就「年老」來談,且必然與死亡相連。
緊密相連的「living」、「ageing」、「dying」
過去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設有課程,專門談死亡和年老的問題。與「ageing」及「old age」相同,「death」和「dying」亦不能混淆。此處與年老相連者,是指「dying」,不是「death」。生命不是概念,因而也並非固定不變;相反,生命恆變流動,正如上述,基本上是個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做「living」。
「living」、「ageing」、「dying」一體,猶如皮肉相連,無以切割。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我們出生當刻,就已經可以死去。」(As soon as we are born, we are old enough to die.)他在生命問題上,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死亡絕非自外於生命,死亡就在生命中。
既然「ageing」與「living」密不可分,而「dying」又在「living」之中,則「living」、「ageing」、「dying」為一體,只是它們乃由不同角度觀察而得出不同結果,亦即多面,故各有名稱。它們既是一體,也是多面。
雖然「living」、「ageing」、「dying」一體多面,但「living」與「ageing」又同時有另一種關係。依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生命對立面並非是死亡,而是年老。」故此,兩者可謂「對立統一體」。無論是在海德格抑或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而言,死亡(death)基本上不屬於我們經驗範圍,我們無人能經驗死亡,死亡一出現就無,什麼都無,自然也無生命。
死亡是否勝於不死?
2007年,英國倫敦薩奇美術館(Saatchi Gallery)曾舉辦「老人之家裝置藝術」(Old Persons’ Home Installation)展覽,展品是若干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人偶,在場內漫無目的遊蕩。這些人偶形象各異,不同種族與身分都有,他們可能過去在社會上叱咤風雲,然如今都聚集於此處。此處是何處?就是老人等死之地,可能是老人院,也可能是歷史上曾出現各式具類似功能的處所,如棄老山、寄死窯、高麗葬。
身陷囹圄者,刑滿就可出獄,甚或終身監禁者猶可假釋;病人入院,痊癒後亦可出院;但要離開老人院,出路唯有一條,就是死路。故老人院是生命終結之所,在老人院中,所有老人都在等死。
即使並非受困於老人院者,其處境亦無太大分別,都是等食、等睡、等死,謂之「三等」老人。那麼,年老究竟有何意義?難道僅代表為疾病、包袱、失智、無用、無助、醜陋、孤獨、絕望、煩擾、固執、痛苦、社會垃圾之同義詞?我並不以為然,因此我開始思考,人類年老後,尚可有何作為?
隨著醫學不斷發展,人類夭折率降低,總人口數一再激增,加上壽命延長,老人所占比例亦越來越大,數據顯示,到2070年,世界將進入超高齡時代。任何生命到後期,都會出現明顯的生理衰退,衰退然後死亡,此自然之理,但如今問題是,衰退卻死不去。
過去不少哲學家,平均年齡都在四十至五十歲,孔子算是高壽,卒年七十二。我常對朋友說,我已活得比孔子長命,七十四歲仍健在,且年紀較我為大者,大有人在,因為如今我們都不容易死亡。過去為人祝壽,每云長命百歲、壽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希望對方長壽,實由於過去長壽並非常態。但長壽就一定是好嗎?如今我們已知道,到八九十歲仍死不去,所需面對問題極多,且這些問題,有時不止是自身問題。由此觀之,死亡是否勝於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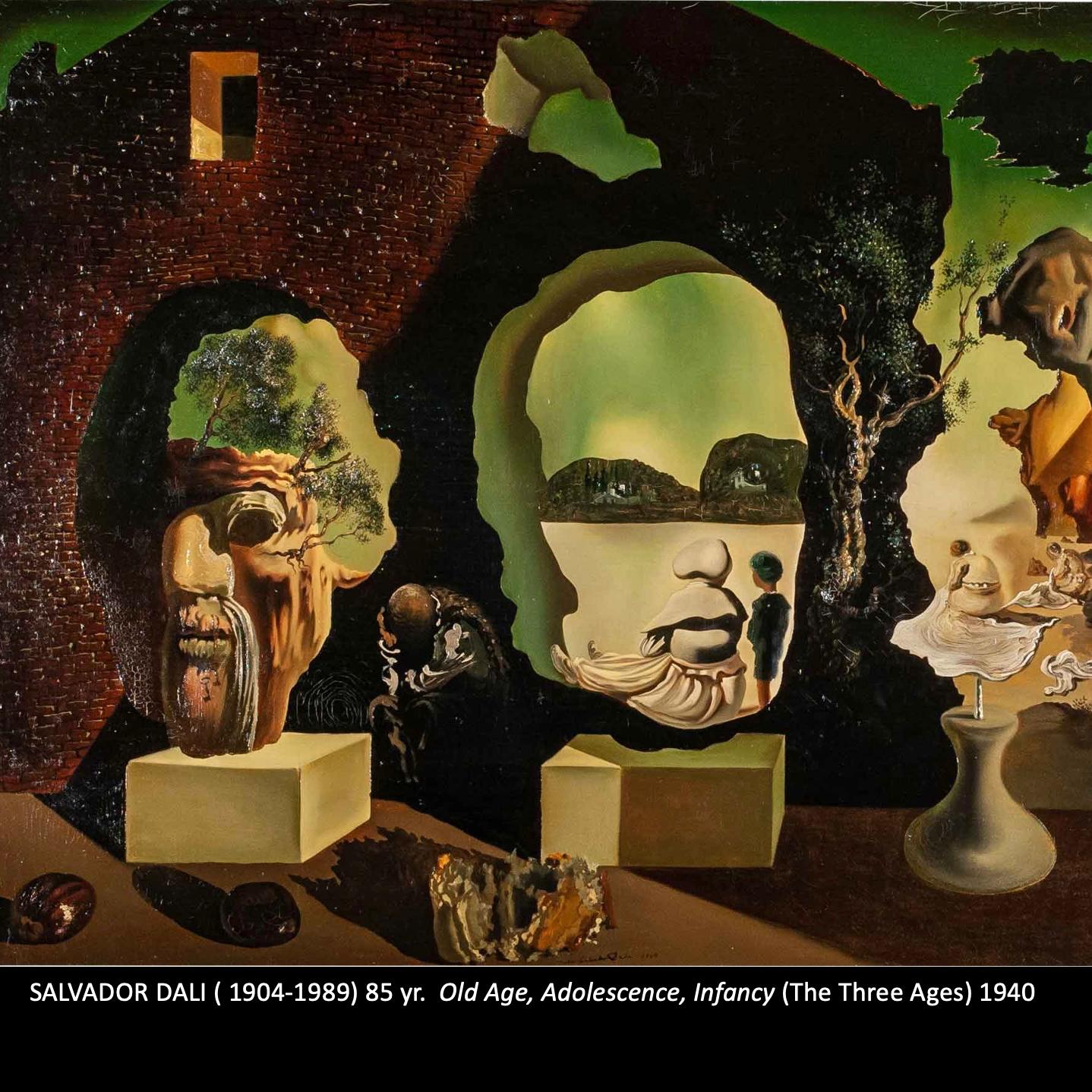
年老代表甚麼?
於是我們不得不問,何謂老年(old age)?年老又如何變老(getting old)?希臘神話中,有位名為革剌斯(Geras)的神祇。希臘諸神皆不朽,且永遠青春年輕,但革剌斯卻是位老人神祇,這相當奇怪。無論是荷馬(Homer)、海希奧德(Hesiod)抑或其他記載,祂都被描述為矮瘦乾癟而又死不去的老人,所代表的正是衰老,是淒涼而悲哀的角色。據我所知,西方不少老人病概念,皆源自這個詞。
過去總認為年老屬於負面,從希臘神話賦予革剌斯的這種形象,即可見一斑。希臘人認為,年老痛苦、艱辛、令人煩惱、一無所有、無事可為、力有不逮,除等死外,別無存在意義。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曾說道:「諸惡皆集,無一可欲。」那些「惡」,就是他接下來所說的:憤怒(wrath)、嫉妒(envy)、紛爭(strife)、不和(discord),這些皆伴隨年老而來。所以年老等於悲哀、痛苦、毫無希望,此即希臘人的看法。面對如此困境,我們可有何作為?
東方人,尤其華人,卻不視年老為負面,甚至年紀越老,其氣彌烈。譬如曹操於五十三歲時,猶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一語;又如東漢名將馬援也說:「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也許我們可借鏡他們的經驗。但是,認為自己已是老驥的曹操,無論是吟詩時的五十三歲,乃至於薨壽六十六歲,對現代人而言仍未算老,或最起碼,他或未能體會到八九十歲者所面對問題;而說「老當益壯」的馬援,當時更值少壯。更何況,他們與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一樣,同屬有一定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者,自然難以明白平民老人景況如何。即就我自身而言,我已七十四歲,活得比他們都長,我如何處理自身時間與生命問題?他們似乎亦不能回答。
變老而死不去的問題
死亡在整個西方哲學,自柏拉圖(Plato)以降,永遠都是重要課題,因為死亡乃屬必然(certain),古希臘相信「人終必一死。」(All men are mortal.)。「終必一死」,但並沒說「終必變老」,年老並非必然,無數人中道夭逝,不一定有機會變老,唯有死亡才是必然。因此,死亡是西方哲學重要課題,年老卻不是,但相關研究可謂少之又少。
然則,年老作為哲學議題,它有何具體問題?
正如上述,首先,是變老而死不去的問題,延伸出來第一個分支問題就是醫療、調理、養老問題。就醫學言,本身視年老為病,但如今這種觀念已逐漸改變。其後隨老人學(gerontology)出現,開始將問題思考轉向如何憑藉控制細胞、藥物調理或醫治、食療、運動等來維持生命,並確保健康。
第二個分支問題是經濟問題,即如何在退休後,長者得以維持原有的經濟水平。從經濟問題,則衍生第三個分支問題,社會問題。譬如福利問題,政府應負上多少責任?作為壟斷社會大部分資源的財團企業,又最起碼應為他們因年老而退休的員工,負上多少責任?更重要問題是,他們實際上負過多少責任?不過,嚴格而言,以上問題都不算是哲學問題,而只是從哲學問題所衍生出來者。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