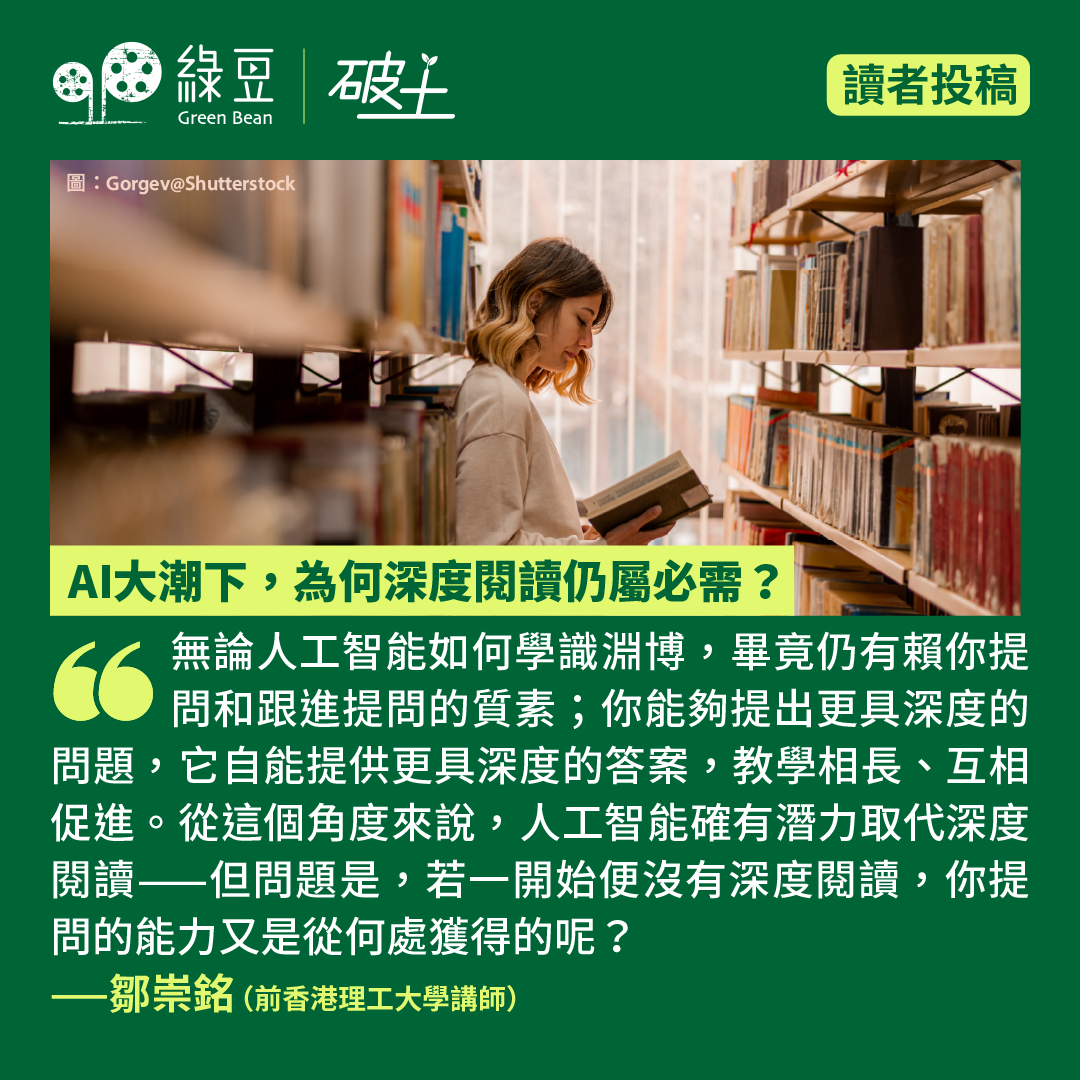山城無聲 | 張燦輝 (中大哲學系退休教授)/ 李煒佳 (中大學生報1977年總編輯)

(筆者按:我們可能言過其實,同時亦可能令不少中大校友、學生會前幹事和學生報編輯不快,請原諒,恕我直言,同時懇請在香港內外的校友批評和指正我的無知與不是之處。)
就造成168人死亡的大埔宏福苑五級火,中文大學學生關靖豐(Miles Kwan)去年就火災發起聯署,列出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關事後被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拘捕,准保釋候查,中大教務處學生紀律委員會於上月召開會議跟進個案。
及後從媒體得悉,關靖豐透露「剛剛俾中大踢出校了」。
關同學到現在並沒有判罪。
關同學哪裏做錯了?退一億步,就算關同學有做錯,難道不應該是大學須諄諄教誨他
嗎?現在竟然當他是毒瘤般急速割掉!
相信海外媒體和KOL肯定會口誅筆伐。但我們關心的是中大現時的教授敢出言批評嗎?中大已沒有學生會和學生報,當然沒有任何學生組織代關同學抱不平!沉默便是現象。心中有多少憤怒悲傷也不表達出來。
但是我們在海外的中大校友呢?
以下文章是幾天已寫好,加上今天的荒謬和憤怒信息,這文更要刊出!
=========================
墳場與職場
二零二六年農曆新年,中大最新通訊發布了一段短片,校長盧煜明以粵語、普通話、英語三種語言向師生祝賀馬年。短片裏的校園依然翠綠,吐露港海景壯麗如昔,校長笑容和藹。一切看起來沒有變化。
從數字上看,中大確實沒有變。QS排名32,泰晤士排名41,都是歷年最佳。研究經費充裕,論文產量穩步上升,國際合作照常進行。每一項指標都顯示這仍然是一所世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
但一所沒有真正學術自由、學生會和學生報已不復存在的中大,還是香港中文大學嗎?
或許是時候正名了。Hong Kong這個名字裏的實質已經名存實亡,不如改稱「湘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Xianggang。「湘港」者,香港的普通話音譯也。這個名字更準確地反映了今天的處境:大學仍然坐落在同一個地理位置上,但那些曾經定義香港的東西:自由、開放、多元、敢言、法治,已經從校園裏消失殆盡。當然,中大從此可以和北大、清華、復旦齊名,同為中國頂級大學。
我們相信現在中大的教授和同學,連同畢業離校、留港或流散世界各地的校友,大概分成了兩批人。一批仍然懷念2019年之前的歲月。那時候的中大自由開放,學生和學生會積極參與校政和社會。2019年6月,Google Maps一度把中大標註為「香港暴徒中文大學」。同年9月開學禮上,時任學生會會長蘇浚鋒說,若因對抗惡法暴政而被冠以「暴徒」之名,他「欣然接受」。11月中大保衛戰後,「暴大」更成為許多校友引以為榮的稱號。
另一批人則順服了。他們接受現實,安分守己,教書研究照常,絕不越過任何紅線。對校政不滿不表達,對社會不公不置評。教書是工作,研究是飯碗,學生上課是接受職業訓練。校方說什麼就是什麼,上面要求什麼就配合什麼。日子還是可以過的,只要不惹事。
這兩批人之間幾乎沒有交往。他們用不同的眼睛看同一座校園,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前者看到的是一座墳場,後者看到的是一個職場。
大學教育難道就是這樣的嗎?當一所大學放棄了培養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識的目標,只剩下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它還配稱為「大學」嗎?學生被當作產品,教授被視為員工,課堂成為流水線,這所機構跟一間職業培訓學校有什麼本質區別?世界排名再高,論文再多,經費再充裕,如果校園裏連一份學生報、一個學生會都容不下,這些數字又說明了什麼?
學生組織片甲不留
2026年1月18日,崇基學院學生會宣布停運。聲明說:「在新時代下,會方或無法再以『學生會』之名,就校政及社政事務為會員發聲,亦難以履行學生代表的核心使命。倘若徒有形表之虛,卻失去代言之實,將與學生會的精神背道而馳。」就在前一天,崇基學院正在慶祝建院七十五周年,嘉年華與啟動禮盛大舉行。一邊是慶典鑼鼓,一邊是學生自治的喪鐘。這種荒誕,恐怕連卡夫卡也寫不出來。
在此之前,逸夫書院學生會已於2025年12月21日停運,伍宜孫書院隨後跟進,新亞書院學生會12月28日發出告別信,聯合書院學生會於2026年1月9日正式解散,和聲書院學生會亦宣布停止運作。九間書院中,六間書院學生會在短短一個月內接連倒下。加上中大學生會早在2021年10月7日解散、校園電台其後停止運作、中大學生報被迫改名為《大學社區報》,再於2024年3月連實體報架都被校方移除——整座山城曾經喧鬧的學生自治生態,已被連根拔除,片甲不留。
這不是自然死亡,而是系統性的扼殺。
六間書院學生會覆滅
讓我們把歷史梳理清楚。
中大學生會1971年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成立,由新亞、崇基、聯合三所書院學生代表共同創立,是校園內唯一獲全體同學民意授權的代表機構。五十年間,學生會在每個歷史關口都不曾缺席:1989年為天安門學生籌款並派代表赴京,攜帶港幣60萬元支援民運人士,協助柴玲等民運領袖出逃;1996年抗議李國章出任校長;2014年參與雨傘運動;2019年投身反修例運動。學生會不僅是校園組織,更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縮影。
2021年2月,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同月,候任幹事會「朔夜」以3983票當選,得票率九成九,卻在上任首日因收到死亡恐嚇而全體辭職。校方指控其參選宣言涉嫌違反《國安法》,不承認選舉結果,拒絕提供場地,暫停一切行政支援,甚至禁止臨時行政委員會使用會室。前學生會幹事、政治理論學者李敏剛當時便指出,獨立註冊一向不是學生會在意的議題,學生會理應是中大架構的一員,校方把學生會逼進「獨立註冊或解散」的假二元對立,是「好錯,甚至好可恥」的做法。
10月7日,學生會宣布解散。同日,民主牆被鐵馬圍封。12月24日,佇立崇基校園11年的民主女神像在凌晨被校方拆除運走,沒有交代去向。
《中大學生報》的命運同樣悲涼。這份1969年創刊的校園媒體,五十多年來報道校園新聞、批評校政、探討社會議題,其集體編輯制和拒絕以客觀中立為名掩蓋自身立場的態度,在香港學生媒體中獨樹一幟。學生會解散後,學生報失去會室與出版資金,2022年8月被迫改名《大學社區報》,編輯自己也形容這個名字「難聽」,但為了繼續服務同學別無選擇。即便如此苟延殘喘,2024年3月,校方以接獲投訴稱刊物內容「不盡不實」為由,在未通知的情況下派職員收走全部報架和已上架刊物。校方聲稱該報「不屬中大刊物」,在校園擺放物品或刊物屬違反校規。一份有55年歷史的學生報,在自己的校園裏連擺一個報架的資格都沒有了。
校園電台在學生會解散後同樣失去會室,因拒絕註冊為校方旗下屬會而停止運作。自1999年開播,二十多年的聲音就此沉寂。
至於書院學生會的骨牌式崩塌,手法如出一轍。校方要求各書院學生會根據《社團條例》向警務處獨立註冊——社團條例的註冊機關正是警務處轄下的社團事務處,意味着學生會必須將自己置於警方的直接監管之下。新亞書院學生會在告別信中透露,校方早於2023年已施壓要求註冊,即使他們「不得不向壓倒性的權力妥協,收起種種控訴」,用盡緊絀人手推動註冊,仍獲告知校方勒令停運,形容「員生共治已經死得徹底」。新亞學生會更引述輔導長張錦少教授的話:「未來學生會可能不完全由學生選舉產生,需要有一定招募程序,並由大學授權運作。」如果這成為現實,那就是以馴服的官方組織取代自治的學生會,不是重建,而是偽裝。學生會曾要求書院簽署協議,保證關係不因註冊而改變,遭到拒絕,校方僅呼籲「信任大學」。
崇基學生會透露,過去兩年校方要求在完成獨立註冊前不得對外使用學生會名義,會室及群發電郵的權限都被收回。聯合書院學生會的解散聲明一針見血:「面對權力壓迫,本會恐難以延續學生會使命。」適逢聯合書院七十周年院慶,「本應傳承的薪火卻被撲滅」。
中大校方四年來的回應始終只有一句:「維持2022年3月1日已發表聲明的立場,只有依法註冊的學生組織方可運作。」面對六間書院學生會的覆滅,連一絲遺憾的表情都懶得裝。
海外校友的集體沉默
在這場對學生自治的系統性清洗中,最令人不安的不是校方的冷酷,權力機器向來如此運作,而是數十年來歷屆學生會幹事和學生報編輯們的集體沉默。
2021年初校方首次向「朔夜」開刀時,確曾有反應。前學生會會長、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公開表達震驚和傷感,憂慮骨牌效應,指學生永遠是社會上比較獨立的聲音,缺少了這種聲音,社會會更加清一色。前會長黎恩灝和楊政賢發起聯署,逾三千名前學生會成員簽名抗議。前副會長馮家強警告校方不要破壞師生關係,校友絕不姑息打壓。
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從2021年到2026年,五年間學生會解散、校園電台停播、學生報改名又被收走報架、民主女神像遭拆除、六間書院學生會接連停運——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的時候,幾十屆的前學生會幹事、幾十屆的前學生報編輯,他們的聲音在哪裏?
中大學生會自1971年成立至2021年解散,五十屆幹事會,每屆至少十數人,累計數以百計。學生報自1969年創刊,歷屆編委同樣數以百計。書院學生會的歷屆幹事更不知凡幾。這些人曾在學生會的旗幟下高談民主自治、員生共治、社會正義,畢業後散布在各行各業、乃至世界各地。如今母校的學生組織被逐一消滅,他們卻選擇了沉默。
留在香港的,或可以白色恐怖來解釋。《國安法》之下人人自危,發聲的風險切切實實。港大學生會四名前幹事因悼念刺警案死者而被控「宣揚恐怖主義」、城大學生在遷離會室時喊口號遭國安處調查、浸大學生會因民主牆上張貼問責訊息被即時暫停運作。在這種氛圍下噤聲,雖然令人惋惜,至少可以理解。
但海外的呢?
散居英美加澳台的中大校友數以萬計,前學生會幹事中不乏已在海外定居多年、早已脫離香港管轄的人,既無被捕之虞,也無被秋後算帳之患。然而在整個學生自治被瓦解的過程中,海外校友社群的反應近乎零。各地中大校友會照常運作,活動依舊是聚餐、旅行、聯誼晚宴。對學生會被取消、學生報被趕走、書院學生會逐一倒下,最多偶有一兩篇社交媒體上的感慨,轉發幾下便消散於網絡洪流中,連漣漪都算不上。無人聯署,無人開記者會,校友們更不曾以此向校方施壓。歷屆學生報的編輯們呢?似乎沒有一個人公開寫過哪怕一篇評論,儘管只是把這段歷史記下來。
五十年的學生會歷史,五十五年的學生報傳統,就這樣在集體的無聲中被埋葬了。當年那些在學生會叱咤風雲、在學生報揮斥方遒的人,大概沒有想過自己日後會以這種方式見證它們的消亡:不是悲憤地見證,而是漠然地旁觀。
沉默並非出於恐懼,而是冷漠使然,是主動的放棄。
海外校友會從來跟母校命運無關
有人會說,畢業多年,與母校漸行漸遠,自然不再關心。但這些人當年在學生會投入的不是一般的課外活動,而是一種信念:民主自治的信念、學生作為大學主體的理想、知識分子應當對社會承擔責任的肯定。如果這些信念只是二十出頭時的感情衝動,畢業即蒸發,那當年的一切宣言都不過是虛妄。
更嚴厲地說:如果歷屆幹事和編輯們連在安全的海外環境下寫一篇文章、發一份聯署、辦一場座談會都做不到,那他們當年口口聲聲捍衛的「言論自由」、「獨立思考」、「社會良知」,究竟有幾分真實?抑或不過是一張漂亮的履歷裝飾?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出,因為它牽涉的不只是中大,而是整整一代香港知識人的精神面貌。
翻查歷史紀錄,海外中大校友會其實極少公開譴責校政或政府不當的傳統。2002年李國章提出中大科大合併時,兩校學生會強烈反對,學生報和校園電台發表聲明,科大學生會舉行全民投票,八成半反對合併——但海外校友會沒有任何組織以校友會名義表態;1996年學生抗議李國章出任校長,校園內有示威,海外校友會同樣默然;即使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大學生會派代表上京、籌款60萬元支援民運,那也是學生會的行動,而非海外校友會的行動。
換言之,海外校友會早已習慣於不對校政發聲。這種沉默不是2020年《國安法》之後才開始的,而是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傳統。在沒有任何白色恐怖壓力的年代,他們已經選擇不以組織名義表態。校友會的功能從一開始就被限定為聯誼、社交、懷舊,與監督校政或捍衛價值無涉。校友聚餐上的觥籌交錯,校慶晚宴上的歌舞昇平,從來都跟母校的命運無關。
這使得2021年後的集體沉默更難以僅用「恐懼」來解釋了。自由年代都不曾發聲的人,又怎能指望他們在不自由的年代挺身而出?冷漠不是一夜之間養成的,是幾十年積習的結果。當年在學生會裏慷慨激昂的青年,畢業後進入社會、移居海外,漸漸習慣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關心但不介入,惋惜但不行動,私下場合搖頭嘆息卻絕不公開表態。這種習慣一旦養成,即使身處完全自由的環境也很難打破。
當年的學生會幹事們日後不少成為律師、大狀、記者、學者、議員、商界精英,擁有資源、平台和影響力。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為各種國際議題仗義執言,偏偏對自己母校的事不置一詞。很多人每年回中大參加校友聚會、在未圓湖畔勞先生銅像拍照留念,卻對大學站前民主女神像的消失視若無睹。面對母校學生自治的消亡,他們選擇了最廉價的回應:什麼都不做。
逸夫書院學生會停運時,末代幹事郭嘉寶說了一句話:「做啱嘅事、讀好啲書、保重身體,有一日可能需要到你。」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學生,對着空蕩蕩的校園說出這番話。她不是在呼喚同齡人,而是在呼喚那些已經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的前輩。可惜前輩們的回應,是寂靜。
容得下學生的躁動才配得上「大學」二字
一所沒有學生會的大學是什麼?它是一座知識工廠。學生進來,修讀學分,通過考試,領取文憑,離開;不涉及任何公共參與,不會集體議政,不對權力質疑。大學不再是知識共同體,而是文憑製造工廠。校方管理層毋須面對任何來自學生的制度性制衡,一切決策由上而下,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者。教務會裏沒有了學生會會長的席位,各委員會裏聽不到學生代表的聲音,大學治理淪為純粹的行政管理。
中大曾經以書院制自豪,標榜「員生共治」。新亞書院的創辦精神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錢穆、唐君毅等先賢的教育理想是師生之間的精神共同體。如今新亞學生會的告別信引用錢穆的話「理想不能沒有憂與困」,卻是在宣告這個理想的死亡。員生共治,一個在中大章程裏寫了六十年的理念,在校方一句「只有依法註冊的學生組織方可運作」的官腔中徹底終結了。
沒有學生報的大學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校園公共空間。學生報的功能不僅在於報道校園新聞,更在於訓練批判思維、培養公共寫作能力、構建校園輿論場。中大學生報五十五年來報道的不只是迎新活動和考試安排,還包括校政批評、社會議題和學術自由的探討。2007年的情色版事件、對校董會組成的質疑、對大學商業化的批判,每一次都刺痛校方,也每一次都引發校園辯論。這些內容令管理層不安,卻正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學生在採訪、寫作、編輯、辯論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絕不亞於任何一門課程。
我們分別自1970年在崇基唸哲學本科,留學後回中大教書超過四十年,以及在1975年入中大哲學系,1977年是中大學生報總編輯。我們見證過學生會與校方之間的無數角力。學生會的立場有時過激,有時幼稚,時而令人搖頭。但那正是大學教育的一部分:年輕人在試錯中學習,衝突中成長,承擔責任中成熟。大學容得下這些躁動,才配得上「大學」二字。如今中大已容不下任何學生自治的聲音,連一個報架、一面民主牆都容不下了。
誰是大樹守護者
我們離開香港之後,在英國和台灣目睹中大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局面。寫這篇文章是想要指出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幾十年來那麼多曾在學生會和學生報付出過青春的中大人,在母校最黑暗的時刻選擇了袖手旁觀。
知識人的責任,從來不是在安全的時候侃侃而談,在風險來臨時退隱江湖。漢娜.鄂蘭所批評的「平庸之惡」,不僅適用於那些執行命令的人,也應用於那些什麼都不做的旁觀者。如果連已經身處海外、享有言論自由保障的前學生會幹事和前學生報編輯都不肯為母校發聲,那我們還能指望誰?
崇基學生會停運聲明裏有一句話:「前人種下的大樹,我們這一代未能守護。」這句話不應該只是在任學生的自責,更是對所有曾經在這棵樹下乘涼的前輩們的叩問:你們在哪裏?
山城已經無聲。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聲明。它宣告的是:我們這一代知識人,終究辜負了自己年輕時相信過的一切。
2026年的中大校園裏,沒有學生會、學生報和校園電台,民主牆和民主女神像也不復存在。范克廉樓裏曾經屬於學生組織的會室已經空了,報架被收走,牆上的海報也被撕掉。這座曾經充滿爭辯與思想碰撞的山城,如今安靜得像一座墳場。而墳場外面,是歌舞昇平的校慶嘉年華,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這是一首哀歌,獻給我們的母校,給那座曾經叫做香港中文大學的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