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慤村的悲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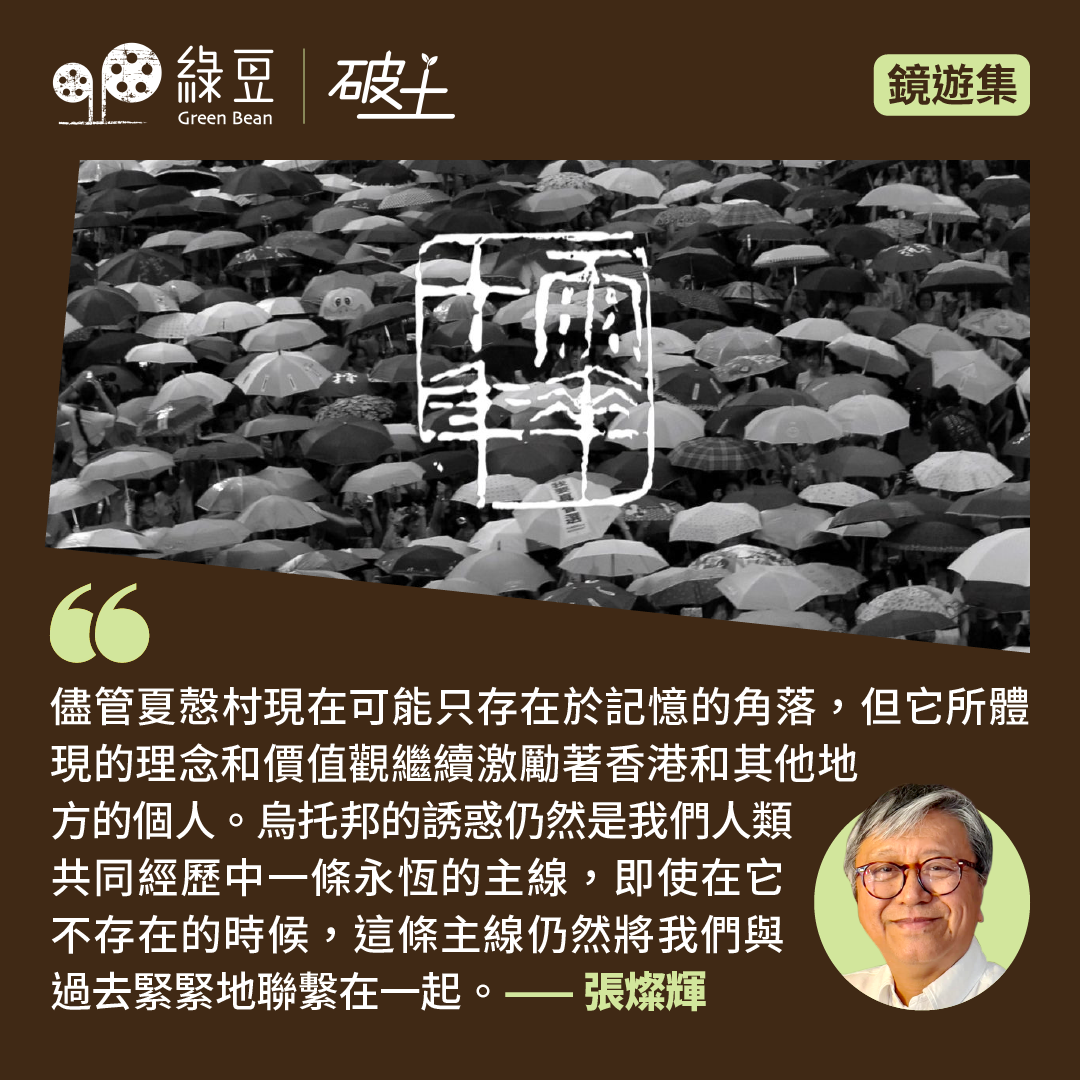
(作者按: 此文原是英文論文 The Tragedy of Harcourt Village,將於本月26日在日本東京大學「雨傘運動十週年紀念會議」宣讀,現翻譯為中文,在《鏡遊集》先刊出。)
序言
雨傘運動至今已有十年歷史,最初的口號是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但後來運動戲劇性地轉化為佔領金鐘79天 —— 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 「奇蹟」。
我們所熟知的雨傘運動,或者更貼切地說「雨傘革命」,重塑了其三個主要發起者(佔中三子) 的初衷,並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香港人的命運。這場運動後來過渡到2019年反修例抗爭,喚醒香港市民意識到他們的未來取決於自己的行動,爭取民主和自由變得至關重要。運動最終的結果令人失望,但香港自此已成為昔日的陰影,慢慢淪為只是內地另一個沿海城市。對於我們這些被迫背井離鄉的香港人來說,痛苦、悲傷和憤怒是無法逃避的。
夏慤村,這個在香港中環被佔領的空間,其獨特的個性仍然無與倫比,在未來也不太可能被複製。當與類似的全球社會運動對比——例如2014年在台北舉行的為期23天的「太陽花運動」、2011年在紐約的63天的「佔領華爾街」,甚至是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為期49天的佔領運動——-夏慤村的79天能脫穎而出,成為真正史無前例的非凡現象。
心臟地帶的小村莊
香港的「雨傘革命」是一場重大的公民抗命運動,從2014年9月28日到12月15日,歷時79天。它始於9月22日,當時數以千計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發起罷課行動,以回應北京宣布2017年民主選舉行政長官的誤導性「普選」。關鍵時刻發生在9月28日,香港警方出動了87枚催淚彈以驅散數以萬計的示威者;然而,這一努力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之後,由學生領導的公民抗命運動佔領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三個主要區域:旺角和銅鑼灣的繁華地帶,以及港島中區的干諾道。我在這篇文章裡的反思,與其說是對革命的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析,不如說是對香港中環被佔領地區的烏托邦經驗之個人探索。
干諾道佔領區(後來稱為「夏慤村」)位於香港金融中心的心臟地帶,長達兩公里。在這個圍繞著香港政府辦公室的區域內,最初只是一連串零散的路障來對抗警察的行動,後來逐漸變成一個由露營帳篷和框架帳篷搭建而成,充滿活力的小村莊。據估計,整個區域約有1,900個帳篷,遍佈干諾道中、夏慤道、添美道、立法會前地和添馬公園。一般來說,這個區域交通繁忙,每分鐘有數千輛車輛經過,幾乎沒有行人的空間。然而,在佔領期間,村內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有數百名學生和示威者全天候居住在佔領區內。
佔領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倡議香港政府行政長官的自由和公開選舉。這個訴求意味著對真正民主和普選的呼喚,而北京政府早在三十年前的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就已經做出了這樣的承諾。
一個本不應存在的環境
讓我們重溫那段歷史:
香港異托邦 —— 夏慤村
與世界各地的許多示威活動不同,這次佔領活動彌漫著非凡的和平與和諧氣氛。夏慤村意外地從群眾抗議中出現,創造了一個本不應存在的環境,受阻的高速公路喪失了往常的功能。站在通往村莊的公路隧道口,感覺很不真實。夏慤村是博柯(Foucault)所描述的異托邦(heterotopia)的典範案例。
《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對這個獨特的環境做了令人信服的客觀描述: 「這裡沒有領導者,但從帳篷到回收桶,一切都運作完美。這是典型的政治無政府主義:一個自我運作的社區。在沒有特定領導人指示的情況下,個人(主要是年輕的專業人士、上班族和學生)自願抵達、搭起帳篷,並以有秩序、和平且互相尊重的方式共處。沒有必要進行金錢交換,人們可以自由取用或貢獻公共用品。現場洋溢著相互尊重的氣氛,每個人都被平等對待,並因共同的目標而團結一致:透過愛、和平與非暴力來追求真正的民主。這次聚會不是一次「派對」,而是一種抗爭。社區成員被鼓勵表達他們的意見,無論是透過書面或藝術表達。大多數人白天回到他們正常的工作崗位,下班後再回到夏慤村。頻繁的晚間聚會提供了分享新聞和聽取不同參與者發言的機會。雖然偶爾會發生激烈的爭論,但從來沒有演變成暴力事件。」
這個村莊擁有各種資源,包括寬廣的學習區、無線網路、輔導站、小型圖書館、回收和宗教設施、安全巡邏、戶外講座點和急救站。在這個社區裡,法國的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所體現的原則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是積極實踐的。因此,夏慤村不僅是一個異托邦,也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
成為希望與社區的明燈
對許多人而言,這樣的烏托邦似乎難以想像。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生中從未遇見過這樣的經驗。然而,它就在我們眼前展開。這種烏托邦的體驗並不是虛構出來的;它顯然是超現實的,是從現實本身的結構中誕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夏慤村所在的干諾道周圍街道,日常生活仍在繼續。然而,從這個「超現實」烏托邦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日常「現實」世界的觀感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夏慤村的出現,是我們在面對政治不公和警察暴行時,對集體良知的有力回應。對於正義、民主和自由的烏托邦願望,在許多與這些理想產生共鳴的人心中,突然覺得是可以實現的。這個臨時村莊看似無中生有,卻轉變成實現這些願望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認,從一開始,佔領就籠罩著深刻的悲劇感。我們當中很少人對香港政府會聽取學生和示威者的訴求抱有任何幻想。大家普遍相信,北京會堅持其於2014年8月31日就2017年選舉程序作出的決定。我們面臨一場艱苦的戰鬥,似乎注定失敗。但是,在這種暗淡的前景中,我們仍然鼓起勇氣來抵抗預定的命運,選擇對冷漠說「不」,對公民抗命說「是」。
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夏慤村捕捉到古典希臘悲劇的精神,同時也綻放出豐富的浪漫劇情。在這個敘事中,美感與無可避免的損失並置,意味深長;它喚起了對藝術的雙重欣賞,以及對生命瞬息萬變的清醒認知。就像古希臘的偉大悲劇一樣,夏慤村的故事情節充滿了雄心和抱負,但卻陷入了沉重的結局 —— 苦樂參半地提醒人們,所有的歡樂,無論多麼充滿活力,往往都隱藏在悲傷的陰影中。
夏慤村在被佔領期間成為希望與社區的明燈,由學生與民主派人士帶領,他們憧憬充滿希望與公民參與的未來。這個「借來的地方」,一個暫時轉變為抗爭象徵的區域,茁壯成長為民主的曇花一現的綠洲——一個名副其實的烏托邦,置身於香港的繁華都市之中。參與者的集體努力將夏慤村變成真誠對話、藝術表達和社區團結的聖地。抗議橫額的鮮豔色彩、慷慨激昂的演講聲音,以及食物攤檔的香味,交織成一曲和諧的交響樂,呼應著共同夢想的浪漫理想。這是人類精神嚮往更美好生活的生動詮釋,也是村莊短暫美麗所蘊涵的理想。
曇花一現的意義
然而,就像所有的古典悲劇一樣,夏慤村的命運已經注定。2014 年 12 月 15 日,也就是佔領的第 79 天,權威的野蠻力量熄滅了社區的活力之火。在高等法院禁制令的催化下,警方的清拆行動標誌着這個充滿希望的篇章之消亡。在集體願望的重壓下茁壯成長的村莊,淪為僅存的回憶,其充滿活力的生命在一天之內熄滅。這個「借來的地方」重新歸於平凡,其本質從都市景觀中抹去。曾經熱鬧的討論與即興聚會消散了,只留下昔日的回聲,鮮明地提醒人們烏托邦的脆弱。
這種迅速的空間開墾,帶出關於人類存在本質的重要問題。夏慤村的最終解散,看似是一種損失,卻揭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事實:烏托邦希望的存在,對於人類的敘事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夢想、野心和對美好未來的追求,我們的生活結構就有可能變得支離破碎、毫無意義。烏托邦稍縱即逝的特性,無論是在夏慤村或其他集體願望的行動中,都提醒我們,構成人類經驗的不僅僅是這些時刻的存在,還有驅使我們朝向這些時刻的希望與願望。
夢想、憧憬一個更公正的世界,成為人類的基本信念,這些願望推動個人採取行動、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並激勵社群為他們的集體未來擬定願景。儘管夏慤村現在可能只存在於記憶的角落,但它所體現的理念和價值觀繼續激勵著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個人。烏托邦的誘惑仍然是我們人類共同經歷中一條永恆的主線,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時候,這條主線仍然將我們與過去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與古典悲劇中英雄所面對的倫理困境類似,烏托邦願望的缺失挑戰我們反思自己的價值觀、意識形態,以及公民參與不斷演變的本質。
在佔領過後,對夏慤村的反思喚起我們在悲劇性的生存弧線中,認清人類能動性的重要性。雖然權力運作系統可以鎮壓臨時避難所,但卻無法熄滅人類與生俱來的夢想能力。夏慤村的浪漫戲劇,在參與者的心中,在香港空氣中持續瀰漫的爭取民主和社會公義的鬥爭中,歷久不衰。在這方面,儘管佔領行動的實際表現可能會消失,但它們所代表的理想卻不必遭受同樣的命運。
回顧過去,夏慤村體現了我們人性中最壞和最好的特徵。它既提醒人們壓迫之後留下的黑暗空洞,也提醒人們社區團結和參與所產生的巨大潛力。烏托邦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但對於我們的存在理解卻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在這些對未來可能發生事情的縮影中,我們找到了創新、創造力和社會變革的動力。最終,夏慤村的精髓就像古典文學一樣,見證了人類對於意義、凝聚力和目的的永恆追求。
夏慤村瞬間之美,同時與悲劇和浪漫交織在一起,反映了一個基本的真理:邁向烏托邦的旅程,無論如何瞬間即逝,在塑造我們的身份和歷史軌跡方面都具有深遠的意義。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提醒:儘管希望的實體表現可能會毀滅,但對更美好世界的嚮往卻永遠存在。因此,當個人面對現實生活時,正是這種持久的希望點燃了精神,激發了對進步的集體願望,提醒我們追求意義與生命本身同樣重要。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