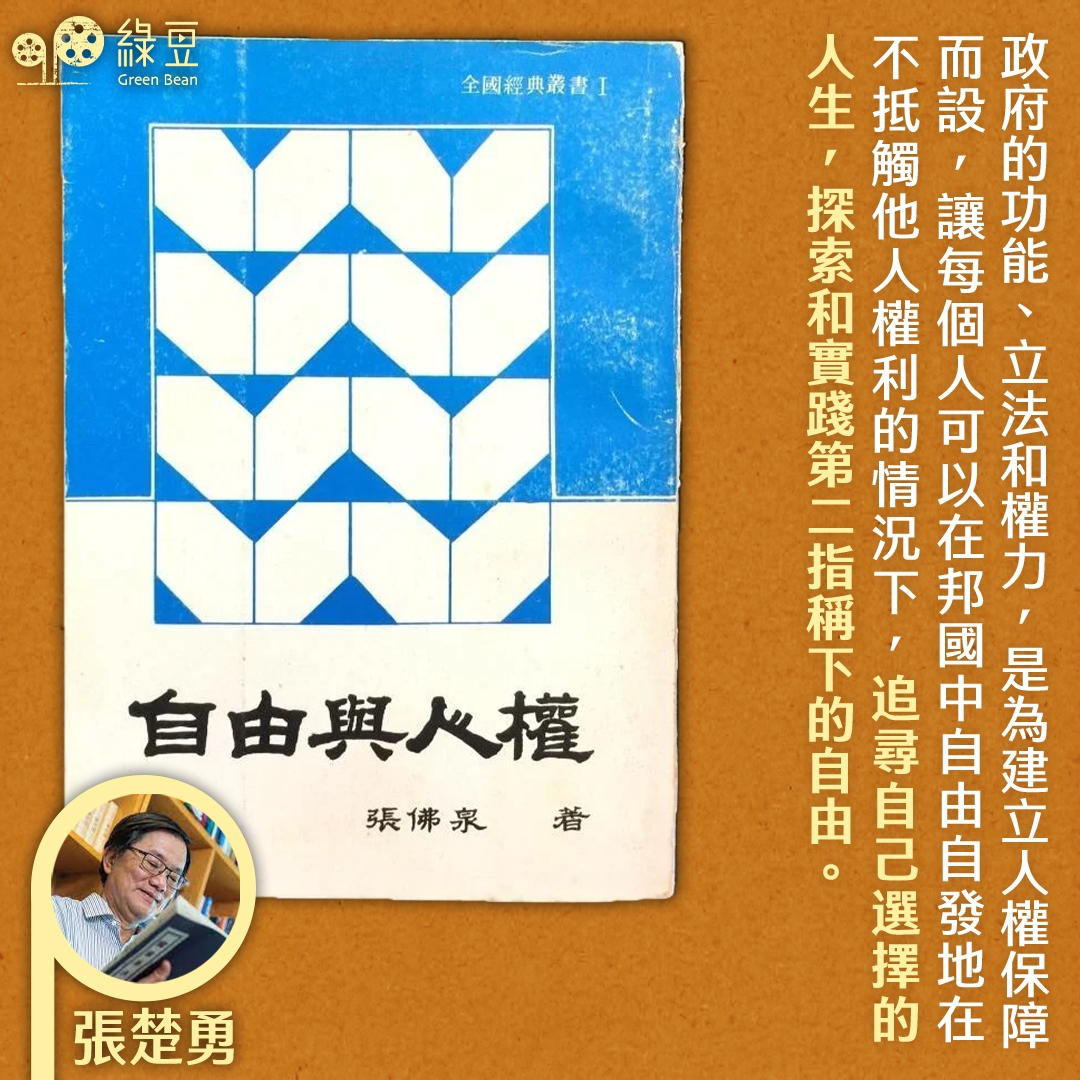在紛亂時代重讀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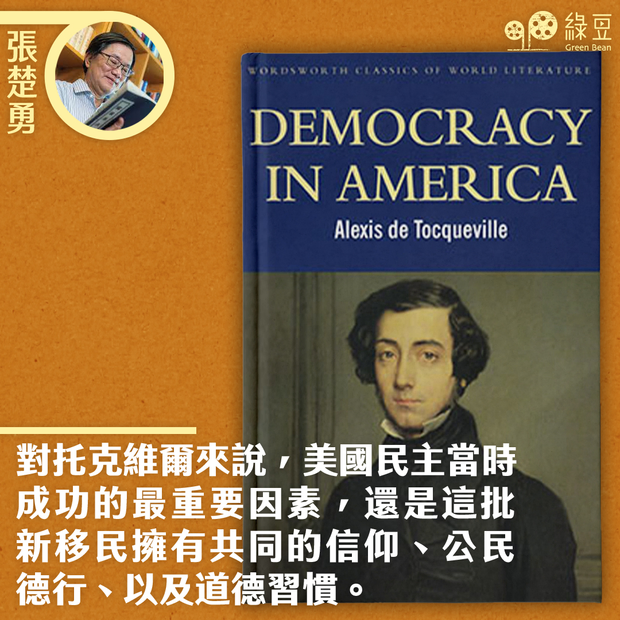
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撰寫和出版傳世之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時,正是個紛亂時代。
1831年他出訪美國長達9個多月,這段時間他到各州的詳細觀察和實地調查,是後來撰寫《民主在美國》的根據。那時美國聯邦憲法實施了只有40多年,距離美國獨立戰爭開始也只是剛超過半個世紀。期間,托克維爾所處的法國經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先後受到革命激進主義血的洗禮和拿破崙歐洲大戰的殺戮,革命狂飆更不斷席捲整個區陸,引來保王力量多次反撲,包括法國自身一而再的王朝復辟政治。
沒有民主革命下的民主
托克維爾出身貴族,但思想傾向民主自由,並認為傳統封建王權的菁英統治社會早晚會被取代。在此新舊交替之際,他同時深刻明白到,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民主,非政治上的萬應靈丹,其內在潛伏的危險(特別是多數人暴政) 如果變成主導,其破壞力和專制濫權以及激進大革命不遑多讓。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托克維爾看到,主要由受清教徒影響的英裔移民群體組成、通過有限的獨立戰爭脫離了英國祖邦建立起來的美國,在存在了半個世紀之後,儘管面臨不少問題,卻似乎成功地維持著一個穩定、繁榮、民主自由的新聯邦國。美國的經驗引起托克維爾極大的興趣,要深入研究這個劃時代新政體的運作之道、成功條件,以及其面對的根本挑戰。1835年和1840年先後出版的兩册《民主在美國》,便是其成果。
我說美國獨立戰爭是「有限」的,原因是爭取到獨立的英裔清教徒在成立了共和國之後,既保留了原有的宗教,也把英倫傳統的法治、有限公權、個人自主、道德習慣等承傳下來。
當然,在聯邦共和制和北美新大陸的環境下,美國的政體和管治模式,必然和帝制英國有很多不同(例如美國各州已實行男性普選制),但背後的原則、價值和做法,卻有不少共通之處。因此,托克維爾說,和歐洲大陸不同,美國在毋須進行民主革命的情況下落實了民主。「美國革命並非是對獨立持有一種空泛和界定不清的感受所造成的,而是因為對自由深思熟慮後的一種成熟的品嚐。」(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result of a mature and thoughtful taste for freedom and not a vague and ill-defined feeling for independence.) 托克維爾如是說。
這本差不多200年前寫成的傑作,自然有些過時的具體背景和分析。例如那時美國只有24個州;疆域未拓展到太平洋彼岸;當時的聯邦政府相對於州政府還是處於弱勢等。但此書至今仍舊值得細讀,我個人認為至少是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民主在美國》既有高度洞悉力的政治分析,同時也有堅實的事實基礎。雖然它研究的對象是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但托克維爾提出的論據和採用的研究方法,到今天還具參考價值。
另一個原因是,儘管全書厚達800多頁,而且相差5年才出版的上、下册在分析層次上前者比較實證、後者比較抽象,但文筆出眾,能作深入淺出書寫的托克維爾,把作品一氣呵成的表現了出來。當中既包含了不少有史料價值的記錄,而且寫得具體感人之處,往往讀來使人動容。上册第十章談到印第安人和美國南方黑奴面臨的困境,和對他們在政治上近乎絕望的具體描述,讓人明白到,最精彩的政治分析,同時是傑出的文學作品。
托克維爾未能預測到美國後來會因為解放黑奴爆發內戰。但他基於南、北就此的分歧,以及正常政治似乎不可能就黑奴一事作出根本解決的這一認識,推測黑奴這個死結,早晚會考驗到美國聯邦會否分裂,而考驗的過程,難免訴諸武力。這一判斷具有驚人的洞悉力。
成功關鍵
在這篇短文餘下的篇幅裡,我將會就上述的第一個原因,作進一步的陳述。
托克維爾認為,不能光靠抽象理論來判斷政府的實踐。因此,要分析聯邦美國,便得既從體制邏輯和實證觀察對美國民主作出解釋。從這個意義說來,《民主在美國》不光是研究美國民主的第一本專著,而且更是現代政治科學意義上第一本以深入個案為基礎的比較政治學著作。
一群歐洲新移民,在前無古人,未來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建立並成功地維持著第一個聯邦大共和國,讓組成聯邦的各州以普選產生行使公權的代表。就這個重大的政治新現象,托克維爾提出了三個解釋因素:第一,北美洲的獨特地理人文背景;第二,英裔清教徒在美洲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制度;第三,這批新移民的道德行為習慣和規範。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得天獨厚,新大陸是一片未被現代文明開墾的大地,外有海洋、極地等天然屏障,因此美國幾乎是沒有毗近的競爭鄰邦。內部而言,新大陸有著等待國民不斷拓展的土地,使美國對外既缺乏有威脅的敵人,對內也不擔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資源問題。加上國民全是宗教文化上相近的新移民,又沒有傳統上存在的階級分野,大家都站在相近的「起跑線」上。擁有這樣優厚的客觀條件,自然有利於國家穩定,大大降低了建立普選共和制的門檻。
不過,托克維爾認為,得天獨厚並非最關鍵因素,因為南美洲同樣得天獨厚,但西班牙人在那裡卻未能保持政治穩定,更不要說建立可持續的共和大國。相對而言,托克維爾相信,美國承襲了英式的法律憲政(特別是司法獨立、陪審員制度、保障財產和人身自由、法治政府)這因素更為重要。
另外,托克維爾在談到美國政府和行政時,以「行政分散、政府集中」(decentr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來形容當時的美國。由於地大人稀,政府在不同層面的地方行政很難通過常設或具規模的官僚組織執行法律和行政指令,因此地方上的治理,包括税收、治安、公共服務、設施等,特別是在鎮(township) 的一層,基本上得靠公民自治,由當地居民自行選出鎮長和幾個在不同崗位的主事公職人員,就其公職範圍差不多全權依據議會制定的法律主理其事。如有需要進行地區公共設施建設,則由全體居民合力負責。
由於普選制度下,國邦議會或地方制定的法律和規條,都是居民自己參與制定或通過普選議員制定的,因此多數人其實基本上都是在遵守或執行自己同意或授權的指示。這種由下而上的自治執行制度能夠行得通,一方面是因為在新開發的疆土上,行政事務的要求比較簡單直接,地方公民可以親身參與其事;另方面也因為美國的立法權、選舉制度、以及違法時的懲罰和監督等都已依照憲法和相關法律集中的貫徹執行,因此讓當時面積是法國5倍的美國,能實行聯邦式的民主管治。
但對托克維爾來說,美國民主當時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還是這批新移民擁有共同的信仰、公民德行、以及道德習慣。
17、18世紀前往新大陸的人,很多都是有教養、虔誠、不滿歐洲舊世界的不公腐敗、或逃避宗教迫害的英裔清教徒。這批人到了美洲後不單重視契約精神、信守規矩和承諾,而且他們的信仰使他們在神面前視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並且要憑良心在世上做個負責和有道德的人。加上他們決心離開舊世界建立新社會,因此社群和公益意識特別強。這對托克維爾來說,正是美國能有效維持民主共和制的主因,否則當時在法律和政制上模仿美國的墨西哥便應該同樣成功。
因此,托克維爾說:「建立在這麽簡單自然的一個觀念的民主政府,其實常常蘊涵著一個非常文明而有教養的社會的存在。初看時,也許會以為民主是屬於最早期的世界,但細心去研究,便會發現,它只能是世界最成熟期的體制。」(”Democratic government, founded upon such a simple and natural idea, nevertheless always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 very civilized and educated society. At first sight, it may be imagined as belonging to the earliest ages of the world; a closer examination allows us to discover that it had to come about last.”)
制度存在的問題
不過,熱愛自由的托克維爾同時擔心,強調平等的民主制度在體制邏輯上和實踐上都存在很多問題。他在《民主在美國》中說,每次總統大選都可以是一次國家危機,例如為了連任,在位總統臨近大選時總是千方百計討好選民,而非理性地去管治好國邦的長遠利益。他更認為事實證明,以為普選是選出優秀人才的保證是絕對的自欺欺人。
此外,托克維爾認為,選舉政治容易導致貪污,民主政客腐敗也是常見的事。更令人擔心的是,民主政治有一種民粹傾向,會因一時的情緒熱情蓋過理性討論,放棄成熟的政策以逞一時之快。他舉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為例。美國當時舉國上下激烈要求支持法國,並向英國宣戰。幸好當時華盛頓總統明智地堅持不介入與美國安危沒直接關連、複雜多變、又鞭長莫及的歐洲政治,以其開國英雄的聲望和總統憲法上全權主理外交的權力,壓住了這情緒的要求。但他以國父之尊,還是受到強烈的抨擊,更被指責為賣國賊,可見民粹政治對民主的潛在威脅。
體制邏輯上,托克維爾對民主最擔心的,就是多數人的暴政。他認為掌公權者總有集權傾向,以政治平等為原則的民主也不例外。以少數服從多數作為決策原則的制度,同樣會不斷要求和嘗試把公權集中起來,使多數的意志和決斷變得越發強大,甚至到了壟斷和不容挑戰的地步。
此外,以平等為最終原則容易變得事事要求齊一,對任何不同難以包容。在托克維爾身處的年代,歐洲一方面以解放之名,對封建貴族政權和社會作出暴力革命式的攻擊;另方面,革命邏輯又迫使解放運動團結力量,絕對服從革命的大目標。在這情勢下,就是民主運動也難避走上多數人暴政的道路,對個人自由構成嚴重的威脅。
儘管如此,托克維爾到底還是相信,建立維護自由的民主制度在當時的歐洲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美國相對成功的例證,可以讓大家客觀了解其優點缺遺,以便更好地鞏固自由民主長治久安的條件。
現世需要托克維爾的洞見
托克維爾在他那個年代是個實事求是、為自由民主建立正面條件和資源、為民主的不足提出警告的思想家。他在《民主在美國》的結論強調,如果能加強公權力之間的制衡、鞏固對社會成功至為關鍵的各界別(例如工商專業等) 的獨立地位、確立高質獨立的司法系統、維護新聞自由、對社會多元或和而不同的風俗習慣多加尊重、以及對公權侵害私人權利的傾向提高警覺,這樣也許可以讓政治平等的民主,難走上多數人暴政之路。
重讀完托克維爾的經典之後,我想,在強權和自由繼續爭持的21世紀,我們更需要有今天的托克維爾,繼續發揮《民主在美國》的洞見,寫出《民主在台灣》、《21世紀的獨裁與民主》、《伊斯蘭文明與民主》、《數碼網絡、大數據、AI:民粹vs.民主》等未來經典,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到,當今的世界,個人自由和尊嚴面對的種種機遇和政治挑戰。
謹以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以下的一番話結束本文:「有這樣的一個權威,無時無刻確保我寧靜地安享我的所好,讓我毋須思索便替我掃除所有在我路上會遇到的危險。假如這個權威,在拔除我腳下荆棘的同時,更是我個人自由的絕對主宰,包攬著這權威所及的一切活動和生命。當權威躺平時所有人都得躺平、睡覺時都得睡覺、滅亡時都得滅亡。這樣的權威,說到底,對我真是好嗎?」
“After all, what good is it to me to have an authority always ready to see to the tranquil enjoyment of my pleasures, to brush away all dangers from my path without my having to think about them, if such an authority, as well as removing thorns from under my feet, is also the absolute master of my freedom or if it so takes over all activity and life that around it all must languish when it languishes, sleep when it sleeps and perish when it perishes.”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