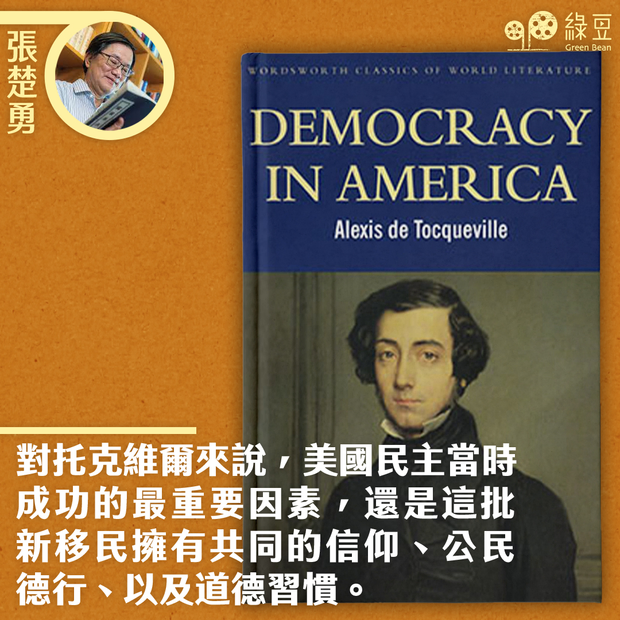哲人與流亡:序《滄海橫流要此身》

20世紀英國學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哲人是「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victim of thought)。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思辨是一種對所有思想內容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不斷進行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任何結論,在哲學上都是臨時的。因為除非我們停止思考,否則,所有思辨在過程中達至的有關結論,其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總是可以作出進一步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嚴格說來,哲學思辨是個無涯涘的追尋。哲人對思想的拷問,是一種不斷啟航的知性釐清和加深認識的行為。哲人在這旅途到達的所有目的地都是過客。因為哲人會對到達了的目的地可能引發出的、未被探索的新路徑或潛在的通道產生不能自拔的好奇,於是便不能自已的再走上思辨拷問的征途,邁向無涯涘的思考。
哲人如果不能在他生活的所在地進行哲學思辨,或者他那不斷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活動,受到了掌管公權者的禁制、懲處,甚至迫逼其思辨活動服務於當權者的政治目的,那麽,哲人為了忠於其無涯涘知性的追尋,便有可能被迫流亡。否則,哲人很可能從「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變成是被政治迫害成為工具者,因而無法繼續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辨。
被迫流亡在外的先輩
我和本書作者張燦輝都是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張燦輝是我的學長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自己則畢業於香港大學,修讀的是哲學和政治學。我們這些在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看到香港1949年後,成為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少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的流亡地。這些華夏知識人,基於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因由,其思想或作為不容於掌控公權的黨國體制,因此只能避秦於這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否則便不能繼續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
在這方面,相信錢穆先生和一些當代新儒家的主要學人,他們在流亡香港後,所產生的文化思想貢獻最為顯著。錢穆和唐君毅等幾位先生在九龍桂林街創立的新亞書院,旨在於香港這彈丸之地延續中華文明的命脈,以抗拒自五四運動以來,他們認為的那股在文化和政治上全盤反中華傳統的狂飆,其在思想和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的流亡知識界中,算得上是表表者。為國民政府草擬1947年頒布的中國憲法的當代新儒家張君勱先生,在1949年國共內戰後,被新中國政權列為43名頭號戰犯之一而流亡海外,他於1958年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新儒家在香港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更是當代以繼承宋明心性儒學為志業的哲人學者,回應中華文明面對現代性和民主科學挑戰的重要嘗試。
被迫流亡在外的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失去了故土,換來的,是保住了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和關懷。離散的知識人,在花果飄零的空洞處境中,必須特別自覺和有決心,否則其流亡便失去意義和憑藉。儘管這些流亡的先輩始終沒有視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英殖民地為家,但他們選擇在香港建立其流亡事業,我相信,他們是絕對明白,當時香港的相對自由開放,不受黨國專權和直接干預的客觀環境,構成了他們流亡事業所必須(雖然並非充分)的條件。而這個他們視為非家非故的異地,卻直接或間接地因他們在流亡時所開創的文化、思想、教育等事業而變得豐富起來。新亞書院發展成後來的香港中文大學,當代新儒家在香港栽培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他們在香港發表的著作,所樹立的風範,是塑造戰後香港成為相對自由而又有現代中華文明內涵的一個獨特地方的一大原因。
內部流亡者的生涯
我相信,流亡者不一定只流散於海外。上世紀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思想學人施克萊(Judith N. Shklar),在談到美國19世紀通過公民抗命和不服從的手段抗議美國憲政中容許黑人奴隸制度存在的梭羅(Henry D. Thoreau)時,形容他在美國國內針對他視之為不義政權的良知抗爭,是屬於最為極端的國內個人自我隔離的流亡者。
殷海光先生
年青時,我讀到在台灣的殷海光先生在1960年代受到國民黨專權迫害的經歷,知道他在堅持其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時,還強調要有「隔離的智慧」。我當時的理解是,殷先生在台灣是過著異議者的內部流亡生涯。雷震、殷海光等這些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國民政府的知識人,在政府戰敗後偏安於台灣,但他們的自由民主思想、主張和實踐,最終卻不容於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黨國體制,以致他們表達政見思想的《自由中國》被查禁,實務負責人雷震等被判煽動叛亂罪身陷囹圄10年。而撰稿敢言、不妥協的殷海光後來不能繼續在台大教書,又不能出國作學術訪問和研究。他們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堅持自由思想的論述,為此而作出了不少犧牲,卻在兩岸兩個黨政專權的體制之間,保持和延續了自晚清以來,嚴復通過系統翻譯介紹西方近代經典著作所開展出的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我認為,這是現代中華政治思想史上,令人動容的了不起貢獻。
顧準先生
內戰後,離散在外的自由知識人張佛泉先生在1954年撰寫其《自由與權利》一書時說:「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正是文窮而後工,思想家在流亡離散的自覺責任催迫下,往往在理念上取得突破。張佛泉對個人權利的以下認知,便是一例:「『無法出讓的權利』之說,其道理並不在人曾有此權利,因之不可以出讓,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覺,即無法將此自覺出讓。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即使有意將權利之形式出讓,無奈自由之自覺卻依然還在。至此,人權已無法與生命撕拆得開。故人在歷史過程中,未至自覺自由階段,尚有被奴役可能,但一朝意識到自由,便已無法再將它排除。人權不但無法由人拋掉,甚至無法為他人所否認。摧殘人權(一如屠宰人群)是可能的,但否認人權則不可能。因一朝不承認人是權利主體,此人便先已自外於人之社會。」
事實上,真正的哲人和思想家,他們就是在處於內部流亡的境况時,那種上下求索的思辨追尋,憑著「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這一意識,是不會消失的。上世紀在中國大陸從反右到文革這段時間的顧準先生,也許是令人印象最深的相關例子。讀他遭受迫害時的經歷,同時看他記下繼續堅持作為「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的日記,使我感到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且看看下面兩段:
1966年9月
“他們將他從窩棚拖出,按在地上剃去半邊頭髮……當眾毒打,再用磚頭猛擊頭部……鮮血噴出來,濺開去,然後將「他」在黄土地上拖來拖去……繼續拳打腳踢,讓血滲進土裏……”。
(1966年9月至1968年8月,被批鬥之餘,顧準記下了以下的事):
“把書架上……讀過的歷史書從頭複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系統地讀了馬恩全集二十餘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費四五個月時間,複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着手翻譯喬安•羅濱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已成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管開始擱筆。”
2019年底,我有機會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談到顧準。當時,我提出了顧準在內部流亡時作出的求索思辨的重要性的三大理由:
第一,1957年,當中國剛在實行社會主義第一個五年的計畫經濟時,他帶頭指出,沒有市場和價格機制(這些都是馬列毛要取消的),根本不可能實行中央規劃。後來他被兩次打成右派,卻成為共產中國主張市場改革的第一人。
第二,1959年大躍進大飢荒時,他被下放到災情最嚴重的信陽地方商城勞改,看到哀鴻遍野,人吃人。通過他的經歷和觀察,得出大躍進的飢荒是政策造成而非自然災害的結論。這比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在1980年代時提出的現代社會飢荒的出現,是權利分配問題而不是糧食不足的解釋,早了二十多年。
第三,在他去世前的1970年代初,分析了人類兩大近現代革命傳統(即法國和俄羅斯的恐怖統治與英國和美國的漸進改革)的分別,並大力主張應跟隨英美傳統的努力,使開放改革後大陸的自由派知識人受到啟發,紛紛在1990年代時提出類似看法。
對烏托邦的重要想像和追尋
張燦輝在書中提到流亡者「無家的自由」和「有家的悲憤」。這也許是流亡經歷最難令人抒懷的悲哀。對流亡在外者而言,就像施克萊提到二戰時德國猶太流亡者的感慨:「我怎可以在這陌生異地高唱上主之歌!」「無家的自由」,對他們來說,總有那揮之不去的空洞;「有家的悲憤」對內部流亡者更是無日無之的經歷。不幸者如顧準般,更要承擔自身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的悲劇。
流亡的經驗,時刻提醒我們,此岸社會人生是不完美的。吊詭的是,人類對烏托邦的一些重要想像和追尋,卻是在流亡期間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便是個最重要而最具威力的現代例子。
現實的不完美,自然會引來哲人和好思辨者的批判,希望尋求改革,甚至是徹底探索臻至完美之道。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柏拉圖的經典《理想國》(The Republic),就是這位古希臘大哲,在老師蘇格拉底被「腐敗的」雅典人民議會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處決後,反思在理念上,如果人類能重頭再來,將如何可能建立一個合理完美又不會腐敗的邦國?
但正如施克萊在反省烏托邦的文章中提醒我們說,如果我們忘記歷史的慘痛經驗,以為現實是可以隨時任意推倒重來,這是極其危險的想法和做法。在討論西方烏托邦思想時,施克萊說,在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之前,烏托邦的意念只是對理想的想像,這想像既有拓展人文思想深度和廣度的抒發作用,也是對評價現實不足的一些可能的參考標準。但重要的是,當時的烏托邦思想既非是革命性的,更不會被認為是可以用來徹底改變世界,把完美帶來人間世的行動綱領。可是,到了摩爾之後的烏托邦思想,卻愈來愈變成是改變世界的意識形態了。
奧克肖特認為,尋根究底的哲學思辨是最具顛覆性的,因為這思辨正是不安於已被接纳的看法,要嘗試質疑思想和社會上的主流和根本的共識。蘇格拉底是位徹頭徹尾的哲者,他雖然深愛他的雅典城邦,並願意為此城邦獻出生命,但其哲思對城邦賴以维持政治社會穏定的傳統理念根據,還是會進行顛覆性的拷問。哲人和政治社群的張力,大概因此是難免的。哲人的流亡或遭受政治迫害,歷史上是經常碰上的事。
鄂蘭 (Hannah Arendt) 在反省納粹暴政時說過,思辨是危險的,但不去或禁止思辨,則是更加危險的事。反思烏托邦的現代思辨經驗,也許印證了鄂蘭這觀點。張燦輝這本談哲者與流亡的書,既是作者近年錐心之痛的個人經歷,其反省的過程,自然又帶出沒完沒了的、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理念和議題,引誘那些「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不能自已的啟航,繼續開往無涯涘之境。至於這航程會抵達到哪些目的地,那卻是後話了。
謹此序。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