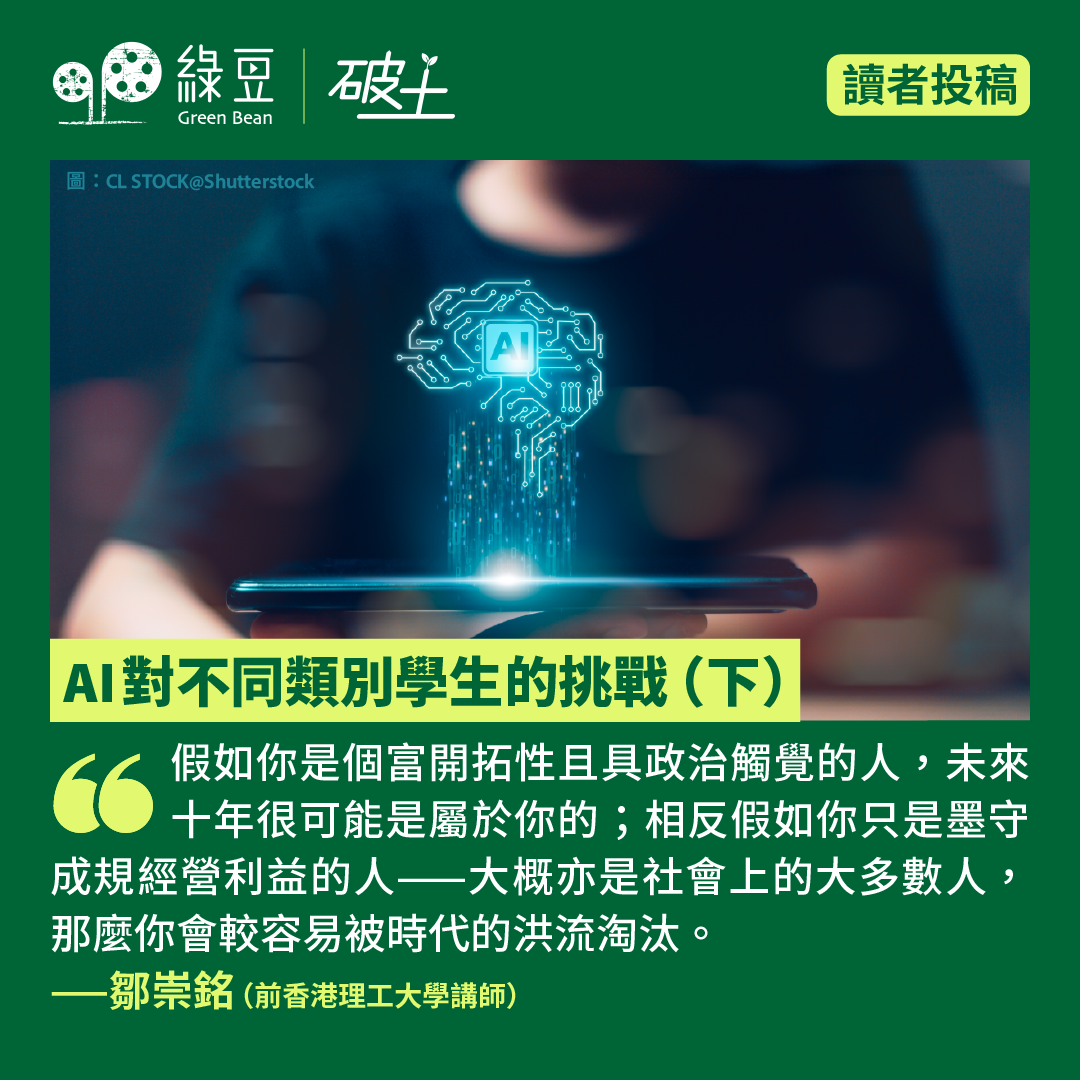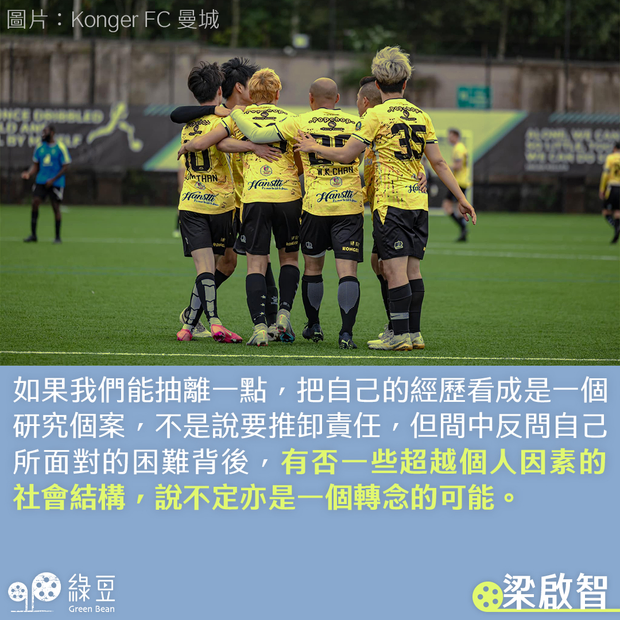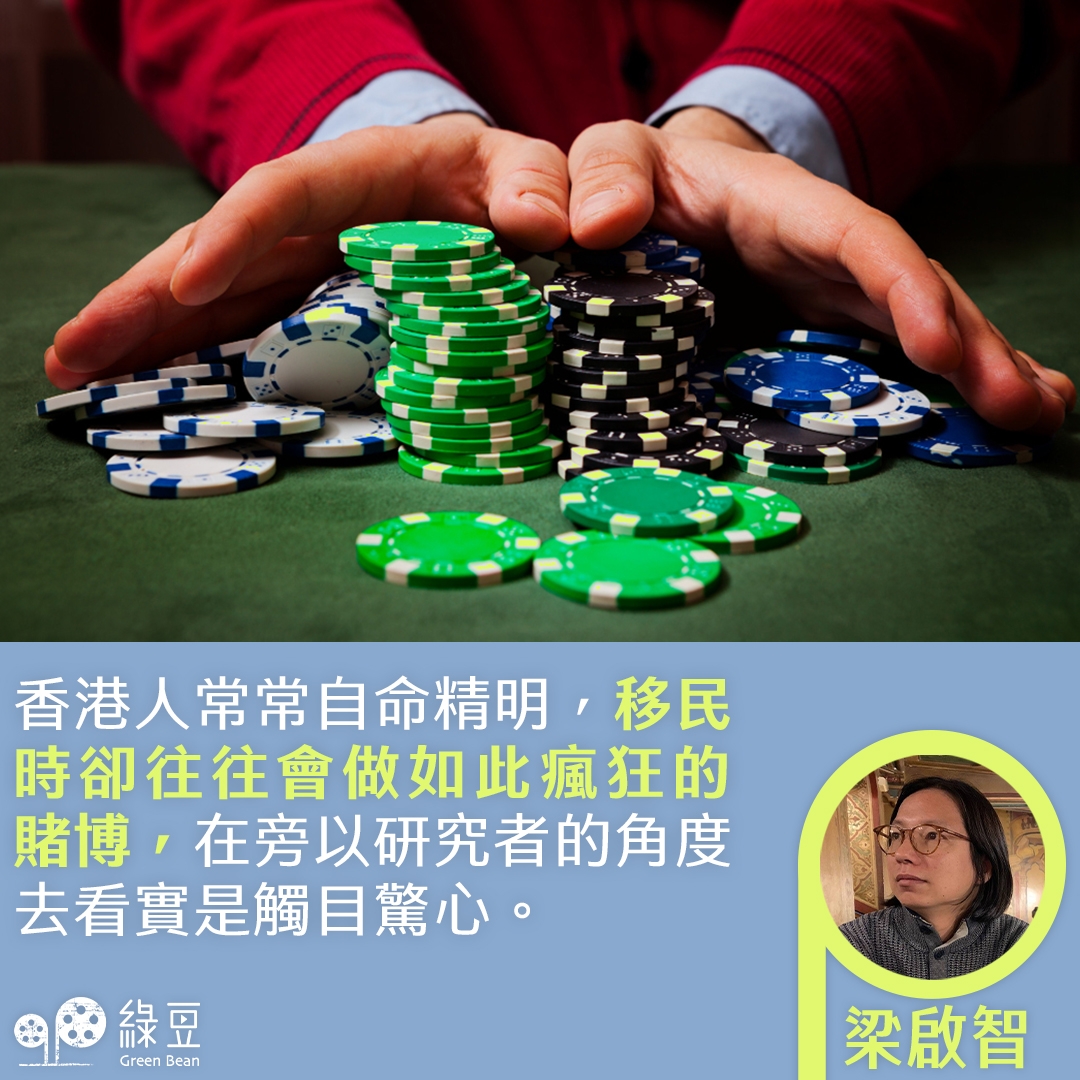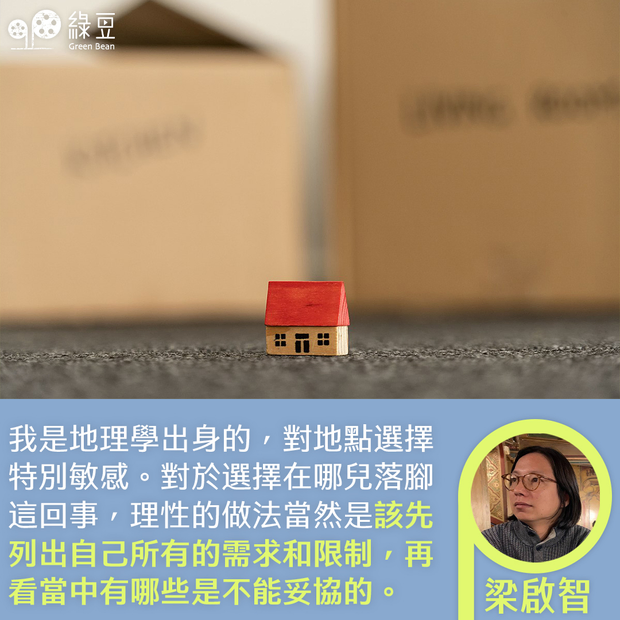倖存者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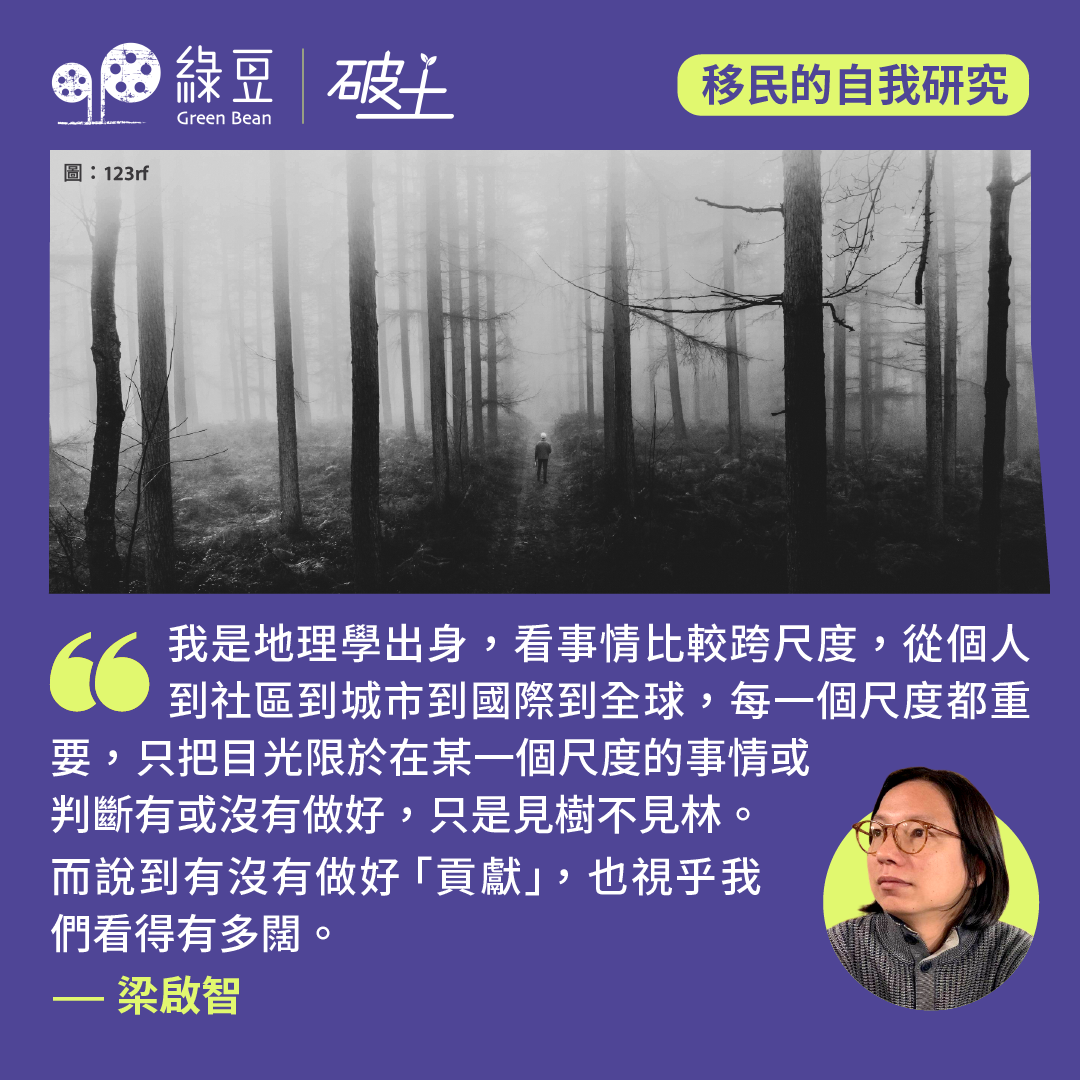
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
第二種方式是自我懷疑,例如不停重演某一個片段,然後質疑自己當初為什麼沒有做某件事,或意識到某些事情將會發生,應該做好準備。我早陣子遇到一位已離港的抗爭者,他到今天仍然對自己在某一次街頭衝突中自己觸覺「不夠敏銳」而耿耿於懷。有些離散港人像他這樣仍然活在2019年,往往認為如果當日能做到某些事,或作出某些判斷,今天的苦難就可以避免,繼而質疑自己當日的「失誤」。
第三種方式是前面兩種的混合體:因為覺得自己離港後過得比留下來的人更自由,又覺得自己過去有些事情沒有做好,便有巨大的憂慮,覺得要作出某些「補償」。而如果自己未能利用相對較多的空間去「做出一點成績」,便會陷入更大的自責。
曾經不止一次聽過有研究者覆述尋求庇護者這樣自我描述:相對於在香港坐牢,現在在外面天天等待當地庇護審核的程序,覺得自己是「廢物」,好像很「沒用」。
抽離一點去看,當然可指出上述的情緒反應都有其過於偏執之處。每個人的客觀條件都不一樣,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做出同樣的事情,才算對社會和自己負責任。社會運動有運轉周期,不是每一刻都要做相同的事情才算合適,有些時候容許沉澱的空間也是必須。
請將尺度拉闊
我們也得明白社會事件的走向在絕大多數時候不受個人意志所影響,後面既有全球宏觀的政治經濟局勢主宰,亦可以算到最微觀的日常生活如何被賦予意義。我是地理學出身,看事情比較跨尺度,從個人到社區到城市到國際到全球,每一個尺度都重要,只把目光限於在某一個尺度的事情或判斷有或沒有做好,只是見樹不見林。
而說到有沒有做好「貢獻」,也視乎我們看得有多闊。離開香港後,要繼續做和香港直接相關的工作,機會不多。自問能在台灣找到相關機會,甚為幸運。但如果我們如上所述,不把在香港的經歷純粹視為香港境內的事情,而是從個人到全球的眾多關係網當中的其中一個章節,則各種貢獻都可以是對香港作出貢獻。
早陣子讀到有位移英港人說他初到英國時,覺得自己有責任向英國人說明他眼中香港的苦況,於是很努力與每一位他遇到的人去談香港的情勢。但當他在英國接觸到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明白到他們很可能比香港人更沒條件和資源去應對他們的苦難時,頓感不知道如何是好。
想深一層,香港從來與世界相連;沒有信奉自由的世界,也不會有自由的香港。那麼幫助烏克蘭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或世上任何受制度壓迫的人也好,都是在幫助香港;因為幫助他們就是促進世界的自由,而促進世界的自由就是為未來的香港保存土壤。
當然,以上僅是出於客觀分析的回答,愧疚情緒很多時候都是不講道理的。從個人出發,練習自我慈悲與實踐復原,應該是一個起點;重點不是消除內疚,而是融入生命當中,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以求重拾自我。而在此過程中,朋輩同儕互相支持,一同梳理各種混雜情緒的糾纏,更是必須!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