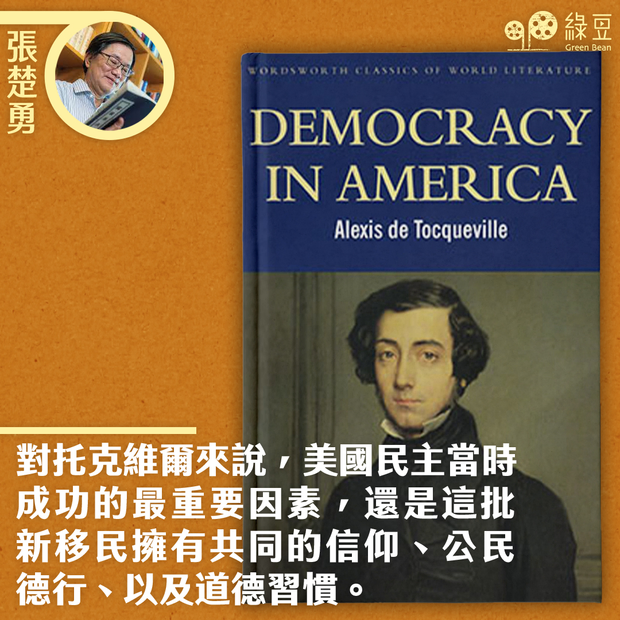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自由與人權》和「無法出讓的權利」

張佛泉的《自由與權利》一書,到今天仍舊被視為是華文世界中關於自由思想的傑作,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他對個人那「無法出讓的權利」的論述。張氏在1954年為該書撰寫序言時說:
「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 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
這是一段沉痛的話。也是張佛泉這類中國自由思想家在去國流亡後的深切反思。
為什麼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個人權利是「無法出讓」的呢?張佛泉在書中作出的以下解釋是至為關鍵:
「『無法出讓的權利』之說,其道理並不在人曾有此權利,因之不可以出讓,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覺,即無法將此自覺出讓。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即使有意將權利之形式出讓,無奈自由之自覺卻依然還在。至此,人權已無法與生命撕拆得開。故人在歷史過程中,未至自覺自由階段,尚有被奴役可能,但一朝意識到自由,便已無法再將它排除。人權不但無法由人拋掉,甚至無法為他人所否認。摧殘人權(一如屠宰人群) 是可能的,但否認人權則不可能。因一朝不承認人係權利主體,此人便先已自外於人之社會。」
如果我們細讀這段話,便會發現,其含意和背後假定的前提,是十分豐富的。如果我們有系統地把這些含意和前提連繫起來,便構成了一個頗為深刻的自由人的人觀。
這段話,說的是對「自由的自覺」。
需通過歷史過程
我認為第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這自覺乃通過一「歷史過程」而成就。換言之,自由的自覺是人的一大歷史成就,這自覺並非是先天的,也不是人類在達至此自覺之前便擁有的。
在西方現代政治學裡,「無法出讓的權利」往往說成是「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自然的是」(natural right) 。如果人類對「自由的自覺」是通過一歷史的過程而成就的,說人權是「天賦」或「自然」,並非意味著人一生下來便擁有這自覺或權利,而是說人的稟賦是有能力發展出對自由的自覺,但如果這稟賦因為種種原因沒能發展出這自覺,那這自覺便不會存在。
人有自覺的稟賦,便假設了人是一有意識的主體。這意識反過來又會把自身作為一認識對象;於是,意識便發展成自覺,這自覺是建立在對主體的自我認知之上,並嘗試理解主體和其身處的環境(包括其他物和其他自覺的主體) 中的種種關係。必須注意的是,對張佛泉來說,「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中的「人」,指的是個人,並非是集體的人或其他抽象的集體單元。因為在《自由與人權》一書中,張佛泉既主張在認識和解釋人類和社會現象時,只能還原到獨立的個人才是真實的個體的分析路徑,這也就是方法學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他同時也強調,權利的載體,只能是個人,不能是任何集體。
自覺既然是一認識和理解的行為,那便牽涉理知。理知的運用使個人的認識和理解水平不斷發展、深化和提高,而這自覺和理知的稟賦在發展至相當程度時,人便發現自身這個主體和已知的萬物並不相同,而這不相同正是因為自覺和理知是人類的獨特稟賦。因此,人之所以為人,正是這些獨特稟賦所構成,而自覺和理知既是通過個人這個主體而進行,每個個人的獨特稟賦便彌足珍貴,個人的價值和尊嚴,便是建立在對這些個人稟賦的尊重之上。既然每個個人同樣是個自覺和理知的主體,那麼每個人都應得到同樣的尊重,以便每個主體自主自覺地在互相尊重的關係下追尋自我和互動,這便構成了社群中自由的自覺的認知。基於此,張佛泉認為,「人之自由及人之價值皆由於理知與自覺」。
西方歷史的人權運動
人對自由的自覺有了認知之後,便不可能自欺欺人地從理知上否定這自覺,抹殺自己是個自由的主體。這就是張佛泉上面「『無法出讓的權利』之說,其道理並不在人曾有此權利,因之不可以出讓,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覺,即無法將此自覺出讓」這番話的根據。當然,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中,踐踏人權、自由、生命的事常有發生,但這在理念上並不能否定個人權利和自由不能讓渡的理據。同時,在價值上踐踏人權自由也正是反映了破壞者不把人當人的道德敗壞。換言之,人有了自由的自覺之後,人之所以為人,離不開個人的自主自覺和理知。把人當人離不開尊重個人為目的,並保障個人的自主和權利不受任何人或組織侵犯。
正如我在本文開首時說,張佛泉是在1950年代「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使像他這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離散流亡之際,才深切了解到「無法出讓的權利」這道理。在現代中華自由思想的發展中,這也許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人」的發現。但為什麼在極權暴興之前,連張佛泉在內的中國自由知識人也輒將「無法出讓的權利」這些西方的自由人權核心思想輕易放過,並且很可能「實在並未懂得」呢?
要充分回答上述這個大問題,將牽涉很多複雜的理念分析和歷史研究,這並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但如果大家讀過我今年9月初發表在《綠豆》的〈離散與經典:向《自由與人權》學習〉,你也許還記得,張佛泉認為,近代的人權運動是到了17世紀才在西方興起的。這人權運動更是由三股不同的西方歷史思潮匯集而成,它們分別是古希臘年代斯多噶派開啟的「自然法」(natural law) 傳統,英格蘭自1215年大憲章以來,為限制王權而發展出的英式的「古老的自由與自由的風俗」,以及自16世紀以來強調個人信仰和個人良知的宗教改革運動。
這三股歷史思潮,在種種的歷史偶然和機遇下,成就了現代人對個人自由的自覺和實踐。張佛泉這些中華自由主義者對我們的貢獻,是通過理念啟蒙的方式,讓中文世界的人開始認識到,理念上什麼是「無法出讓的權利」。但如果對個人自由的自覺無可避免地是一歷史實踐過程而成就,中文世界既沒有「自然法」,又沒出現過大憲章式的古老自由風俗,也缺乏基督教宗教改革的背景,要在中華文明發展出對個人自由的自覺實踐,除了對中華近、現代的極權統治造成的苦難必須作出深切反省和改革之外,在前面等待著我們的,看來是一條路漫漫其修遠的上下求索的艱辛之旅。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