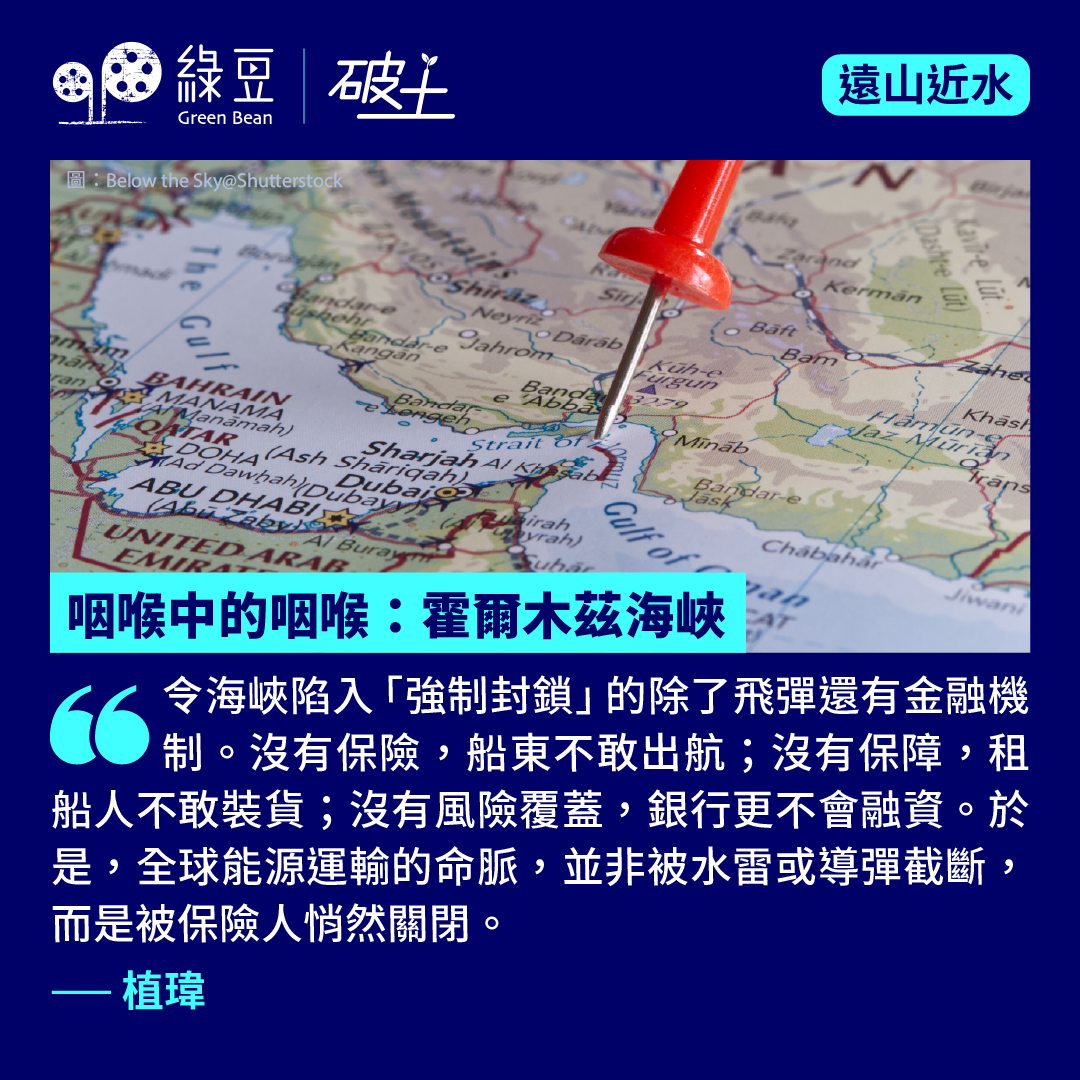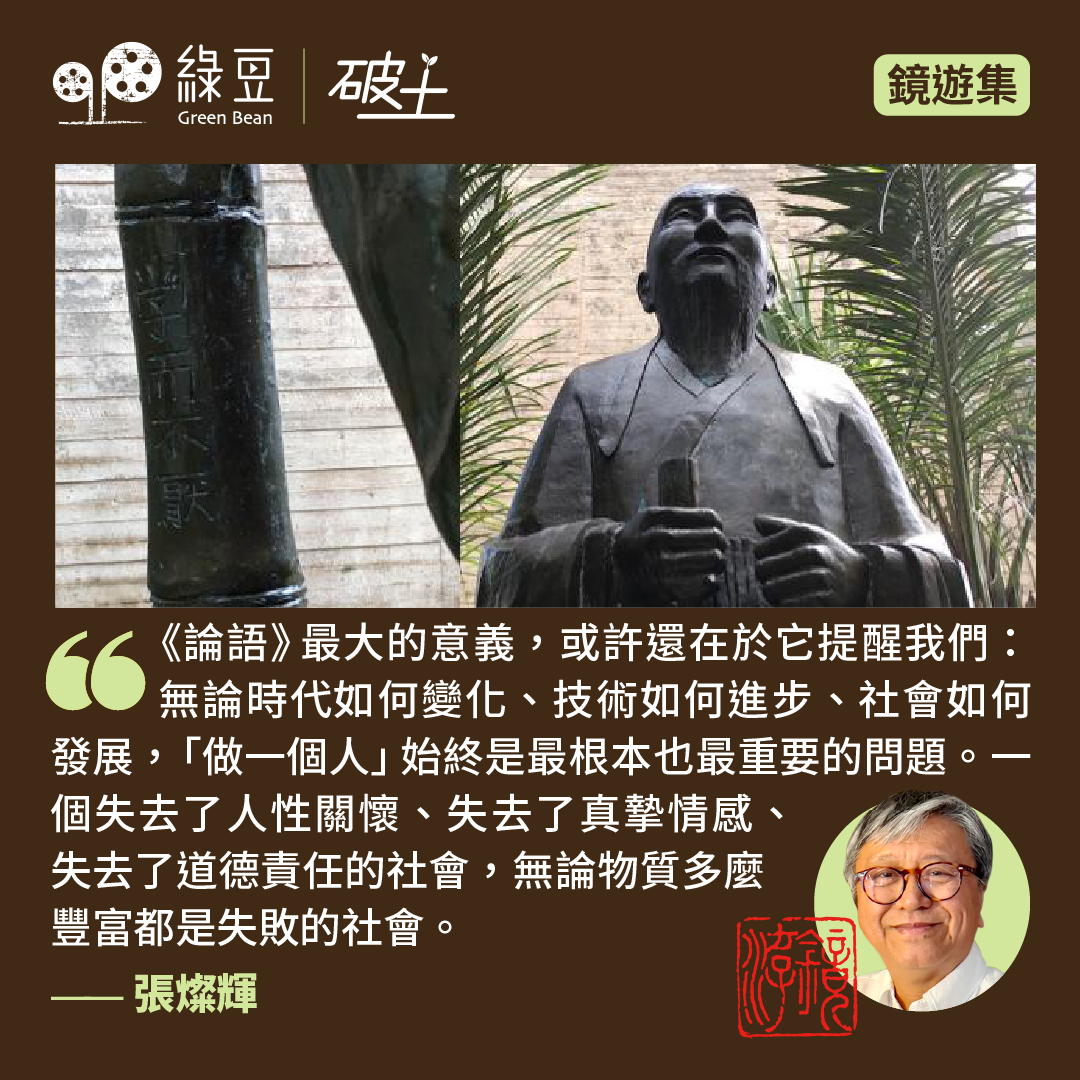《滄海橫流要此身》:唐君毅與香港 (下)

(編按 : 上文提到唐君毅先生1949年避秦南來後,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
==============================
唐君毅先生認為,為使中國文化重生,故必須重新肯定儒學,這個肯定首先在自由的香港,其後傳到台灣,以及美國,如今講中國文化與哲學,都在這三個地方。論重振中國文化與哲學成就,台灣是否最高,我不無懷疑。但如今台灣,正如過去香港,皆是華人世界中較為自由之地。因此,在台學者可藉此優勢,推動新儒家運動,正如當初唐先生利用香港這個特殊位置,實踐其理想,儘管這個理想與香港本土毫無關係。他似乎沒有思考過,如何運用此思想推動香港文化,因為他認為兩者完全無關。他所思所想,都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對立與融通,他的中國文化,從完全抽離香港此地之普遍意義上出發。
正因如此,《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雖由唐先生起草,並有幾位先生聯署,卻並不完全為當時學者接受,其中反對最力者,莫過於錢穆先生。他堅決不參與,且表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宣言是「在」香港發表,但不是「為」香港而撰寫。在唐先生心中只有大中華,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和空間」。
花果飄零的概念
除重振中國文化外,唐先生另一個最著名理論,就是他於1962年所發表中國人花果飄零的概念。所謂花果飄零,就是說中國文化失去凝聚力。過去中國就是披上儒家外衣的古老國度,但從民國以來,儒家受全盤批判,其中被指斥尤烈之處,就在於它自春秋戰國後,逐漸被統治者利用為統治工具,因此,它失去價值,失去吸引力,自然再無凝聚力可言。中國文明進入虛無狀態,如同大樹枯萎而其花葉果實,紛紛落下,隨風四散。此即花果飄零。大家離開中國後,無論在香港、台灣、美國、歐洲,都是花果飄零。他於1962年時如是說。
其時我讀過這篇文章,沒有多大感覺,因為我出生於香港,本根就在此,自然不能體會花果飄零的感覺,亦不覺得需要肯定中國文化,並不禁懷疑,中國文化果真如此重要,因而值得研究嗎?似乎不然。但是,就唐先生而言,他身歷目睹中國文化受共產黨打壓,並慢慢瓦解,隨風四散這個悲劇,中國學者流亡到全世界,這是他那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故此,不難理解何以他思想重心都放在重新肯定中國文化,如何存亡繼絕,如何處理眾學者流亡在美國、英國、歐洲及其他地方等等。因為如果花果飄零是個悲哀的事實,則我們便要將其扭轉,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以再次建立凝聚力。花果飄零雖是悲劇,可是唐先生毫不悲觀。他覺得中國人仍具反省精神,以及自我肯定的能力。此即何以他會為重振華夏文化而奮鬥不懈之故。
可惜,世事相當無奈,供其自由奮鬥機會之地,卻是其「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的香港,這個「既非吾土,也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冑」之英國殖民地。他與牟宗三先生均曾說,香港及香港人與他們無關,他們都覺得香港沒有任何意義。若香港果真具有某種意義,那麼該種意義,亦僅限於為他們提供立足之地,以及自由發展機會。他們從沒有當香港人是同胞,在他們心中,香港人並非真正中國人,他們與這殖民地建立的緣份,不過是一段「隨緣」。
然而,其思想後來似乎有所變化,正如上述。他曾撰有《花果飄零》,當中談到靈根自植,指出我們要在所待之地,肯定自己,要從自覺性發展出知覺性,進而肯定整個儒家精神。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怕飄零,並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根,待根深蒂固後,那地方就是中國。然而,他對於現代中國花果飄零的困局,所能作出解答,亦僅止於此。面對「中國之五六億人,無一能逃馬克思思想奴役」,以及一直以來,別人問他如何回家、如何與父母親朋重逢、如何重朝祖宗廬墓、花果飄零何日止息,他自言「無可回答」。這是種絕望態度。但唐先生依然不失為樂天知命之人,他永遠樂觀。
正由於這種樂觀,故他認為生命不能完全物化,生命知覺依然要在中國哲學最根本處,開花結果。由是生命乃有心性內容。正因為心性,所以中國哲學才不至於完全淪亡。
香港與他無關
余英時在其回憶錄中,引述唐先生的一段描述,或許可以說明,唐先生這種樂觀精神,多多少少與香港的自由風氣有關,儘管他本人可能不自知:
「我在香港五年(1950至1955年),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相確是如此。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去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與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由此可見,1978年前,香港對唐先生而言,就只是個提供自由的地方,讓他發展自身思想與教育事業,至於香港本身,與他無關。除教育思想外,唐先生對香港社會似乎無甚想法。
( 註 : 本文為 《三代流亡哲學學者與香港:唐君毅、勞思光、張燦輝》流亡哲學人講座系列之內容撮要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