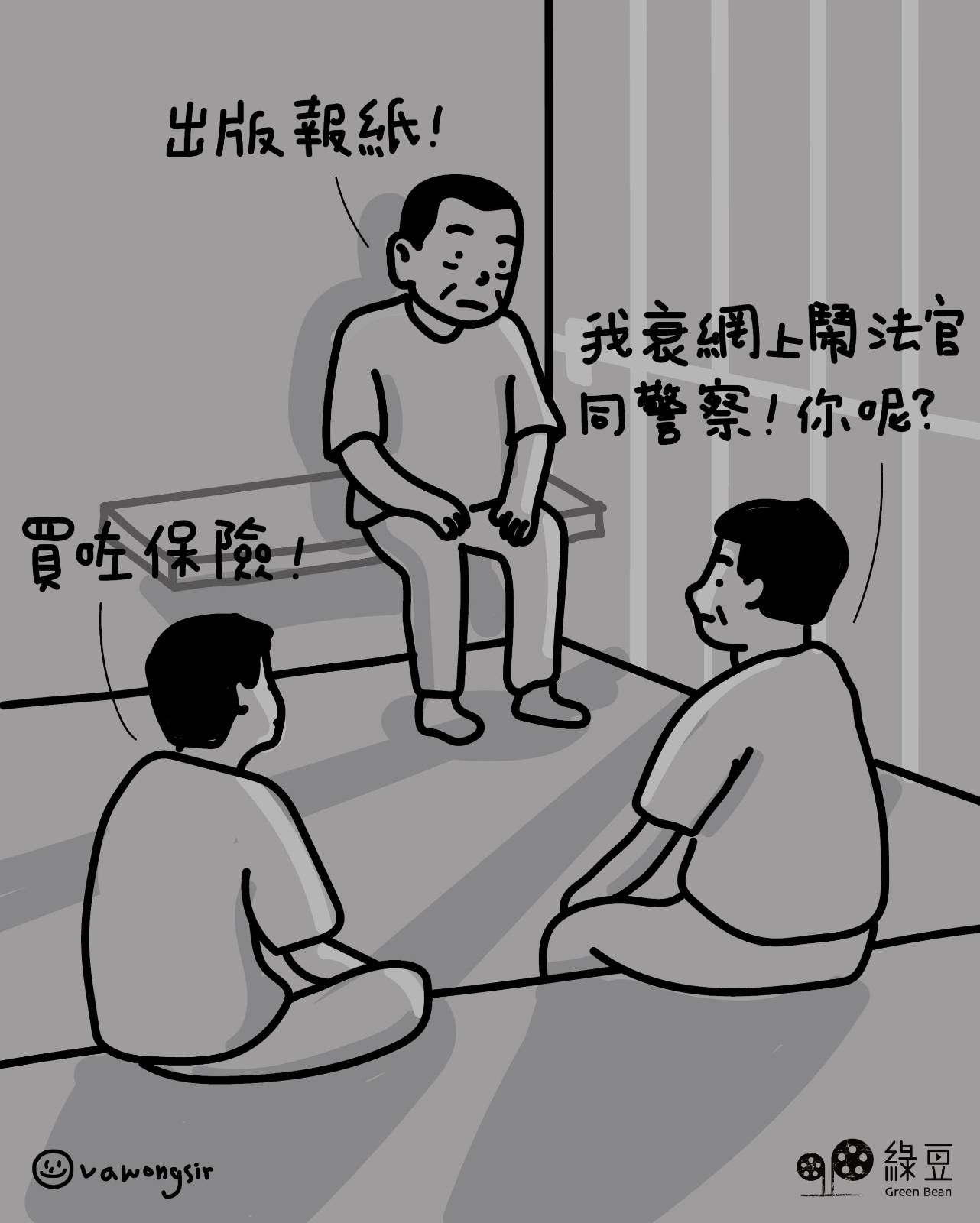《夕陽西下幾時回》- 由盛而衰的中大哲學系(上)


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我1992年重回母校任職哲學系,開始哲學老師的生涯,同時是對我多年來哲學訓練如何實現的挑戰。是否安於在大學教席、過平穩「學術」生活?教學不過不失、每年寫一兩篇學術文章、參加國際研討會和找時間服務大學或書院?教授哲學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不相信如此,應該多做一點!
明慧,「哲學生命」是我幾十年前回應父親的死亡,離開建築課程的決擇,回到中大便是實踐我理想的場所。由入職到退休,晃眼二十多年便如斯過去,是時候和你細説這段歷史和反思。
先寫中大哲學系的歷史,我不是以「客觀」研究方法整理中大哲學系的歷史,而是從我的主觀體驗和觀察去敘述中大哲學系的盛衰。系中同仁不一定同意我的想法,「真實」的系史留待將來的學者去寫吧。
哲學系的四期
1970年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92年由浸會返回母校任教直至2012年退休,我在中大度過了人生四分三的寒暑。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與中大哲學系的情深。幾十年之後,重新審視哲學系過去70年來的歷史,我覺得可以大概分為四期。
第一期:南來避秦的哲學家
初入中大的時候,我入讀崇基學院。崇基由美國基督教教會創辦,承傳西方開放的傳統哲學與宗教文化。1963年納入中文大學成員書院的新亞,眾所周知,是從大陸逃亡來港錢穆、張丕介和唐君毅於1949年所創辦,致力傳承中國儒家,弘揚宋明儒學。崇基與新亞兩者風格迥異,造就了中文大學哲學上多元的博雅文化開端。
唐君毅先生不只是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同時是教育及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唐先生由大陸逃亡來到香港,有如30年代從歐洲逃亡到美國的猶太人,本以為留在異鄉一段時間就可以歸家, 結果終生未回故鄉。唐先生的四川話不易聽得明白,但講書很有感染力,名符其實的文化巨人。
錢穆先生最初在桂林街授課,原址現已成為地產樓房,牟宗三先生1960年才到香港,他們這一代的中國文人及學者,沒有把香港作為他們自己的家,這裡只是他們暫時居留的地方,他們盼望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返回大陸,是真正熱愛大中華的文化人,對中國文化危機深切反省,反對中國共產黨馬列唯物主義,在花果飄零的艱難下培育從大陸同樣是逃亡而來的學生,余英時便是其中一個最出色的學生。
1958年唐先生與徐復觀、張君勱、牟宗三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新亞書院成為大陸流亡學者重新反省亞洲文化及中國文化的唯一地方。他們重要的時光都在香港渡過,不過,香港對他們來說仍是中途站,並非紮根的安心立命之地。他們教學及發展的方式都是遵照傳統中國書院的方法,不要官方插手,著重教導平民子弟立志重建新儒家。
唐君毅、錢穆和牟宗三積極發揚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反省、重整中國哲學、深化中國文化的做人道理。不過,在文化關懷上未有對香港作過什麼有意義的探討,新亞承傳著的新儒家,對香港的影響不大,對中文大學哲學系的發展亦沒有甚麼前瞻性的願景,他們沒有想過要將中國哲學國際化。
上世紀六十年代勞思光先生加入崇基書院。勞先生出道較早,是唐君毅及牟宗三的後輩,因為不是出身於新亞,反而得到獨立的發展空間,不受唐牟的直接影響。我是崇基書院的本科生,當時書院只有五位教授,學生也不多,師生關係非常密切。沈宣仁先生、陳特老師、勞思光先生,還有何秀煌老師和一位外國學者。1970年唐牟退休 (崇基及新亞加上聯合三間書院1963年組成了中文大學),1977年新亞與崇基合併成為今天的中大哲學系,期間哲學系的發展有了新的轉變。

唐君毅銅像
第二期:台灣留美哲學教授
哲學系第二階段的發展可數劉述先、何秀煌和石元康等學者的執掌。他們多在台灣或國內成長,隨後到了美洲(美國和加拿大)取得博士學位回流香港。與唐牟年代不同,他們受西方教育,學術精神較為接近西方的一套,多了民族反省,重視自由開放精神,是新一代的學者。
劉述先是新儒家份子,亦同時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學者。他回港後,繼承了唐牟的新儒家,被稱第三代新儒家其中一個代表。劉述先當了多年的系主任,期間以美國大學的模式將中文大學哲學系仿效美國哲學系來發展,對學系進行了課程改革,重整結構。與美國哲學系不同,我們多了的是中國哲學。何秀煌是邏輯、語言哲學出身,石元康專長政治哲學,兩者在廣義上都是分析哲學。因此第二階段的哲學系包含了中國哲學與西方的美式哲學。中國哲學與廣義的分析哲學、邏輯哲學、語言哲學及政治哲學成為這段時期的重點。
除了何秀煌老師之外,第二期的老師大部分都只視教學為工作,大部分都沒有將香港作為自己的家。他們是非本土出生的學者,殖民地的香港只是他們寄居的地方,責任上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對學生沒有足夠的感染力。他們這些第二代人在受美國接受教育,但不喜歡美國。與上一輩相同,他們沒有太重的文化使命,不喜歡香港,台灣及大陸又不能回去,只有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在香港教書和生活。他們對香港哲學系的承諾不大,亦不會刻意走出亞洲或是國際,哲學系對他們來說也算是個身份象徵。劉述先與石元康都是異鄉人,沒有把香港如何成為獨特的哲學系這個想法納入工作的重點。
唐先生在學問與人格上都是巨人,著重中國傳統,非常關懷照顧自己的子弟及親屬。勞思光先生出生崇基而非新亞,不以新儒家自居。與前輩不同,勞先生給予哲學系開放及自由的發展,從來沒有要我們成為勞門弟子。唐牟在台灣有唐牟學派,勞先生沒有學派,我們承繼了他自然開放的精神,一個開放體系,對權威的批判性。
勞先生認為儒家的問題很大,要將儒家重新塑造成為新儒家是行不通的,不能回應當前中國和世界文化危機。勞先生不似第二代的劉述先等人在外國回流,他在大陸及台灣居住過,對共產黨的批評比唐牟兩位前輩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公共知識人,面對香港97回歸共產政權問題,在香港創立前景研究社探討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寫了很多相關的文章,與《七十年代》的李怡積極探討香港前途問題。其中《歷史的懲罰》(1971)一書尤為深刻,對中共政權的面目說得很清楚,勞先生批判共產黨由始至終都沒有變過,1956年他翻譯過一本書《共產黨是很認真的》序言中他說得很確定,對權力的擁有,共產黨是一步都不會放過。勞先生早說過共產黨不可信,現在一語成讖。
另一方面,勞先生在我們作為學生的年代,寫《中國的路向》、《中國文化要義》等,可以看到他與中國文化有著深厚的理解和智慧。但另一方面,他不是大中華的信徒,不會在中國文化不可動搖的基礎下思考,因此,他不是新儒家,最重要的地方是他關注中國在世界哲學的位置,他精研康德哲學。在中大時去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知道西方哲學和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他對我們的教育是開啟性、開放性以及批判性的,為我們埋下種子、為未來哲學系跨進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勞先生除了曾任職研究院學部主任,沒有擔任其他行政職務,直至離開中大時都不曾是講座教授或系主任。勞先生正規的哲學訓練只是本科學士畢業,直到2003年,中文大學頒授勞先生榮譽博士。勞先生常言,他的教學理念不在傳道和授業,只是解惑而已!他對同學的開放、包容、接受及教導,沒有私心,亦沒有野心,勞先生不介意自己有否做過系主任,有否做過講座教授,以自己的學問及理念來教導我們,強調哲學不是文字語言遊戲,是要進入人間,關心政治和社會,對不公義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批判發言,是以勞先生不是象牙塔的學者,是公共知識人。這些情操對我們影響深遠。
下週再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