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幾時回》- 生死愛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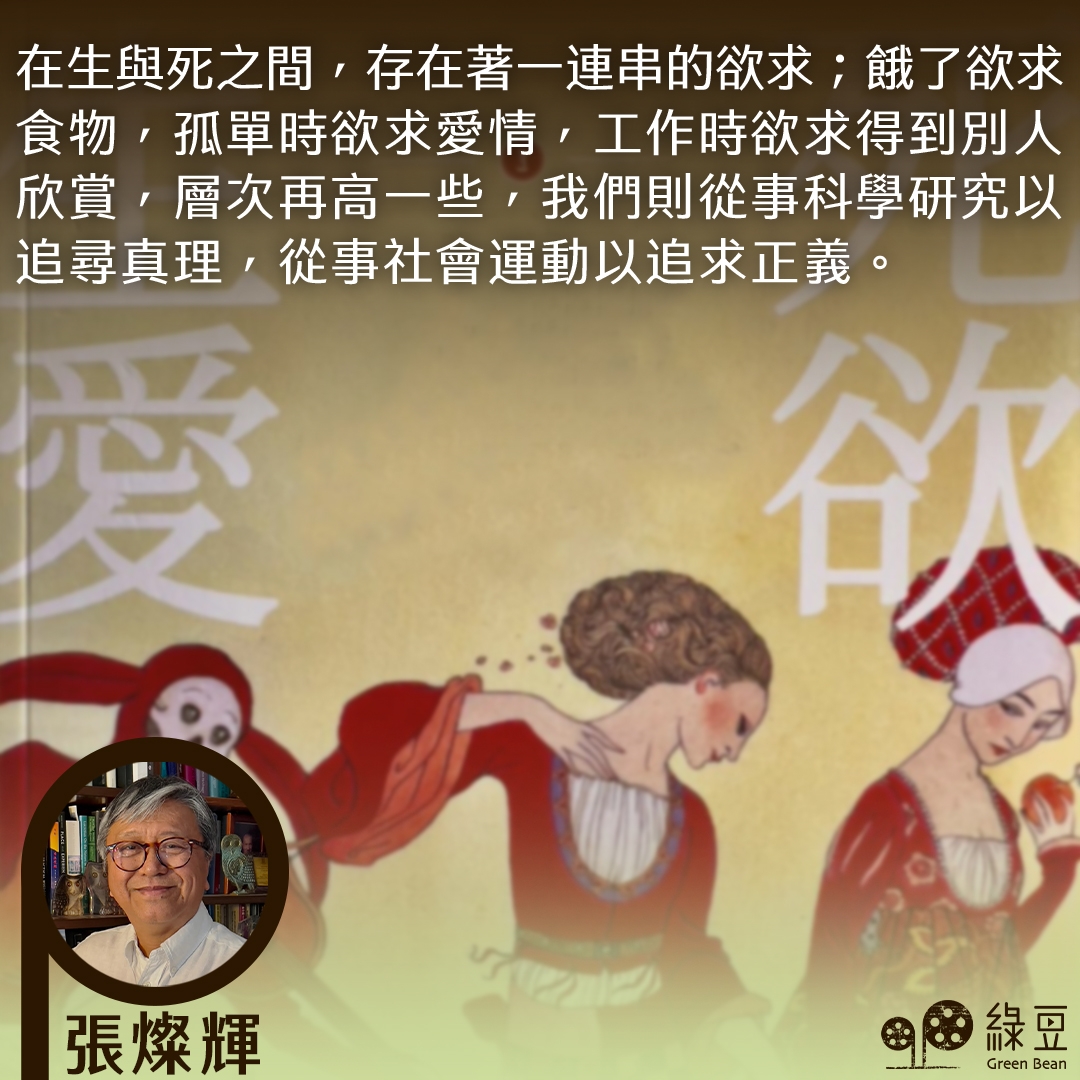

第八封信 8.1
明慧,
現代研究型大學不重視人文價值和生命意義,不只是香港的大學問題,而是國際性的。本世紀初在哈佛大學當了三十年的哈佛學院院長魯易士(Harry Lewis)寫了本語重心長的書《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2006),批評哈佛大學教導學生最尖端科技和知識,但沒有培育他們成為有智慧的人。他説:「哈佛教育學生,但並不使他們變得智慧。他們可以在學術和課外活動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但和整個教育經驗並不連貫……就像好的父母一樣,一所好的大學應該幫助學生理解人生處境的複雜性——或者至少幫助他們通過前人的智慧,了解生活的困難,如何過一個反省的人生。」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耶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科郎曼 (Anthony Kronman) 呼應魯易士的批判,出版了《教育的終結: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放棄了生活的意義》(Education’s End –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2007)。書名已開宗明義叩問現代大學的教育理想在那裡!科朗曼説:「生活的目的是什麼——人應該關心什麼,以及為什麼關心——是一個人能夠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然而,在現代研究理念的影響下,我們的大學將這個問題從課堂中排除,認為它不適合有組織的研究。」
哈佛和耶魯大學兩位資深教授同樣慨嘆,現代研究型大學忘記了大學最重要的目的,不只是研究和傳遞知識,而是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有反省和自由的人。無論是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他首先要成為一個人,才能實踐學科的知識;他不是專業人士,只懂學科知識而沒學習人生智慧,不理解生命價值和意義。魯易士和科郎曼是回應我在第七封信提到牟宗三先生的感嘆:《大學》的「明明德」還可以在大學那裡呈現。
重新面對問題
我和幾位學者前輩有共同信念,大學的目的,首先是「為人之學」。
明慧,當然「為人之學」不是一個學科,沒有學系開辦這課。不過我在上幾封信提過,我在中大教學中,嘗試將其中涉及的課題,發展成不同的哲學通識課程:幸福、死亡,性愛等等,是將我所學所思回應人生存在問題。
是以從這封信開始,暫時再不談社會文化教育課題,回來探討人生處境。這些問題我們幾十年前在《將上下而求索》簡略談過,是時候重新面對,希望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在《將上下而求索》(1977)的第一封信開始說:「地球上出現過生物億萬種,獨有人會問為何活著,凡不願行屍走肉糊塗此生,就非要找到答案不可。
宇宙無涯時光流不盡,我的存在竟是唯一又偶然的一剎,生命乃是最大的謎,每個人忽然給推出舞台前,邊演邊揣摩角色。」
幾十年過後,這幾句話仍然適用。那時是年輕,之後在人生舞台演出不同角色後得到的經驗,應有多點領悟。這些理解在我不同課程和文章中闡述,今年在台灣出版的兩册《生死愛欲》可算是一個總結。當然我不能在這封信詳細論述書中思想,但想和你分享這書導論的看法,和你談論「生死愛欲」的問題。
沒有答案的問題
生而為人,我們總是在生存與死亡之間。人的一生數十年,到底人是什麼? 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King Lear)有段精彩的對白:
「人不過是如此嗎?要仔細盤算一下。你沒有取用的蠶絲、獸的皮、羊的毛、麝貓的香。哈!我們三個倒是虛偽的了;你纔是本來面目;赤條條的人也不過就是你這樣的一個可憐的祼體的兩腳動物罷了。」
人類不外乎是動物;生存、繁殖、死亡。這整段文字的意思,說出了人的 factum brutum,也就是人類「明顯的事實」。我們活了這麼多年,還是離不開吃飯、睡覺、上廁所、做愛,最後死亡。這就是人生了。人類的存在不過如此,赤裸裸而來,赤條條而去。無論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不也就是出生數十年,之後死亡?人的現象就是這樣簡單:出生,死亡。那麼生而為人,又有什麼意思呢?
當我說「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出生,死後不知何往,也不清楚人生的目的。」這的確說明了人生悲哀的一面。我們的出生並非由自己選擇,沒有人問過我們,我們就出生了。無論是男是女、姓張姓李、當中國人或美國人,從來沒有人在我們出生前問過我們的意願。當生命完結以後,又到底會往哪裏去,我們依然不知道。
當然我們會聽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哲學的也有宗教的,這些都會告訴我們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往深層思考,這些似乎都是聊勝於無的解答,藉以消解我們的荒謬感。有些問題真的沒有答案,比如說,為什麼我會在這裏?為什麼我生而為中國人?香港人?為什麼我是男子漢而不是女兒身?這些問題,沒有人知道答案。
對於以上這些問題,上世紀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曾經作過相當深入的反省。他在 1961年出版了一本小書《人生之體驗續篇》。書中的一章〈人生之艱難與哀樂相生〉,指出人生說到底不外乎求生存、求愛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求神聖,這七種欲求囊括了所有人類生命的現象。剛才說到一個簡單事實,人類的生命就是出生,最後死亡。問題是,我們在這段時間之間都做了些了什麼?
在生與死之間,存在著一連串的欲求;餓了欲求食物,孤單時欲求愛情,工作時欲求得到別人欣賞,層次再高一些,我們則從事科學研究以追尋真理,從事社會運動以追求正義。凡此種種,在在顯示人類的生命中必然會出現「欲求」(desire)。
在求真善美前
我的說法可與唐君毅所說的互相呼應。他說到人類在欲求真、善、美之前,得先明白頭三項欲求。
第一項是「求生存」。他警告我們不要輕看「求生存」。一個人如果不必為三餐奔波勞碌,那會是個怎樣的人?他可能是二世祖,家裏有的是錢。但是,就算家裏有錢,也不要以為理所當然的不必努力。唐君毅在文章中有個子題──〈生存之嚴肅感,與人為乞丐之可能〉,他指出,人類永遠有成為乞丐的可能,就算今天回家有飯可吃、有屋可住,但這些都沒有最終的保證。我們能否想像,自己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
曾經有個真實的例子,一個坐擁97億美金的德國富翁,因為金融海嘯而傾家蕩產,於是自殺死了。唐君毅是對的,生存並非必然,財富無法保證。一旦我們明白到這一點,就明白生存本身的嚴肅性。
第二項是「求愛情」。愛情好像是自然不過的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無論是電視的肥皂劇、傳媒的八卦雜誌,都充斥著各式情情愛愛。所謂愛情,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著愛情,好像很容易了解,但是仔細追問,卻又不是那麼回事。
唐君毅提到,「愛情」是許多哲人不屑提及的課題,但是這種欲求是普遍的,常人都會有渴求伴侶的欲望。在我們的一生中,第一次向愛人說出「我愛你」,而對方回應「我也愛你」的時候,那種甜蜜無可比擬。因為我們知道追求一個人是很困難的。經過歲月的洗禮,感情原來是會失色的,變得沒有意義,甚至有愛人背叛自己,我們慢慢明白長期維繫一段感情,是很困難的。當然,也有人拒絕愛情,嘗試離開欲海,走到無欲的彼岸。例如和尚、教士斷絕自己的情欲。不過這樣種斷絕情欲的方式很不容易。唐君毅很精闢,他指出做聖人很難,難道做賊又會容易了嗎?上升不易,墮落也難。人世之中,無數的悲哀就是從此而來。於是不求愛情難,求愛情亦難,求取愛情之後能夠維繫亦難。總而言之,就是艱難兩字。
第三項是「求名位」。想想日常生活之中彼此的交流溝通,我們談論最多的是什麼?難道是哲學嗎?肯定不是。我們多數談論的,是他人的短處,是關於別人的閒話。我們在別人的心中,都有一個位置;我們被人談論,也會談論別人。這是個很難克服的普遍現象。我們總是渴望,在別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比如說,我擔任這麼多年的教職,當然希望能得到學生的好評。因為我希望在別人的心中有個位置,可以得到別人的尊重。事實上,人渴求得到名位,反映了人想在人際之間建立關係。最淒涼的人就是斷絕六親者,因為沒有人承認他的身分價值。而所謂名位,表面上是一種令人不屑談論的東西,卻同時也讓人很難逃避。
上述三項欲求已經佔據了普通人絕大部分的生命。當然也有人可以跳出這三者之外去追求更高價值的真、善、美、神聖。這是一種超越,屬於科學、道德、藝術的領域,但卻不是普通人一般在生活的日常中所企盼的。
其實我想說的,是當我們談及「生命存在」的問題時,首先遇到的並不是真善美神聖。日常生活的實存問題、愛情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艱難。不要以為,求生是容易的,戀愛是容易的。有多少人,經歷了愛情而苦惱,有人想嫁想娶,卻同時有人嫁娶之後不快樂。在人的一生之中,想想自己,想想身邊的人,有多少人能獲得童話故事般的美滿結局?美滿,實在是不容易的。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