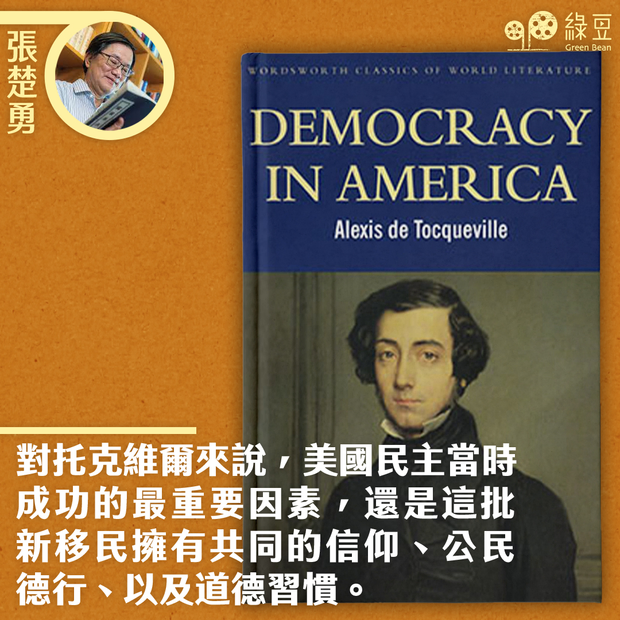英式的專業自由傳統與戰後香港管治:郭伯偉與積極不干預政策

自由市場經濟, 公共理財, 不干預政策, 知識分工, 量入為出
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投考港英政府的政務主任職位時,到了最後一輪的個人面試階段,是我這個申請人面對7個首長級官員,回答他們向我提出關於政策和政治的難題,並就著我答案中提出的建議和分析,跟他們進行辯論。
在論及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課題時,我發覺這些首長級官員無一例外的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和做法很是支持。他們在公共理財方面都非常審慎,認為必須量入為出,並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各國實行財富二次分配式的福利政策,很不以為然。我當時感到,這些坐在我對面、絕大部分來自英國的首長級港府官員,在提到宗主國的福利主義思想時,很有種忿忿不平的情緒,認為這是管治上的誤入歧途,是經濟上日益繁榮、市場自由開放的香港萬萬不能引進過來的。
這次面試給了我兩大體會。首先,香港當時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這些大部分來自宗主國的港府決策官員,卻是主要根據他們所了解的在地情况,以及他們認為的長遠公共利益來制定政策,並不是把宗主國二戰後的主流政策和主張,直接應用到來香港。另外,那次面試也讓我深深的感受到,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 (John Cowperthwaite),在他任內發展出來的香港政府財經政策,在香港經濟蓬勃起飛的年代,可說是成為了管治香港的金科玉律。

(圖:圖中為郭伯偉)
熟悉戰後香港管治的人,對郭伯偉不會感到陌生,因為港英政府在財經範疇中著名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他被認為是奠基者和貫徹始終的大旗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佛利民在內的不少評論者,視郭伯偉為戰後香港經濟從第三世界水平飛躍成為發達地區水平的主要推手。2017年英國商學兩棲的作者莫納里 (Neil Monnery)發表了研究郭伯偉管治香港的專書,書名用上了《繁榮的建築師:郭伯偉爵士與香港的締造》 ( Architect of Prosperity: Sir John Cowperthwaite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這個標題,充份顯示出郭伯偉在香港的重要性。
郭伯偉蘇格蘭出生,在英國的頂尖學府聖安德魯士大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修讀經典學和政治學,並跟隨自由經濟學家尼斯貝特(James W. Nisbet)進修經濟。1941年他考取了大英帝國香港見習官 (Hong Kong Cadet,即香港政務官的前身)的位置,但在往香港履新前日軍已經攻陷香港,因此他被轉派往斯里蘭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香港光復,才回到香港政府,負責協助戰後香港重建的工作,並在不同的貿易、工業、財經政策範疇出任要職。郭伯偉1961年成為財政司,直到1971年年中退休,用上了近30年專業文官的生涯,為管治香港服務。
讀者如果希望能較全面和深入去認識郭伯偉,《繁榮的建築師:郭伯偉爵士與香港的締造》是一部不錯的參考專著。作者莫納里雖然在書內對郭伯偉作為一個人物的個人著墨不算深刻,但對他履行港府公職時的政策論述,卻引用了不少文獻資料解釋郭伯偉的理念、立場、管治價值取向,對我們了解當時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很有幫助。
戰後的香港
在這篇短文的餘下篇幅,我希望簡要地勾畫出郭伯偉對管治香港財經政策的理念,是如何呼應了英國自亞當•斯密 (Adam Smith)以來的自由經濟思想。另外,我也會從他在立法局辯論的發言中,簡述他對公共財政的管治哲學。最後,像他這樣的帝國專業文官,離鄉別井到了一個文化歷史很不同的地方,卻長時間專注為當地的發展盡心盡責,致力進行良政善治,我認為對這種公共行政管治傳統進行反省,是很有意思的。這傳統也許不是方方面面都令人滿意,但對建造出一個現代的香港,卻頗為關鍵。
其實,在郭伯偉出任財政司前,香港政府在戰後已逐步建立起低稅、公共財政盈餘、貨物和資本自由出入的財經管治框架。作為一個细小又不能自給自足的港口型經濟,香港要生存既不能閉關,更必須要吸引貨物和資本自由出入,才能夠發展經濟活動。加上大英帝國建立的一大目標,是促進英國跟全球的商業和貿易活動,殖民地的香港在遠東,正是帝國中一個重要的開放經濟基地,它一方面要吸引外面的資本和貨物到來 (因此稅制必須簡單並維持在低水平),又不能成為宗主英國的財政負擔 (所以香港得要有自己的財政盈餘),這在戰後百廢待舉的香港便更得如此。
早在1950年,當時的財政司霍勞士 (Geoffrey Follows, 1945-1951)便已提出,香港政府應致力儲存足夠一年公共開支的財政儲備,以保障不斷上升的公共財政開支,在平穩而持續發展下可以應付不時之需。
到了歧樂嘉 (Arthur Clarke, 1951-1961)接任財政司之後,由於朝鮮半島戰爭導致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進行禁運,嚴重影響香港作為中國與外界的轉口貿易港的經濟,迫使香港轉型向輕工製造業方向發展。歧樂嘉認為,要促成這個轉型,靠的並不是什麼工業政策,而是政府得提供在價格上有競爭力的土地供應,對外大力鼓勵自由貿易,讓資本在香港愈能自由流動便愈好,對內保持低稅制吸引投資者前來投資。餘下的,就得相信敢於冒風險的投資者和工業家的企業眼光和市場判斷,以及勤奮上進的香港居民改善自身生活和經濟環境的努力,讓經濟在自由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地方發展開來。
郭伯偉就是在繼承這個管治哲學的傳統上,進一步發展自由市場主導的財經政策,並勇於在觀念上有系統的闡述當中思想的理據,以論證為什麼在大多數的情况下,政府干預市場在香港是既不可欲、又不可行。
不要對商人或工業家指手劃腳
1962年他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時,在立法局的辯論中,郭伯偉便曾開宗明義的陳述,他為何反對在香港就整體經濟發展進行規劃。郭伯偉是這樣說的:
首先,我必須表明我對為香港經濟整體發展進行政府規劃的深切反感和不信任。最近有篇社論把官方反對經濟規劃和計劃控制形容為反映了政府那「老爺子最懂得」的性格。但正正是老爺子並非是最懂得這一點使我相信,政府不應該自以為是地對任何商人或工業家說,什麼你應要做,什麼你不該做;更不要指手劃腳般說你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不管你如何作出修飾,這些都正正是經濟規劃。
郭伯偉緊接著說:
有經濟體是可以進行政府規劃的,儘管我不去說其成效如何。在一個有限、封閉的内銷市場,如果有仍未用上的資源,又有可能同時控制生產和消費、供應和需要,這便可以進行政府規劃。但香港情况並非這樣,決定上述相關因素的力量存在於我們邊界以外。對我們來說,眾多不同的商人和工業家各自個人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及其所產生的後果,我深信比起政府或其計劃委員會的單一決定所產生的後果,要來得好和優勝,因為政府不可避免地對市場內存在的無數的相關因素所知有限,而且政府又是很缺乏彈性的。
在我們經濟體中一大片的範疇內,倚靠19世紀以來所說的「隱藏的手」還是優勝過讓官僚系統內那笨拙的手指去干預自由市場那敏感的機制。具體而言,我們承擔不起對企業的競爭自由這機制主軸的破壞。
從郭伯偉在立法局辯論的這番發言,我們清楚看到他借用蘇格蘭思想家亞當•斯密那「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來形容自由市場那互動自發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協調機制。無可置疑的是,郭伯偉深信「老爺子並非是最懂得」的。對他來說,中央規劃者在面對市場中千千萬萬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那訊息萬變、不斷互動所產生的需求和供應,其所知必然是掛一漏萬。而且規劃者對無時無刻出現的市場供求的變動所能作出的反應,無可避免地是嚴重缺乏彈性的。
知識分工
從經典經濟學的理念來看,郭伯偉以上所提到的,正是像海耶克 (Fredrich A. Hayek) 這些自由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知識難題」。在社會和市場互動中,處於缺乏全面全知視野和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情景下,散落在不同角落,並經常隨著變動環境而作出應對改變的、那千千萬萬的個人的需求和行為,是如何能夠得到協調而獲得滿足,並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和市場秩序的呢?如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在19世紀初提出了勞動分工是經濟領域中提高整體生產力的要訣,那麽,像海耶克這些20世紀的自由經濟學者則進一步提出了知識分工,嘗試解答上述觸及到的知識難題。
簡要來說,知識分工的觀點認為,人非上帝,我們是不可能有全面全知的視野。人類理性不管有多發達,只要理性還會發展,未來還是構成人間世的一個維度,今天的理性和知識,只是已知的理性和知識,其未來的發展和創新,均是已知之外的未知。我們當然可以基於已知對未知作出預期,但這預期可對可錯,甚至可以和未知是不相關的。因此,除非沒有了未來,理性和知識的發展也終結了,否則,人類是不可能擁有全面全知的視野,對仍在發展互動中的開放社會和經濟作出整體規劃。
那麽,在社會和市場中,那千千萬萬個人散落在不同角落的知識和需求,是如何能協調和分工的呢?就市場來說,那便得倚靠不受自由需求以外干預的價格機制。
通過這個機制發出來的價格訊息,每個社會或市場參與者在參考了有關訊息後,可自由決定是否進行互動交易,以滿足其自身的需求和目的,並對有關的互動交易行動後產生的後果負責。每次互動交易的達成,便是社會和市場發揮協調行動的例子。交易雙方或多方的需求得到滿足,需求中所涉及的知識、技能和資源也得到了有效的運用,滿足了各方的需要。當然,互動交易的行動也可能會產生預期之外的或好或壞、或對或錯的後果。如果後果是錯是壞,互動交易者便得承擔損失和責任,當然也不排除嚴重者會對社會整體秩序或利益造成傷害。因此,自由的互動交易有些時候也得有適切的監管和公正的法規權責作為保障。
我這篇短文是不可能把自由經濟學中的知識分工這課題充份解釋清楚的。有興趣了解海耶克觀點的讀者,可參考他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和三册的《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尤其是前者的〈經濟與知識〉(”Economics and knowledge”)一章,以及後者的第一册。
政府規劃與封閉經濟
郭伯偉認為,在香港,與其倚靠政府規劃,不如相信自由市場。經驗告訴他,後者往往帶來更好和更明智的後果。郭伯偉更提到企業競爭自由的重要性。顯然,只有在自由市場運作下,企業才能自由競爭。這類競爭預設了高度的資訊透明和流動、產權的保障、公平的法規,就業、投資和行動的自由等等。
郭伯偉雖然沒有詳細分析經濟上政府全面規劃的弊病,但要進行這種規劃,有關的經濟必須是封閉、有限、內銷而不開放的。權力擁有者更得完全控制了社會上的生產和消費、供應和需求。在這樣集權的地方,個人自由是必定保障不了,有關的政府規劃並不會滿足個人的自主需求,而是首先使用集中了的權力去實現政府預先制定的目標。對重視個人自由的人來說,政府全面規劃不但比不上自由市場的靈活,更是對公民自由的重大威脅。這一點正是海耶克在《通往奴役的路》(The Road to Serfdom )試圖反覆說明的一個重點。
在郭伯偉掌管香港財經決策權的年代,香港還是個發展中的非發達經濟。但戰後的世界潮流,似乎都傾向政府規劃。1957年中國便推行了中央全面規劃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英國工黨上台後也推行全面的、二次分配式的福利主義政策。郭伯偉視前者基於意識形態的信念推行中央規劃,後者則嘗試在相對富裕社會的基礎上,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以福利惠及多數的中產和低收入人士。郭伯偉認為,香港沒必要因為意識形態的理由實行政府全面規劃;經濟財富當時只及英國三分一的香港也沒條件擁抱福利主義。如果我們細心分析郭伯偉的理據,他對中央規劃的保留並非只是權宜的考慮,因為他認為所有中央規劃的模式,歸根究底都是以封閉經濟作為前提。強行執行這模式並非只是不適合開放型的香港經濟,封閉的模式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對個人自由的影響,如果推行到極致的話,將會是災難性的。
量入為出的公共理財原則
郭伯偉根據他的財經理念,認為在公共財務管理上,香港政府要致力的不是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而是盡最大所能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愈好,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愈豐裕,於是便更有公共資源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務,這比起通過加税進行再分配或政府舉債「先洗未來錢」更有利於香港,也有利於限制公營部門過份增長,讓私營部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基於以上考慮,也基於公共開支容易展開卻很難收回或削減的性質,郭伯偉因此非常重視量入為出的公共理財原則,並把此原則引進政府的經常性收入和經常性開支的關係上,防止公共開支失控。他還特別關心政府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以備不時之需。他知道,香港不具備隨時加印港幣以應付公共開支增加的能力,赤字預算對港元和政府未來的公共財務能力又會構成巨大壓力。但如果有豐厚的儲備,政府便可以在經濟艱難的日子增加公共開支紓解民困,在好景的年份因此要更加審慎理財,這樣香港才能長治久安。
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郭伯偉對在沒有累進稅制的情况下,他不傾向主要通過稅款提供低廉的全民公共服務,因為這既增加政府經常性開支的負擔,又津貼了毋須津貼的人。他比較贊成公共服務應盡量收回成本,但對有需要的市民提供資助。
我想,香港人對上述的財經政策和公共理財的原則不會感到陌生。不少人更同意香港戰後成功之道,跟這些做法大有關係,而郭伯偉正是這方面的一個關鍵人物。
當然,積極不干預不等如放任。1965年香港出現的銀行危機,便迫使郭伯偉對銀行業大大加強監管。而戰後香港的房屋、教育、醫療等範疇,政府也介入得愈來愈深。但總的來說,香港長時間以來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從第三世界變成發達經濟,是很得益於像郭伯偉這些有識見、有承擔和努力不懈的官員的。
香港其實只是郭伯偉這個蘇格蘭人旅居之地,但他卻把一生的專業公職服務,投入到讓香港經濟繁榮、長治久安的努力上。這種戰後英帝國式的公共行政管治傳統,是怎樣在香港施行的呢?我將會在下月於本專欄中論述一下。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