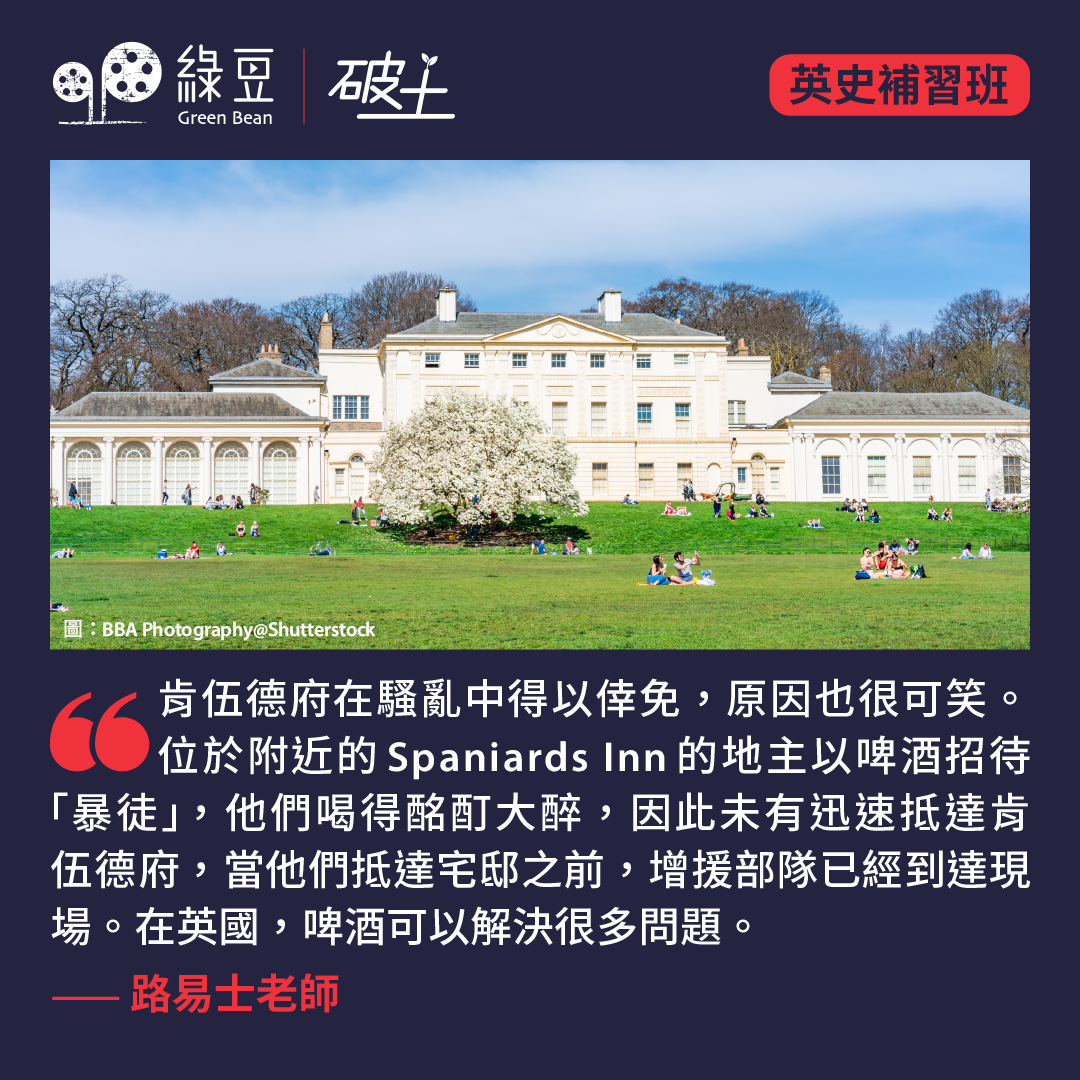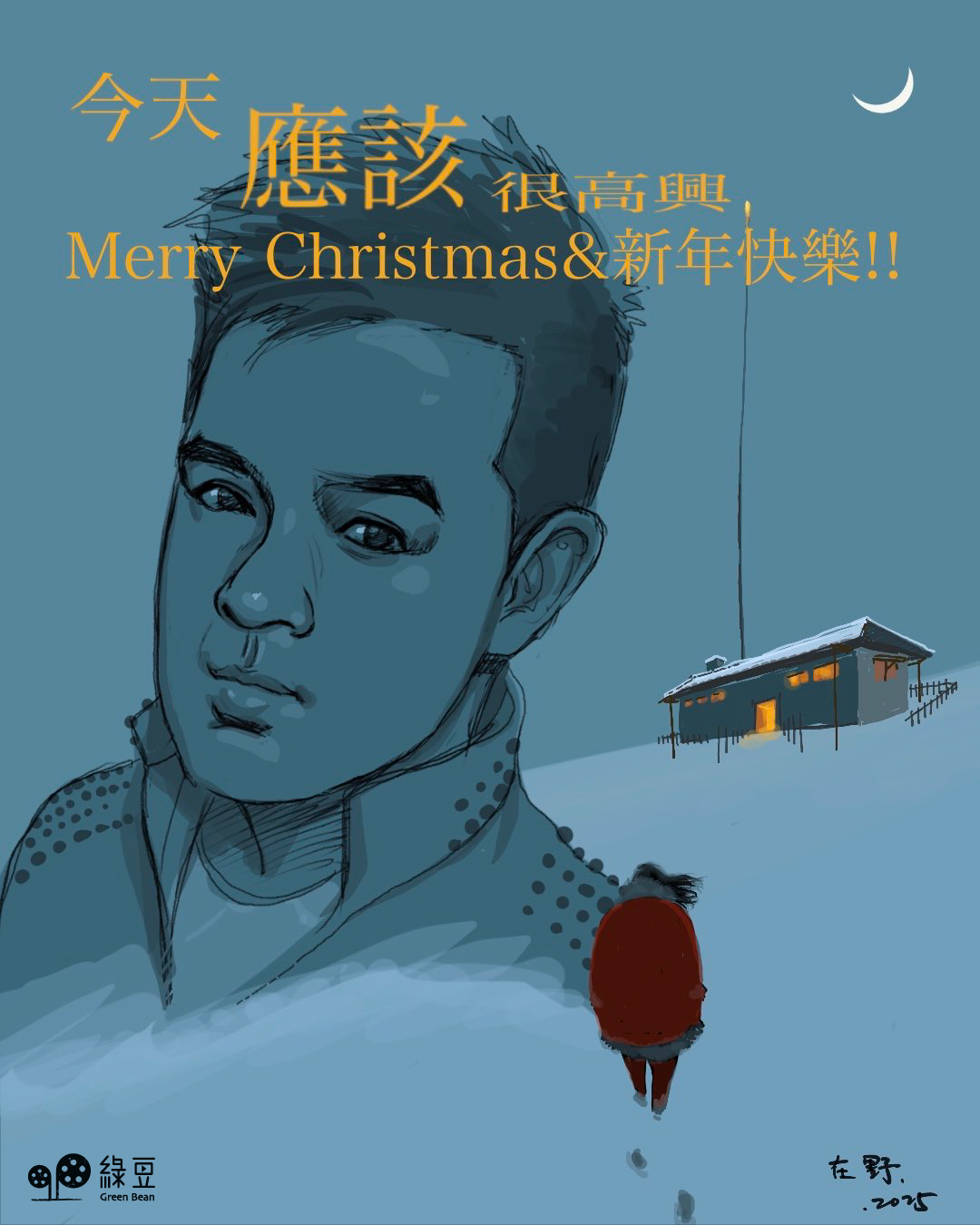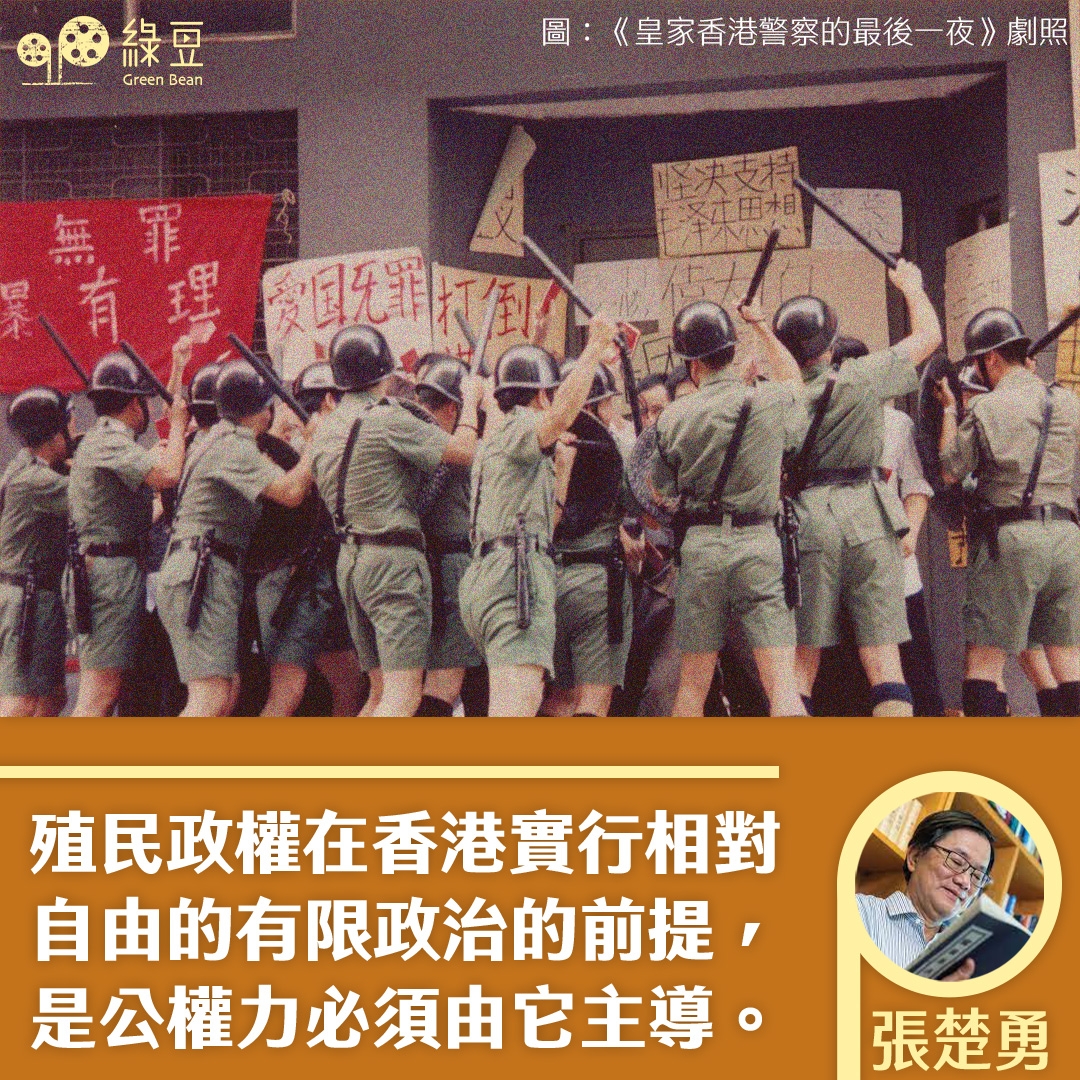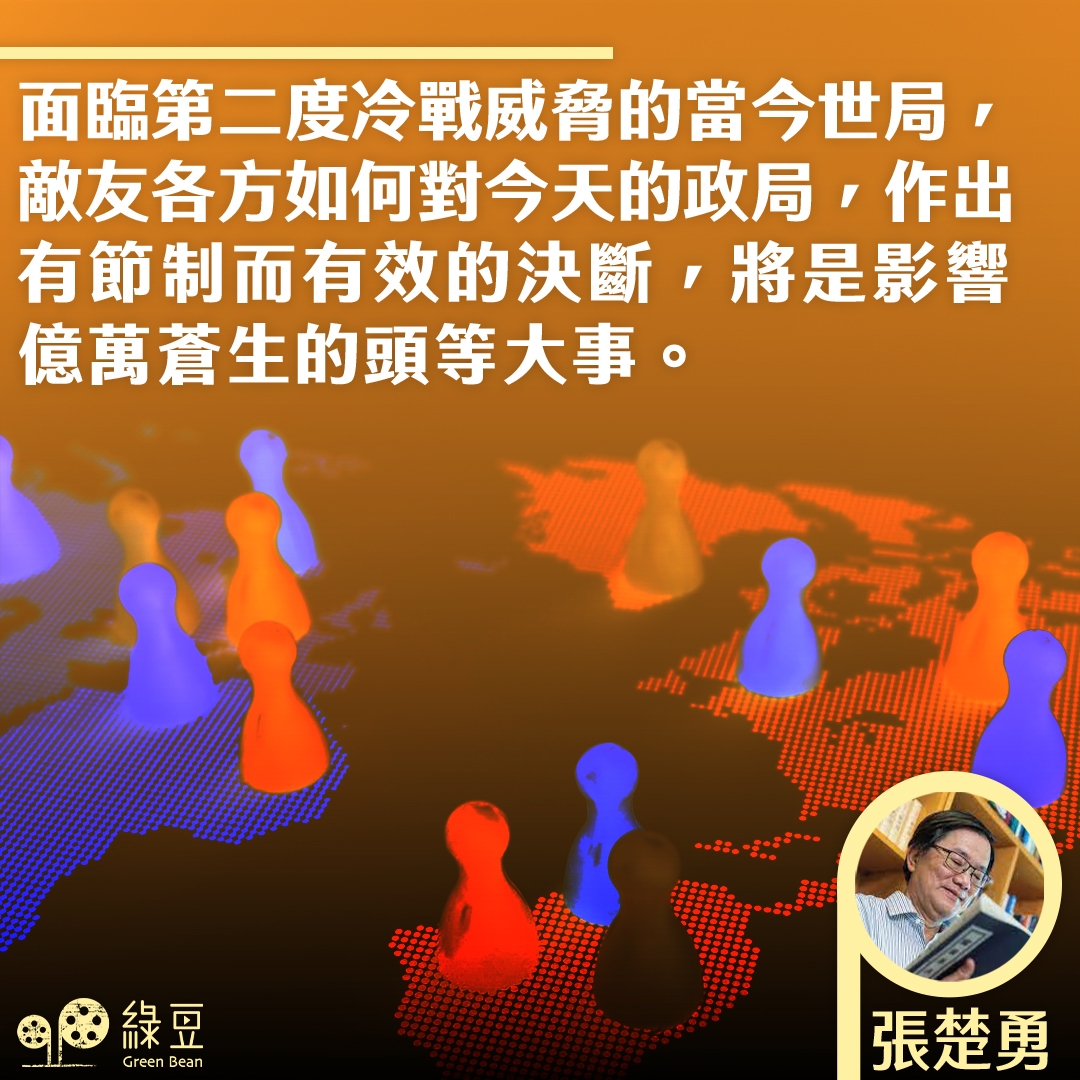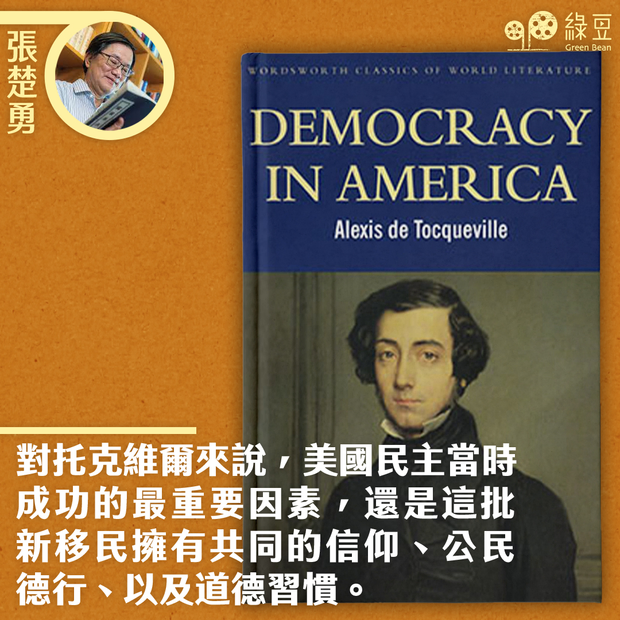歷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出席「香港歷史日」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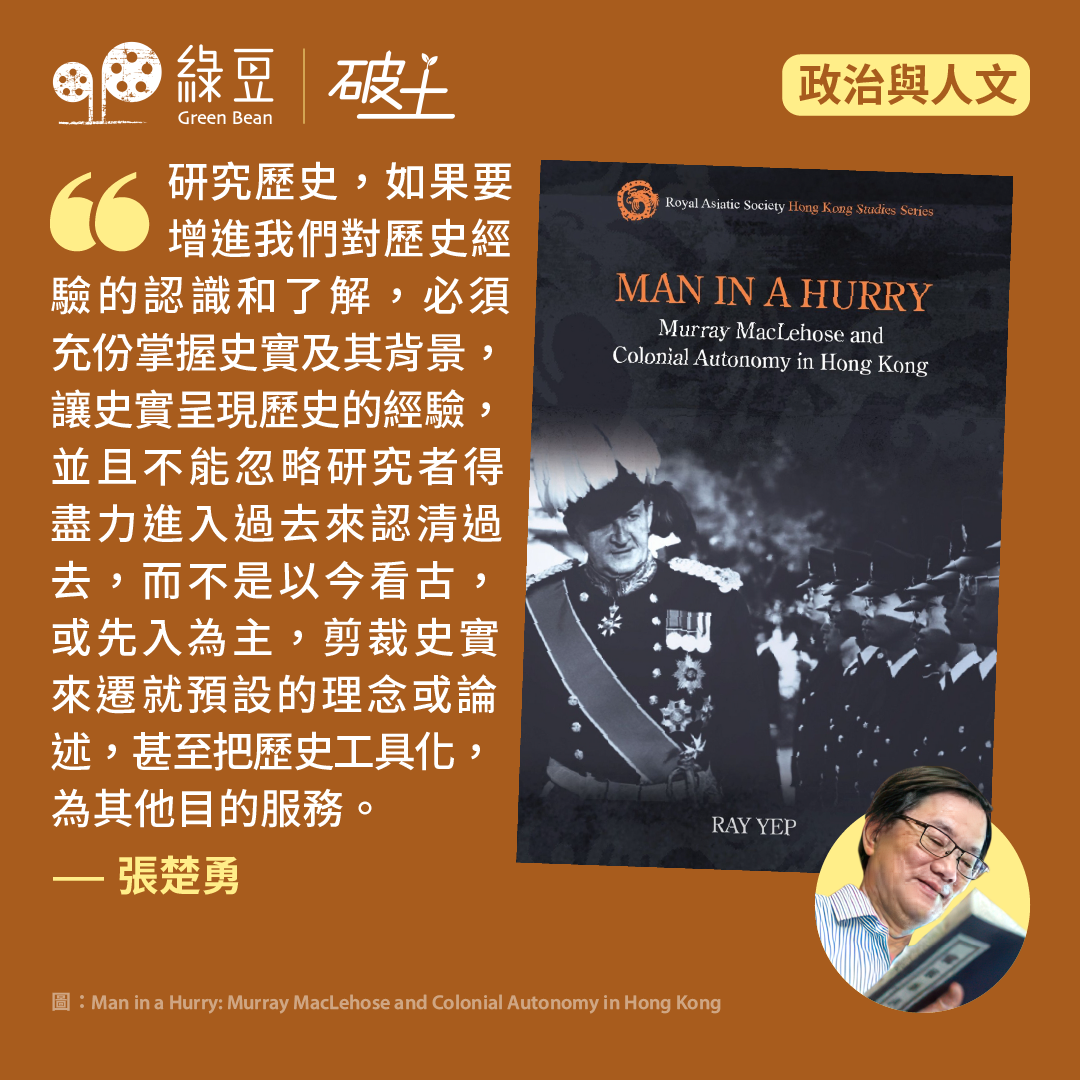
布里斯托爾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的香港史研究中心,是英國學界研究香港歷史的重鎮。2025年9月6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香港歷史日」,吸引了200多人出席。
那天的研討活動十分豐富。第一部分由三位資深的居港英裔歷史學家進行討論。其中新界鄉鎮史專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 介紹了他40多年來深入研究新界歷史的心得;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談論大英帝國管治之下,香港這個殖民地關於死刑的審訊和執行的情况;主持這兩位香港史學家的研討者,正是香港大學另一位歷史學家高馬可 (John Mark Carroll)。我對香港歷史只知皮毛,這三位居港英裔歷史學家的介紹和探詰,對我啟迪良多。
「香港歷史日」的第二部分,是中心裡的一群年青學者和香港紀錄片《尚未完場》的導演,剖析他們從事香港家族史的研究。其中一些學者通過偶然的機遇,發現了自己家族裡的先輩不少饒有意義的經歷:例如早期香港的大洋行華人買辦的活動,以及曾任香港工會骨幹成員的社會參與和對公義的追尋。這些學者通過深入發掘有關親人的經歷,看到在不少方面都反映到早期香港歷史的種種發展。這些發現,提醒人們今天的香港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香港歷史中心為此更向有興趣者提供工作坊,讓參加者學習歷史研究,以先輩親人的事跡為起點,實行自家歷史自家撰。
最後,歷史日的第三部分,是由呂大樂與陳冠中對談,回顧相對被忽略的香港1970年代,以及雜誌《號外》的源起及其對後來獨特的香港文化和社會的影響。
怎樣的史實
我並沒有專門研究歷史,但卻對各人文學科及相關學問深感興趣。參加了這個題材廣泛和內容豐富的「香港歷史日」,刺激了我對歷史研究的一些反省。
在這之後,我又拜讀了香港史研究中心研究總監葉健民去年出版的 Man in a Hurry: Murray MacLehose and Colonial Autonomy in Hong Kong (我權且將之翻譯為《席不暇暖的人:麥理浩和香港的殖民地自治》),深覺研究歷史,如果要增進我們對歷史經驗的認識和了解,必須充份掌握史實及其背景,讓史實呈現歷史的經驗,並且不能忽略研究者得盡力進入過去來認清過去,而不是以今看古,或先入為主,剪裁史實來遷就預設的理念或論述,甚至把歷史工具化,為其他目的服務。
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個現象,就是頗有一些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英裔官員,成為了終身的香港史研究者,特別是在新界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上文提到的夏思義和文基賢均曾任港英政府官員。早他們一輩的前新界民政處處長許舒 (James William Hayes),在不少方面也許算是新界史在西方學界的奠基者。包括夏思義在內的不少歷史學人,都感謝許舒對他們的啟迪和鼓勵。我有幸於1980年代中在港英政府工作時,跟許舒有短暫的接觸,當時感到他像學者多於像個殖民官員。
夏思義在談到他任職新界理民府官員時,每星期都有3天跟村民晚飯,讓他多了解村民的生活、關懷、習俗、過往的經歷及新界村落的人際關係及社區連繫等等。他更說通過多年的交往,彼此逐步建立信任,至使一些鄉村領袖願意向他展示村內不曾公開的古老文檔,成為他接觸到的珍貴的一手新界史料,捕捉到已被今人遺忘或不甚了解的新界舊貌。
夏思義說,他比較願意從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歷史,因為這些歷史充滿血肉和十分「貼地」,替帝王權貴為焦點的歷史觀提供了另一角度。他強調,以香港本身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對了解香港十分重要,因為以其他角度為主來看香港,很容易湮沒了香港本土的歷史經驗。
跟這幾年移居英國的香港社群人士在布里斯托爾聽夏思義談這些觀點,讓我反省到,目下香港人說離散和移民潮,很多時都以97回歸前的移民潮為第一波,2019年後的離散潮為第二波。今天這些流行觀點自有其重要之處,但卻忽略了1967年因文革導致的暴動引來的移民潮,更少有記起在1960年代早期另一次的移民潮。當時因著大陸平價農產品主導了香港市場,令到原居民難以通過務農在新界謀生,致使大批新界青壯者在當時英國法例容許下,移居英倫尋出路。
記得1970年代初,當童軍的我到西貢18鄉進行實地調查。那次意外地發現,企嶺下地區的每一條鄉村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那時鄉民跟我說,青壯者都已移居英國。這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夏思義在談及這課題時說,據他了解,戰前新界不少鄉村,已有整條村的男子都離鄉別井往外謀生的情况。如果我們要認識移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忽略了上述任何一方面都會是重要的遺漏,這是研究者必須注意的。
歷史解釋
歷史不可能重演。過去了而又能保留下來的史料史實,自然也不會保留得歷史全貌。史學家如何理解、詮釋、重組、論述相關的史料史實,以建立其相對完整的歷史解釋,自然也受到史學家自身採用的理念和認知架構、以及這些架構的前設視點所影響。因此,歷史解釋不等同歷史真實的全面還原,它們只是嘗試對已掌握的歷史經驗現象,作出令人有理由相信是最合情理、最好懂的解釋而已。
但這並不等如說,歷史解釋是主觀隨意的。不同的歷史解釋之間,還是可以嘗試比較以判斷高低優劣。例如,中國究竟是8年抗戰還是14年抗日,似乎並不應單從國民政府甚麽時候宣布全面抗日這一史實作唯一解釋根據。其中自九一八事件至七七蘆溝橋事變之間的史實關連、歷史脈絡起承轉合相關程度的估量,以及那一種論述更能合理地呈現整段歷史進展的肌理,可能是更有説服力的判定標準。
另外,我從前在東京參觀靖國神社時注意到,日本承認和美國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卻不承認二戰時發生了中日戰爭,認為中、日只是發生了軍事衝突。靖國神社對此的解釋,是因為日本向美國宣了戰,但卻從未對中國宣戰。不過,這樣的立場和解釋,在歷史研究上有多大說服力呢?「戰爭」和「軍事衝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以後者來解釋這段歷史,其目的反而更可能是政治考量多於增進歷史認識。
歷史與回憶
「香港歷史日」致力推動家族史的研究,我認為是很有意思的,這類努力很可能會大大豐富了以平民百姓為焦點的歷史解釋,與夏思義上述的歷史關懷很有共通的地方。
歷史是研究過去的。除非我們能夠證明人類歷史是有既定的規律,否則,歷史的過去,都是由具體、獨特、單一的事例組成。我們每個人都有過去的經驗。家族成員和先輩當然也各有其獨特的經歷。這些經歷儘管都是潛在的史料塑材,但日常經歷本身並不就是歷史。要揀選研究哪些個人經歷以形成有意思的歷史解釋,研究者必須提出一個有機會增進我們對過去認識的歷史問題,以緊扣有關家族成員的經歷,然後把這些經歷呈現在當時的社會脈絡和時代的起承轉合的事態之內。如何通過說好先人的具體個人經歷,以促進我們對香港歷史不同面相的了解和認識,正是我對香港家族史的期待。
不過,我對於歷史日提到「自己歷史自己寫」這一說法也有些看法。記得在閱讀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時,他提醒讀者,這不是歷史,這只是他個人的回憶。我想這是很有智慧的話。邱吉爾當然是二次大戰的主角之一,但他的回憶並不是希特拉、史太林、羅斯福等等的回憶。歷史的解釋是要放進歷史脈絡中去呈現的,這脈絡不是一方面的紀錄所能構成的。家族史要增進歷史認識,便得超越回憶錄的層次。
邱吉爾的自知之明,還在於他認識到,撰寫歷史要與該段歷史保持相當的時間和感情距離方為妥當。這一方面是要減低撰寫者對歷史事件的個人偏向太過投入,另方面也要有時間讓充份的史料能夠問世。
重新認識麥理浩
葉健民的新著《席不暇暖的人:麥理浩和香港的殖民地自治》其中一大貢獻,正是他通過整理和解讀英國近年的官方解密檔案,讓我們重新認識麥理浩這位為現代香港奠定良政善治的總督的管治理念和風格。在這篇短文內,我只想簡要的談及這本書對我的兩點啟發。
首先,一直以來,大家都視麥督執政的1971至1982年,是香港戰後實行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年代。其中表表者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興建地下鐵路、大幅增加社會及勞工保障、建立沙田屯門等新市鎮、開闢郊野公園、成立區議會等。葉健民通過詳細的檔案研究,發現麥理浩在推行上述多項改革之餘,卻同時是堅守當時殖民政府非常審慎的量入為出的公共財政政策,反對甚至拖延執行當年英國執政工黨政府在1976年為香港制定的、更為全面和富有財富再分配和福利主義意味的《香港計劃書》 (The Hong Kong Planning Paper) 。葉健民在書中形容麥督「實際上是個勉強的改革者,並強烈信任低稅制和嚴守財政紀律。」(頁79)這結論是紮實的、根據新發掘的史料所得的歷史研究結果,同時也使我們對麥理浩執政歷史有進一步認識。
其次,這本書是聚焦於大英帝國的管治框架下,香港的殖民地自治是如何存在和運作這課題。在這課題當中,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張力?對峙?配合?從屬?還是互動?這些究竟都是怎樣具體地呈現出來的呢?擁有主權的宗主和不受中央直接治理的地方殖民地的自治關係中的強項、弱點、其中開啟出的機遇、避免不了的局限,是如何在歷史經驗中展現過來的呢?
葉健民在此書通過麥理浩時代的四個政策範疇,為香港的殖民地自治這一歷史課題,作出了有根有據、深入、饒有新意的解釋。這四個範疇分別是:
1) 麥理浩怎樣在英國不特別熱衷的情况下,成功成立廉政公署和應付後來的警察叛亂;
2) 在社會改革上,麥督如何冷處理倫敦福利主義式的香港計劃;
3) 在越南船民問題上,香港如何不得不配合宗主國的地緣政治和外交考慮以作出應對;
4) 在97問題上,麥理浩如何採取主動策略,使北京和倫敦正式正視香港前途問題。
此書通過具體詳盡的歷史解釋,使我深刻明白到,大英帝國管治其偌大的版圖時,其中一個重要的傳統 (儘管不一定常常堅持到),正是服膺以下的一套治理原則和實踐:即「在地」的殖民地官員,如能真誠致力地去維護當地的良政善治,便是服務宗主國的最佳明證。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