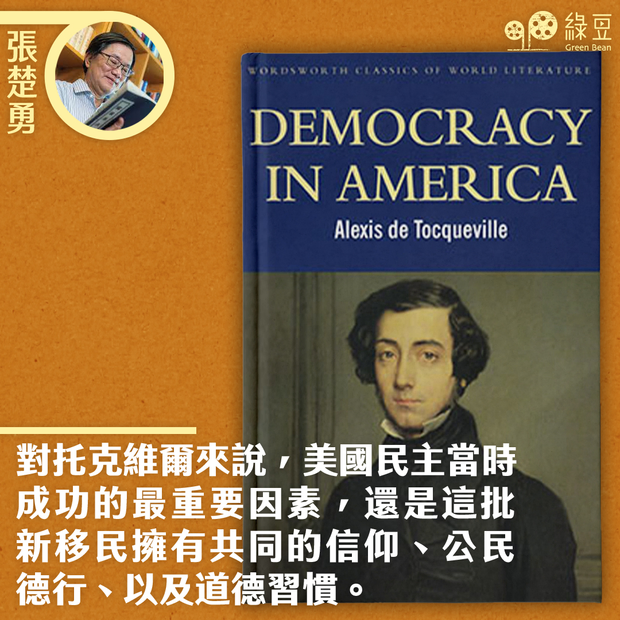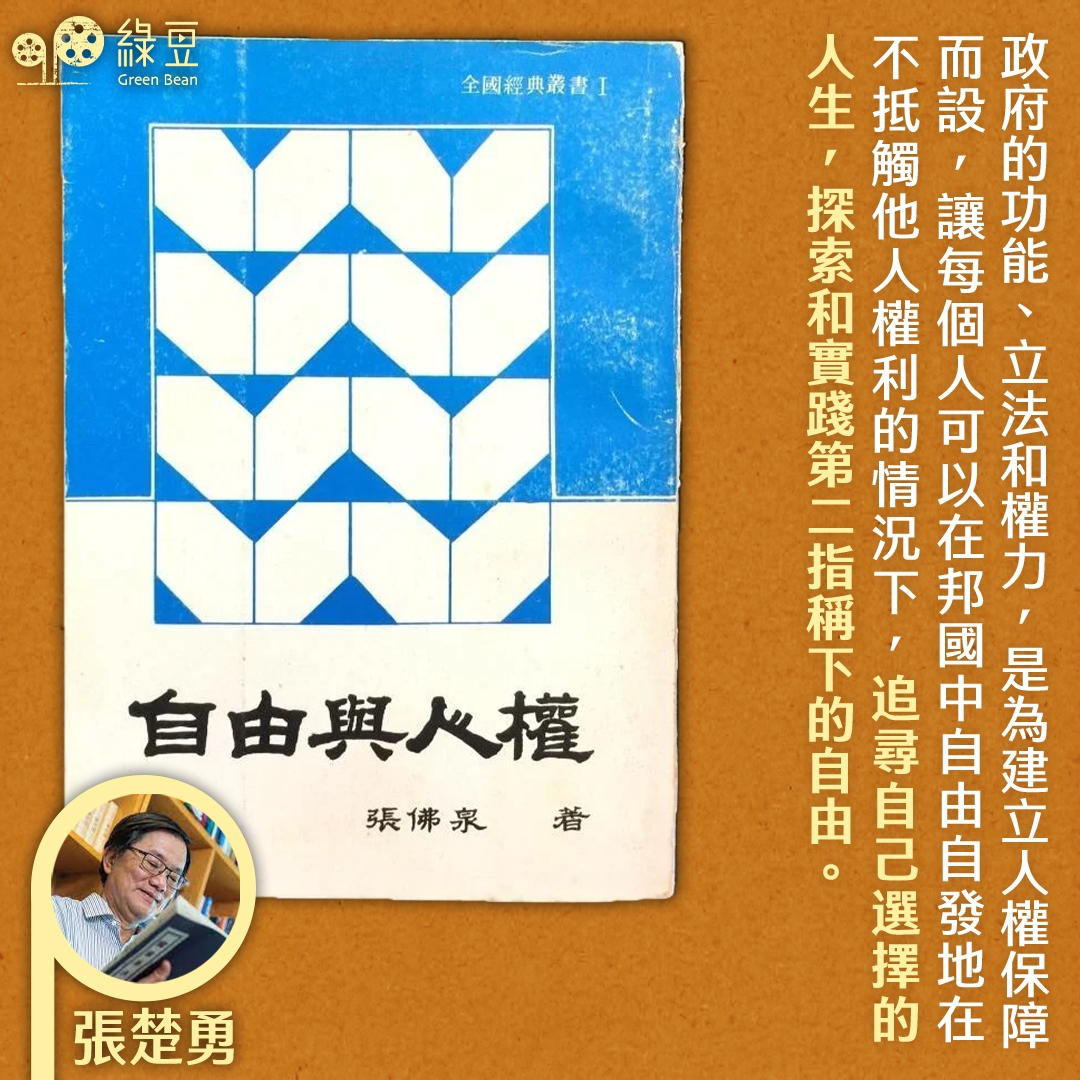世道紛亂:政治上的「敵、友」思考

編按:綠豆團隊再有新農夫加入一起鬆土翻泥!張楚勇博士將在破土分享其閱讀的領受,對這紛亂的世道作出思考與分析。或許沒有答案,但多一分認識,也許會少一點困惑
==========================
去年中從香港城市大學退休後,我有較多時間閱讀和重讀一些政治、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
閱讀經典,除了是向人類文明中最傑出的作者學習之外,更是與具有超越一時一地視野的文化遺產對話。換言之,閱讀經受長時間考驗的經典,往往有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身處的人文世道。因為能穿越世代仍具參考價值的作品,必定有其深邃的洞見。
最近承蒙《綠豆》編輯不棄,希望我能為這媒體撰文。書生如我既然還有一些閱讀空間,面對當下種種人間世道的重大挑戰,自然會不能自已的作出思考。能夠有這平台與大家分享我的淺見,是榮幸。雖然書生之見多不能解決實際難題,更遑論「改變世界」,但多一分認識,也許少一點困惑。如能做到這樣或已不辱使命了。
我用「紛亂」來形容當今的世道,大概並不過分。5月20日出版的英文時事週報《經濟學人》,發表了與最老資格的政治評論家基辛格的訪談,其標題正是「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戰爭是人類面對最嚴峻和危難的一種處境。在這核武和人工智能當道的年代,戰爭更可能是人類文明存亡的大考驗。這當中自然是最敵我分明,任何決斷都不容失誤。
熟悉當代法理政治學的人,在談到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友」關係時,自然要提到20世紀在這方面的主要德國思想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
施密特由於在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並在期後3年成為納粹德國的首席法理學家,又發表反猶太人的言論,因此在戰後知識界成為一位很受爭議、甚至是在道德上不能被接受的人物。施密特在德國威瑪(Weimar) 共和年代,更是議會民主制的尖銳批評者。他認為當時威瑪共和的議會已被只顧自身利益、分崩離析的幾個政黨騎劫,使議會爭議不斷,卻沒能力作出代表國邦整體公益的決斷,因而導致國邦衰敗,國民對政治體制不信任,他因此主張讓政治公權集中到共和國總統身上,實行某種形式的獨裁統治。職是之故,不少支持自由憲政和議辯民主的思想家(例如海耶克(Hayek) 、哈巴馬斯(Habermas)等) ,對施密特的思想都是持非常批判的態度。
我這篇短文不能對施密特的思想作出全面評價。不過,在我對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的有限理解中,我認為其中一些關鍵和根本的論述,對我們理解今天身處的紛亂年代,還是很有啟發作用,讓我們能頭腦清晰的去面對這世道帶來的挑戰。
施密特其中一個著名和根本的論斷,便是他認為在政道(The Political) 這範疇內,國邦或政治群體的最根本決斷,便是「敵、友」的界定(請參看他的《政道這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一書)。這決斷顯然是國邦中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根本,而決斷是否能達致實效,往往影響該政治體制的穩定甚至存亡。
要更好地理解施密特的這一論斷,我想得簡要說明一下他的國邦理論。他認為國邦理論和憲政理論是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範疇。政治群體的存在,是和該群體不得不通過權威機構或程序,作出集體而強制的決定分不開的。該群體還得有效地推行和維護這些決定。這些決定在現代邦國往往通過法律形式存在,而邦國在常規政治下的最高法律,一般就是憲法。
憲政理論自然是探討和憲法有關的理論,闡述立國的原則,公權的分佈和權限、適用的範圍,界定公民的身分、權利義務等等。但國邦作為一個有效的群體,是不得不面對和處理常規政治以外的問題。例如在憲法闡明國邦的立國原則前,誰可以決斷這些原則?決斷這些原則應有的過程該如何?如果國邦面對前所未有或憲法沒有預期的危機,誰可以界定有關危機並作出最終的政治決斷?如果面對衝突威脅,應怎樣決斷是戰是和、甚麼時候戰甚麼時候和等等。
上述這類問題,施密特稱之為「非常態政治」(Politics of Exception) ,而國邦在面對這些情況是不得不處理,亦必須進行政治決斷的。施密特認為,誰在此情況下能有效作出決斷的,便是實質的國邦主權擁有者(見他所著的《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換言之,這類問題,推到最根本之處來說,就是「政治決斷」決定誰是國邦的主人,決定國邦的政治秩序該如何。當國邦或該政治秩序受到威脅時,應如何採取果斷有效措施,分清敵友,以維持國邦的存活、發展和穩定,更是「政治決斷」必須發揮的功能。
如何理解施密特這一論斷的理論含意,不同的理論家有不同的說法。我自己的看法是,這一論斷提醒我們,根本的政治問題有一不能忽視的決斷層面,這層面是政治群體作出集體強制性決定的前提,我們必須清醒地給予重視。無視這決斷層面作出的政治分析,說到底難免是片面的。
當然,政治決斷絕對有其令人不安的地方。因為決斷的一念之差,可以是天堂和地獄之別,既可使國邦成為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堡壘,也排除不了政治社群成為專政獨裁者主導的地方。施密特的理論在此「一念」的取態和論說究竟如何,是學界一個眾說紛紜的爭議課題,其中一個關鍵是他如何理解「敵人」這個概念。日後如有機會,也許可以分享我的淺見。
如果在分析香港的管治和政道問題時,能夠同時參考施密特的政治決斷論,我想我們在解釋戰後殖民地年代「去政治化」的相對寬鬆環境,和隨之而來的政治穩定時,顯然不是金耀基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框架所能概括的。
正如施密特說:「去政治化是一種特別又極其强烈的政治行徑。」(Depoliticization is a political act in a particularly intense way.) 記得我1995年還在皇家香港警務處任職文官時,留意到在不到兩年香港主權便將移交中國時,這個殖民地最重要的紀律部隊的指揮官(即警司級或以上官員),有75% 的成員還是由英裔同僚擔任。殖民政權在香港實行相對自由的有限政治的前提,是公權力必須由它主導。可見殖民政權的政治決斷,當時還是在起著重要作用。當然,北京1949年對殖民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策略,也是影響香港戰後政治秩序的重要決斷。
1997年中國行使香港主權後,儘管常規政治理解下的「一國兩制」,在回歸後一段長時間在特別行政區保持了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大致不變,但「一國兩制」背後的政治決斷,和殖民地年代的政治決斷實際上已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改變。
回歸後香港憲政的背後已接上了近、現代中國由列寧革命政黨及其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決斷模式。從國際政治格局而言,香港政權對外的「敵、友」界定,也是由跟從英國或西方轉為由中國決斷。這些根本的改變,對香港1997年後的政治、民主化發展、以及對由香港議題所產生的內、外紛爭和衝突,都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正視這些根本的改變,對理解近年香港出現的矛盾和衝突、以及香港的對外政治定位等課題,是很重要的。
我們過往對上述政治決斷層面課題的忽視,也許正是一直以來,香港很多政治分析難免顯得片面的因由。
▌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