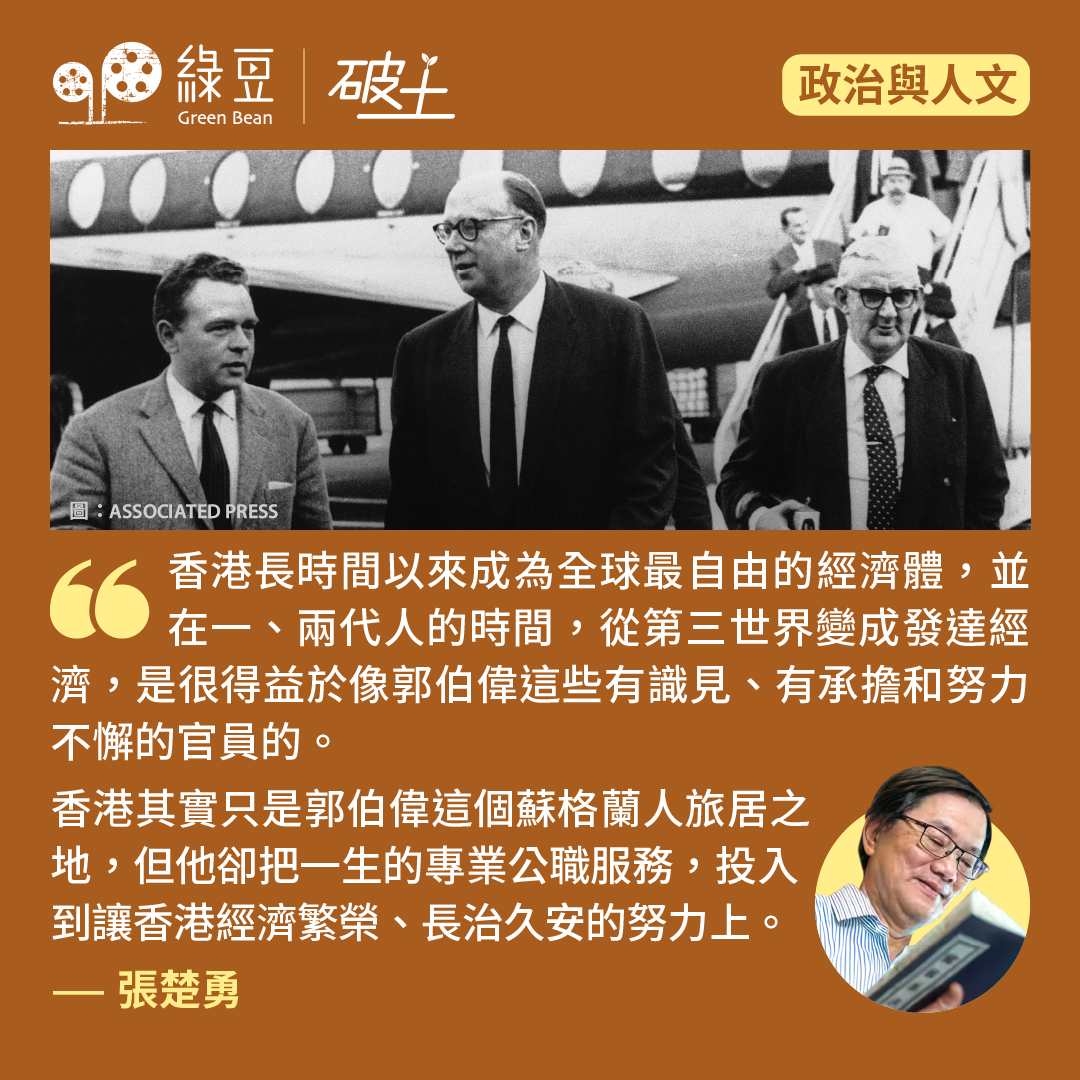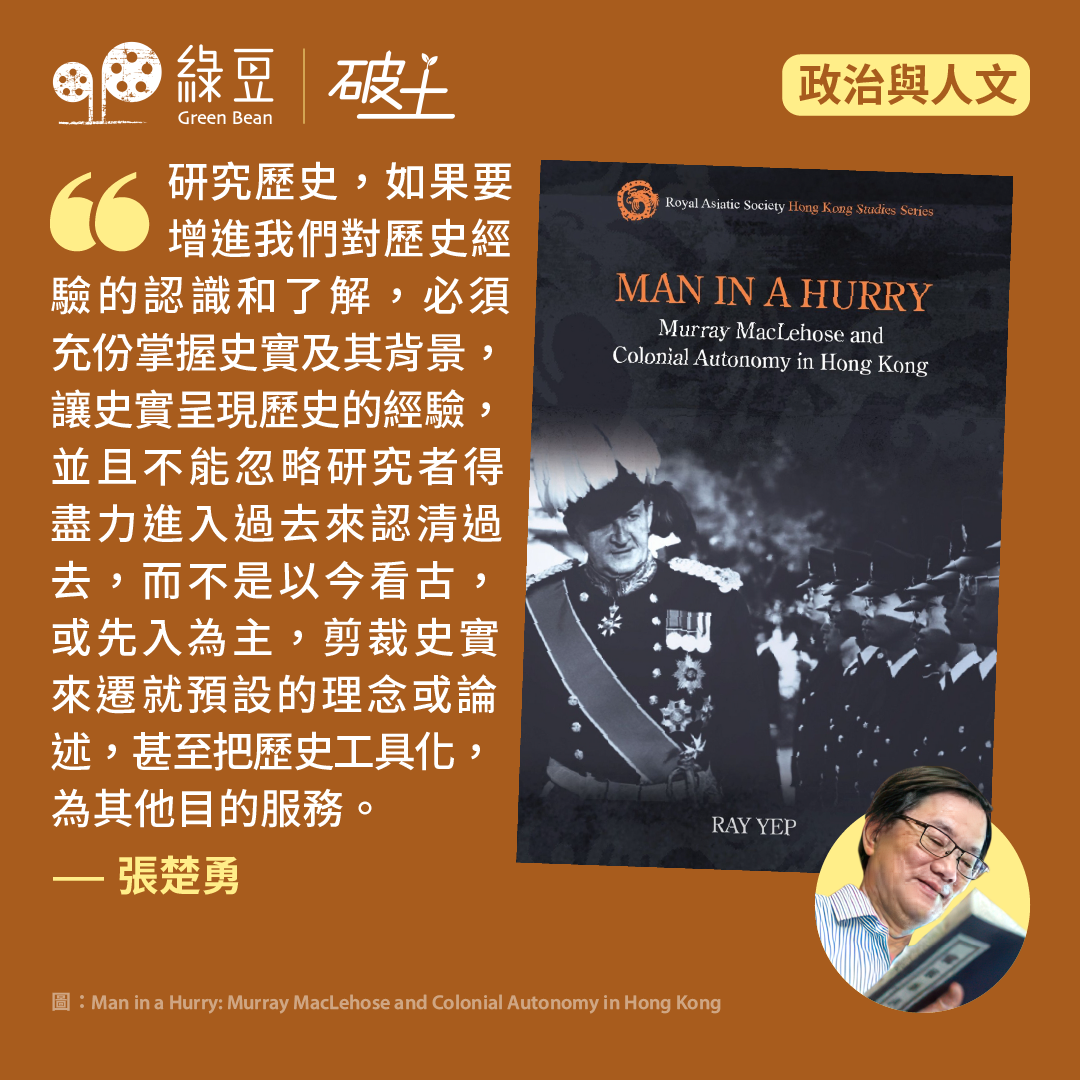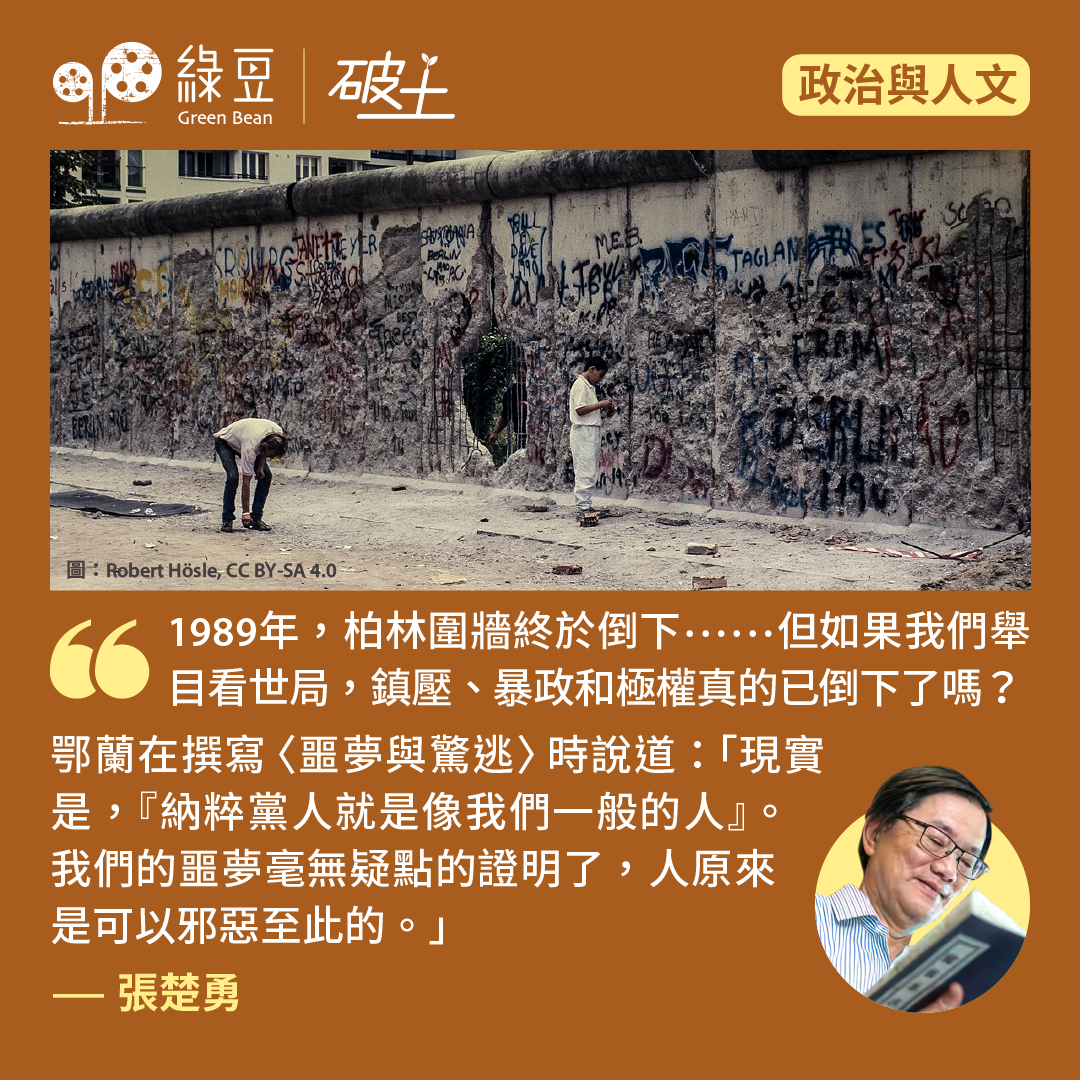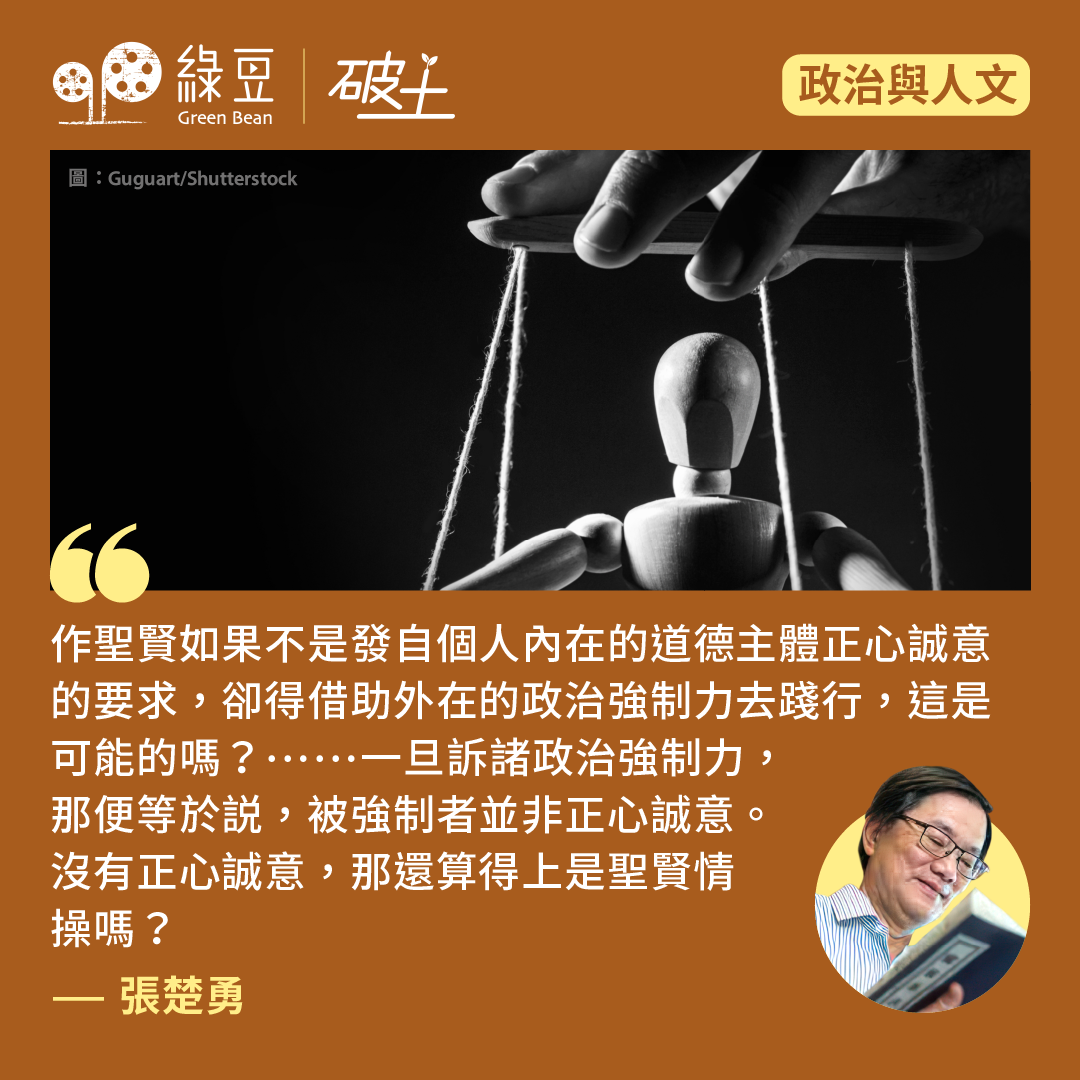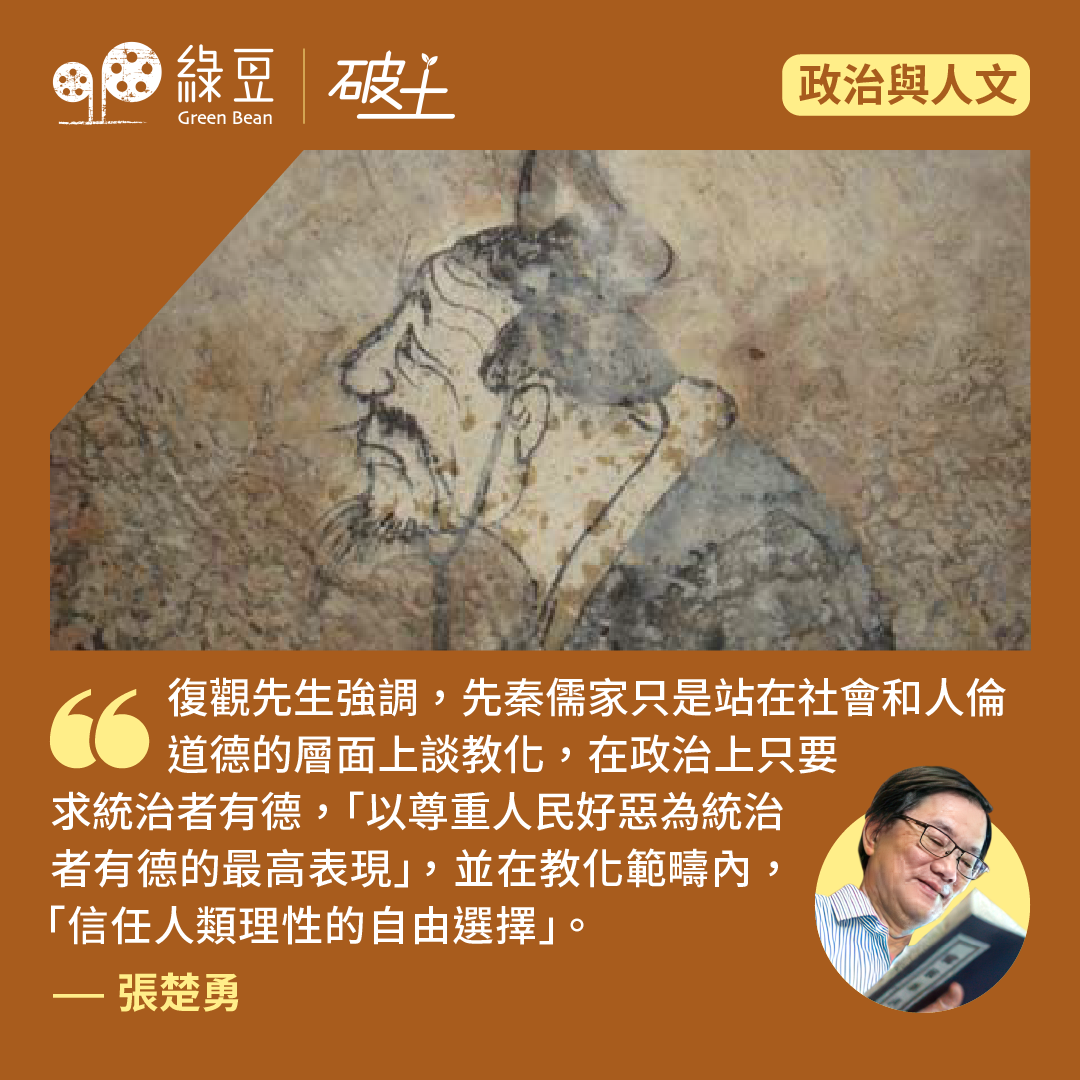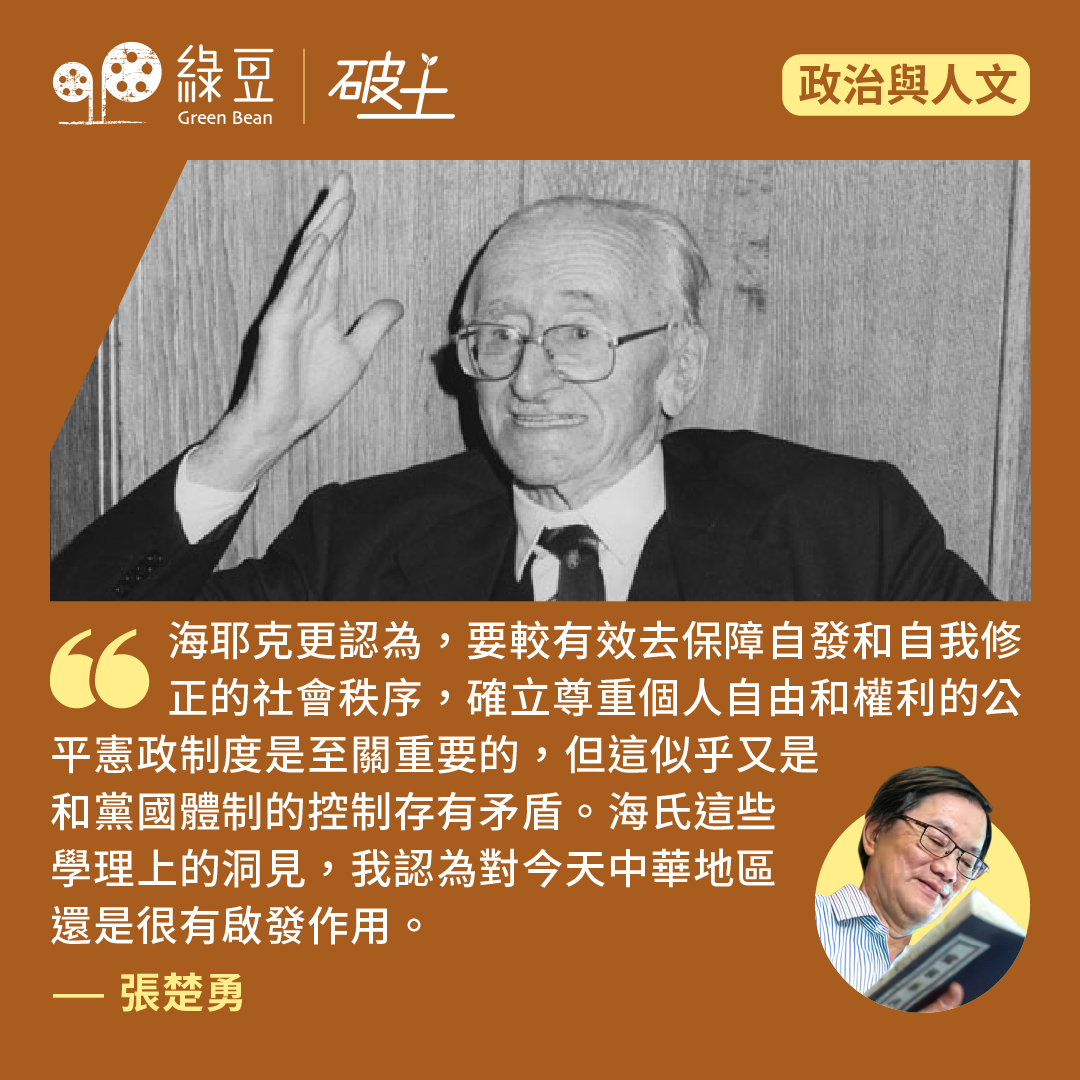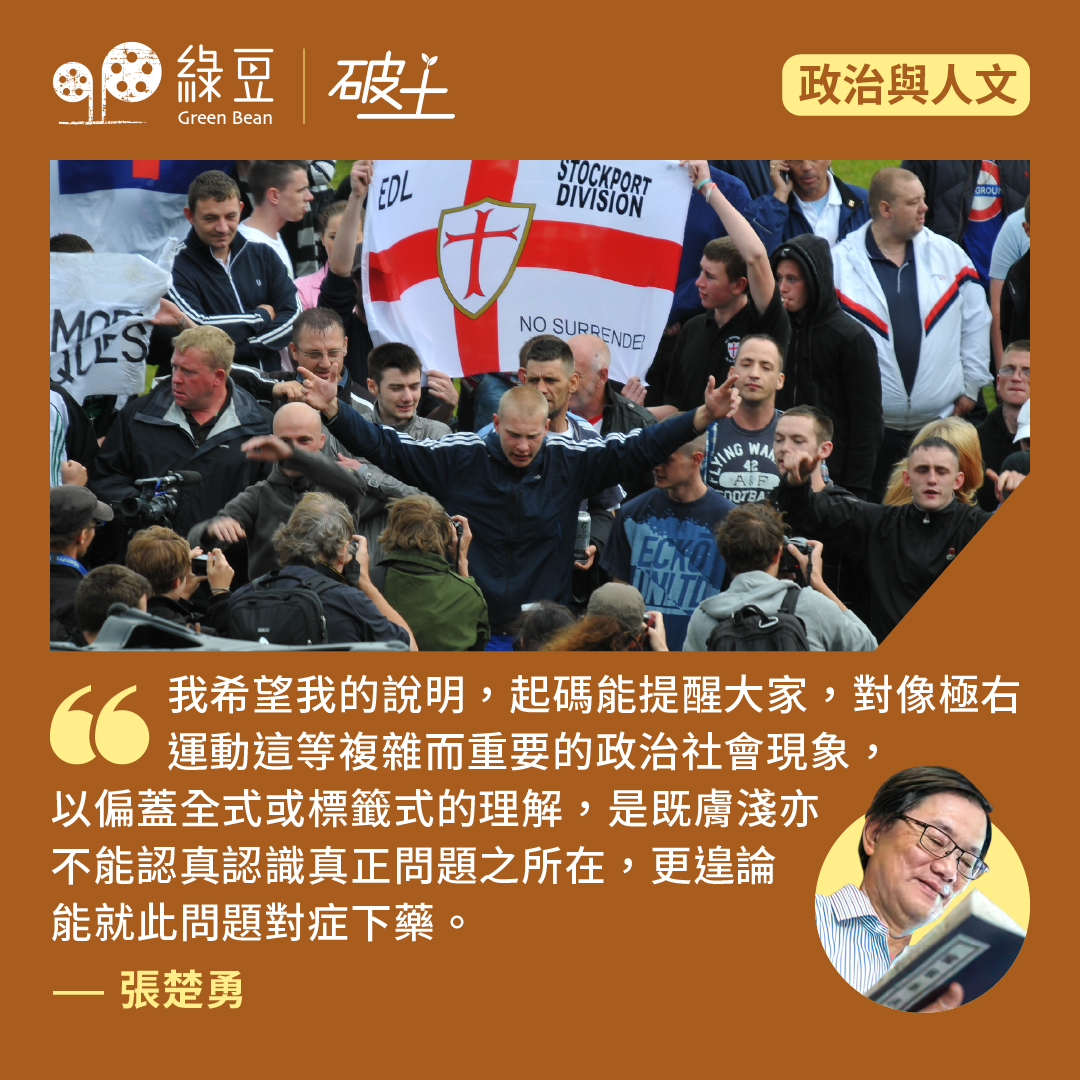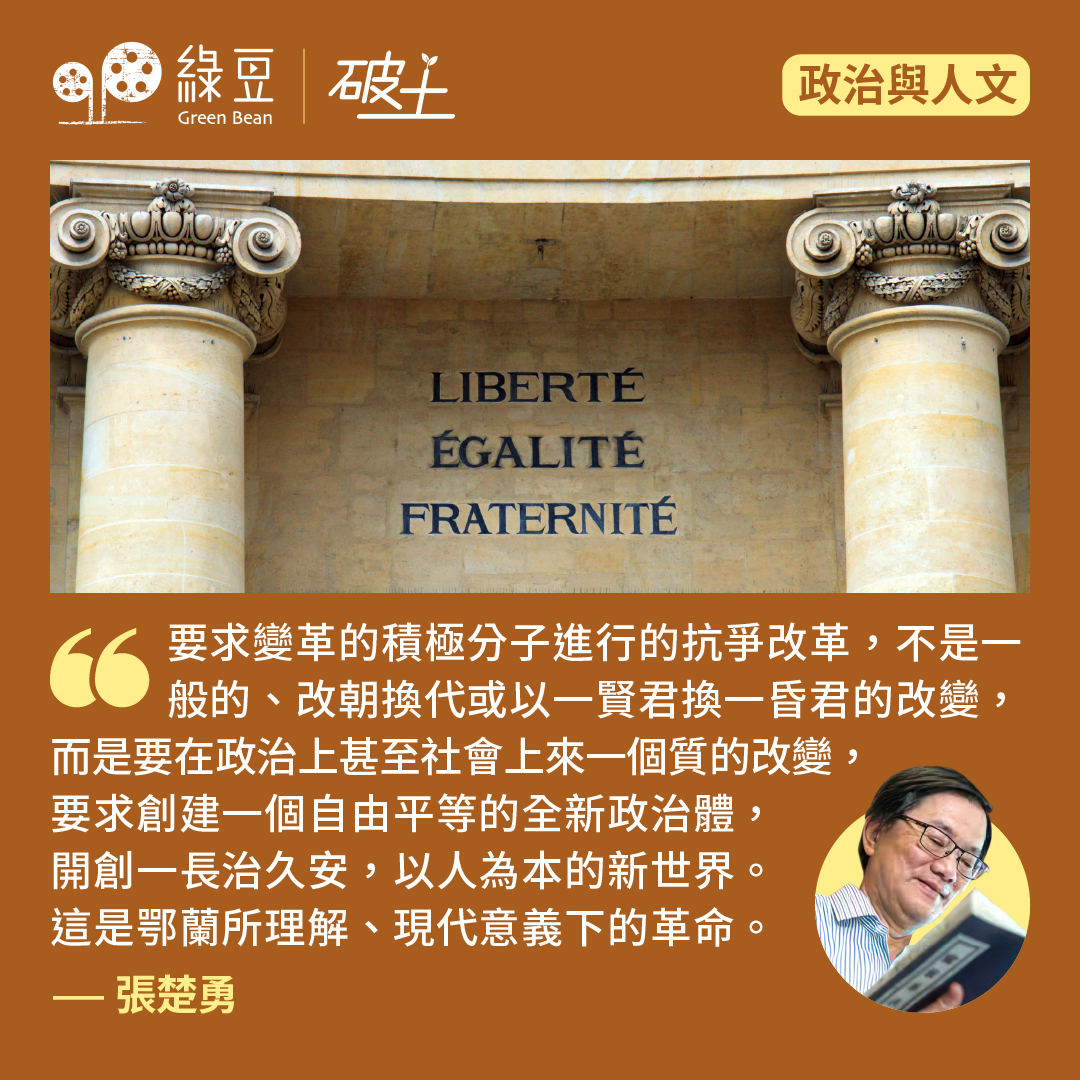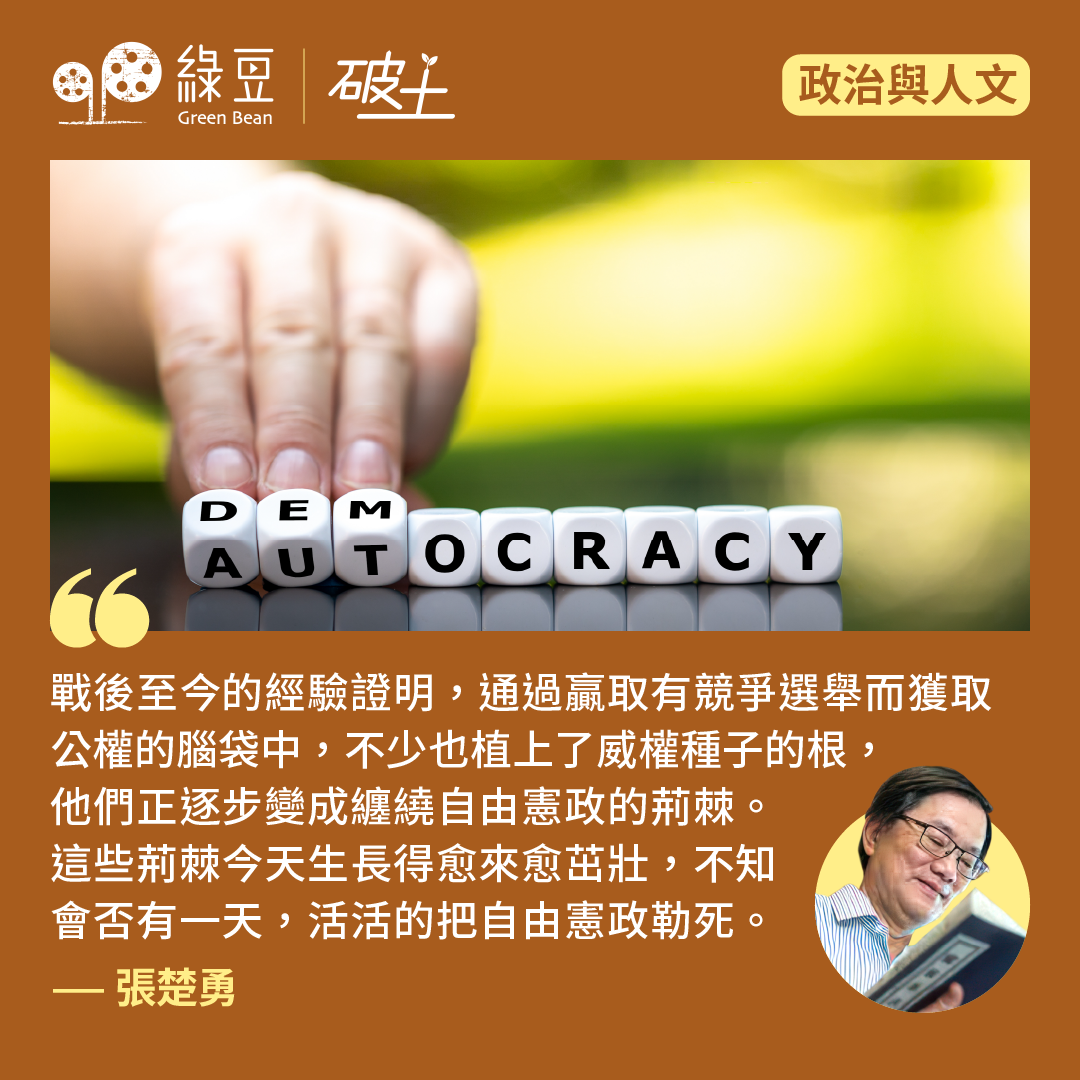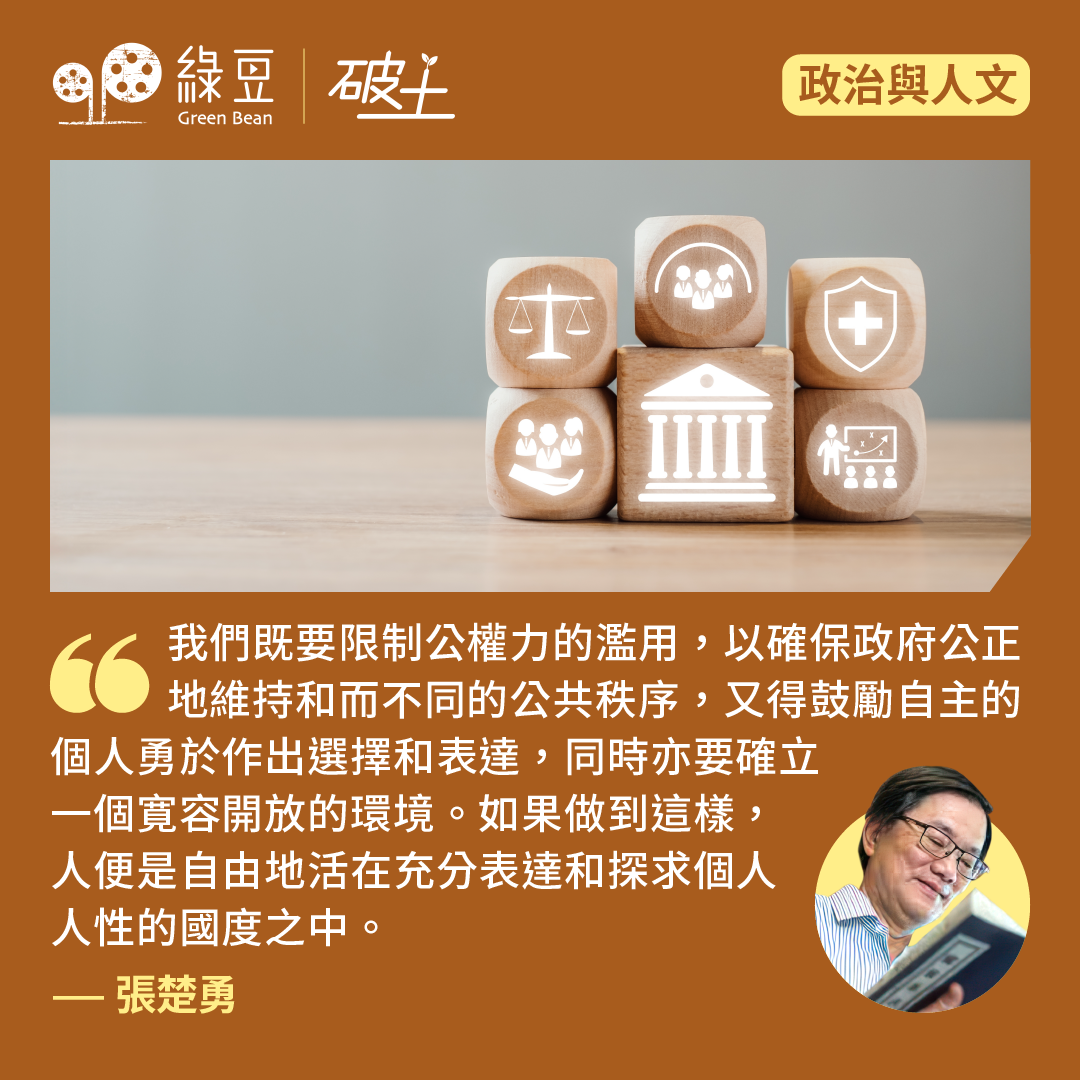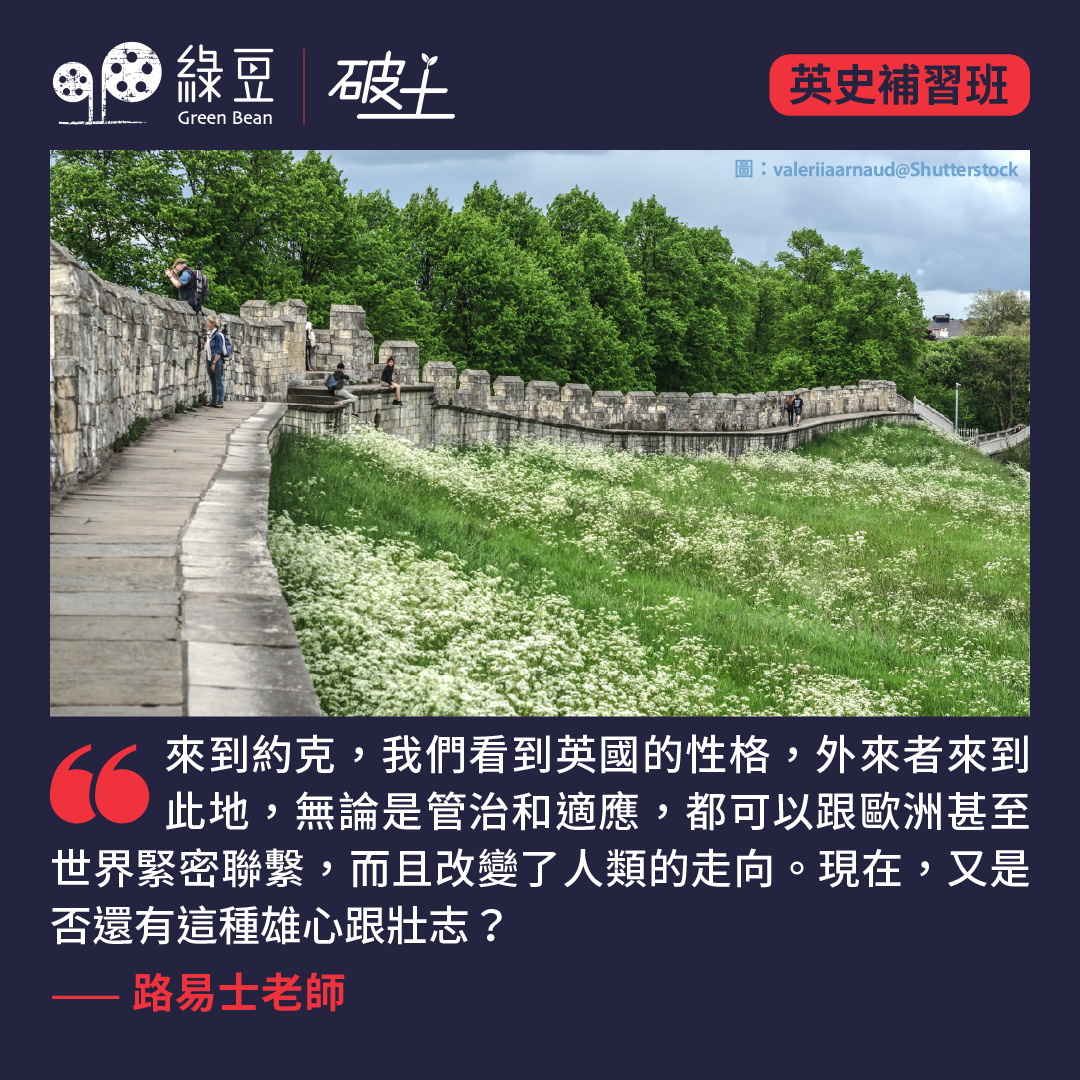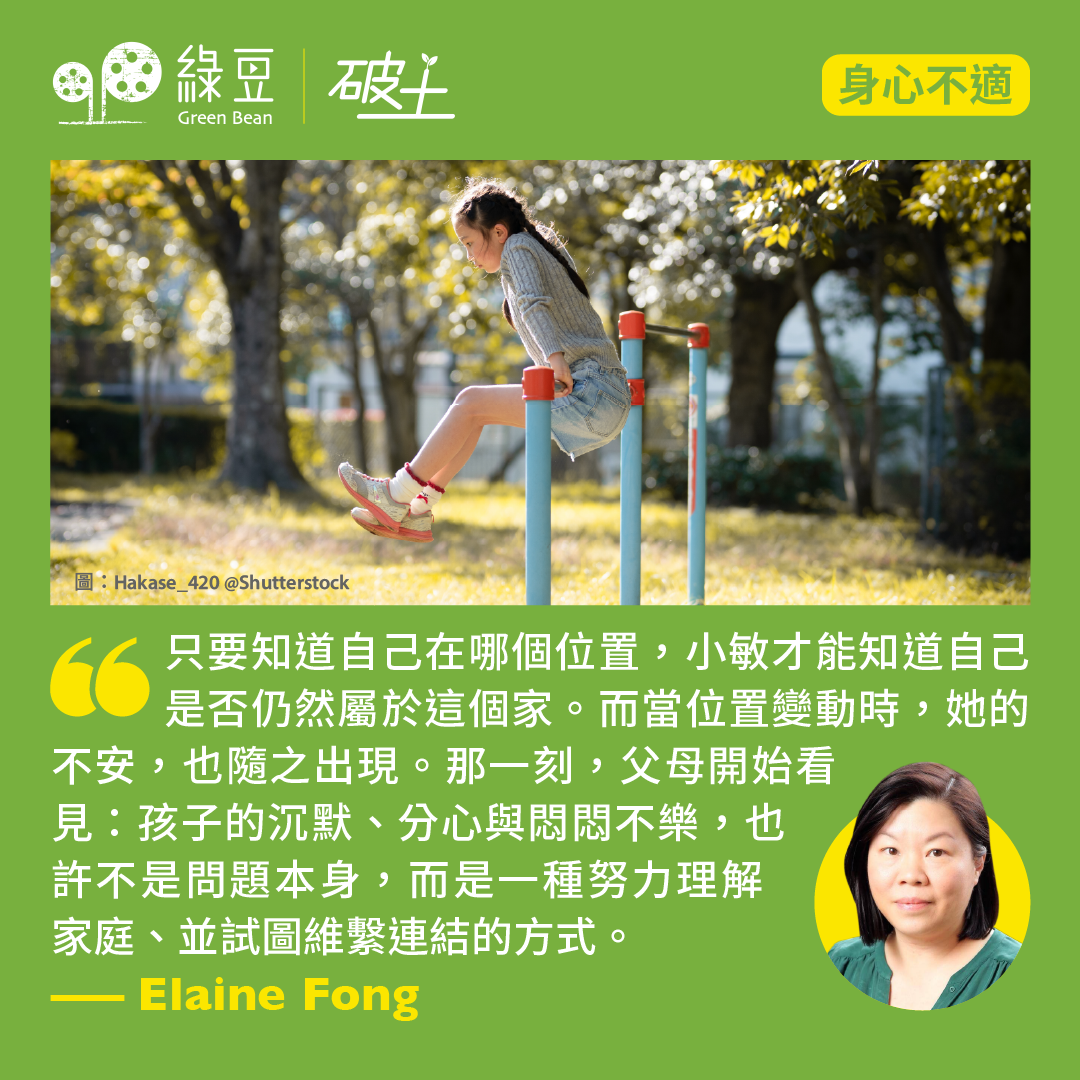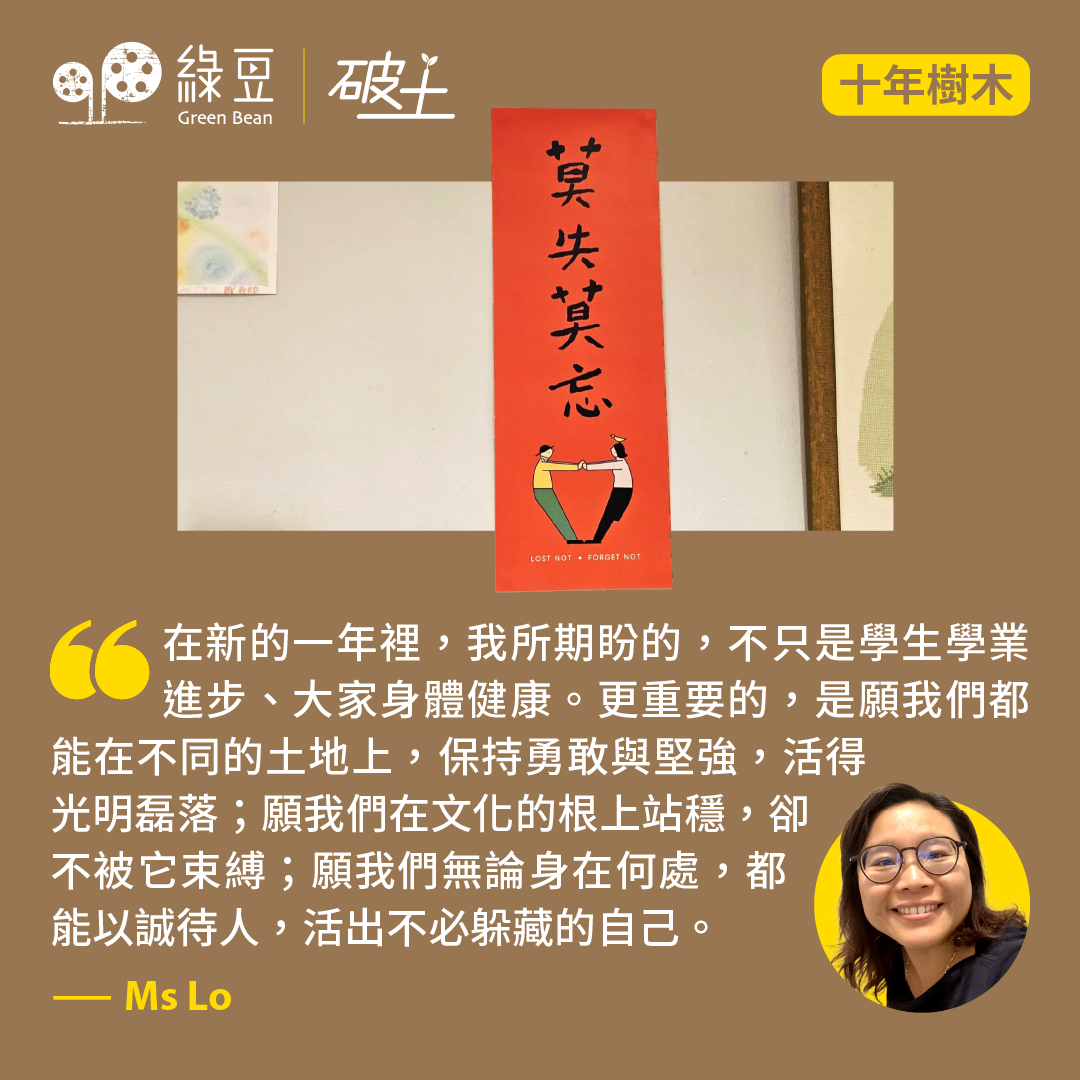自由市場經濟, 公共理財, 不干預政策, 知識分工, 量入為出 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投考港英政府的政務主任職位時,到了最後一輪的個人面試階段,是我這個申請人面對7個首長級官員,回答他們向我提出關於政策和政治的難題,並就著我答案中提出的建議和分析,跟他們進行辯論。 在論及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課題時,我發覺這些首長級官員無一例外的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和做法很是支持。他們在公共理財方面都非常審慎,認為必須量入為出,並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各國實行財富二次分配式的福利政策,很不以為然。我當時感到,這些坐在我對面、絕大部分來自英國的首長級港府官員,在提到宗主國的福利主義思想時,很有種忿忿不平的情緒,認為這是管治上的誤入歧途,是經濟上日益繁榮、市場自由開放的香港萬萬不能引進過來的。...
布里斯托爾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的香港史研究中心,是英國學界研究香港歷史的重鎮。2025年9月6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香港歷史日」,吸引了200多人出席。 那天的研討活動十分豐富。第一部分由三位資深的居港英裔歷史學家進行討論。其中新界鄉鎮史專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 介紹了他40多年來深入研究新界歷史的心得;文基賢...
最近,我和太太到了柏林一趟。這個曾經是上世紀納粹暴政的心臟以及冷戰最前線的火藥區,對學習政治、歷史和人文學科的我,自然是深具意義。 我們抵達的頭一天,便前往了在離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不遠的「歐洲遭殺害的猶太人紀念館」(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上個月,我在《綠豆》發表的〈修己與治人的關連與區分—徐復觀論儒家與民主人權〉一文中,提到20世紀新儒家徐復觀先生以下一個重要的觀點: 「儒家思想,主要是『規定人的行為的思想』。這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把修己和治人的行為作出區分,其基本用心之一,便是要執政者明白,『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要人人作聖賢,即使是真的,也會成為莫大的罪惡。』」 為甚麽「以政治強制之力」使人民做聖賢會是「莫大的罪惡」呢?我在這篇短文內,將會提出一些看法,並就此對規範行使政治公權的公共道德的性質及相關議題進行思考。 政治強制力與正心誠意 公權是構成人類政治社群並保障該社群存在、發展和有效運作的中樞元素。掌握公權者對政治社群的安危興衰,負有重大的公共責任。如果他們在這方面不稱職,嚴重者將影響政治社群的存亡。公權力要保證有效運作和執行,必須符合嚴謹、公正以及正當的程序,也得大體上為人民所認同和接受。必要時,公權力更得訴諸合法和適切的強制力作為推行的手段,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利益,和維護政治社群的安全法治和秩序等等。 作聖賢,是個人修身的崇高的道德要求。這往往需要慕道者裡外如一地終身不懈的努力去踐行。孔子不是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賢如夫子,也只敢說自己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吧了。再者,個人修身的道德必須重視正心誠意,因為這是發自慕道者個人内在的道德主體的要求。根據這要求化為個人行為後,其所產生的客觀實踐結果是成是敗、是差強人意還是盡善盡美,自然是重要的事。但如果個中缺乏了個人內在道德主體的正心誠意,那有關的行為是否可稱為聖賢行為便頓成疑問。 試想伸出援手拯救將墜於井的孺子的人,如果不是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心裡盤算著孺子家人會否因此而感恩圖報者,其道德情操離聖賢有多遠呢?...
20世紀新儒家的一位主要思想家徐復觀,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灣學生書局,2013) 一書中說:「由中國政治思想以接上民主政治,只是把對於政治之『德』,客觀化出來,以凝結為人人可行的制度,這是順理成章,既自然,復容易,而毫不牽強附會的一條路。」 (頁248) 這大概是中華近、現代政治思想中,對傳統儒家和現代民主政治的相容性所作出最樂觀的一個判斷。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之聲不絕於耳,認為以三綱五倫為主導的傳統中華文化,跟強調民主科學的現代思想和制度格格不入。這類觀點強調,要帶領中國邁向現代民主,便須改變傳統中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當時最為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要全盤西化。到了今天,全盤西化已沒有人支持。但在中國大陸掌控公權者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仍舊認為,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中國的未來必須走中國特色的道路,而不是西方政治上以保障個人自主的權力分立的民主制度。 儒家的政治思想...
2025年7月中,我將會參加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個學術會議,宣讀一篇名為〈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與戰後中華自由思想〉(‘Hayek’s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Post-War Chinese Liberal...
極右政治在西方世界捲土重來,是近年的一個重要和令人憂心的現象。 我目前主要生活在英倫,對此發展自然特別關注。我也曾在《綠豆》這專欄裡,發表過一些文章討論這課題。早些時候,在倫敦的公立圖書館裡,我找到了一本關於英國極右的專著,閱讀後覺得獲益良多,也有不少感受,希望在這篇短文裡跟大家略作分享。 我讀的那本書,英文原名是Angry White People: Coming face-to-face...
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當中,最能啟發我的其中一位。 她對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思考、對二戰後針對納粹戰犯審訊的分析、對權力/力量、權威、暴力的探究、對獨裁統治下個人的道德責任的反省等等,都是學富五車,深具原創洞見和鞭辟入裡的傑作。她那些充滿抽象哲理的著作,例如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的系統反思、對思考活動尋根問底的討論、以及對康德三大批判中的判斷...
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民主制度備受挑戰的年代。 激進和敵我的政治形態,在愈來愈多地方主導著世局發展。中東的衝突、俄烏戰爭、歐洲極右政黨的抬頭甚至執掌公權等,正表徵著温和共識政治的大退潮。特朗普今年第二度入主白宮。他那「美國優先」的功利對外政策,以及他運用總統權力,試圖把關鍵的行政專業部門 (包括檢控、税務、情報、教育、外援等)全面由他及其政治親信主導,並通過政權所擁有的資源、財力、物力、權力,抵制甚至打擊和他政見不同或價值取向上有分歧的人、計劃和組織,這等做法和事態發展,已引來了美洲一些頂尖的政治學者撰文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就是保留了有競爭的選舉制度,未來也可能會過渡成威權管治的國邦。 在這個背景中,我近日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其中上文提及的警告,正是出自今年2月11日,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李維兹基 (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尼(Lucan A....
隨著年事漸長,近來我的視力,受到白內障的困擾,看書寫文章的活動,暫時受到影響。因此,今期的《綠豆》文章,恕我回到一些我比較熟悉的、相信還是與當今人文和政治息息相關的課題,與讀者分享一下。 每天,我主要通過媒體了解世局。雖然樂見個別獨裁暴虐政權倒台,但眼看中東、東歐戰爭衝突不斷,地緣政治緊張,東西方的政體不斷受到極端政黨、民粹主義、威權政治的挑戰;民主邦國也出現了總統宣布實行軍管、立法機關與行政當局差不多陷入互不相容的僵局;這些都使人對世界政局憂心忡忡,更不要說當今世界第一大國,首次由一位罪犯出任總統,並對跟他立場或利益不相符者往往以威嚇方式對待。也許,2025年的世局,很難是一個平和、文明與寬容的格局。這使我特別缅懷17世紀英格蘭的哲者洛克 (John Locke)的自由思想的洞見。 我認為,洛克於1689年發表的《關於宗教寛容的一封信函》,在今天讀來,還是很有啟發意義。 洛克發表此文,是希望當時的歐洲,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宗教衝突和迫害的慘痛經驗之後,能痛定思痛,於是他提出理據,主張基督新教的不同教派之間,不管由誰人執掌政權,都應該寛容對待其他教派,停止公權迫害或強行改變其他教派人士的信仰或禮儀。在這方面,我認為洛克在信函中提出了至少三個不同但是相關的論據,而這些論據,我相信其合理性和說服力,並不限於基督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