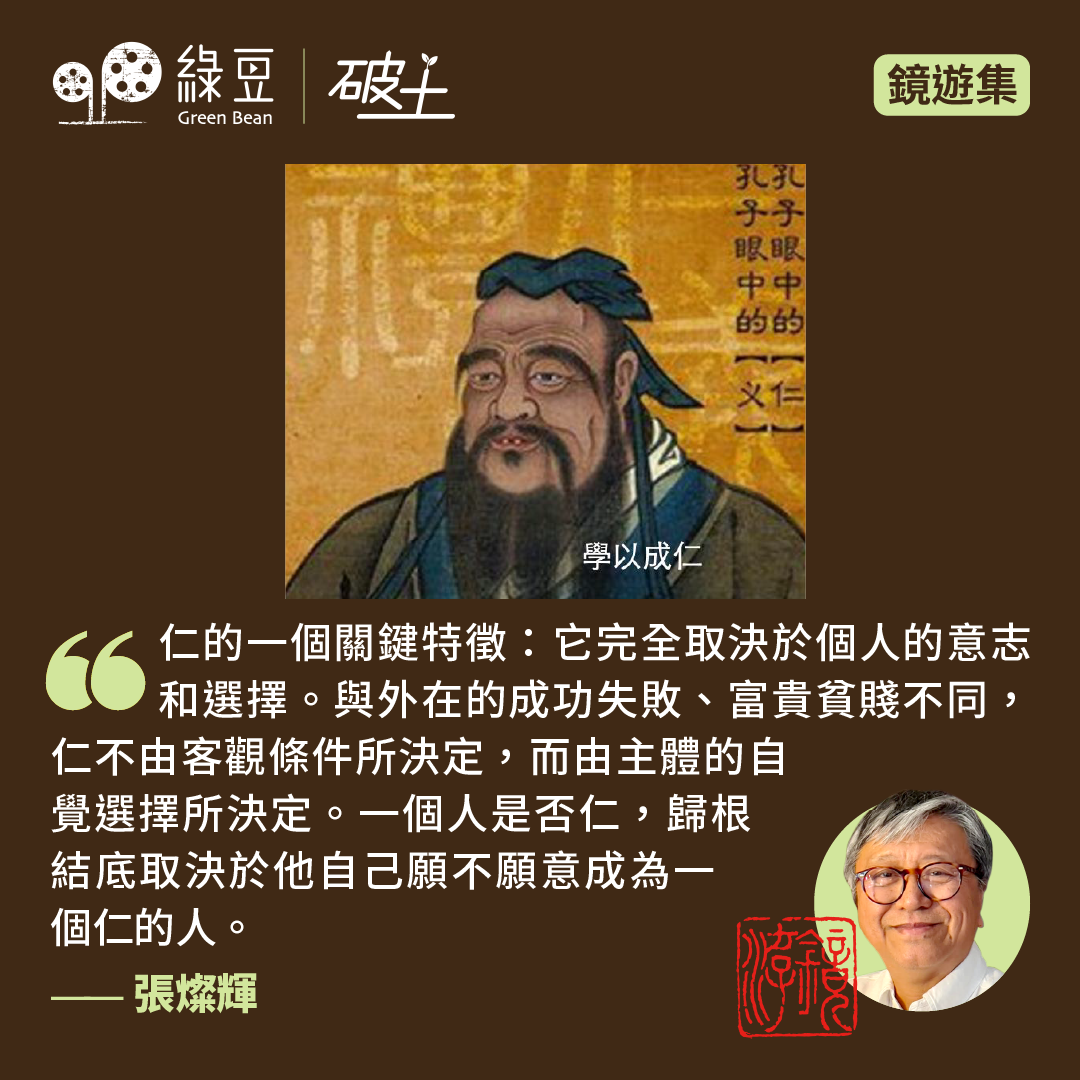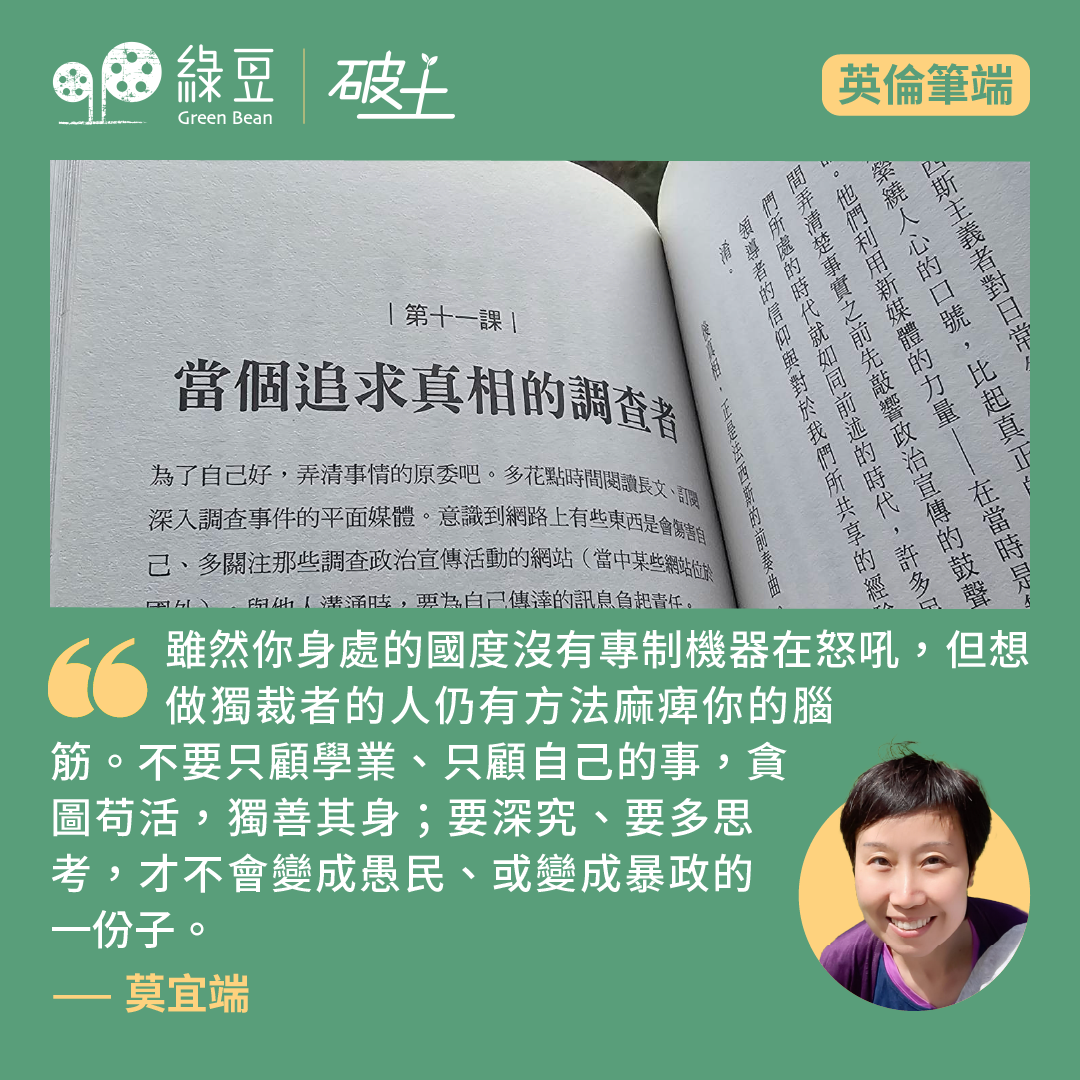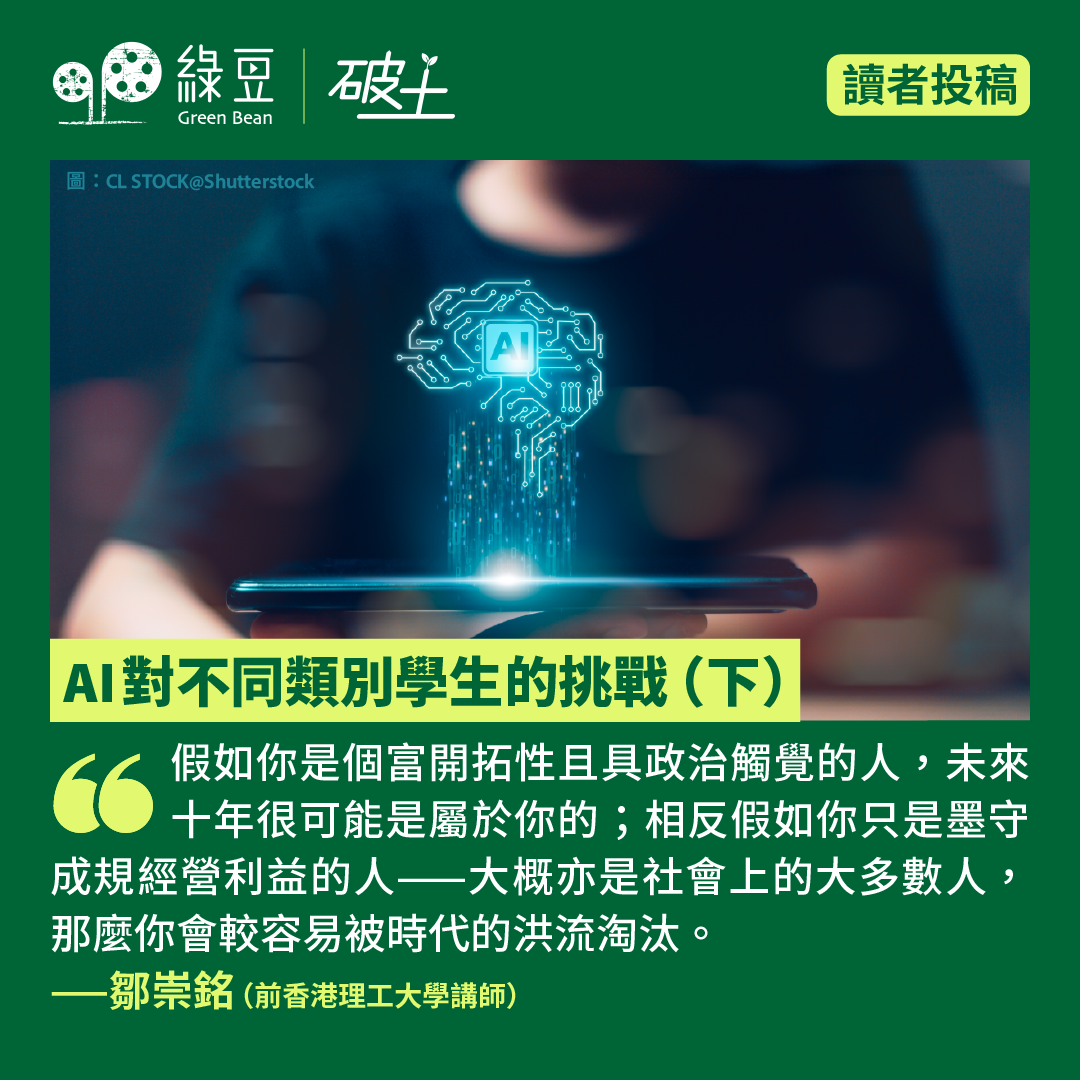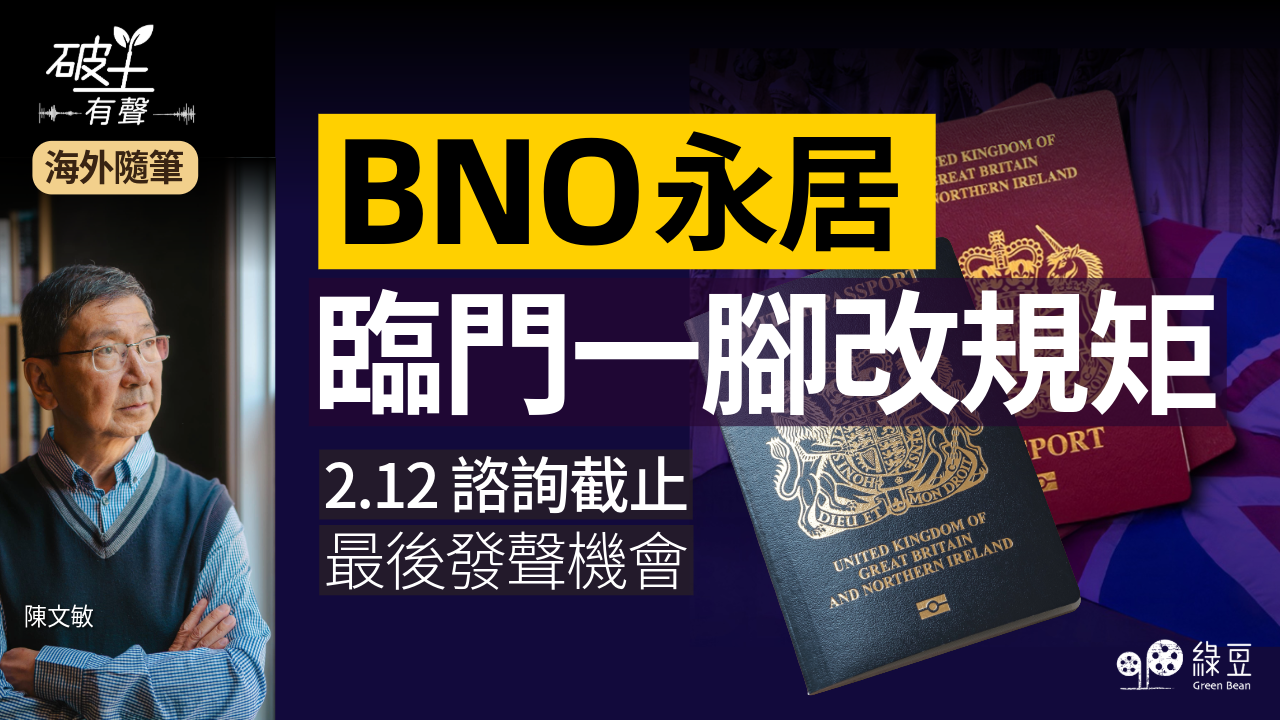破土圖文
儒家的根本問題 要深入理解《論語》,首先需要把握儒家思想關注的三個根本問題:人禽之辨、義命分立、仁禮之辨。這三個問題構成了儒家人生哲學的基本架構,也是理解「仁」這個核心概念的必要前提。 人禽之辨:為甚麼要做一個人? 儒家思想的起點,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追問。孟子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之間的區別其實只有一點點,普通百姓把它丟掉了,君子卻把它保存下來。這「一點點」的區別,就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 在《論語》中,孔子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區別。子游問什麼是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2.7)如今人們講孝,不過是說能夠養活父母就夠了。然而犬馬一樣能得到飼養,倘若不存心孝敬,贍養父母和飼養犬馬又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例子深刻地指出,人之為人,不僅在於外在的行為,更在於內在的情感與態度。單純的物質供養構不成真正的孝道,因為那只是生物性的需求滿足。真正的孝必須包含發自內心的敬意與關愛,而這種情感正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差異。 孔子對此的態度非常堅定。當長沮、桀溺兩位隱士譏諷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勸子路跟隨他們避世時,孔子失望地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18.6)人不能和鳥獸同群,我不同人打交道又同誰打交道?天下太平的話,我也就用不著提倡改革了。...
讀預科的兒子,間中會在我煮飯沏茶團團轉的時候,把在網路上見到的政治笑話、或時事熱話跟我說。我當然會口水多過茶,忍不住發表一番偉論。但少年言不多,到我終於停下來,他才簡潔地分享自己看法。 很喜歡這種感覺 早前美國當局公開海量的愛潑斯坦檔案文件,我們討論了好一陣子。由哪個名人涉事,到為何在美國除了淫媒大亨和前女友,從未有人被捕被調查?所謂 institutions,包括憲法、法治、民主制度,也包括各種組織發生甚麼事?在英國皇室和政團的地震,是否代表institutions崩壞,抑或是沒有人above the law的明證?! 不成為暴政的螺絲...